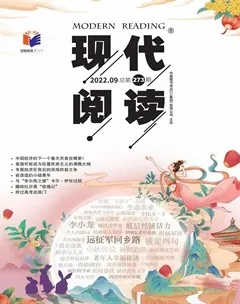科幻作品中的疯狂科学家
2022-12-29屠思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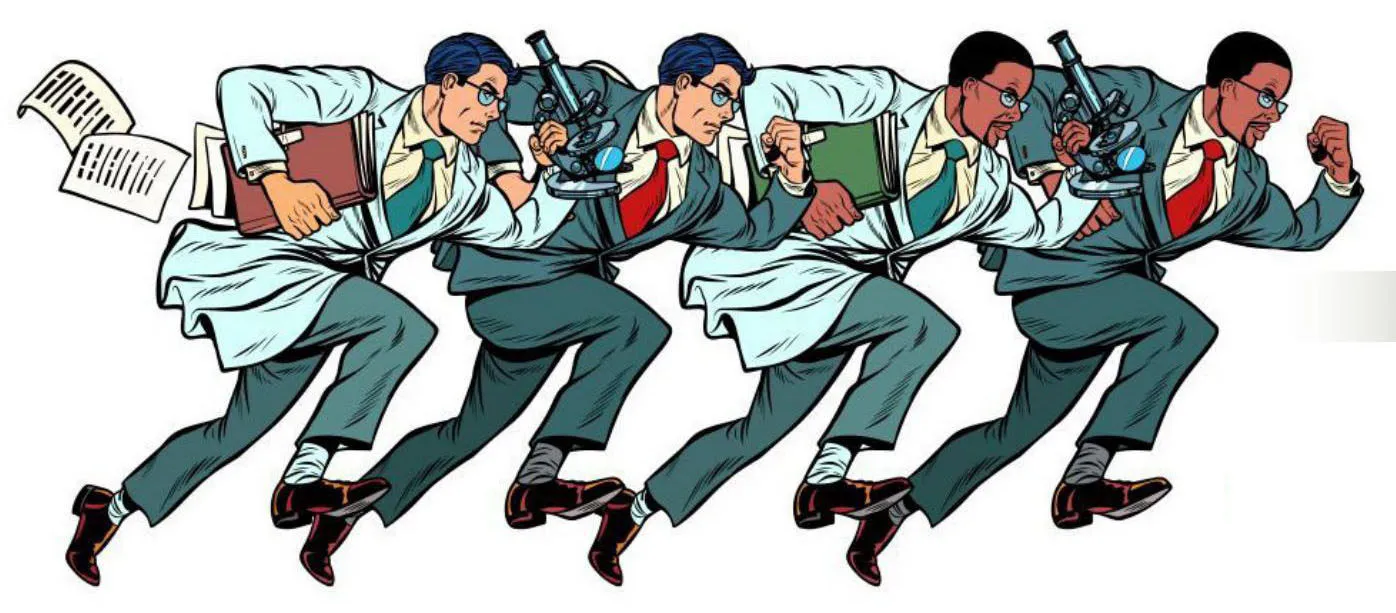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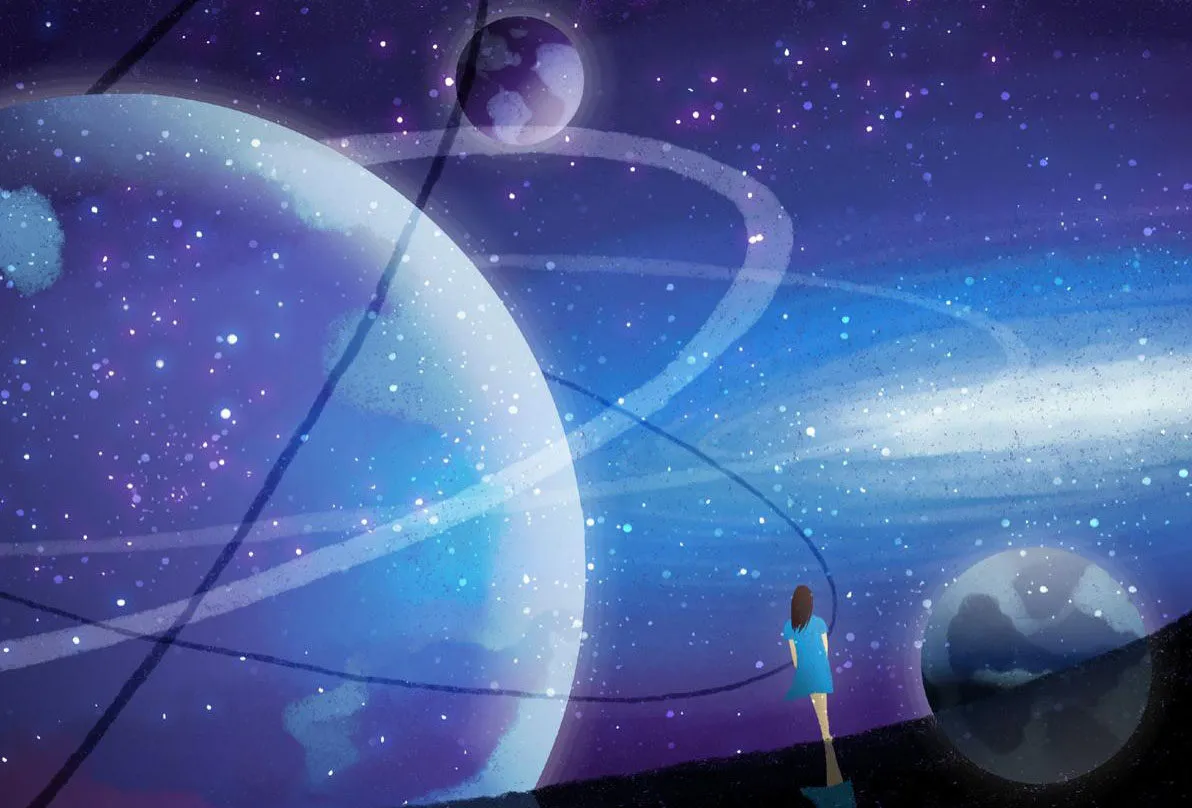
重要的不是作为答案的真理,而是探求真理的行为。
格拉多大科学院的科学家
当科学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初次登上历史舞台时,世人对其怀抱的态度并非憧憬和崇拜,而是困惑、恐惧和憎恨。这有很多原因:一方面,科学否认人类在宇宙当中的至尊地位;另一方面,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世界,很多时候缺乏肉眼可见的实用价值。一些作家将科学家描写成不可理喻的疯子,整日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研究。
在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主人公格列佛参观的格拉多大科学院中的科学家便是这种印象的集中体现——他们研究如何从黄瓜里提取阳光,如何将人的粪便还原成食物,如何将冰烧成火药,如何用猪耕地。诚然,这些研究荒诞不经,但对这些研究和研究者的书写却也彰显出作者的局限性——就像引发强烈争议的“大鼠雌雄同体受孕实验”一样,研究这些课题的重点不仅仅在于研究方式和结果,还在于其中揭示出的规律:从黄瓜里提取阳光的价值并非单纯的“日后可以用储存的阳光取暖”,而在于发现植物细胞的光合作用原理。
当然,这种被荒唐化的古典疯狂科学家形象也反映出了世人们就科学的价值而产生的争议,即“科学有什么用?”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星际穿越》等科幻电影当中看到相关的讨论。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我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霍夫曼博士
在惯常的认知中,即便是最疯狂的科学家,也服从着科学层面的理性,他们之所以疯狂,只是因为他们的理性有别于世俗。相比之下,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笔下的霍夫曼博士显然更加放飞自我——他利用自己的天赋打造了一台欲望机器,借由这台机器,生成了一个逐渐蚕食世界的反理性、反秩序的宇宙。
小说《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的主人公德赛得里奥临危受命,从理性之城启程,深入博士所创造的混沌大陆的腹地,其间见证了各种荒诞不经的疯狂景象——从街头恣意生长的超现实生物,到随意肢解、拼贴身体的摩洛哥人……这些景象以它们汹涌的生命力照亮了死气沉沉的城市,彰显着纵欲式的狂野,却逐渐沦为华而不实的花架子,透出深沉的寂寞和空虚。
造就并代表这一切的霍夫曼博士可以被看成一个符号——他昭示着科学技术不仅指向理性和进步,也可以造就噩梦般的荒诞光景。在现实当中,这并非不可能,我们正在经历的“娱乐至死”的社会状态也许正是它的真实写照。
雷先生
科研要耐得住寂寞,而一旦生不逢时,要抵御煎熬,就需要更强大,甚至偏执的信念。这便是“生不逢时的偏执天才”这一关于疯狂科学家的常见主题的情感动力。出自现代作家许地山《铁鱼底鳃》的雷先生则同时集中了这一主题的诸多子题。
雷先生生在一个国家多灾多难的年代,是一名海外留学归来的工程师,带着强烈的救亡图存的信念,创造出了极为超前的潜水艇“铁鱼”(不仅能进行深海潜航,还能投放微型探测机器人,将机器人探测的情况传输到潜艇中)。但是国内落后的制造业和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让他的才华无处施展,贫困和战乱又让他奔波于生活的琐事。逃难途中,不明就里的同路大妈又将他的设计图纸拿来给孩子擦屁股了,最终,伴随着铁鱼的模型和核心图纸一同坠入大海,科学家本人也终于崩溃了,纵身一跃,随之而去。
这类科学家的形象能够为我们带来两层不同的反思,其一是这种偏执是否真的有意义,其二是容不下这样的天才的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丁仪
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格列佛游记》所拋出的那个问题——科学有什么用?只不过,在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笔下,这个问题被以另一种方式提了出来:为了真理,献身科学的人究竟愿意付出多少?在他的小说《朝闻道》中,人类的科学技术遭到“排险者”的碾压,后者建造了一座真理祭坛,在上面回答所有学科的终极问题,代价是听到答案以后,听者只有10分钟的存活时间。
这个十分浮士德的情景赋予了传统的问题以更多的讨论空间——首先,兑换来的真理无从得到验证;其次,这些真理也仅限让听者自身领悟,其幸存时间不足以完成知识的传承和分享;再次,所谓的终极问题的答案指向的可能并非一种至高无上的醍醐灌顶,而是一种渐进式研究的终结——这似乎也呼应了规则当中的短暂的幸存时间。
在这三重否认之下,丁仪等科学家们偏执与否的选择就十分值得玩味了,因为他们的选择既无法带来社会效益(无法共享与传承),也不能实现个人价值(无从验证)。
在这个语境当中,唯一有意义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发问(最终也正是小说中的霍金抛出的无解问题难住了“排险者”,才终止了这场荒唐的闹剧)。
这便是这些科学家们留下的遗产:重要的不是作为答案的真理,而是探求真理的行为。
(摘自中央编译出版社《E=mc³:边角料科研奇思录》 主编:杨枫 王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