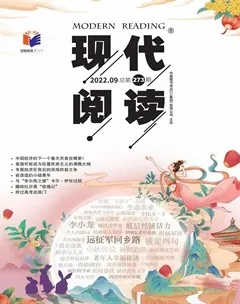香椿树街的故事
2022-12-29章远阳

海晏河清原本难得,因为允许存在对乏善可陈的世界的讽刺,矛盾才有被看见和克服的可能。
还是想从最喜欢的苏童的《城北地带》聊起。故事其实很简单,不过是讲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椿树街4个不良少年的荒诞少年事。讲他们在不正潮流与执拗心性的双重裹挟下横冲直撞,怀着喜忧参半且不知所措的情绪长大或没能长大的故事。
主要人物达生、叙德、红旗、小拐原是香椿树街唯一一个小帮派的成员,是被东风中学同一批开除的不良少年。
达生,梦想成为城北第一号人物,急于证明自己实力的心情孤独而焦躁,他向对他充满敌意和蔑视的帮派宣战,不可避免地死在一场1对10的较量中;叙德,离开学校后被家人安排到玻璃瓶厂上班,与厂里的有夫之妇金兰“搞腐化”,金兰生下孩子后随其私奔;红旗,因猥亵奸污幼女罪被判有期徒刑9年;小拐,常小偷小摸被邻里嗤之以鼻,因发现潜伏多年的所谓特务的秘密成了街道的重点培养对象。
故事简单,但淋漓的真实感不简单。
逻辑可靠的人物形象
无论是18岁的达生还是红旗,那时都毫无缘由地羡慕着那些以统一文身为标志的帮派成员。我至今不明白达生渴望一战成名的念头从何而来,他为此几次远道拜师未果,做沙袋练拳击,一次次主动挑衅他人甚至为此丧命,他不考虑执意成为所谓的英雄需要付出的代价及需要承担的后果。
我认可这样的人物形象和结局,许多人付出努力的过程的确就是这么的没有道理,人们抱着无章可循的执念前行,功成名就或行差踏错都是常态,原没有对错之分。
又如耍蛇人滕文章。书中描绘达生外公滕文章的那段话我一直记忆深刻——
耍蛇人滕文章在20年以后重游香椿树街,视线里的街景也似乎沾上一层模糊的白翳,但所有居民、工厂、店铺甚至垃圾堆的面目都依然熟稔。他记得在这条街上呆了5天,嫁掉了唯一的女儿,记得他拿着新女婿给他的钱,在澡堂里泡了一个下午………现在他竭力回忆着新女婿的职业和模样,却一点也想不起来,只记得那个人的双腿又粗又短,那个人穿着沾满油污的蓝色工装。
以前读余华的读书笔记,他说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教会他,当心理描写应该出现的时候,不必真的叙述心里的想法,而是可以通过全面叙述人物的视觉感受来呈现其内心状态。这里就是类似的用人物感官去映射心理活动的写法。于滕文章而言,“嫁”女更像是一笔一次性的交易,而交易后喝茶泡澡、饮酒食肉的满足感才是历久弥新。
生活的本质是偶然与残忍
我明白生活的构成是偶然事件集,当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将人们敲打得措手不及时,生活的残忍本质就展露无遗了。
比如当金兰在火车站邀叙德私奔时,叙德的郑重决定是临时掷硬币决定的,他上火车时仍然趿着一双人字拖鞋,神色一半欣喜一半迷茫。他根本没明白金兰口中的“我带的烟够你在火车上抽到青岛”“我织毛衣给你穿,以后什么都会有的”需要他牺牲掉当前的一切去换。他丢掉了家里的钥匙,体验了第一次坐火车的确定的喜悦,可他的迷茫感是没有落脚点的。而生活残忍的地方在于,以他这种松软的性格,这种没有头绪的迷茫感大概率会因为他的孤注一掷永远伴随他,至少在我看来他成了一个缺乏可能性的人。
比如红旗犯事的那个盛夏黄昏,他本该和达生、叙德、小拐一齐去游泳,可那天他的朋友们不约而同地失了规矩,达生和叙德瞒着他去双塔镇找了他们共同崇拜的武师,小拐没有知会他就去偷偷扒了邻居家的狗皮卖钱,他怀着对他朋友以及整条香椿树街的深刻绝望独自下了水。当晚霞散去,红旗站起来朝岸上走时,凉凉晚风里打渔弄口女孩美琪的一举一动都显得格外温暖。那天美琪一个人在家,事后红旗总想起为了制止美琪的叫声慌不择物地在女孩嘴里塞满的东西——包括半块肥皂、一把钥匙和女孩穿的绿裙的一角。那年红旗18岁,被判有期徒刑9年,被监狱生活折磨得不成人样;美琪14岁,在人们的疏远与指责中投河自杀。
其实残忍的何止是当事人的结局,更多的是一种蝴蝶效应。美琪煎熬至死是因为千夫所指,她死后也就以一种以牙还牙的姿态幻化为人们心里的幽灵贯穿全文,这象征着罪恶发生后助推者与旁观者心里过不去的坎,也意味着痛苦的持续影响。红旗的母亲孙玉珠为给儿子脱罪,试过用钱求美琪改口,试过散播当日之事乃美琪自愿的谣言,试过多次上诉均被驳回。
孙玉珠最后一次去法院是在春意盎然的4月,耳畔回荡着儿子要求半年内必须出狱的最后通牒,迷离的视线里又一次看到湿漉漉的美琪的幽灵在法院门前游荡,她就在努力想抓住幽灵美琪的绿裙子的瞬间心痛而死,最后的面容凄苦而悲恸。
夹杂讽刺的社会环境
故事背景应该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的评价体系与参照标准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
在故事里,大人们的出发点似乎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得意地享用掌控权力带来的快感——叙德的母亲撺掇玻璃瓶厂主任组织女工批斗金兰、王德基打着治安联防队的手电筒深夜去城墙附近照“野鸳鸯”、派出所的人抽犯人屁股非得扒了人家的裤子。而真正该解决的问题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比如——
在香椿树街,有人喜欢温和的春天,也有许多女孩缝好了去年上海流行的白裙等待着夏季来临。而街头更多的孩子则东跑西颠地寻觅那些发生过死亡事件的场所,他们喜欢看死人,铁路道口、护城河的木排、钢轨厂的建筑工地,即使需要横越整个城市,他们也在所不惜。
在“划清界限”概念盛行的时期,下定义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人们对于事物的评判标准太过单一,“不一样的可能性”刚刚提出就被标注为“对”或“错”,从中抓取快乐就更难。
而依托这样单一的评价体系评出来的标兵就显得有些滑稽。比如小拐,因长期小偷小摸被邻居嗤之以鼻。东风中学曾想在小拐身上做试点,完成把一名污点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新人的指标,但他回学校的第一天就往政治老师李胖的讲台上扔了包粪便,气得老师暴跳如雷直接请辞,也让学校忍痛放弃了试点计划。
小拐形象的转折点在于发现了潜伏30年的特务老康家的地窖。他为此获得了市里的表彰,突然就成了众人艳羡的标兵。连他的父亲都始终怀疑儿子的发现是瞎猫逮到了死老鼠,他猜儿子事先可能是看上了老康屋里的某件东西。最讽刺的在于,学校定义的最无法培养的污点学生也是街道决定重点培养的先进个人,其间竟然可以无缝链接、毫无边界。
海晏河清原本难得,因为允许存在对乏善可陈的世界的讽刺,矛盾才有被看见和克服的可能。
《城北地带》给我的感觉跟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像,同样的真挚、尖锐、暴躁、活得固执且不知所措的人们的奋不顾身的故事,同样的带点遗憾。
我喜欢这种有些残忍的手法,充分相信人即便没能如愿迎着万里东风快意成长,即便不得不被动遭受或享受自己大量不经意选择造就的随意人生,也会永远记得恣意的过往。
(本刊原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