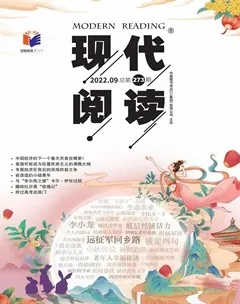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
2022-12-29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傅佩荣\\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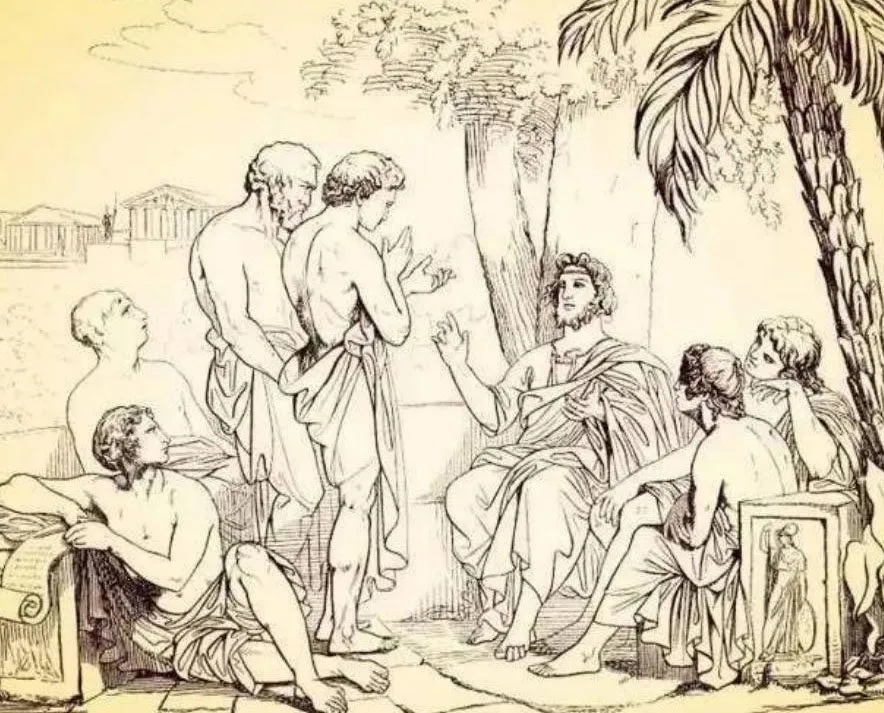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的形象并不是当时历史情境、对话、言语的精确记录。它虽不是精确的记录,但也绝不是纯粹的杜撰。柏拉图所添加的部分有其事实根据,根据便是他对这位无与伦比的神奇思想家的精神体认。当这幅形象全面展开时,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认识亦包含其中。
要想与苏格拉底认识及交往,必须透过他的学生柏拉图之眼。我们可以跟着柏拉图的对话录一道看看,苏格拉底在临死之前的状况(《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以及生平之所为(《会饮篇》《斐德罗篇》)。
苏格拉底之死是一幅静穆庄严的画面,其中呈现出对于“无知”不可言传的肯定。一切讨论死亡的言论都是基于无知,并且止于无知。苏格拉底说:那些恐惧死亡的人自以为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事。他们把死亡当成最大的恶兆而恐惧,殊不知,那也可能是最大的好运。死亡的两种可能情况都不坏:它或是等于虚无,失去一切知觉,就像无梦的安眠,因而永恒并不长于一夜;它或是灵魂迁往某处,与一切死者会合,在那儿,公正的法官维护真理,我们也将遇见许多被不义判刑而处死的人,大家整天交谈,继续探问谁是智者,尤其是能够结识往圣先贤,更是无上的幸福。无论死亡的真相如何,正直的人是不会遭遇不幸的,生前如此,死后亦然。
至于灵魂不死,“那是毫无疑问的”,苏格拉底继续强调,心灵的平静正是基于这一确定的事实。要想免除这方面的疑惑,还需行事合乎正义,并不断追求真理。这里有几个“证据”。首先,基于理性的证据并非完全站得住脚。事实上,苏格拉底也公然主张,生活要怀着不死的希望去“冒险”。因为不死的观念形成“一种绝对正确的信仰,值得我们冒险为其献身。因为这种冒险壮丽无比,并且心灵的平静也需要这些具有魔力的观念”。但是,若要凭借知识来肯定这一事实,苏格拉底又以一贯的冷静态度提出质疑。“若我所说为真,则我正是秉持真理而行;然而死亡之后若为虚无,那么在这仅存的片刻中,我也不愿看到朋友们哀伤悲恸,因为我的无知即将结束。”
克里托请示苏格拉底愿意如何安葬。他回答:“随你们的安排。”“但是你们要看紧我,别让我远离了你们。”然后,他露出平静的笑容说:“我没法让克里托相信我就是那个平常侃侃论道的苏格拉底啊。他总觉得我是另一个行将就木的苏格拉底。别忘了,你们所埋葬的只是我的躯体,今后你们仍当一如往昔,按照你们所知最善的方式去生活。”在他死前,环绕他身旁的朋友们都怀着复杂的心情,既昂扬又绝望。在悲伤哀恸与兴奋莫名的气氛中,他们领悟到一种神妙的境界。
在苏格拉底看来,死亡并无任何悲恸意味。“西米亚斯、克贝(苏格拉底的两位学生),你们和别人一样,都将先后离开世界。我呢,就像一位悲剧诗人所云,已经听到命运之声的召唤了。”换句话说,死亡的时刻已经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了。苏格拉底超越了死亡。
他不许朋友们哀伤恸哭。“人必须在庄严肃穆中离开尘世。请保持安静,耐心等候。”因为苏格拉底在沉静的真理中寻求同伴,而哀伤无法成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他温和地遣人送走妻子克珊西帕,此时他不想聆听悲泣。一直以来,是思想而不是随感而发的哀伤,使他灵魂超脱。不错,人的一生常为哀恸所袭,我们也难免悲叹。但是当大限已至,就须停止哀恸而代之以平静及认命。苏格拉底立下了伟大的典范:面临哀恸,他能够解放灵魂,展现一派伟大而仁慈的安宁气象。死亡本身不重要了。这不是在掩盖死亡的真相,而是肯定生命的真谛:真正的生命不是走向死亡的生命,而是走向“善”的生命。
在临终前的这段时间,他的精神似已超凡出世了,但仍慈爱地关怀着周围的细节,比如他亲切周到地对待狱卒等。
他想起了一些恰当的安排:“或许在饮用毒酒之前,最好先沐浴更衣,因为这样就可以省去妇人很多力气,不然她们还得为我清洗尸体。”
一切痛苦都在这种轻松的语调以及对具体细节的关切中逐渐消逝。这些都是心灵宁静的征象。相较而言,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更着重事物的表面。他相信要获得心灵宁静,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节制有度,且应忠于分内之事。他不了解的是,内在的震撼所带来的启发,给予苏格拉底一种更深刻的、更明觉的心灵平静。苏格拉底能在“无知”中确立人生目标,然后生死不渝地奉为圭臬,他也由此摆脱了羁绊。
柏拉图的《斐多篇》以及《申辩篇》《克里托篇》,都属于人类史上少数无法替代的珍贵文献。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爱智之士在拜读之后,学会了如何坦然接受自己残酷和不义的命运,在平静安详之中坦然离世。
然而,这种平静安详背后隐含着无限深意。当我们阅读这些对话时,内心无法不被深切的情感所震撼,思想亦会随之产生变化。我们体验到一种要求的命令,而非一种虚妄的幻觉;那是至高的期许,而非伦理的教条,让你敞开心怀,来接纳独一无二的绝对者。切勿彷徨他顾,除非你已抵达此境,因为只有在它之中,人才可以平静面对生和死。
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是一个神奇的人物,甚至连他有形的身体也带着神奇的色彩。他的健康无懈可击,既耐得住贫困饥寒,也经得起饱餐痛饮。他可以在通宵达旦饮酒之后,继续与阿里斯托芬及阿伽东讨论深奥的哲学问题。
直到别人都支持不住睡着了,他才起身离座。“他到利西翁洗个澡,然后一如往常地度过这一天,直到傍晚才回家休息。”但是他的行为有时也非常古怪。有一次,他同一位朋友走着走着,忽然止步不前,陷入深思。他就这样站了一整夜,两眼凝视空中。第二天清晨,“他向太阳祷告之后,这才举步离开”。
苏格拉底的容貌虽丑,但是却有魔法般的吸引力。他特立独行,深不可测,我们无法将他划归任何范畴。他所谈论的一切事物,从来不会只具有一种意义。
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冷静扼要的描绘则大不相同。不过,基本要点上,色诺芬与柏拉图并无矛盾。色诺芬只就个别的事迹及零星的观点来看,他看到的是一位能干、健壮、聪明绝顶的苏格拉底,他也打算用同样聪明的做法去检视苏格拉底,可是竟找不出任何缺点来。柏拉图则深入了解苏格拉底的内在本质,而这只能通过比喻式的描绘来呈现。从这些象征的描绘来看,他所达到的深入程度,已非任何第三者的判断能够置喙。
色诺芬采取客观认识的态度,所以他收集一切有关苏格拉底的资料,并如实记录下来;而柏拉图却是被苏格拉底深深震撼,苏格拉底给他带来的影响和感动贯穿其一生,所以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是透过这种震撼而呈现的。
对他们二人而言,苏格拉底都是人,而不是神:只是色诺芬认为,苏格拉底这个肯定某些真理的人,是可以完全被认识和了解的,他是“合乎理性而具有道德的存在者”;而在柏拉图心中,苏格拉底的言语源自永不枯竭的心灵深处,他生命的来源和归宿都是高深莫测的。
(摘自商务印书馆《四大圣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