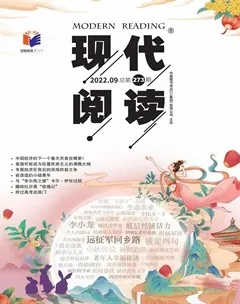张载的22字格言影响千年
2022-12-29艾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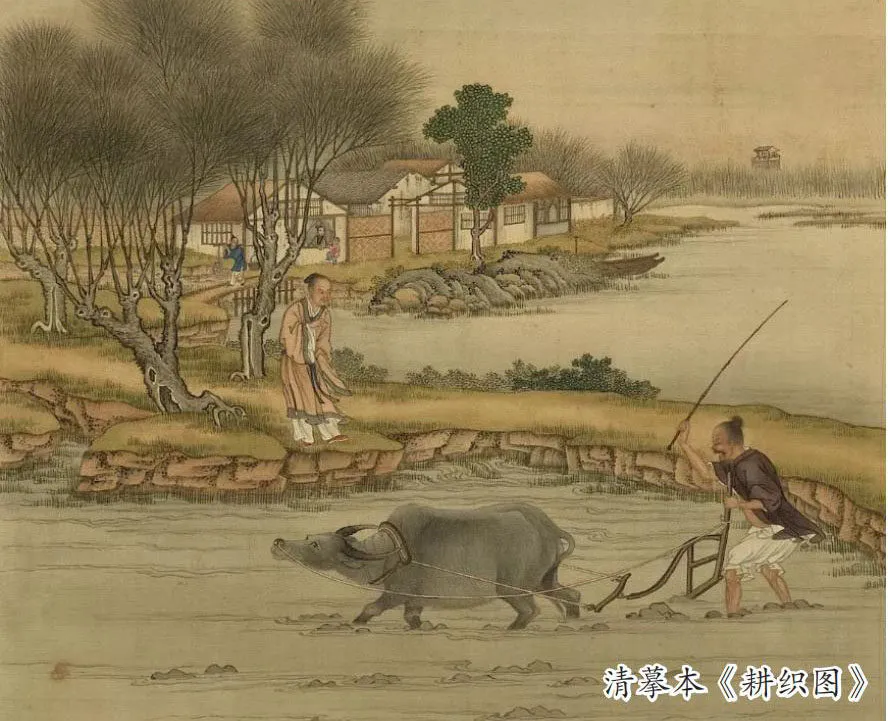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22个字出自北宋张载的《横渠语录》,学界对它有一个专称,叫“横渠四为”或“横渠四句”。
横渠四句的作者张载是“北宋五子”之一,生于1020年。因为长期在今陕西眉县横渠镇生活和讲学,故被后世称为“横渠先生”。
毫不夸张地说,“横渠四句”影响中国达千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各个时代的牛人当作立身和做事的最高标准,并以一生践行之。
而且,它最有生命力的时刻,都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文天祥在南宋末年讲过,黄宗羲在明清易代之际讲过,马一浮在抗战时期讲过……有学者说,“横渠四句”是中国人的精神绝句。
千年来,如果有哪一句话自始至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国为民而努力奋斗,那一定是“横渠四句”。
在和他同时代的人看来,张载并不是天才。在11世纪璀璨的星空中,张载最终能够成为照亮千年的那颗星,有一大半的功劳源于他的勤学苦读。
张载曾自撰一副对联,“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贴在书房两侧,时刻激励自己。他是苦读熬出来的一代宗师,因为苦读,还曾遭到表侄程颢、程颐的嘲笑。
嘉祐二年(1057),张载参加科举考中进士。那一年,他已经三十八岁,在当时属于超大龄考生。在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下,张载在开封相国寺开坛讲易经,名动京城。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两个表侄——程颢、程颐兄弟。经过一番秉烛夜谈,第二天,张载对他的听众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辈可师之。”此言一出,二程声名大振。张载的虚怀若谷,由此可见一斑。
1068年,登基不久的皇帝宋神宗召见王安石,询问治国之道。王安石直接说“每事当以尧舜为法”,直接对标尧舜。
第二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了张载,推荐理由是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在五十岁这一年,张载已在思想界奠定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创立的门派,后来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一起并称为“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四大主流之一。
像询问王安石一样,宋神宗也问了张载治国之道。
没想到,张载的答案跟王安石的答案差不多,都要皇帝直接对标最高标准。张载的原话是:“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
皇帝听完很兴奋,这说明当时国家最聪明的脑袋,想法都是一致的。
一年后,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了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邀请张载加入协助,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从与宋神宗的问答来看,张载也属于变法派,但他为什么要拒绝加入王安石的队伍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张载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太过于激进,违背了他本人作为一个温和变法派的初衷。
最终两人“语多不合”,王安石“默然”“不悦”。
没多久,张载突然被派去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等到张载办完案子返回朝廷,新旧两党已经因为变法措施撕破了脸皮,旧党代表人物都被贬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张载的弟弟张戬。
看到此种局面,张载辞官返回横渠讲学。
而王安石在变法的艰难推行与内讧中,最后罢相归隐南京钟山,绝口不谈国事,一心研究佛学。张载尽管没有权力和舞台,仍然孜孜于自己的变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
辞官回到横渠后,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划成井田,中间留一块公田,四周8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这些改革试验,基本都没有取得成果,不过,张载的较真儿和实干精神还是值得敬佩。
看一个人的执着和毅力,不应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而要看他饱受挫折之后的表现。
张载在仕途上并不如意,这跟他的理想追求有所出入——他不是那种只躲在书斋讲学传道之人,他的终极追求是他苦读、冥想、彻悟得来的东西:要有利于百姓。在他眼里,“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对百姓有好处,这才是意义所在,对自己有好处,甚至对国家有好处,都意义不大。
张载一生得不到更大的机会去实践和推行他的理念,只能在自己当官或者讲学的地方,一点一滴去做。他没有抱怨,没有放弃,在重建社会秩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的一些弟子正是得到他毕生力行的真传,陆续开始做乡规民约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士大夫。
张载的思想深邃,但落脚点很细微,格局高远,又很接地气。
听到他这些乡村治理的事迹,你可能很难想象,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探索宇宙本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并被誉为北宋诸儒中“对儒学真能登堂入室并能发展出一个新系统”(学者韦政通语)的大师。
张载跟周敦颐一样,他们开创的关学和濂学,为宋代理学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然而,两人都只活了五十多岁,没等到理学的黄金时代到来就走了。相较而言,二程就好命了,尤其是程颐活到了七十五岁,从11世纪熬到了12世纪,洛学在他手上发扬光大。
张载走得早,他的一些弟子如吕大临,在老师逝世后转投到二程门下。此消彼长,门派间的影响力差距,无形中又拉大了。
张载讲了很多道理,但从不用于苛求他人,而是用来要求自己。面对问题,总是反躬自问,从不指责别人。包括他最为著名的“横渠四句”,也是用于自律,不是用于他律。
尽管我们在无数场合听过“横渠四句”,但要知道,它随时指向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根据他的学生回忆,张载是听到灾荒、百姓没饭吃,就自己也吃不下饭的那种人。当他无能为力的时候,只好要求自己“感同身受”。张载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但财富的有无和多少,从未影响他修炼成为一个颜回式的大儒。
在公道大义面前,他从不畏惧。而对于自己,则了无所求。他愿意为理想献身,但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也绝不苟且,辞官回乡、讲学、种地……富贵于他如浮云。
无论读历史,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用道德大棒指挥别人的人。千万记住了,一个人一旦要求别人高尚,他自己已便不高尚了。你要拿着“横渠四句”去要求他人,张载听到了也会不高兴。
1077年,张载获推荐再次回京任礼部副职。因为不能实现他的理想,很快他再次辞官。
同年冬天,在返回横渠的路上,行至临潼,五十八岁的张载安然辞世。
他去世时,身边仅有一个外甥。在长安的学生闻讯后赶来,筹资将老师的灵柩送回横渠安葬。
大雪纷飞,圣人无声离去。
但千百年来,他的理学思想,他的“横渠四句”,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座右铭,象征着最高的理想境界和精神坐标:
张载死后大约180年,文天祥在殿试时,一字一画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成为那一年的状元,也成为一个朝代最后的脊梁;又大约400年后,黄宗羲在书中击赏张载,击赏“横渠四句”,他最终活成了榜样的模样,少年刺奸,中年抗清,晚年鸿儒,抨击君主专制,成为千年一遇的大思想家;又大约280年后,马一浮在抗战烽火中,向大学生们普及了“横渠四句”,寄希望于抗战的胜利,国族的复兴……
或许,张载并未真的离去。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文治帝国:大宋300年的世运与人物》)(图注:横渠书院内的张载像;清摹本《耕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