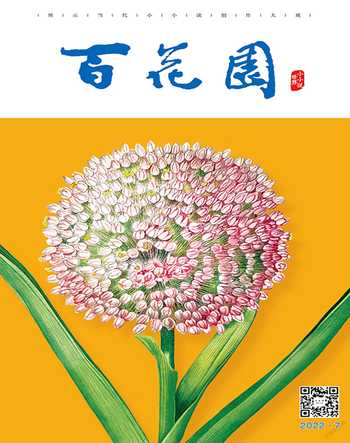美酒加咖啡
2022-12-29蒋冬梅
蒋冬梅

每次见到兰海金,我都会说:“给我放一场电影吧。”他总是吃力地站起来,拖着那条瘸了的腿,一边走一边把头摇得像一个钟摆。他明明很老了,还穿着花衬衫、喇叭裤、尖头皮鞋,头上戴一顶牛仔帽。据说,这身行头是当年地道的上海货,可这身打扮不合时宜,无论当年还是现在。
兰海金一直看守着靖安街上的电影院。从前他是25号工厂的仪表师傅,上海厂支援建设时派来的,专门修校飞机上的仪表。兰海金修好过厂长的雷达表,自那以后,他总是把花衬衫的领子很放肆地翻在工作服外面。
据说,从前找兰海金修表的人不少,至于修表的酬勞,只是一张周末舞会的门票。
舞场在靖安街西边,露天的,只在周末开放。舞池的地面是用红砖铺的,高低不平。红砖是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粘着敲不掉的水泥疤。舞场边上有四根柱子,挂着俗气的塑料花和小彩灯。票价两块钱,能打一瓶散白酒。舞曲有很多,兰海金最喜欢的是《美酒加咖啡》。
可是,我从未看见过兰海金跳舞,他瘸了之后也不再修表。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起《美酒加咖啡》,他会吃力地站起来,挪动瘸了的那条腿,带着斥骂声离开。
其实,靖安街的电影院大门已经好多年没打开了,看电影仿佛是遥远年代的事情。这样的电影院看守也是可有可无,可厂长还是派兰海金去看守电影院。工人们每天上班路过那里,都会看到已经瘸了的兰海金坐在电影院的蓝漆大门前,像从前一样,等着铃声响起,然后看人流如潮水般涌出来。
有天傍晚,我又一次对兰海金说:“给我放一场电影吧。”这一次,他没有把头摇得像钟摆,反而有点儿郑重地说:“没有片子了。从前,片子是从县里租来的,县里是从市里租的。”不过,他还是说:“我翻翻老柜底吧。年头久了,谁也记不住柜子里藏了什么,有时候,一架老柜子,一翻能翻一下午。”
兰海金拿来一大串钥匙,踩着梯子摸到储物柜的最上排,稀里哗啦地把柜门挨个儿试,终于打开了一个柜子。他开始在积满灰尘的柜子里翻,结果,真让他翻到了几盒片子,每个片盒子都很重,里面盘卷着一两个钟头的时间。
放映机转动起来,兰海金把胶片放上去,转动的胶片发出吱吱的声音,像从火堆里发出来的。然后,他带着我下楼,穿过悠长的边道,准备找位置坐下来。已经多年没人坐了,椅子都静默着。我们惯性地猫着腰,脸上带着歉意,假装穿过一双双人腿,寻找电影票上的号码。我们终于各自坐定在一个位置上,这时,一些人影开始在银幕上跳,跳跃了一会儿,光影稳定下来,现出清晰的画面。
画面上出现一个人山人海的广场,黑白的画面里传出了忧伤的音乐,那音乐像从几百年前传来,透出陈旧的味道。广场中央有一块不大的舞台,一群人正在跳舞。他们一律穿着喇叭裤、花衬衫、尖头皮鞋,他们神情忧伤,他们动作夸张,他们都有一张年轻的面孔。舞台周围的柱子上,缠绕着彩色的塑料藤蔓,上面开放着俗艳的塑料花朵。
台下观看的人群很安静,但眼神都很复杂。他们穿着规矩,打扮平庸,千人一面——男人的发型一律三七分,女人的卷发一律大众烫。他们被舞曲的声音捆绑起来,像工厂里捆扎成束的钢筋,僵直而灰暗。
后来,镜头开始拉近了,能看得清台上每一张似笑非笑的脸。一个留两撇小胡子的年轻男人穿着花衬衫、喇叭裤,动作夸张地在跳舞,看上去竟有几分面熟。他的舞姿在跳舞的人群里显得那样突出,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串东西,或许那是一块塑料奖牌,但这并不影响他鹤立鸡群。后来,大概是舞蹈进行到高潮时, 他被人们高高地举起来,像站在高山上的攀登者,脸上带着骄傲的笑容。舞曲还在忧伤地唱着,我一下子想起来,那不就是《美酒加咖啡》吗?
“这个人不是你吗?”我转过头去问瘸子兰海金,却发现他已经不在座位上了,只有荧幕上那个留两撇小胡子的兰海金,似笑非笑地从镜头前划过。他灵活的双腿在不停地交叉摇动,像工厂里那些转动的机床。他整个身体都慢慢地摇动起来,像一道卷起的风要从地面上拔起来似的。对了,他也有一张很年轻的脸。
黑黑的影院里,放映机的光束突然晃动起来,画面也随之晃动,飞出了银幕,在影院里左冲右撞。片刻后,银幕上闪出大片的雪花点儿,发出刀剑一样的声响,像要刺穿人的耳膜。放映机的光束一下子熄灭了,楼上的放映室传来轰隆的巨响,好像柜子被人一排一排地推倒,什么东西被用力摔打,摔得稀里哗啦,隐约还能听见时有时无的哭声。不一会儿,一切就戛然而止了。
我大声喊兰海金,没有回答,黑洞洞、空荡荡的电影院,把我的喊声弄得变了形。我拔腿往外跑去,路上空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连一盏路灯也没亮。
我用力地跑着,当我跑过靖安街西边的舞场时,看见四根柱子上的小彩灯还在眨着眼睛。舞场上竟然有几个打扮怪异的人在扭臀抖胯,跳着奇怪的舞。他们一律穿着花衬衫、喇叭裤、尖头皮鞋。那个穿着蓝红相间花衬衫、戴着一顶牛仔帽、留两撇小胡子的,不就是兰海金吗?破音箱里放的舞曲,正是他最喜欢的那首《美酒加咖啡》。
我一边跑一边冲他们大声喊着:“美酒加咖啡什么味儿?”回答我的,只有空荡荡的、长满青苔的、高低不平的红砖地面。
[责任编辑 吴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