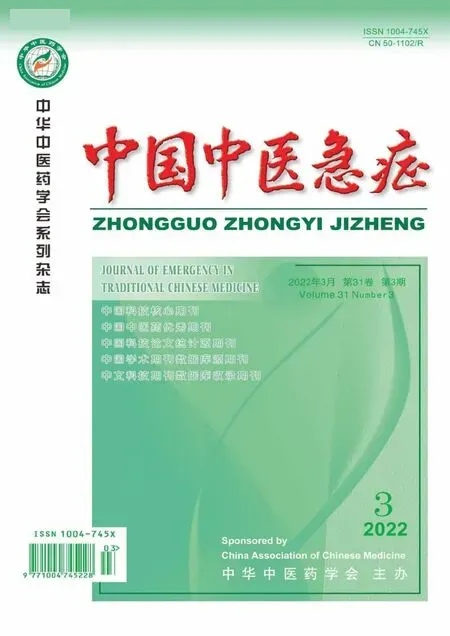从“肺为娇脏”论脓毒症肺损伤*
2022-12-28陈波林海
陈 波 林 海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福建 福州 350003)
“肺为娇脏,最易受邪”,肺叶娇嫩,百病易伤,而肺气一伤,百病蜂起。肺在机体氧输送及器官功能调节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脓毒症中更是核心脏器及窗口脏器。从解剖生理基础到病理反应特点,从治疗时机强度到治疗相关再损伤,均体现脓毒症之“嗜肺性”。“焉有脓毒症不伤肺”,脓毒症患者易出现以肺损伤为基础的多器官功能损害,治疗过程中应贯彻以肺保护为核心的全身多器官功能保护,重视肺的前哨作用,从中西医角度出发,认识脓毒症肺损伤,有利于更好地治疗脓毒症,以改善脓毒症患者预后。
1 脓毒症肺损伤之解剖生理基础
吴敦序曰“肺叶娇嫩,通过口鼻直接与外界相通,且外合皮毛,易受邪侵,不耐寒热,故有‘娇脏’之称”[1]。解剖上肺处高位、空虚多腔,上连气道,开窍于鼻,外通大气,可直接感受外邪而为病。“肺为清虚之府,一物不容,毫毛必咳”[2]。肺脏清洁空虚,依赖呼吸吐纳维持机体功能,而邪气于外,通过呼吸入肺,可直接造成外邪伤肺。肺具有全身最大面积的上皮细胞,巨大的肺泡面积直接与外界相通,各种病原体及致病因素可经呼吸道引起肺损伤。
生理上“肺朝百脉、主治节”,各脏腑通过血脉与肺相连,所以肺在病理上不仅易于感受外邪,他脏邪气也易传之于肺。因此有学者提出“五脏的非均衡性”理论[3]。肺具有丰富的血液循环,大量的血管内皮细胞,感染可经血行播散、微循环异常引起肺损伤,除原发于肺部的脓毒症,其他来源的脓毒症所产生的炎症风暴[4]、失调性免疫反应[5]可经血液循环进入肺循环引起肺血管内皮损伤,血管通透性增大,引起渗出性改变。另外肺循环与体循环密切联系,尤其是心脏,肺循环作为右心的后负荷并承接左心的前负荷,心功能的变化极易导致肺循环的改变,造成肺的气血交换异常,引起肺损伤。
同时“肺主卫气,外合皮毛”,肺具有保卫肌表、抗御外邪之作用,邪气外犯皮毛,可内应于肺,肺失宣肃而为病。肺主司卫气的生成,并宣发卫气以温养皮毛、滋养腠理、开阖汗孔。所以“肺主皮毛而在上,是为娇脏,形寒饮冷则伤肺”[6]。肺脏为人体之藩篱,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在机体受邪侵扰时最先发病。《大众医药·卫生门》曰“肺居五脏最高之部位,因其高,故曰盖。因其主气,为一身之纲领。恰如花开向荣,色泽流霞,轻清之体,华然光采,故曰华盖”。肺具有良好的屏障功能和代偿能力,可作为机体异常反应的代偿器官。肺循环是一个低压力、低阻力、低容量的循环结构,储备能力强,有利于承接右心压力及左心容量,在机体应激、容量状态、血管张力改变时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而在出现失代偿时肺循环首当其冲,最早出现变化,亦体现“肺为华盖,保护他脏”之生理特性。
因肺空虚多腔,外通大气,易受邪侵,且肺朝百脉、主治节,主司卫气,职司华盖。肺具有最大面积的内皮细胞与丰富的血管上皮细胞,并与体循环、心脏产生密切联系,在脓毒症中作为机体的第一道门户,为感受外邪而引起肺损伤奠定了基础。
2 脓毒症肺损伤之病理特点
脓毒症属于温病范畴[7]。“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一方面外感温病早期病位在肺,而肺叶娇嫩,风寒暑湿痰燥火多种外邪均可能损伤肺部,提示脓毒症患者常表现为肺损伤,且多种致病因素均可能导致肺损伤。流行病学调查亦显示肺部感染占脓毒症首位[8]。《临证指南医案·肺痹》亦云“肺为娇脏,不耐邪侵,凡六淫之气,一有所著,即能致病”。《难经·七十五难》中言“东方肝也,则知肝实;西方肺也,则知肺虚”。肺脏病理特点为正气易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肺之正气亏虚则易受多种病因及病理变化的影响。《黄帝内经》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在病因上,肺可因感染、炎症、休克、液体治疗、体位、镇痛镇静、心脏、手术、创伤等多种原因造成损害,表现为肺之疾病易感性。同时脓毒症肺损伤常表现为ARDS,呼吸窘迫及过强的自主呼吸可导致肺容积伤、压力伤及生物伤。脓毒症患者早期易出现急性胃肠损伤,基于“肺与大肠相表里”,胃肠功能障碍所导致的营养不良及肠道菌群移位,均可能加重脓毒症之肺损伤。反之,治疗脓毒症肺损伤,可通过通腑驱邪达到宣通肺气之效。
宋代张杲在《医说·喘嗽》中最早提出“肺为娇脏”,其指出“古人言肺病难愈而喜卒死者,肺为娇脏,怕寒而恶热,故邪气易伤而难治”。病理上他脏邪气易传之于肺。全身脏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联系密切,他脏受邪易于损伤肺脏。基于心肺交互,心肺在氧输送中密切配合以维持人体生理功能。而在脓毒症早期,心脏代偿性增强,右心动力的增加,可持续对肺循环进行冲刷,引起肺毛细血管内皮损伤及渗漏。反之,脓毒症可抑制心肌,心肌收缩力的下降导致肺循环瘀血,特别是左右心功能不匹配时,左心无法承接右心高输出量状态,使肺循环容量及压力增加,加重肺部渗出性改变。
肺脏生理特点决定其疾病发生时易受邪侵扰,病理上肺叶娇嫩,正气亏虚,邪气易伤。同时五脏六腑密切联系,肺为华盖,而最易受邪。脓毒症作为致命性的器官功能衰竭,其多种病因均可能引起肺损伤,特别是循环系统的改变,导致脓毒症伤心而伤肺。
3 脓毒症肺损伤之治疗与再损伤
程钟龄在《医学心悟·咳嗽》中言“且肺为娇脏,攻击之剂,既不任受,而外主皮毛,最易受邪”,故临床肺病治疗当取“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为法则,用药以轻、清、宣、散为贵,肺非喜润恶燥[9],过寒过热过润过燥之剂皆所不宜。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言“肺为娇脏,且属金,最畏火刑”“冷热皆足以伤之也”。肺叶娇嫩,攻击之剂不任受,过之则伤。强调肺叶娇嫩,不耐侵扰,治疗稍有偏颇便可致病。在脓毒症治疗中,强调治疗时间性及精准性,早期准确及时的液体治疗改善脓毒症患者预后,而大量液体复苏极易导致血管内皮糖萼受损,加之盲目的液体复苏可能引起肺循环压力增加,诱发肺损伤。而在脓毒症肺损伤治疗中,良好的镇痛镇静有利于实施肺保护,减少自主呼吸驱动及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反之,呼吸机使用不当及过度镇痛镇静均可导致肺损伤及呼吸功能障碍。
“肺为脏腑之华盖,呼之则虚,吸之则满。只受得本然之正气,受不得外来之客气。客气干之,则呛而咳矣。亦只受得脏腑之清气,受不得脏腑之病气。病气干之,亦呛而咳矣”[2]。肺脏洁净空虚,不耐邪侵,肺具有完整的解剖屏障与良好的免疫功能,而脓毒症患者出现低氧血症时常需建立人工气道,这便为病原体的入侵引起肺损伤提供了天然腔道。
肺抵抗力弱,不耐邪侵,各种病邪及外来干预均可损伤肺的功能而发生疾病。“肺为娇脏,寒热皆所不宜。太寒,则邪气凝而不出;太热,则火烁金而动血;太润,则生痰饮;太燥,则耗津液;太泄,则汗出而阳虚;太涩,则气闭而郁结”[10]。药物太寒、太热、太润、太燥、太泄、太涩皆可能损伤肺,故治疗应明辨阴阳寒热虚实,以平为期。在脓毒症治疗中,液体、组织灌注、机械通气、体位治疗均可能引起肺继发性损伤。在治疗监测中,肺水(包括重症肺部超声评估肺水含量、分布及有创血流动力学评估血管外肺水)是观察脓毒症的窗口,重症患者持续体位制动,导致肺渗出呈重力依赖性改变,动态评估肺水的同时应重视体位治疗。同时脓毒症疾病微循环异质性、高/低灌注、高血管活性药、高CVP、过高的非携带氧液体、血管屏障破坏的液体过负荷等因素均可能影响肺的微循环而引起肺损伤。因此,在脓毒症治疗中应密切关注“肺为娇脏”之前哨作用,并准确评估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及器官功能状态,做到有的放矢,避免治疗相关再损伤。
“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脓毒症治疗应贯彻目标与目的、连续与动态、治疗与再损伤等治疗理念,在治疗过程中应精准目标,及时有效的液体复苏,准确评估容量状态及容量反应性,及时足量合理地使用抗生素,正确使用血管活性药物,避免单一血管活性药物的过度使用,有利于实现治疗最大化,减少治疗相关再损伤。同时在中医“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指导下进行治疗,树立“即病防传”理念,重视脓毒症治疗过程中肺保护的核心作用。
4 验案举隅
患者,男性,55岁,2020年11月7日初诊,因“畏冷、发热3 d”就诊于急诊科。患者3 d前出现畏冷、发热(体温未监测),自行服用“感冒药”未见明显缓解,后发热持续,伴气促,于笔者所在医院急诊,测体温39 ℃,血压89/54 mmHg(1 mmHg≈0.133 kPa),心率121次/min,呼吸 29次/min,氧饱和度 85%,查血常规WBC16×109/L,GR#89%,CRP>200 mg/L;降钙素原>100 μg/L;血气分析 pH 7.317、PCO226.6 mmHg、PO243 mmHg、HCO3-13.6 mmol/L;乳酸8.38 mmol/L。腹部CT示肝区存在混杂密度占位(肝脓肿可能),急诊遂予穿刺引流、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抗感染、液体复苏,考虑病情危重收入ICU。入ICU症见:高热,呼吸急促,腹胀,少神,撬舌见舌暗红、苔黄腻,脉弦数。入院中医诊断:肝痈病(阳明热盛证);西医诊断:1)肝脓肿、感染性休克;2)ARDS。治疗予液体复苏,去甲肾上腺素升压,美罗培南联合左氧氟沙星抗感染,瑞芬太尼镇痛,丙泊酚镇静,维持水/电解质平衡、营养支持等治疗。中医治以通腑泻肺、清热解毒,予宣白承气汤合仙方活命饮加减:生石膏30 g,生大黄9 g(后下),金银花12 g,栀子9 g,杏仁6 g,瓜蒌皮9 g,白芷6 g,防风9 g,天花粉9 g,贝母12 g,芦根12 g,赤芍9 g,当归9 g,桃仁9 g。每日1剂,早晚2次,浓煎100 mL。综合治疗3 d后,患者热退,气促较前缓解,血压较前改善,动态评估患者容量状态维持液体负平衡,监测肺水含量,并逐渐下调镇痛镇静药物剂量,尽可能保留自主呼吸,但患者表现为气短,倦怠,舌淡暗、苔薄黄,脉细沉,表现为邪去正伤,肺气受损、宗气亏虚之象,治以补肺气、益宗气,予补中益气汤加减:黄芪60 g,人参9 g(另煎),川芎9 g,桔梗9 g,仙鹤草12 g,柴胡9 g,白术12 g,陈皮6 g,当归6 g,紫菀9 g。每日1剂,早晚2次,浓煎100 mL,配合早期康复,呼吸锻炼,患者呼吸循环稳定,神志清楚,脱机拔管转至消化科进一步治疗。
按:本例患者急性起病,畏冷、高热,迅速进展为气喘、腹胀、少神。肺为娇脏,温邪上受,首易犯肺,患者病情初起便可见气喘、气促,综合舌脉,以阳明热盛、火毒凝结为主,阳明温病,胃肠肝胆热邪壅滞,腹部胀满,腑气不通,致肺失宣肃,喘促不宁,治以通腑泻肺、清热解毒。方用宣白承气汤合仙方活命饮加减,方中生石膏清泄肺热,生大黄通腑泻热,金银花、栀子清热解毒疗疮共为君药。臣以杏仁宣肺止咳,瓜蒌皮润肺化痰。赤芍、当归、桃仁行气活血,白芷、防风通滞散结,贝母、芦根、花粉清热化痰散结,均为佐药。肺与大肠相表里,病理上阳明经证易出现肺脏病变,经宣白承气汤通腑泻肺,仙方活命饮清热解毒,阳明热邪得解,娇肺之气机得以宣通。西医上采取肺保护通气,动态评估液体量及肺水含量,重视脓毒症患者之肺保护,终使患者病情得到阶段缓解。但患者仍有气短、倦怠等,结合患者早期阳明腑实、邪热壅盛,采用苦寒攻邪之剂易伤肺气,同时西医抗生素、镇痛镇静药物均可损伤人体正气,故后期治以补肺气、益宗气,采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方中重用黄芪、人参补肺气、益宗气为君药,臣以柴胡、桔梗举陷升提,川芎、当归行气活血,仙鹤草益气补虚,紫菀宣肺化痰,佐以白术、陈皮健脾益气,开宗气生成之源,最终患者肺气得益、宗气得复,病情得以最终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