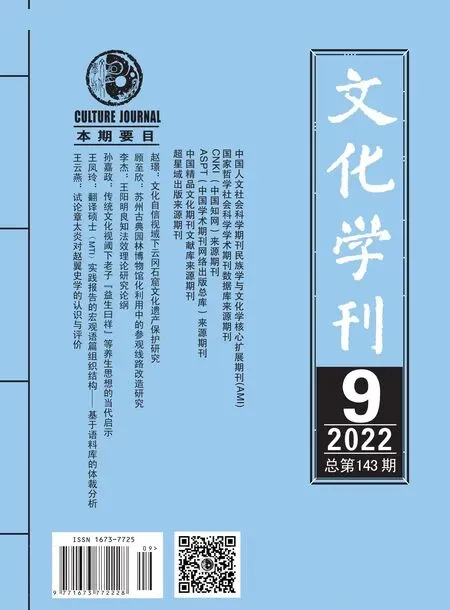女权主义视域下的《花园中的处子》
2022-12-28刘宇
刘 宇
A.S.拜厄特是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1990年布克奖得主,2008年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以来英国50位伟大的作家之一,1990年发表的《占有》使得拜厄特一时之间扬名文坛。《花园中的处子》作为《弗雷德丽卡四部曲》的首部,讲述了女主人公之一弗雷德丽卡在剧作家亚历山大所创作的纪念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历史剧《阿斯翠亚》中扮演了女主角伊丽莎白女王并因此展开了与其中的几位男性的爱情角逐。
一、蒙骗的处子
女性主义是国内研究拜厄特主要的视角之一,在《花园的处子》中,拜厄特运用伊丽莎白一世和生殖女神狄安娜作为其内在隐喻机制,以宏大而厚重的历史神话开篇,书写了英国战后五六十年代女性的成长历程。拜厄特“四部曲”的书名与每一章的题目都带有着关键的隐喻特性,《花园中的处子》这个题目将读者的阅读视野率先聚焦到了扮演伊丽莎白一世的弗雷德丽卡。弗雷德丽卡不仅有着与伊丽莎白相似的外貌,在性格、处女的身份等内在层面上也与伊丽莎白有着高度的同一性。不同于在家庭中默不作声的母亲和温柔隐忍的姐姐斯蒂芬妮,弗雷德丽卡在波特家的女人中是一个另类。她凡事擅长主动出击、努力争取,积极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像一头狮子一样富有雄心壮志。这样的弗雷德丽卡让母亲温妮弗雷德认为“攻击性”这个词用来形容自己的小女儿再恰当不过,她甚至认为弗雷德丽卡有时是被魔鬼迷住了。弗雷德丽卡扮演的伊丽莎白一世以“童真女王”而著称,甚至有人认为她的力量就来自于她的童真,她是使英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国王,但她也曾是被母亲的情人在花园里羞辱的弱小处女。站在成人礼当口的弗雷德丽卡无疑与伊丽莎白一样,面对着失去童真的危险。
可弗雷德丽卡所面对的时代要比伊丽莎白一世所处的时代堕落得多。事实上,弗雷德丽卡是十分急于摆脱自己的处女身份的。她希望自己不再是处女,这样亚历山大或者其他的男人就会开始考虑她,注意到她。加拿大人类学家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用顿悟来指代象征所表现的尚未移位的神谕世界与循环的自然世界彼此契合的点,并指出显灵或顿悟的地点不仅仅是《圣经》中出现的梯子与塔,在爱情中,它就表现为两性交欢的场所[1]294。“她指望从这位玩具娃娃旅行推销员那里获得一场顿悟。她希望自己的无知,至少一部分,能被驱散。她想变得见多识广。她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不满的源头[2]304。”对于弗雷德丽卡而言,性行为并不是由爱引起的,而是一种获得性知识的途径,为她带来一场顿悟,为她答疑解惑。这也是为什么第一部的结尾弗雷德丽卡草率地选择了被威尔基带走,了结了自己的童真。性为什么成为了女人必须要获取的知识?为什么失去女人珍贵的童真才能获得被男人注意的资格?
战争结束后,当男人从战场上返回,女人就不得不退回到家庭,而怎样使已经展现出才智与能力的女人重新心甘情愿地被套上枷锁呢?当然是为这个枷锁塑造一个美丽的神话。这个神话的内核是来自遥远的女神和他的爱人,但它的形式继续发展为劳伦斯和福斯特等男性作家为女性构筑的性爱谎言,而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力比多学说更是为男性在生理上与心理上的优势提供了“科学”依据,一切都来源于力比多,对于力比多的解放与追求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
二、典型的妻子
比起像火一样张扬的妹妹弗雷德丽卡,姐姐斯蒂芬妮性格温柔,隐忍成性。人们倾向于将《花园中的处子》的女主人公定为弗雷德丽卡,这也许是因为斯蒂芬妮最终选择了走向婚姻与家庭的老路,但斯蒂芬妮回归家庭的路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无疑产生了新的特点与意义。
拜厄特在塑造斯蒂芬妮这个人物时,将乔治·艾略特所认为的温柔、忍耐、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化特质毫不吝啬地给予了她。读者对于斯蒂芬妮的印象同书中剑桥里的男人一样,认为斯蒂芬妮是典型的妻子。斯蒂芬妮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摆脱那些疯狂向她求婚的男人们,“他们不说我们去跳舞,我们去度假,我们去上床或者什么,却只说我想跟你结婚,带着某种庄严的敬意。我不知道怎么应对。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2]163。”可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在她回到家乡并偶然认识了牧师丹尼尔时,这样的情况又重复上演。斯蒂芬妮无意中救了几只刚出生的小猫,它们的母亲难产而死,于是她便将它们带回家。牧师丹尼尔发现了斯蒂芬妮身上那种细心温柔、富有同情心、乐于奉献的精神,并谋划着斯蒂芬妮可以帮助进行宗教援助。当丹尼尔直接了当地同斯蒂芬妮提出结婚时,斯蒂芬妮哭了起来,这是她少有的表达出自己不再说没关系的时刻。“我想我大概没有性吸引力,都只是为了结婚[2]164。”从这里也能看出劳伦斯的性爱神话对于斯蒂芬妮也是有影响的,她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对于男性的性吸引力,而看不见两性关系中其他的方面。“他们谁都不了解我。我大概长了张脸,就像他们为香烟广告而选择的脸,一张典型的妻子脸。这简直是侮辱[2]164。”斯蒂芬妮好妻子的形象符合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宣扬的主流价值观,尤其是当媒体大肆渲染伊丽莎白二世不再作为一个女王而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的形象时。这样的形象来源于英国现实社会的需要:“离婚率激增、堕胎率上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由的单身主义而人口增长率却越来越低[3]。”当伊丽莎白二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之时,情况与伊丽莎白一世的神圣严肃完全不同。女王的名字肆意地在男人嘴里遭到各种各样的谈论,人们需要一位世俗的妻子,需要这样的伊丽莎白二世,也需要这样的斯蒂芬妮。
丹尼尔带给斯蒂芬妮的打击不仅是来源于和那些剑桥男人无二的凝视,这种意图还具有着另一层深意,即斯蒂芬妮是适合奉献于宗教的女人。丹尼尔通过斯蒂芬妮照顾刚出生的小猫这一举动敏锐地发现了她新的“价值”——隐忍、宽容、奉献、富有同情心,如此适合从事宗教职业的性格。在结婚前斯蒂芬妮与主教的谈话中,主教甚至认为她比丹尼尔做得更好,更适合从事这一职业。在第二部《静物》中,丹尼尔也表达了这样的反思,他迟钝地意识到自己不仅将自己奉献给了上帝,连同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也一并奉献了出去。而这一点是细心的斯蒂芬妮在婚前就考虑到的,但是最后斯蒂芬妮因为与丹尼尔发生了关系选择了与他结婚,走向了婚姻与家庭。她掩埋了自己所有的文学才华,掩埋了济慈《希腊古瓮颂》中的那只瓮。浪漫的文学世界与枯死的现实世界所形成的巨大的落差,让人心痛。在第二部《静物》中,当斯蒂芬妮将儿子交给母亲与弟弟照看,自己逃到公共图书馆想要有一点时间去读一会儿书时,儿子的受伤仿佛是一个诅咒,印证了在家庭中她必须牺牲爱好与梦想,没有任何余地。一点点的抗争与忤逆,都会让她受到惩罚。最后斯蒂芬妮为了救一只误入家中的鸟儿,被电冰箱的接地线电死,她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让所有人措手不及。斯蒂芬妮的死亡方式固然是拜厄特对劳伦斯关于死亡看法的强烈愤慨,但将此置于宗教的背景中去看,死亡就具有了反抗的意味。而那只误入房子的鸟,恰恰隐喻了富有才华却被囚禁在家庭牢笼中的斯蒂芬妮。
三、失声的母亲
对于《花园中的处女》中的女性形象,读者与学者们的目光都会集中在妹妹弗雷德丽卡与姐姐斯蒂芬妮身上,往往忽视了她们的母亲温妮弗雷德。实际上,温妮弗雷德是英国战后五六十年代“家庭女性”的典型形象,更直观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对于抹杀女性声音的残忍现实。同时她在家庭中的失声,意味着一位母亲的缺席。这种精神上的不在场对于儿女来言是一场灾难,间接造成了大女儿斯蒂芬妮成为牧师之妻的不幸的命运与二女儿弗雷德丽卡在性方面的放纵以及小儿子马库斯性格怪异最终被男教师卢兹斯引诱而出现精神问题。
拜厄特在第一部《肉》这一章中以温妮弗雷德的视角讲述了她是如何变成一个在家庭中失声的女人的。温妮弗雷德对于小儿子马库斯奇怪的行为默不作声,原因之一是因为她的丈夫比尔脾气火爆,温妮弗雷德不希望出现任何能刺激他的因素。当她回忆起自己与比尔相爱相知的过程时,她明确地知道自己爱上比尔是因为他的热情与才华,但当比尔强势而具有压迫性的力量向温妮弗雷德涌来时,温妮弗雷德选择了隐藏自己的力量而接受比尔的全部。“面对比尔这种疾风暴雨般的爱,她只能保持沉默。能量化成惰性。无所作为。消灭棱角。也许她这样做不对。这样做让人很不甘心[1]126。”温妮弗雷德也是一个受过教育、富有才华和自己的想法的女人,可这种惰性的选择导致了在她与比尔的关系中她的声音一直被比尔压抑着。比尔并不喜欢《冬天的故事》,温妮弗雷德却曾勇敢地思考到戏剧里赫米奥娜的命运:“她就那么失去了自己全部的女性岁月,她的两个孩子,一个死了,一个失踪了,除了感激和欢喜,她没有别的感情诉求[1]121。”可悲的是,温妮弗雷德选择成为了同赫米奥娜一样的人,对于丈夫的怒火逆来顺受、不发出一点声音的女人。
温妮弗雷德将在与比尔的关系中所采取的消极态度继续沿用在面对自己的孩子上,她将教育孩子的权利全部交给丈夫比尔,任由比尔不顾女儿们自己的意愿将她们送去可怕的文法学校,给学校写信,让女儿们接受了不正确的性启蒙知识;任由比尔将小儿子马库斯的数学天赋抹杀。作为一个母亲,她放弃了捍卫自己儿女们的幸福与自由的权利。可如果能够发出温妮弗雷德为何如此的疑问,我们就能发现“母亲”这个身份对于所有女人的意义和影响。不可置否,温妮弗雷德的失声一方面是由丈夫比尔造成的。也就是说,女人的失声一方面是由男人造成的。可当温妮弗雷德想起自己的母亲并发誓绝不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女儿们抱怨家庭婚姻中的不幸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女人的失声一方面又是女人造成的,这个女人就是“母亲”。
“她最害怕像母亲那样生活,孩子那么多,钱那么少,被一个家和丈夫制约着,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履行的道德责任和身体的持续的破坏者[1]122。”母亲的影响,让她选择了比尔。她本以为她选择了一条与母亲截然相反的道路,她就能走向幸福的婚姻,可结局却是极具讽刺性与诅咒性的殊途同归。正是因为温妮弗雷德的母亲总是向她抱怨,正是温妮弗雷德自己也曾作为女儿感受到那种压抑与烦恼,所以当温妮弗雷德自己做了母亲时,她选择了对子女们保持沉默。“她发誓,绝不像母亲跟她说的那样跟自己的女儿们说这些,绝不。她要沉默不语。沉默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广,到了原本尚存希望的地方[1]123。”而显然,温妮弗雷德矫枉过正,失去了与子女正常的交流以及参与子女成长的权利。
温妮弗雷德作为“母亲”形象的典型,正体现了拜厄特对于女性问题独特的思考和更高的目光。在二战后的欧美国家中,无数女孩儿都像温妮弗雷德一样,意识到母亲对自己的影响,极力摆脱却无可奈何。“在我那个时代,尽管我们都很爱自己的母亲,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想做像母亲那样的人[4]。”可当女儿的身份转换为母亲时,她们的想法也是如此矛盾。“奇怪的是,许许多多热爱自己女儿的母亲也不希望她们的女儿长大以后像她们自己那样。”拜厄特通过母亲温妮弗雷德与两个女儿的人物关系指出了女性自我成长中的矛盾性,女权主义者往往将所有的怒火都对准二元对立模式下的男人,男人作为女人的敌人,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与批判。但拜厄特显然关注到了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更多原因,这其中就包括来源于女性内部的因素。女性主体自身作为女人也不可避免地忽视甚至是不肯承认女性自己的影响力与价值,那么持此立场的女权主义者足够让人反思其中的狭隘与盲见。
四、结语
“拜厄特对女性主题表现出了特有的偏爱,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极具女性特质的女性人物形象,彰显了妇女解放的相关思想,尽管她本人也不主张评论界把她的作品看作女权主义的宣言,但其创作思想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女权主义意义[5]。”拜厄特作为知识型作家,以后现代主义实验的手法反映了英国特定时期的现实,塑造了新的女性人物形象,书写了女性新的历史,诉说了女性的生存处境,发出了被忽视已久的来自于女性的声音。[6]但拜厄特显然在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别样的思考,她打破了劳伦斯、福斯特等男性作家构筑的性爱神话,否定了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弗洛伊德主义将一切都归于力比多的男权主义。[7]同时她也表现了女性性解放后带来的新的压迫、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等新的问题,对偏激的女权主义作了镇静的思考与理智的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