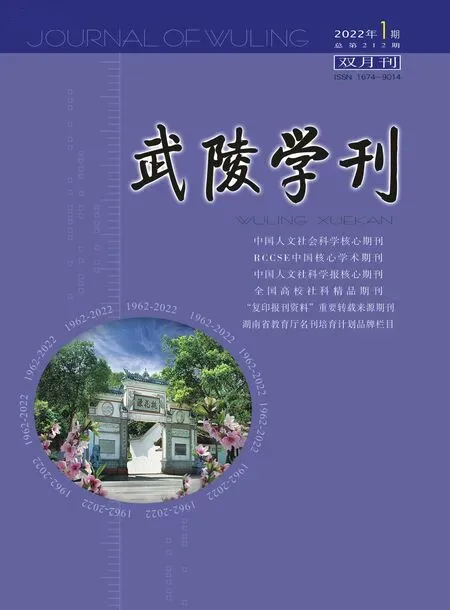介子推与春秋时期晋国忠德传统
2022-12-28桑东辉
桑东辉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国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介子推(亦作介之推、介子绥、介推、介子)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臣子,其随主流亡、割股食君、功成逃禄、母子偕隐、焚死绵山的故事千古流传,更衍成寒食节、清明节等风俗,其昭示出的忠贞不贰、功成身退、死以明志等优秀道德和高尚品格,鲜明地反映出传统忠德在春秋时期的价值取向。把介子推放在春秋时期的时代大背景下和晋国这一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挖掘和分析其忠德内涵,不仅有利于揭示春秋时期晋国忠德的样态和作用,而且有利于系统考量中国传统忠德的精神实质及其变迁历史,有利于传统忠德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文化自信,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介子推的生平事迹考索:以传世文献为中心
介子推是历史上实有的真实人物,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介子推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被不断添附上一些新的情节。因此,客观地讲,历史上有两个介子推:一个是历史真实的介子推,一个是形象流变的介子推,后者更多地代表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文化现象。
最早记载介子推故事的史书是《左传》。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除了《左传》有介子推的记载,在先秦典籍中,一些诸子著述和《楚辞》也多处提到介子推。如,在《庄子·盗跖》中,借盗跖之口说出了:“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又如,在《韩非子·用人》中也有“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结其德,书图著其名”的说法。再如,在《吕氏春秋·季冬纪·介立》中记载:
今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穷矣,贱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国有万乘,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能其难,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悬书公门,而伏于山下。文公闻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簦,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人心之不同,岂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干嗌,日夜思之,犹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务疾逃之,介子推之离俗远矣。
《楚辞》中亦有对介子推品格的歌颂,如《九叹·惜贤》曰:“若由夷之纯美兮,介子推之隐山。”又如,《九章·惜往日》曰:“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再如,《九章·悲回风》曰:“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
到了秦汉时期,介子推的故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一是关于“龙蛇之歌”。在《说苑》中,三处提到介子推,其中卷六《复恩》基本是对《左传》和《吕氏春秋》相关记载的整合,区别在于围绕“龙蛇之歌”的作者,《吕氏春秋》认为是介子推“自为赋诗”,而《说苑》却归之于介子推的“从者”。汉人的《新序》和《韩诗外传》则与《吕氏春秋》同,均持介子推自作“龙蛇之歌”的说法。只不过在不同记载中,“龙蛇之歌”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意思都是一致的。二是关于介子推割股疗饥。介子推割股一事首见于《庄子·盗跖》。《韩诗外传》与《庄子》一样,提出“重耳(在曹国)无粮,馁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后能行”的说法。三是关于介子推焚死。介子推被烧死的说法在《左传》《吕氏春秋》《楚辞》《说苑·复恩》中都没有提及,均持介子推隐居之说。最早提到介子推被烧死是《庄子·盗跖》,《说苑·杂言》亦采《庄子》之说,并借孔子之口说出“介子推登山焚死”。《新序·节士第七》对此事说得相对详细,即介子推隐居介山之上(就是所谓绵上之山),“(晋)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此外,在《说苑·尊贤》中还曾提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的说法,此说缺乏佐证,不详其所何据,除了《说苑》,很少被人提及,兹不采信。
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对介子推故事进行了整理和完善,其取材主要来源于左氏史书记载以及先秦秦汉相关传说,其叙事提到了介子推不言禄、与母归隐绵上之山、从者作“龙蛇之歌”等事迹,但没有提到介子推割股和焚死之事。因《史记·晋世家》文字较多,兹不全文通篇迻录。概言之,尽管太史公没有提到介子推割股和焚死的事,但在民间,有关介子推割股和焚死的传说却非常流行,并分别衍生出不同的文化现象。一方面,介子推割股食君的忠在汉晋时期被敷衍成孝子割股疗亲的孝道精神;另一方面,介子推宁死不出被烧死在绵山的事成为寒食节、清明节等民间习俗的源头。
关于介子推与寒食节的关系,在《太平御览》《初学记》等类书中多有辑录。以《初学记》“岁时部下寒食五”为例,其辑录晋人陆翙《邺中记》有关寒食节的记载,以及汉人周举和魏武帝曹操曾经尝试对寒食习俗的纠偏,如其引《汝南先贤传》曰:“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烟爨。”又引陆翙《邺中记》曰:“并州俗,冬至后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今之糗是也。”说明了因介子推焚死,当地人有断火、冷食、食粥的习俗。又因这种习俗不利于人的身体健康,后汉并州刺史周举和魏武帝曹操都对此有过纠偏的举措。正如范晔《后汉书·周举传》曰:“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魏武帝《明罚令》曰:“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推独为寒食,岂不悖乎!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从寒食节习俗的传衍看,周、曹等人纠偏的努力有一定的效果:一方面纠正了长期寒食的陋习,一方面又保留了纪念介子推而短期寒食的习俗。
随着介子推故事的传播和流布,出现了一些神话化和附会的趋势。据《拾遗记》卷三“鲁僖公”记载:
僖公十四年,晋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鸦绕烟而噪,或集之推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种仁寿木,木似柏而枝长柔软,其花堪食,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寿之华焉。”即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数百里居人不得设网罗,呼曰“仁乌”。俗亦谓乌白。臆者为慈乌,则其类也。
介子推的故事经过先秦、秦汉、魏晋的流衍,在宋元明清时期逐渐成为话本、杂剧、戏曲、小说的创作素材,并衍生出元杂剧《晋文公火烧介子推》、清传奇《介山记》《晋春秋》、秦腔《火烧绵山》、清代世情白话小说《介子推火封妬妇》(见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等不同文本,特别是明代的《东周列国志》依据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将历代流传的介子推故事进行文学化处理,极大地渲染了“介子推割股啖君”“介子推守志焚绵上”等忠德内涵。
关于介子推的事迹,《左传》是最早记载介子推的史籍,其记述大体可信,但过于简略,很多地方语焉不详。《史记》在《左传》的基础上有所丰富和完善,也相对可信。但《左传》和《史记》都没有关于介子推割股疗饥和被晋文公烧死绵上之山的记载。介子推割股和焚死之事首见于《庄子》,这里不排除附会虚构的成分,但在历史研究中,所谓“说有容易说无难”。尽管有人质疑介子推割股的真实性①,但这并不足以否定介子推割一小条股表肉做成肉汤以奉君充饥的可能性。同样,介子推焚死绵山的事迹也存在真伪之辨。但由于世事久远,史料阙如,很多有关介子推的真实事迹已经湮没无闻,难以考索和最终定谳。
尽管“介子推传说的文本记忆从历史发端,经过岁月沉淀,已经从记忆链条的顶端走向了底端,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演变成广为流传的传说故事”,但在“变”的过程中,“一系列故事情节都层累地合理粘连在一起,使介子推传说演变为一个系统的历史记忆体系”[1]。笔者暂视介子推割股疗饥、焚死绵山等为历史实迹,而不采过于荒诞不经的火封妬妇、封神升仙等演绎传说,重点以先秦、秦汉等早期文献为基础,围绕介子推之忠及其与春秋时期晋国忠德传统的关系,做一研究和论述。
二、春秋时期晋国的忠德状况
根据现存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看,最初的“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这说明,最晚在春秋时期,忠德已经成为一种道德规范。下面,简要概述一下春秋时期晋国的忠德状况。
(一)利国利民为忠
在春秋时期,忠体现为一种利国利民的政治道德。就利国之忠而言,所谓“忠,社稷之固”(《左传·成公二年》),且“杀身赎国,忠也”(《国语·晋语四》)。至于利民之忠,随国大夫季梁说得很清楚,即“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左传·桓公六年》)。从根本上讲,民为国之本。利国与利民虽然一字之差,实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赵盾作为晋国的忠臣代表,其忠就在于爱国爱民。围绕刺客鉏麑对赵盾的评价,《国语·晋语五》载:“赵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贼国之镇,不忠。”而《左传·宣公二年》则载:“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二者记载虽略有差异,但不可遽断哪一个记载为讹误②。在《左传》中,“不忘恭敬”即“民之主”;而在《国语》中,“不忘恭敬”乃“社稷之镇”。因此,在鉏麑看来,贼杀“民之主”和“国之镇”是一回事,二者具有可通约性和可替换性。
(二)忠君卫主为忠
一是委质为臣,食禄卫主。自古就有委质策命(一说委质策名)之说。作为臣子,一旦委质策命,就要对主子效忠,所谓“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国语·晋语九》)。正如晋国狐突所言:“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委质策命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臣对君的义务,关键在于君臣之间的利益交换。君主赐臣子以食邑、食禄,臣子则献出自己的忠诚,效忠于君主。“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从君而贰,君焉用之?”(《国语·晋语一》)由此可见,食人之禄,就要誓死效忠。
二是层级效忠,各为其主。西周以来实行的是等级分封制,即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封卿大夫,由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家臣等,形成了逐级分封、层层效忠的“金字塔状”政治格局。这也决定了臣子之忠的对象是有层级性的,而不可躐等以求。在晋国历史上,家臣忠于主子的例子比比皆是。《国语·晋语九》记载了魏献子的家臣阎没和叔宽,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尹铎、伯乐等对主人魏献子、赵简子的竭己之能和忠心卫主。在君臣冲突面前,春秋时期也是普遍认可“各为其主”的,如晋国栾氏之臣辛俞违抗君命,追随栾氏。因为辛俞坚守“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和“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国语·晋语八》)的古训。在时人看来,即便是父子、兄弟也不应为了亲情而背叛主子。早在曲沃武公进攻晋侯夺取晋国政权时,栾氏家族就上演了父子各为其主的一幕。“武公伐翼,杀哀侯,止栾共子曰:‘苟无死,吾以子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辞曰:‘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君何以训矣?且君知成之从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从君而贰,君焉用之?’遂斗而死。”(《国语·晋语一》)栾共子的父亲栾宾是曲沃老臣,而栾共子则效忠晋哀侯,并为其战死,可谓父子各为其主。对同一历史事件,《左传》注者杜预曰:“父子各殉所奉之主。”(见《左传·桓公三年》杜注)这是最典型的各为其主。
三是骨鲠谏诤,为臣必谏。臣子享君禄,谏诤就是作臣子的分内之事。所谓“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国语·晋语六》)谏诤不仅仅是为社稷、为君主负责的行为,更具有忠德的内在价值。“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国语·晋语六》)因此,聪明的君主都是鼓励臣子积极进谏的。忠谏可以说是做臣子的首要义务和行为准则。“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臣行君明,国之利也。”(《国语·晋语三》)反之,“有纵君而无谏臣,有冒上而无忠下。君臣上下各餍其私,以纵其回,民各有心而无所据依。以是处国,不亦难乎!”(《国语·晋语一》)
四是事君以义,不阿其惑。与君王意见不合,臣子可选择离去。所谓“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国语·晋语一》),将道义置于片面迎合君主意愿之上。当与君主道不同、谋不合时,臣子可转投他国。《左传·成公十七年》载,晋国发生内乱,胥童、夷羊五与长鱼矫联手,灭掉三郤,进而主张杀掉栾书和中行偃。晋厉公不忍心“一朝而尸三卿”,长鱼矫曰:“不杀二子,忧必及君。”遂出奔狄。这个故事说的就是谏而不听则去的道理。
五是勇不逃死,愚忠效节。晋国太子申生在士蒍劝其仿效吴太伯远走以避祸时,回答说:“为人子者,患不从,不患无名;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无禄。今我不才而得勤与从,又何求焉?焉能及吴太伯乎?”(《国语·晋语一》)随着郦姬陷害的不断升级,有的人劝太子“君必辩焉”,向晋献公揭穿郦姬的阴谋,但太子坚持:“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别人劝他出奔,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左传·僖公四年》)最后自缢而死。愚忠在晋国是有传统的。晋国大臣荀息也是竭力事君乃至愚忠而亡的典型:“吾闻事君者,竭力以致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国语·晋语一》)最终在未完成晋献公托孤之命时自杀。
六是君父不校,事君不贰。所谓“事君不贰是谓臣,好恶不易是谓君。君君臣臣,是谓明训”(《国语·晋语四》)。面对骊姬之祸,重耳虽然没有像申生那样愚忠殉死,但也不敢与君父之命抗争。“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事君不贰的品德被普遍认可。一方面,事君无贰会受到表彰和颂扬,另一方面,如果臣子有贰心不忠诚是要受到惩罚的。国君是最恨贰臣的,尽管有的是依靠贰臣得到国君之位,但他们往往过河拆桥,以不忠为借口除掉帮助过自己的贰臣。如晋惠公主政晋国后,首先杀了大臣里克。“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其君者不亦难乎?”(《左传·僖公十年》)里克的悲剧证明了不忠怀贰的必然结局。
(三)公正无私为忠
一是分配公平之忠。春秋时期就将忠上升为保证分配程序正义的重要手段,所谓“忠所以分也”(《国语·周语上》)。周内史兴在赐晋文公命服后,归告周王曰:
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义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仁行则报,信守则固,义节则度。分均无怨,行报无匮,守固不偷,节度不携。若民不怨而财不匮,令不偷而动不携,其何事不济!中能应外,忠也;施三服义,仁也;守节不淫,信也;行礼不疚,义也。(《国语·周语上》)
内史兴将忠视为忠、信、仁、义等四德之首,作为“礼所以观”的重要内容。这个忠不是通常所说的忠君、为人谋忠一类,而是分财上的公正,是一种保证公平正义的道德实践工具,故“忠分则均”,“分均无怨”。所谓“忠自中”,“中”本身就具有公平、公正的意蕴,这种内在的公平、公正意识体现在分财等社会活动中,则表现为“忠”的原则。
二是公而忘私之忠。忠的公平公正必然是建立在对私利、私情、私欲、私怨的控制和规制上。晋国发生政变,大臣贾季奔狄。赵宣子出于同僚之谊派臾骈护送贾季家人到狄国。此前,贾季曾因事当众惩罚过臾骈,此次护送其妻子,臾骈部下劝他乘机尽杀贾氏以报昔日之仇。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指赵宣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左传·文公六年》)于是,臾骈亲自带人护送贾季的家人和财物出境,他用自己的言行很好地诠释了无私的忠道。
(四)尽心竭力为忠
忠是由中和心组成,是人从内心坚持“中”的原则之外显。晋国叔向说过“忠自中”(《国语·晋语八》)。韦昭注曰:“自中出也。”忠就是发自内在心意的绝对真心流露,强调的是表里如一,考中度衷。尽心竭力的忠更多地体现在在下者为主子的出谋划策上,如董安于等为赵简子谋,以及在晋阳为赵氏收买人心的尹铎等,都是忠于主子的例子。《国语·晋语四》盛赞晋公子重耳“从者之谋忠”。重耳的从者之谋忠到什么程度,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重耳流亡到齐国时,“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重耳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跟随重耳一起流亡的狐偃、赵衰等设计灌醉重耳,驾车载着他离开了温柔富贵乡齐国,重耳酒醒后拿戈来追打狐偃。但就是因为有狐、赵等一批忠心耿耿的谋士,重耳最终才得以复国。
(五)尽职尽责为忠
忠就是要恪尽职守。这方面春秋史官做得最直截。晋灵公与赵盾矛盾升级后,赵盾的弟弟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左传·宣公二年》)也就是说,尽管赵盾本人没有参与弑君,但作为大臣,只要没有出国境就应该讨伐弑君逆臣,如果跑出国境外就不算弑君了。因此。连史家都为赵盾惋惜,但晋国史官董狐却不得不把赵盾弑君记录于史册。
三、介子推忠德精神的主要表现
介子推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传统忠德的内在精神和道德践履,多角度、多侧面反映了传统忠德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一)忠于主子,誓死追随
在晋国发生骊姬之祸后,特别是在太子申生被迫害自缢后,晋献公的诸公子惶惶不安,纷纷踏上流亡之路。按照春秋时期“君亡臣从”的政治道德和习惯,公子的臣属也应跟随并保护主子出奔。介子推是作为公子重耳的臣属而随重耳出奔流亡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谓“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一语道破介子推是重耳的“从亡者”身份。在追随晋文公流亡的臣属中,介子推并不是最突出、最有名的。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文公重耳,从小就喜欢养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这五个人也跟着重耳一起流亡各国,“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鞮趣杀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从此五士,其余不名者数十人,至狄”。也就是说,重耳流亡到狄时,除了赵衰等五人追随外,还有不大知名的数十人,介子推就在这“不名者数十人”之中。但按照《韩诗外传》的说法,介子推并非“不名者”,而是帮助重耳复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其功绩和地位与狐偃、赵衰比肩,所谓“晋文公困于骊氏,疾据咎犯、赵衰、介子推而遂为君”。
在春秋时期,追随主人出奔流亡是臣属忠德的基本规范。追随主人出奔不仅要遭受道路艰辛之苦、绝粮断食之饥,而且有时往往伴随着政治迫害。因此,没有誓死相随的忠贞是无法做到始终追随而绝不携贰离叛的。关于重耳随从所遭受的政治迫害,据《史记·晋世家》载:“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国中诸从重耳亡者与期,期尽不到者尽灭其家。”《史记》记载了狐突因儿子追随重耳而遭政治迫害身死的情况。“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肯召。怀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数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怀公卒杀狐突。”尽管史书中没有关于介子推家人是否遭到威胁和迫害的记载,但从“令国中诸从重耳亡者与期,期尽不到者尽灭其家”的情况看,介子推的家人应该也遭到了迫害。周朝是血缘宗法世袭社会,介子推作为大夫,其父亲也应该是大夫这样的贵族阶层,但从史书记载看,重耳复国后,介子推只有母亲,其父应该在此之前就已经死亡。介子推父亲死亡的原因史籍缺载,但不排除因介子推追随重耳而遭到政治迫害死亡的可能性。因此,介子推追随重耳流亡,不仅要忍受饥寒,自己和家人还要受政治迫害。但越是这样,越能体现介子推委质为臣、忠贞不贰的品质。
(二)竭忠尽力,割股食君
作为从者,介子推始终竭忠尽力,赤胆忠心。《庄子·盗跖》曾记载:“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关于介子推割股食君的故事,在很多典籍中都有记载,如《韩诗外传》载,“晋文公重耳亡过曹,里凫须众,因盗重耳资而亡。重耳无粮,馁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后能行”。此处将重耳绝粮的原因和地点都交代清楚了,即重耳是因为在曹地被不忠的臣属盗资而去导致绝粮断炊,这才引出介子推割股食君的。用里凫须后来的话说,“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闻”。而《东周列国志》则将介子推割股的故事与重耳五鹿绝粮、野人授之以块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但不管怎么说,介子推竭忠奉主、割股食君的故事千古流传。《琴操》曰:“介子绥割腓股以啖重耳。”《吕氏春秋》盛赞介子推的忠诚,曰:“以贵富有人易,以贫贱有人难。今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穷矣,贱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
(三)绝不贪功,辞禄隐居
在最早记载介子推史事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集中记载了介子推辞禄的言行。史载:“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子推的观点是:“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也就是说,介子推认为重耳能够复国,绍继晋国大统,实际上是一种天命的结果,并非重耳身边这些臣子的功劳。这些臣子贪天功以为己力,实际上是一种厚诬欺罔、类似偷盗的不道德行为,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比“窃人之财”的偷盗行为还要可耻。介子推的这种言行,在《史记·晋世家》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先是在鲁文公元年,重耳渡河归晋时,咎犯提出:“臣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臣犹知之,况于君乎?请从此去矣。”重耳表态说:“若反国,所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并投璧于河,作为盟誓。当时介子推在船中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乃自隐渡河。等到重耳复国为晋文公后,大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但因靖王难而未尽行赏,是以赏从亡者而未及介子推。介子推本人亦不言禄,故而禄亦弗及。在此,太史公将《左传》的相关记载迻录于此,表达了介子推关于天命所归、非二三子之力的不贪功主张。
从《史记》的记载看,介子推在归国渡河时就因不满咎犯的苦情要挟行为而与他们分道扬镳,“自隐渡河”。晋文公赏不及介固然有君王遗忘疏漏的因素,也与介子推“不言禄”的功成身退、自隐辞禄性格有关。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介子推曾写了一首表明心迹的“龙蛇之歌”,并悬书公门。晋文公虽然以“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的赏格来寻找介子推,但介子推宁可负釜盖簦也不肯出山,终身不见。《吕氏春秋》盛赞道:“反国有万乘,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
(四)不忘初心,以死明志
对介子推不贪天功、辞禄隐居的行为,不仅世人不理解,介子推的母亲也曾试探着表示:“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但介子推表示:“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同上)介母又表示:“亦使知之若何?”(同上)介子推坚定不移地表示:“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同上)在介子推母子的对话中不难发现,介子推既不想邀功求禄,也不想效尤随俗,更不愿违背初心。在介子推看来,既然通过“龙蛇之歌”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发了牢骚,那就相当于不再委质策名,从此不食君禄,君臣义绝;既然下定了决心隐居,那就不必大张旗鼓向世人表明己志。
《左传》记载介子推母子偕隐,“遂隐而死”,没有交代介子推的死因。《庄子·盗跖》将介子推的死因归之于火灾,所谓“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并将介子推的离去归之于晋文公的背恩和介子推的负气怒去。《说苑·杂言》亦曰“介子推登山焚死”。《新序》“节士篇”对介子推的死亡描述得比较全面,其记载:介子推隐居介山之上,晋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后来,“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不论介子推是隐居而死还是遭焚山而死,最终介子推都坚守了自己不贪天功、隐居避世的原则,还不惜以死明志。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介子推追随重耳流亡和割股食君无疑都是臣子忠德的一种体现,而他功成身退、辞禄逃赏和隐居山里、宁死不出的行为,也体现了忠的精神特质。其中,功成身退、不贪天功、辞禄退隐是历代忠臣的行为圭臬,而不忘初心、宁死不出则是忠于自己人生选择的一种超越狭隘忠君意识的自为之忠。
四、介子推忠德精神的多元价值
介子推的忠德是春秋时期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变迁的规律。从道德哲学角度看,介子推的忠德具有较为丰富的价值内涵,其多元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介子推忠心卫主、割股食君体现的是一种规范伦理
英国伦理学家西季威克曾经指出,在人的道德判断中,“正当”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被判断为正当的行为是实现某种被理解了的——若不是被直接表达了的——目的的最适合的或唯一适合的手段”[2]。按照规范伦理的理论,目的论和道义论是规范伦理的基础。特别是从道义论的角度讲,对某一行为的善恶或正当性的判断,“不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带来或可能带来怎样的实质性价值或效果,而取决于该行为是否符合某一相应的普遍道德规则,是否体现了一种绝对的义务性质”[3]72。介子推的忠君和割股食君的奉献精神,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规范伦理的意蕴。
在春秋时期,“委质策名,有死无贰”是臣子的最基本责任和义务。作为晋公子重耳的属下,按照“君亡臣从”的政治道德要求,在晋国发生骊姬之乱后,介子推追随公子重耳出奔、流亡,颠沛流离,忍饥挨饿,这是臣子应尽的责任。此外,当重耳君臣在路上绝粮、饥馑难捱时,介子推割股食君,更是将这种规范伦理高扬为一种更高层面的奉献精神。有研究者指出:介子推“割股并非为了图报,也绝非为了取宠重耳,而是他对重耳的满腔忠诚的体现。从现实的观点说,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就是无私奉献的精神”[4]。这种舍己救人的奉献精神因其效忠的对象为君主,故而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和仁爱之心的体现,而主要表现为一种臣子忠君道德的规范伦理。
(二)介子推功成身退、辞禄隐居体现的是一种美德伦理
相对于规范伦理而言,美德伦理凸显人的道德动机,其道德选择的前提不仅仅是道德规则,而是“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自主自愿的主体精神”[5]41,“他们不再是机械地遵守道德原则的人,而是有其自己的情感、动机及能力作出道德判断、进行道德选择并过着真正道德生活的人”[5]42。也就是说,“美德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6]242,如悲剧中所表现的那样,“悲剧主角的道德使命完成得是好是坏,与他的取舍选择无关——假如他没有什么正当的选择可作的话。悲剧主角的行为可能是英雄式的或非英雄式的、慷慨的或吝啬的、优雅的或卑劣的、审慎的或鲁莽的”[6]285。介子推的功成身退乃至为了个人主体精神的选择而宁可焚死绵山不仅体现了其个人的道德自主性,而且表现为一种非功利、超越规则约束的自我价值的获得,并以英雄般的悲剧将这种美德高扬到顶峰。具体而言,在坚守竭诚忠君的规范伦理的同时,介子推始终清醒地坚守住内心的道德底线,将美德伦理看作是与规范伦理同等重要的道德红线。在介子推看来,晋公子重耳能够在流亡19年后成功复国,接任晋国国君之位,这实际上是天意,并非狐偃、赵衰等人(包括自己)的功劳。介子推认为,做臣子的不可以“贪天功以为己力”。介子推对咎犯等人贪功要主行为不以为然,对臣子邀功争赏行为更是不齿。
当介子推用“龙蛇之歌”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怨望后,晋文公曾表示:“嘻!是寡人之过也。吾为子爵,与待旦之朝也;吾为子田,与河东阳之间。”但介子推认为“君子之道,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新序·节士》)。也就是说,靠请求和牢骚等方式来争得爵位和财禄是违反清廉之士道德操守的,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在介子推看来,自己选择辞禄退隐是完成了忠君这一规范伦理之后的一种自我选择,完全是一种自主的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无疑体现了一种君子美德。某种意义上说,介子推功成身退、不贪天功的归隐美德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伯夷、叔齐的隐逸精神,对后世范蠡功成身退、泛舟五湖具有启示作用。
(三)介子推不忘初心、坚守贞悫体现的是一种信念伦理
信念伦理是万俊人先生提出的概念,他定义信念伦理为“一种纯粹理想和终极目的层面上的道德精神”[3]37。尽管万俊人先生主要是从宗教信仰层面来阐释信念伦理的,但从其名之为信念伦理而非信仰伦理来看,信念伦理无疑具有超越狭隘宗教视域的广义内涵。从介子推的言行看,他自始至终都坚守着不可移易的个人道德操守和自我价值旨归,有着明显内心贞悫和初心意识。具体而言,介子推的初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即天道。按照中国传统观念,道(或者天道)是指导人类社会的圭臬和铁律。道分天道、地道、人道,具体又包括政治生活中的君臣之道,社会生活中的父子、夫妇之道等。介子推时刻坚守道,道就是他的初心和使命。当自己所服务的公子重耳因政治迫害而流亡时,介子推坚守“君亡臣从”的臣道而随重耳出奔流亡;当途中断粮、困顿饥馑时,介子推竭己为君、割股食君;当风云突变、重耳复国前后,介子推不耻同僚贪天功、争禄赏的行为,而坚守功成身退的天道,飘然隐退;当晋文公以追赏和焚山的软硬两手来逼迫介子推出山就范时,介子推坚守个人信念,不为所动,以死明志。从介子推上述行事中可见,其在仕宦则不违臣道,遇名利则不违天道,事母则不违孝道。概言之,介子推是一个在天道指导下奉行人道的典范人物。而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于其坚定的个人信念,体现了其尊奉道(天道)的信念伦理。在诸侯力征、天下逐利、上下相蒙的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介子推的特立独行、独标异格和超迈绝伦,充分彰显了道德信念的强大力量和永恒价值。
(四)介子推辞禄逃赏、隐居不仕丰富了忠德的核心价值
在春秋时期,忠君不贰、竭己卫主无疑是臣子忠君道德的主流,但在构成先秦忠德的核心价值方面,介子推的辞禄逃赏、隐居不仕,以及他的人生态度,对忠君道德核心价值的塑造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一方面,介子推故事彰显了臣子忠谏精神,丰富了谏诤的形式。在忠君的谏诤形式上,自古就有犯颜直谏、兵谏、诗谏、尸谏、微谏、讽谏等多种形式。介子推以辞禄的方式,表达了对“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种君主滥赏、臣下争赏的谏诤意蕴。介子推通过“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和“为人子而不能成其父者,则不敢当其后;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新序·节士第七》),采取正话反说的委婉劝谏方式,表达了英明君主应该明察秋毫、赏功罚罪的忠告。不仅如此,介子推还是较早采取诗谏的人。其龙蛇之歌虽然不同典籍记载有所出入,但“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的表述,不仅仅表达了自己高洁的本性和被忽视的委屈,也是对君主的一种委婉劝谏。尽管《史记》将“龙蛇之歌”归之于介子推的从者,但大多数典籍提到“龙蛇之歌”时都视其为介子推所作。在介子推的故事中,介子推通过渡河时对咎犯邀功和重耳沉璧盟誓行为的异议、论功行赏时不言禄和对“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的批评、归隐前后作“龙蛇之歌”等方式,对君王进行了多次、多侧面的劝谏。
另一方面,介子推故事凸显了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君臣之道,体现了双向度的忠君价值取向。介子推对晋国臣子忠君的不同观念进行了扬弃,他抛弃了荀息的“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的迂腐和非理性,也没有采取里克静以待变、唯利是从的骑墙态度,而是继承发扬了丕郑“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国语·晋语一》)道义原则下的臣子忠德。他对晋文公复国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带来的“上下相蒙”的政治乱象表示出极大的鄙夷,并选择了用脚投票。如果说,咎犯软逼重耳河中盟誓的行为使介子推对子犯的为人产生反感,并与道不同的同僚进行了切割和疏离的话,那么,面对晋文公滥赏而不及己的忘恩背义③所发出的“上下相蒙,难与处”的喟叹,则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晋文公。当晋文公忘却了自己割股食君的奉献、忽视了自己的功劳和存在,介子推认为维系君臣之间“食禄尽忠”责任义务的契约关系就到了应该终止的时候。在介子推看来,所谓“君子之道”表现为“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则不敢当其后。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继而在与母亲对话中,介子推反复表达了“出怨言,不食其禄”“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的观点,并以“至死不复见”晋文公的态度,表现出君臣道乖、归禄辞君的主体自我选择精神。介子推的这一行为不仅表达了对春秋时期日益恶劣政治生态的一种反抗,而且继承发扬了“从义不阿”的理性忠君精神,并将其发展成责任与义务相统一的双向度忠君精神,为后世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向度忠君的道德规范提供了实践经验。
(五)介子推母亲与子偕隐赋予传统女德以理性色彩
汉代刘向非常重视女德,并将一些先秦、汉代的女性事迹编辑入《列女传》。随着儒家伦理的熏染,“三从四德”逐渐成为传统女德的主基调。在春秋时期,“三从四德”还没有成为女德的规范。但这一时期也不乏有独立思考的智慧女性,介子推母亲的言行就闪烁着智慧和理性的光芒,“表现出了不同于常人的见识,成为千古美谈”[7]。
在介子推面对人生选择、由名利世禄转向听从自己内心信念的关键时刻,其母亲通过“盍亦求之,以死谁怼”“亦使知之若何”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来一步步显明、衬托、坚定介子推之志,并最终以“能如是乎?与女偕隐”表明了支持儿子人生选择的态度,展现出一个具有广阔视野、宏大格局的智慧理性的母亲形象,丰富和提升了中国古代女性的思想境界。
五、介子推之忠在晋国忠德变迁史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传统政治伦理中,君臣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君明臣忠”。惟其如此,才能做到国泰民安,霸业有成。在春秋时期,晋国之所以能长期垄断霸主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君明臣忠”。在春秋时期短短的200多年间,晋国涌现出晋献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悼公等有为君主,贡献出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出现过晋悼公复霸的良好局面。像晋灵公这样的昏君(关于晋灵公是否昏庸,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是赵盾专权导致晋灵公与赵盾之间矛盾,引发弑君惨剧)在晋国史上并不多见。而臣子中则涌现出栾共子、赵衰、狐偃、狐毛、先轸、魏绛、赵盾、士匄、叔向等一大批忠臣楷模,形成忠臣云集的局面。有研究者注意到地域上的忠德盛衰与霸业成败的关系④。在灿若繁星的晋国忠臣群体中,介子推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在晋国忠德变迁史中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和作用。
(一)介子推对晋国早期忠德传统的扬弃
在周代的诸侯国中,晋国始封于西周初年,周成王“桐叶封弟”的戏言成为晋国受封的始因。从《左传》《国语》的记载看,晋国的忠德传统亦可追溯到春秋初年。在曲沃坐大、武公伐翼时,栾氏家族就上演了父子各为其主、有死无贰的一幕。到了晋献公时期,忠德更是成为晋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道德,并表现出各种样态:有太子申生的愚忠、荀息的忠贞、士蒍的忠谋等。对晋国的忠德传统,介子推采取的是批判继承的态度。具体而言,介子推继承了栾氏父子各为其主的“委质为臣、忠贞不贰”的精神,在公子重耳出奔时,矢志不渝地追随左右,绝不背叛。他还继承了士蒍的忠谋、忠谏传统,希望用自己的不言禄和隐居行为匡正晋国臣子争功贪赏的风气。对于荀息的忠贞守信,介子推是活学活用的。他敬仰荀息的“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的忠贞观念和“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左传·僖公九年》)的忠信精神,坚持“且出怨言,不食其食”的个人操守,执意逃禄隐居。对于申生的愚忠精神,介子推也是有所扬弃的。一方面,他感佩太子申生受屈不辩的隐忍,也不主动言禄;另一方面,他通过创作“龙蛇之歌”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平。对于申生的愚忠,介子推进行了有选择地践行。一方面,介子推没有像申生那样认同“违命不孝,弃事不忠,虽知其寒,恶不可取。子其死之”(《左传·闵公二年》)的迂腐观念,而是勇敢地逃禄隐居,既没有选择不弃事的仕宦之忠,也没有一死了之,做愚忠的殉道士。另一方面,他虽然做不到申生那样的“仁不怨君”,但却能秉承其“勇不逃死”(《国语·晋语二》)的精神。事实上,介子推虽不乏怨望之言,但当被困绵上之山时,仍坚定地选择了“勇不逃死”,用宁死不出彰显了对个人价值选择的坚守。介子推与同时代的忠臣狐氏父子、赵衰、先轸等不同,表现出一种超越狭隘君臣之忠的更高层次的忠德精神。
(二)介子推对其身后晋国忠德精神的影响
介子推的忠德精神对同时代人和其身后的晋国政治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臾骈所谓“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左传·文公六年》)的“忠之道”,就与介子推之忠有着精神上的呼应。介子推追随重耳多年,但没有邀宠争功,而是选择功成身退。介子推口出怨言后不食君禄,是一种政治智慧的表现。更可贵的是,介子推不仅没有以私害公,而且还表现出割股食君的忠而忘私的奉献精神。介子推逃禄隐居以及借龙蛇之歌表达独立理性之忠,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晋国的忠德传统,而且也为晋国忠德精神注入了理性成分。这种包含理性智慧的忠德,为后世晋国臣子所继承和发扬。如面对晋侯提出的“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的问题,师旷没有逢迎晋侯的观点,他指出:“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左传·襄公十四年》)无独有偶,对于赵简子关于“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的问题,史墨则主张:“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师旷和史墨作为晋国大夫,面对君主和权臣能够直抒己见、理性分析,甚至大胆批评当权者的不仁民爱物和以名器假人,参之以介子推直言忠谏、大胆批评晋文公滥赏和晋国臣子贪功的言行,师旷和史墨的言论与介子推之间是具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和承继关系的。
(三)介子推忠德精神在晋国忠德变迁史中的作用
介子推的忠德对晋国忠德变迁具有重要的承接、助推、校正、发展等综合作用。一是承上启下的作用。介子推是春秋早中期的晋国大夫,其批判继承、发扬丰富了晋国早期的忠德传统。同时,也对同时代以及其后的晋国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某种程度上范型、陶铸了晋国中后期的忠德精神。当然,随着诸侯争霸的加剧,越到春秋后期,狭隘的忠君观念越是得以强化,也就越是背离了介子推那种超越狭隘忠君的理性忠德道路。二是纠偏校正的作用。介子推的忠德主要是一种理性精神,无论其忠君不贰、割股食君的规范伦理,还是功成身退、隐居不仕的美德伦理,它更多地是对个人信念的坚守和道德操守的坚持。他的忠德精神体现的是人的独立性、自主性,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是对太子申生、羊舌大夫、杜原款等愚忠偏狭的纠正。三是丰富完善的作用。介子推的忠德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忠德精神。中国传统忠德的主流是忠孝、忠信、忠贞等精神。介子推的忠德中不乏这些精神,其与母偕隐将忠于个人理想与孝养母亲结合起来;其誓死追随重耳流亡是一种忠信的体现;割股食君的奉献则表现出忠贞的精神。更为可贵的是,在主流忠德精神之外,介子推的忠德还丰富发展了忠清、忠廉、忠义、忠隐等精神,其“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将忠与清廉结合在一起,“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则彰显了忠义精神。与伯夷、叔齐饿死首阳而不食周粟的忠于故国那种忠隐不同,介子推的忠隐还增加了对个人理想信念坚守的内涵,是一种“离俗”、远俗的忠隐。
总而言之,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国践行忠德的杰出代表。他追随公子重耳流亡,体现了委质策名的忠之精神。重耳复国后,介子推不肯贪天之功,选择功成身退,隐居不仕,即便是大火烧山也不出山,把对国君个人的效忠上升到对个人志向的坚守。介子推的故事不仅彰显了臣子忠君的君臣伦理,而且因其“关系到士阶层的道德操守和群体利益”,而凸显了“士人作为独立群体的自尊和气节”[8]。虽然在介子推故事的流传过程中,被不断加入了更多的情节,使得介子推不仅是忠臣孝子的代表,而且还是辞禄远俗的节士、功成身退的隐者和忧国忧民的爱国者,更是一个忠而被弃、不得寿终正寝的悲剧人物[9],一身肩负了多种文化象征元素,但忠无疑是介子推人格精神的底色,而介子推的忠又超越了忠君顺上的简单机械和片面的单向度,为春秋时期忠德的养成和中国传统忠德的发展变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客观地讲,介子推对晋国忠德传统的型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忠德在晋国忠德传统、乃至整个春秋时期甚或先秦时期都是一个特例。从理论元点和现实基础上看,介子推的忠德是建立在当时那种“委质策名”“食禄卫主”的君臣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基础上的。但介子推既不同于栾共子、荀息那种“委质策名,有死无贰”之忠,也不同于先轸因无礼于小君而免胄战死于阵的自我惩罚式的武夫之忠,更不同于赵盾朝夕恪勤的孜孜忠勤,而是体现一种尽职尽责的规范伦理,并在责任尽到后选择功成身退的美德伦理,高扬了遵从自己内心贞悫的信念伦理大纛。难能可贵的是,介子推还坚持“口出怨言,不食其食”的操守,在忠君责任尽到后与君主在食禄方面进行了彻底切割,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更要特别指出的是,介子推的忠德理性精神一反太子申生的愚忠,对传统忠君道德滑向愚忠的趋势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滞和延缓作用。
注 释:
①参见杨皑《对诸古书所载介子推事迹的一点思考和分析》(载《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1年第1期)的相关论述。
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鉏麑死前这段话,人们早就提出质疑,认为其既已自杀,其死前的心理活动,后人何以得知。钱锺书就曾指出,鉏麑自杀前的慨叹,生无傍证,死无对证。钱氏引述古人的观点,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一曰:‘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与。’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鉏麑论》曰:‘又谁闻而谁述之耶?’”(见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第164—16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钱锺书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春秋时期忠德观的解读。即便鉏麑死前的心理活动是史家的理解,这也一定程度代表了春秋时期的一种看法和观念。
③关于晋文公封赏介子推的问题,研究者是有分歧的。有的认为晋文公不是不打算封赏介子推,而是因为归国后日理万机,且中间出现了周王室内乱、晋文公忙于勤王靖难而延误封赏的情况。后来晋文公下令追封补赏介子推,只是介子推因个人性格因素逃禄隐居而未果(上述观点参见张丹、蒋波:《介子推封赏问题新论》,载《晋中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有关介子推封赏的具体事实已经湮没在浩渺的历史尘埃之中,但从介子推表达出的怨望之气看,晋文公无疑是轻忽了介子推的。即便介子推没有那么小气,晋文公也足称贤君,但君臣之间的隔阂和龃龉并非完全无征。
④在王子今的《“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王成的《中国古代忠文化研究》(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中,都对春秋时期地域与忠的关系有所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