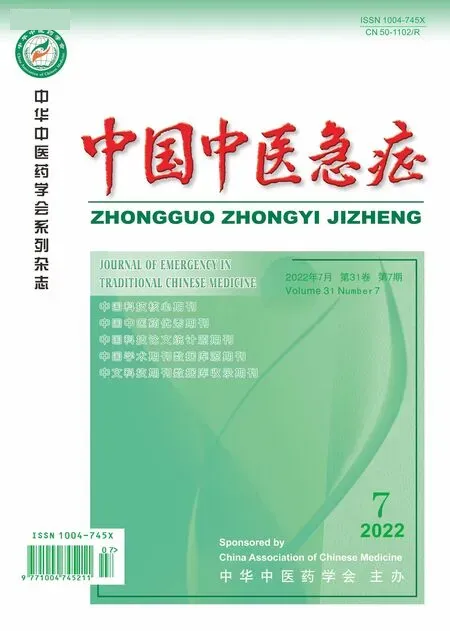运用截断扭转思维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体会
2022-12-27刘亚峰陈超武李晓良
刘亚峰 陈超武 李晓良 马 洁
(1.广东省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广东 深圳 518100;2.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福山社区健康卫生服务中心,广东 深圳 518000)
2020年2月11 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3月11日,世卫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该病以发热、干咳、乏力等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腹泻等上呼吸道和消化道症状。重症病例多在1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等。我国采取的中西医结合的救治模式,其疗效值得肯定。笔者所在医院为深圳市定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医院,在临床救治中,运用截断扭转的思维指导中医临床,疗效较满意。今结合具体案例分析阐述这一思维模式的临床指导意义和判断关键点。
1 病案举例
1.1 病案1 患某,男性,42岁。2021年12月16日20:24入院。主因“咽痛干咳1 d,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1 d”入院。患者于12月16日起无明显诱因出现咽痛,并偶有干咳,无鼻塞流涕,无发热,无头痛肌肉酸痛,无腹痛腹泻,无嗅觉味觉障碍等不适。12月16日13∶00东莞市疾控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CT值,ORF:18,N:14)。患者无吸烟饮酒史,入院前1周于麻将馆打麻将,其牌友均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并多次随行就餐。患者入院后病毒测序分型为Delta分支毒株。患者入院后16日肺部CT示少许磨玻璃影,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普通型。12月19日胸部CT:新见双肺感染。12月22日胸部CT:病灶较前多发。入院后西医予以维生素C+连花清瘟+阿比多尔+左氧氟沙星+化痰+俯卧位通气+机械排痰。12月22日患者氧合指数下降,换用高流量湿化治疗仪。患者病情进展迅速,有转重症倾向。22日中医四诊:患者无发热,无明显咽痛,咳嗽有痰,痰液黄白夹杂。气紧,乏力,汗出频繁,大便不成形,日2~3次,舌色淡白,舌边齿印,苔白质地润,脉沉缓弱,重按着骨始得。腹软,扪之不热,跗阳脉弱。中医诊断:湿毒疫普通型(元气不足,肺气郁闭,浊邪阻肺)。患者邪实与正虚并见,有转重症倾向。遣方用药以温元气,开郁闭,化痰浊为法,归一饮、苇茎汤化裁:淡附片10 g,青蒿10 g,薏苡仁30 g,桃仁10 g,芦根30 g,西洋参10 g,薤白10 g,桔梗10 g,枳壳15 g,五味子10 g,细辛5 g,炙甘草20 g,干姜15 g(免煎颗粒)。冲服,三餐后40 min温服。服上方2剂后,患者汗出止,气紧减轻,喘促渐平,呼吸较前顺畅,痰液较前容易咯出,仍乏力,大便不成形。26日复查CT:双肺多发感染(磨玻璃灶),对比前片(2021年12月22日),较前轻度吸收减轻。27日复诊,患者咳嗽咯痰减轻,痰液减少,汗出减少,乏力胸闷缓解,大便仍不成形,舌色淡白,舌边齿印,苔薄质地润,舌体裂纹,脉较前有力。上方有效,续方再进,仍以温元气,开郁闭,化痰浊为法,加升麻、葛根升阳止泻。28日复查CT示:双肺感染复查,对比2021年12月26日CT双肺病灶吸收减少及密度变淡。2022年1月4日患者连续两次新冠核酸阴性,评估符合出院标准后出院。
1.2 病案2 患某,男性,32岁,于2021年12月16日00∶37入院。主因“咳嗽咯痰1 d,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1 d”入院。患者12月15日东莞市CDC复核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无吸烟饮酒史,为东莞本土患者密接排查时发现。入院时患者无发热,无流涕,无头痛肌肉疼痛,无咽痛,无嗅觉味觉障碍,咳嗽少量白痰,饮食正常,无腹痛腹泻。17日患者出现咳嗽、咳白痰量多,大便次数增多,每日解2~3次稀便。查胸部CT示双肺磨玻璃影,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普通型。19日患者出现乏力。入院后西医对症予以阿比多尔抗病毒,维生素C抗氧化,氨溴索60 mg每日2次静滴,联合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0.3 g,每日2次雾化吸入化痰,低流量吸氧,机械排痰,俯卧位通气同时配合呼吸操。12月21日胸部CT:双肺病灶,较前增多。患者出现乏力胸闷气短憋气,氧合指数下降,转用高流量湿化治疗仪。患者病情进展迅速,有重症化倾向。21日中医四诊:患者咳嗽明显,白色黏痰,胸闷,憋气,后背疼痛,乏力,气短,汗出频繁,食欲差,无发热,无味觉、嗅觉减退,大便不成形,日2~3次,舌色淡红,舌边齿印,苔腻略黄,脉沉弱,肤冷。腹软,扪之不热,跗阳脉弱。患者邪实正虚均见,考虑中医诊断湿毒疫(元气不足,肺气郁闭,浊邪阻肺)。治以温提元气,宣肺开闭,化痰泄浊,以归一饮、葛根汤、苇茎汤化裁:炙甘草20 g,葛根30 g,淡附片10 g,蜜麻黄10 g,干姜15 g,枳壳15 g,桔梗10 g,薤白10 g,细辛5 g,五味子10 g,西洋参 10 g,青蒿15 g,芦根30 g,桃仁10 g,薏苡仁30 g,地龙10 g,桑白皮15 g(免煎颗粒)。冲服,三餐后40 min温服。3剂后,患者汗出已收,后背疼痛缓解。胸闷憋气好转,乏力感减轻,饮食增进,大便较前成形。仍咳嗽,白痰量多。26日复查胸部CT示较2021年12月24日双肺病灶较前吸收,范围缩小。患者服前方症状减轻,肺部CT好转,前方续进,仍以温元气,散湿毒为法。12月28日复查胸部CT,双肺病灶进一步吸收,面积缩小,咳嗽咯痰已平。12月29日患者先后两次新冠核酸检测阴性,评估符合出院标准后办理出院。
2 分析
2.1“截断扭转”理论内涵 “截断扭转”这一理论,归属于“治未病”的大范畴。中医学理论源远流长,自《黄帝内经》始,就提出了“治未病”的概念,后人根据《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提炼出了“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这一思想。“即病防变”,可谓截断扭转理论的指导思想。东汉大家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体系中,“阳明三急下”“少阴急当救里”就充分体现了这种领先一步的先期治疗主动权思想。到了明清时期,瘟疫理论、温病学说逐渐成形,其中所蕴含的“截断扭转”的思想,也为当时医家所重视。如吴又可在《温疫论》中强调“客邪贵乎早逐”,应“疏利膜原,扭转病位”,以“逐邪为第一要义”为核心[1]。温病大家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指出“先安未受邪之地”[2],杨栗山在《伤寒温病条辨》中提出“治法急以逐秽为第一义”,刘松峰《松峰说疫》中说“真知其邪在某处,单刀直入”,均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出了“先证而治”“除邪务早”的理念。
近代名家赵锡武先生,在1962年提出,针对肺炎的治疗,应突破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的窠臼,当采用直捣巢穴的治疗手段[3]。在上述理论思想基础上,上海名医姜春华教授明确提出了“截断扭转”这一概念,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含义:1)“截断”是指采取果断治疗措施和具有特殊功效的方剂,直捣病所,迅速祛除病原,杜绝疾病发展迁延;如不能快速祛除疾病诱因,也要果断救危截变,拦截邪气向内深入,尽可能阻止疾病恶化的趋势;必要时可以先证而治,迎头痛击病邪,掌握主动使疾病早期痊愈。2)“扭转”指扭转疾病发展趋势,使疾病的发展向上向外,向好向轻的方向发展。当疾病深入到一定程度,正气已衰,邪气未减,通过调整正邪交争态势,扭转病势,由危转安,由逆转顺,正盛邪却,步入坦途。
2.2 截断扭转法应用关键,在于早期判断伤津或耗气的状态 在正邪交争最剧之时,气机阻碍最为严重,同时正气消耗也最为剧烈。在此时,由正气决定疾病的走向和转归。这一阶段,是决定病情恶化或向愈的最关键期,也是采用截断扭转法最宜之时。而因患者体质的不同,正气抗邪能力的不同,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是从阳化热,合于阳明而阳气内闭,津液欲涸。此时邪热最炽,气机内闭最甚,以伤津剧烈为最典型特征,当迎而击之,姜老之“截断“一法,为此而设。《伤寒论》[4]中有阳明三急下,少阴三急下,条文有云“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便难,身微热者,此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清,心下必痛,口干燥者,可下之,宜大承气汤”“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吴又可《温疫论》指出“温病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但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予达原饮加大黄下之”。并告诫“大凡客邪贵乎早逐”,勿拘于“下不厌早”之说,并阐释说“应下之证,见下无结粪以为下之早,或以为不应下之证,误投下药,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非为结粪设也”,从先贤论述来看,只要出现明显津液耗伤倾向,气机内闭明显,就当荡邪逐寇,急下存阴,予陷胸、承气汤急投,而不应拘泥于见燥粪方用。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提出不必拘于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破除“温病三禁”,提出“通下岂止夺实,更重在存阴保津,既能泄无形之邪热,又能除有形之秽滞”的起病初期即当表里双解的学术思想[5],正是深谙其中三味。二是从阴化寒,直趋三阴而阳气外脱。此时以阳气剧烈损耗为典型特征,正气虚损进行性加重,已达到量变引起质变的变化,急当救逆、扶正、固本,姜老之“扭转“一法,为此而投。针对新冠肺炎,前期有临床报告指出,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病情更易加重、甚至致死[6],充分说明了“耗气外脱”是新冠肺炎趋向重症乃至死亡的重要病机。在出现三阴证倾向时,急当固护阳气,固本救逆,逆转病势向重症转化。
2.3 早期判断,重在四诊合参,观其脉证,知犯何逆,尤需重视独处藏奸 截断扭转一法正确的运用,要点在于如何早期判断。先贤张仲景有示,《伤寒论》第16条“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此条高度概括了基本的方法和步骤。1)脉。若内闭,则脉象多洪,大,或沉滑实,或细数;若外脱,则脉象多沉,弱,虚,重按着骨始得。2)证。若倾向于内闭,多现身体灼热,汗出黏腻,连绵,口咽干燥,胸腹满闷,大便不通等症。若倾向于外脱,则多乏力气短神疲,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四肢厥冷等候。3)舌。叶天士《温热论》[2]有着详尽的总结“前云舌黄或浊,当用陷胸、泻心,须要有地之黄,若光滑者,乃无形湿热,已有中虚之象,大忌前法。其脐以上为大腹,或满或胀或痛,此必邪已入里,表证必无,或存十之一二。亦须验之于舌:或黄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黄色;或老黄色;或中有断纹。皆当下之,如小承气汤,用槟榔、青皮、枳实、芒硝粉、生首乌等皆可。若未现此等舌,不宜用此等药。恐其中有湿聚太阴为满;或寒湿错杂为痛;或气壅为胀,又当以别法治之矣”。其舌若现黄燥或如沉香色、灰黄色、老黄色、中有断纹,有津液损伤之像,则为内闭,当急下存阴为法;若舌津液尚存,舌色淡白胖大而现正气虚损之像,当以固本救逆为法。
若证候错综复杂,则尤需注重独处藏奸之处。可佐以腹诊、跗阳脉诊共参。若腹部按之软,扪之肌肤不热,压之无满痛,跗阳脉沉弱,则多为正气虚馁,易倾向于外脱;若腹部膨隆,按之坚,扪之肌肤烙手,满痛明显,跗阳脉大、浮、涩,则阳气充足,正邪交争较剧,易于内闭。
3 讨论
结合所举两例病案来看,其中运用的正是“截断扭转”理论的扭转法。患者虽表现为肺系疾病之表现,然已现外脱早期之候,症现乏力,气短,自汗频,为元气不足之兆;其舌色淡,或淡红,质地尚润,津液尚存,其非内闭可知。第2例患者虽舌苔泛黄,然舌苔不干,无咽干口燥,无腹满痛,无便秘结,内闭证据不足。两例患者脉象均现沉弱之虚象,且腹部软,扪之不热,跗阳脉弱,综合分析,其病机均为元气不足,肺气郁闭,浊邪阻肺。治当温元固脱佐以祛邪,方选归一饮、苇茎汤为主方。
归一饮为广安门医院张东教授总结之方[7],脱胎于四逆汤。制附片在方中的比例最小,取少火生气之意。炙甘草用量最大,张东教授认为炙甘草最接近元气之性,所以炙甘草是引诸药归引脾胃中枢之药,其剂量也最大。干姜连接制附子和甘草,是为佐使。用小剂量制附子少火生气不是只为了温补肾阳,而是为了修复元气。同时加入参、五味子加强元气的修复。在治病的同时,先修复元气,调动元气来治病,也体现了《道德经》元气无为的思想。枳壳、桔梗、薤白、细辛、苇茎汤等品,则佐助元气荡涤肺脏之邪。基于截断扭转理论的组方原则,料敌机先,方可扭转病势,使病患不至向重症转化,出现外脱之凶险证候。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和发病机制极其复杂,当前仍在研究与探索当中。临床实践表明,在早中期运用截断扭转理论遣方用药,料敌机先,可有效达到“即病防传”的目的,在扭转病势,防止重症转化的治疗中,疗效确切,值得进一步挖掘总结,为后期的疫情防控治疗,提供经验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