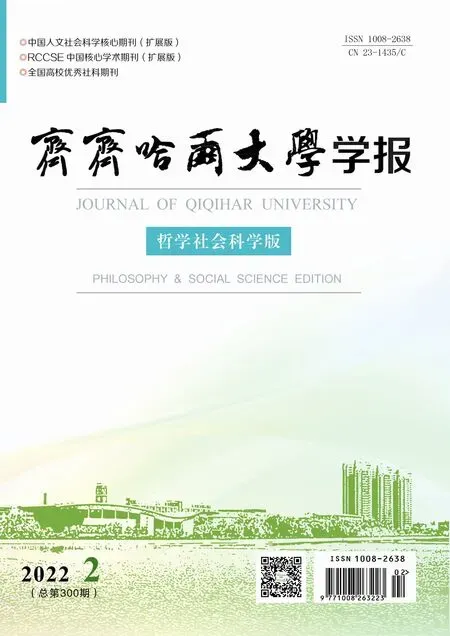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思想及现实关照评析
2022-12-26张传恩
张传恩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思政教研部,安徽 芜湖 241002;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儒家思想以其积极的“入世精神”强调以礼化人,培育统治阶级的理想人格,以实现去乱为治、天下太平之目的。荀子作为战国后期集大成式的思想家,其思想固然庞杂,内容涉及自然、社会、哲学、政治、军事、文学等诸多领域,但观其要旨亦在于此。司马迁说:“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1]456在荀子看来,“禹”是道德楷模(圣人)的人格符号,“涂之人”(普通人)经过内修外砾可以达到禹的境界,即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这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有其内在逻辑。
一、人性质朴,辨义善群:“涂之人可以为禹”之前提
荀子主张“人性恶”似无争议。梁启超认为“荀子之最大特色,在其性恶论”,[2]89甚至将“人性恶”作为荀子哲学的出发点,且作为典型的价值判断而存在。但通观《荀子》全文语境,荀子所说的“人性”既有事实判断也有价值判断,甚至更倾向于“人性质朴”的事实判断,而这正是“涂之人可以为禹”的重要前提。
(一))人性质朴,璞玉待琢
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3]392性是人的本始“材质”,与生俱来。他还对“性”“伪”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即“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3]476荀子这里的“性”是专指人生而具备的自然属性,即“不可学”部分,如“目之明”、“耳之聪”,不仅无待于学,而且即使学也无济于事,凡是后天人为通过学习形成的品行,都是人为的,也就是荀子称之为“伪”,这显然是不具备道德倾向的“事实判断”。但荀子又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3]474荀子所指的“恶”,是人的行为偏邪阴险、悖理混乱之意,即“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3]480结合荀子对“恶”的内涵界定可以看出,从表面上看对人性是否定性价值判断(即“恶”),但实际上他否定的只是人发展的可能性结果,因为荀子在论证人“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等等所谓的“恶”的现象时,其后总有“顺是”二字相随,因此,荀子只是将“顺是”的结果列为“恶”而非“人性”本身,同时,这也蕴含其另一观点,即人性“可导”,与其“天人之分”、“性伪之分”等观点相互呼应,从而在人性“可导”的基础上认证了“化性起伪”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涂之人可以为禹”结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辨义善群,人畜两分
先秦思想家认为,世间万物皆为天地所生,唯人是万物之灵。《尚书》有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4]287荀子也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3]392且深入分析了人与其它万物相比更高级的原因,是人所独有的“辨义”之“性”,即人有辨别是非、辨明事理的能力,即“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3]70当然,这里的“辨”主要是指辨别人与人之间长幼尊卑的等级区分,这也与儒家所坚持伦理道德原则相符合。荀子进一步论证,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156《中庸》原文中将“义”解释为“义者宜也”,[5]32朱熹进一步将“宜”解释为“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5]33《说文解字》将“宜”解释为“宜,所安也”,[6]340即适宜之意,因此可以推断荀子所表达的意思是,人与其它万物相比不仅有生命、有知觉,而且还能各安居其所不僭越。
此外,荀子还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唤醒人对自己“之所以为人”的自我认知。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3]156人之所以能驾驭牛马等其它动物,是因为人是按照一定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群体,即“善群”。当然,荀子这里所说的“群”是建立在礼义之分基础之上的,即“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3]156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人只能通过群体协作才能更好地生存生活,即“故人生不能无群”。[3]156因此处于社会群体之中的人,必须在一定伦理道德基础上每个人各司其职,社会秩序便会井然有序,才能实现其“人定胜天”的宏伟蓝图。
至此,荀子深入探讨“人是什么”的问题,为其“涂之人可以为禹”观点奠定了基础,即为进一步探讨“化性起伪”、“以礼化人”提供了可能。
二、化性起伪,积渐致理:“涂之人可以为禹”之路径
荀子认为“涂之人”成为“禹”的关键是个人主动作为,博学修德,去陋至僩,积善为德并身体力行,尊崇礼制、隆礼近师以渐染成人。,即从现实的人出发,基于“日用人伦”以增进道德的社会认同,将道德主体的责任自觉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发挥礼制礼义的教化作用,以最终实现“涂之人”成为“禹”的人格塑造价值目标。
(一)去陋至僩,思虑辨择
既然就自然本性而言人人同一,但为何有人成为禹那样的圣人,有人则会成为桀那样暴君?荀子认为是因为“陋”,荀子说:“凡人有所一同……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何也?曰:陋也。”[3]55-56荀子将“陋”解释为少见,即“少见为陋”,[3]22即人对先哲的大道无知(少智),其结果是对个人、对国家都必将是为祸至深,因此荀子说:“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3]56因此人要修德至理,首先就要获取知识,去“陋”而至“僩”(博大之意),以变愚为智。荀子认为影响人获取知识有两个心理条件,一是依据其对于“人性”的分析,人有“喜己非异”感情偏私本性,偏信固有知识而不愿听到不同的意见学说,即“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3]418这种个人主观感情的偏私,使人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往往容易误入歧途。二是因为“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3]419万物外在表现多面,且皆有两端,很容易使人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偏执于一端而以偏概全,不能理解事物的真谛,即所谓“蔽一曲,而闇于大理”[3]418,其结果就致使大谬绝伦。荀子在《解蔽》中,列举了夏桀、殷纣、唐鞅、奚齐等人因“蔽”至祸;文王、鲍叔、召公等人因“不蔽”而得福的事实,因此荀子认为此祸不除,则真知不可得。
孔子认为心是思维的统帅,荀子也提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3]429因此要实现“去陋至僩”就需要积极主动去“正心”,即注重理性思考,经由“思虑辨择”以认识大道。荀子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3]426所谓“虚”是不为成见所左右;所谓“壹”,除了指“专一”之外,还有综合事物两面为一之意;所谓“静”则是指保持自身灵明善察的状况,即“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3]432因此在荀子看来,学习新知、认识事物,必须先扫除情感、摒绝一切主观偏向,且以理导心、以清养心,以理性辨别而“去伪存真”,方可达到“知道明理”之境界。
(二)积微力行,化性质移
荀子认为,性虽然成于自然而非人力之所为,但是“可导”、“可化”。荀子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3]134这里的“积”是后天教育学习、积善成德之意。关于“化性”之法,荀子认为涂之人只要能潜心学习贤圣之理、认真参悟,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就能达到禹(贤圣)的境界。荀子说:“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於神明,参於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3]484荀子在《劝学篇》中用“骐骥”、“驽马”、“螾”、“蟹”等物来类比论证“积微”的重要性,只要锲而不舍、自强不息,就可达到理想之境界,即“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3]7
荀子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3]486就是从理论上说,普通人都可以成为禹那样的贤者,但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能成为贤者,其原因在于涂之人往往止步于学习,将所学之理存储在脑子里,最多停留在口头上;而君子一方面是通过学习明白道理,更重要的是以所学之理指导行动、矫正行为,最终化性为善,正如荀子所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3]11荀子同时认为,身体力行不能眼高手低,也要坚持积小善为大德,最终达到至善的境界,所谓“蹞步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3]26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三)隆礼近师,渐染成人
荀子以射干之茎、兰槐之根的成长为例,说明人性转化需要外部环境的渐渍、浸染。荀子说:“射干,茎长四寸……木茎非能长也,所以立然也。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3]5在荀子看来,涂之人如一味“顺是”其“性”,缺少外力引导、感染,则会“恶习”漫延,最终产生恶端。因此荀子主张隆礼以治之,即以礼制为外力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以防因过分追求物欲而导致社会纷争,“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求”。[3]375荀子在《富国》中,对“礼”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界定:“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所称也。”[3]173可以看出,荀子的“礼”是对西周前后社会的典章、制度、规矩和礼节的延续,是“对儒家忠、义、孝、悌等礼义规范的细致描述”,[7]25也就是在承认、维护社会尊卑差别前提下,主张以礼制、礼义来规范社会行为,以使社会各成员各得到所宜,以实现社会之良治。当然,除隆礼之外,荀子还主张辅之以刑法,以赏待贤、以刑制恶,即“以善至者待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以刑”,[3]142但从总体性分析看,荀子主张以政教(礼)为主“本政教”,因此隆礼仍是主流,这与儒家哲学相一致。
荀子认为,因受人的本性使然,人易受外部环境(人和事)的影响,正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3]5因此人应该“居必择乡,游必就士”,[3]5善于假借外力而“近师”,在良师益友的教化(影响)下远离邪恶、坚守正义。荀子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3]475荀子甚至认为“近师”比“隆礼”更为重要:“学之经莫速于好其人,隆礼次之。”[3]13当然,荀子这里的“师”一方面是指普通意义上的师长,即“师者,所以正礼也……夫师以身正仪”,[3]28同时还泛指所有品行高尚、能帮助自己之人,“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3]19
“涂之人”能转化为“禹”的首要条件是个人主动“为之”,即荀子所说的“夫师以身正仪,而贵自安者也”,[3]28其次是外部环境的“使为之”,内外因共同作用最终才可能实现“涂之人可以为禹”的预期结果。
三、正心修身,明德向善:“涂之人可以为禹”之现实关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8]173荀子的思想始终关注道德建设,其“涂之人可以为禹”的价值指向便是引导人提升道德修养以塑造社会“理想人格”。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其内容及其建设途径和方式具有历史沿承性,因此批判继承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观点,对我国当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然有启示价值。
(一)关注引导道德的社会认同
作为社会规范,道德属于“他律”的范畴,影响道德发挥社会治理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道德的社会认同程度,即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在对某一道德有了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再从自身的感情或信仰层面对这一道德体系及其要求产生由衷的敬仰服膺的态度,并使这种态度升华为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9]61
荀子从分析人性出发,认为人之所为人是因为人能够辨别人之间的长幼尊卑(即“辨”),论证了提升道德修养的必要;认为人“生而同质”,论证了提升道德修养的可能;基于隆礼从师、积善成德,论证了提升道德修养的路径。以“人畜相别(辨)—材质同一(朴)—隆礼化性(学)—积善成德(积)—内圣外王(禹)”逻辑,表明通向圣人的道路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并非遥不可及,即“涂之人”积习成德、隆礼崇法,便可提升道德修养而最终可成为“禹”。因此,荀子从基本的人伦关系出发阐述其“涂之人可以为禹”的道德主张,并在“人伦日用”的视角中赋予其向人的亲近性。荀子还认为,道德实践并非动辄惊天动地,努力从身边小事实践也是“涂之人”转化为“禹”的有效途径,正所谓“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3]26这种近人具体的道德建设路径,使得道德原则更易于得到广泛社会认同,从而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支撑。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道德原则必然通过一系列的道德目标来体现,比如不同的职业有其具体的职业道德目标,处于社会不同角色的人,其预设道德目标也不同,这就要求在设定具体的道德目标时,应充分考虑现实社会的人伦关系,关切个体存在,关注其现实操作性,使公民道德修养犹如涟漪,由近及远,以形成道德社会情感认同。
(二)发挥礼制礼义的教化作用
荀子认为,人应该按照礼制规范行为,否则必然会伤害自身,正如荀子在《大略》中所说的“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3]544《孝经》将“礼”解释为敬重之意,即“礼者敬而已矣”。[10]2698“敬”是“礼”的内容,因此必然(也必须)通过恰当的形式来体现,所以荀子非常重视礼的外在形式(即礼制、仪式等),《礼制》《大略》等篇章中,荀子详细规定了“生”、“死”、“祭”、“行”、“师”等等日常礼义,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些礼制仪式始终与国家政治藕联,其蕴含的引导和约束功能,也有助于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正如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评论古代中国时说:“中国人的无休止的各种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中梳理克制和正直的品行,使民风既庄重又文雅。”[11]217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礼制仪式随着历史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从未退场。因此,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等场域中,应该发挥其育人功能,以塑造时代新人。实践表明,党和政府开展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纪念日的纪念仪式,能激发国民的国家认同情感,起到了重要的育人效果。在当前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也应该充分发挥民间传统礼制仪式(主要体现为传统民俗)的独特作用。“民俗则是文化塑造人格的重要方面,人类的每一个生命……的每一个历程,都可感觉到特有民俗文化的关照和影响,成为一种民俗文化锤炼下的具有特定民族魂的人。”[12]6当然,这需要批判继承,本文不赘述。
(三)强调道德主体的责任自觉
荀子在其对人性分析的基础上主张“涂之人可以为禹”,但同时也提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圣人君子,即“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荀子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个人不愿意积习解蔽、化性起伪,反而“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礼争夺”,[3]483最终成为夏桀那样的人。荀子的思想体系中,他明确关注人的外力(如隆礼尊师,择乡而居)对人“化性起伪”的功能,但他同时认为事物变化总是先由其内因引起,因此“涂之人”为“禹”的起始点和落脚点都在人自身,即内心自觉自为。荀子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3]6荀子以刚柔材质的不同用途、柴堆燃烧、水往低流等比喻来说明,所有的灾祸皆来源于自身,因此“涂之人”成为“禹”的关键就是主动积善成德,这一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当社会上出现一些不良现象时总能听到所谓“人性贪婪”、“人性本恶”的说法,甚至把道德问题直接归结为外部环境,拿荀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来为自己开脱,这既是对荀子思想的歪曲,同时在唯物辩证法上也很难说得通。因此,道德建设关键在于道德主体自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每个人只有坚持道德底线,才能行稳致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总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荀子屡遭儒家“主流”思想家批判,但其思想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始终没有缺席。如果我们撇开阶级立场,将荀子的“涂之人可以为禹”中的“涂之人”置换为每个现实中人,“禹”理解为积极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时代新人,那么这一思想就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彰显其重要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