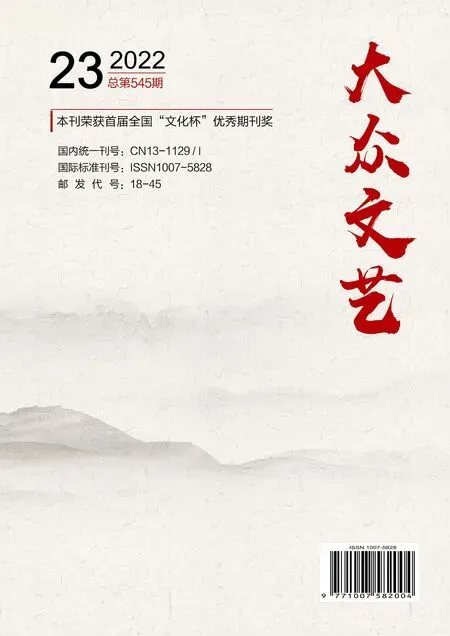中立缓冲区:明代河西走廊边外“弃地”探析
2022-12-25贺凯
贺凯
(青海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西宁青海 810001)
河西走廊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区域,不同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范围都有差异,不同研究视野下的河西走廊范围也会有变动。学界对河西走廊的区域划定众说纷纭,当代的河西走廊位于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乌鞘岭以西、星星峡以东,仅指甘肃敦煌、嘉峪关、金昌、武威、酒泉五个地级市。因为西北地区地缘政治的特殊性,明代河西走廊的范围仅在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乌鞘岭以西、嘉峪关以东,明朝在这一区域设置十卫三所。有明一代,河西走廊的疆域变化不大,仅有肃州以北的疆域有较大的盈缩。洪武时期,明朝河西走廊地区的疆域达到鼎盛,北抵亦集乃(居延海),南至祁连山、东达兰州、西极嘉峪关。但自永乐之后,瓦剌崛起,明朝北方的边防态势转向防守,西北疆土逐渐收缩,[1]34陕西行都司北部的控制范围自亦集乃南移至肃州边墙附近。正嘉年间,明朝两度将哈密内迁之民迁居肃州以北、亦集乃以南的区域。嘉靖年间,杨一清、陈九畴等高级官员将肃州以北、亦集乃以南的这一区域称为“弃地”[2]1442。
明代河西走廊在明朝西北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领域皆涌现了较多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弃地”与明代西北疆域变化密切相关,《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以地图标识了洪武至永乐时期的河西走廊疆域变化,其中包含“弃地”所在地[3]400。闫天灵以明清西北地区的“寄住”政策为切入点,讨论了明代哈密等族群寄住肃州和“弃地”等区域的时间、规模。[4]33-46+148-149但是相关研究并未关注“弃地”的概念、范围、变化。而且,“弃地”与明代西北边疆经略有何联系联系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将围绕明代河西走廊北境边外的“弃地”,讨论“弃地”的概念、范围及在明朝西北经营战略中产生的作用。另,文中的黑河特指今甘肃境内的黑河。
一、“弃地”的概念
“弃地”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河渠书》和《史记•匈奴列传》两个不同的文本,杨长玉认为《史记•河渠书》中的“弃地”对应——荒地,《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弃地”对应——中立缓冲区,因此这一词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杨长玉认为先秦秦汉时期“弃地”与中立缓冲区的基本内涵一致,是指相邻政权之间互不归属的中立地带,这种中立缓冲区一般是相邻政权经约定而建成。[5]10-25
那么,杨一清等明朝大臣提及的“弃地”一词则可以对应两种词义——荒地、中立缓冲区。“弃地”相对应的两种词义截然不同,唯有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辨识明朝大臣提及的“弃地”一词的真实含义。
按《全边略记》记载,嘉靖五年三月,陈九畴、金献民上奏:“议将肃州北境弃地威虏旧址,量与筑室修城,以安插之。”[6]750“弃地”有明确的地理指向,即威虏旧址所在区域。陈九畴、金献民商议将“弃地”——威虏旧址用于安置“哈密二种”。从中透露出两种含义,其一,“威虏旧址”即威虏卫旧址。按《大清一统志》威虏城条言:“在州东北,明初置威虏卫,寻废。”[7]5389又《肃镇华夷志•沿革》提及“永乐三年,裁革威虏卫。”[8]9至此肃州北境的威虏卫不复存在。直到嘉靖年间,威虏旧址才得以重新利用。根据《陕西行都司北部边界变迁略图》[3]400,永乐三年之后,明朝北方疆土内缩,明朝退守肃州,威虏卫附近地区不再是明朝的疆土。其二,明朝将威虏旧址一带用于安置哈密内迁之民,其后甚至为内迁之民“修理城郭,改造屋庐”[9]1804。哈密诸部的经济生活方式农业、游牧兼蓄,这一地区适宜哈密内附者的生活。根据《安插夷属以靖地方疏》言:“羔剌等部落安插肃州威虏、金塔寺一带,向因威虏等城堡残破,各番尽移肃州寄住。”[10]11491据这份上疏推测,直到哈密二种定居之前,威虏旧址一带城堡残破且没有汉人或少数族群定居于此。从杨一清称威虏旧址为“空闲”[9]1799之地,以及明朝安置哈密二种的举动,可知,这片“弃地”横隔河西走廊与蒙古诸部,并非明蒙双方稳定的控制区域,实质是明朝疆域边缘的“空闲”之地。因此,这片“弃地”基本符合中立缓冲区的特征,可以将河西走廊北境的“弃地”视作中立缓冲区。
那么,“弃地”就是永乐三年西北边疆内缩时被放弃的区域,“弃地”隔绝河西走廊和蒙古诸部,明朝和蒙古诸部常常围绕这一区域发生冲突和战争。因此,“弃地”实际上就等同于中立缓冲区,明朝依靠边墙和堡寨抵御蒙古诸部的入侵,维护了河西走廊的边疆安全。
二、“弃地”的范围
河西走廊“北据蒙古,南捍诸番”,[11]3608是明朝抵御蒙古诸部的重要战场。洪武永乐两朝,明蒙双方在此角逐,边疆形势因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不断发生变化。“弃地”就是河西走廊边疆形势变化的产物。划定“弃地”的范围,必须梳理这一区域的历史变迁。
洪武五年冯胜经略西北,《明史》记载了明军的进军路线:“戊寅,冯胜等克甘州、肃州,进克亦集乃路,追元岐王尕儿只班至瓜沙州而还。[11]17”冯胜西征曾一度来到亦集乃①,但是冯胜西征虽然胜利,但是北伐的中路、东路主力接连失利。另为北元残余势力依旧强大,为了防止北元的反扑,冯胜不得不弃退至陕西。明朝第一次短暂的控制了亦集乃附近地区。
洪武十三年和洪武十七年濮英和宋晟的军事行动沉重打击了故元的势力,明军一度攻占“弃地”内的白城、亦集乃等地区。此后,明朝在河西走廊设立卫所,但是仍为在“弃地”设立卫所。自洪武二十九年之后,明朝在肃州卫东北设立威虏卫、白城子千户所和威远千户所②。威虏卫、白城子千户所和威远千户所远离肃州,地处边外,扼守要道,成为抵御蒙古诸部与“西控西域”的前沿。《边政考》记载:肃州卫“北至黑山一百八十里,东北至天仓墩三百二十里”[12]391。居延海连接弱水,水草丰美,附近就是亦集乃城,乃南北要冲之地,地处险要。威远千户所距离亦集乃较近,这表明是明朝设立威远千户所是为了控制亦集乃(居延海)。因此,亦集乃(居延海)应当是洪武晚期明朝河西走廊疆域的最北部[3]398。
建文帝登基后一边削减塞王的实力,一边裁撤部分的卫所,河西的威虏卫、白城子千户所和威远千户所于洪武三十二年(建文元年)被撤。[13]109-117。尚不能断定建文年间,明朝失去河西走廊以北地区的控制,但是明朝极有可能对河西走廊以北地区的控制能力减弱。永乐初,明成祖积极拓边,一改建文时消极的边防政策。明朝恢复被撤卫所,加强西北军备。“(永乐元年)八月庚午,复甘州前后卫、威虏卫、镇夷千户所”[14]506,然而史籍中未见恢复白城子千户所和威远千户所的记载,考虑到永乐时期瓦剌的崛起,北方草原力量的威胁加大迫使东胜卫撤销,以至于宁夏甘肃防线出现漏洞[15]17。洪武之后的历史记载中不见白城子千户所和威远千户所,或许因为明朝北境边防压力的加大和永乐初年的政治因素,明朝在河西走廊疆域的控制范围最北只能达威虏卫一带,白城子千户所和威远千户所不再复设。因此,明朝河西走廊的疆域出现内缩。“(永乐三年)三月甲辰,并威虏卫吏卒于肃州卫”[22]536,自此明朝的势力退出威虏卫一带。《西域考古录》载金塔寺“自肃州东北四十五里”[16]75,地处肃州边外,位于威虏卫境内。“威虏城,明初置威虏卫,寻废”[17]336。可见,永乐西北边疆内缩之后,明朝失去了对金塔寺的控制。
那么,洪武年间,明朝多次进入肃州北境的,“弃地”但由于北元力量的反扑,不得不放弃这一区域的控制。直到洪武二十九年设置一所而成卫,明朝短暂的控制这一区域。永乐三年,明朝迫于各种政治因素废撤威虏卫,西北边疆内缩,明朝控制区退至肃州,“弃地”成为中立缓冲区。如图1所示,亦集乃以南至肃州的这一区域即所谓的“弃地”。

图1 河西走廊“弃地”的范围③
三、“弃地”的作用
“弃地”曾是陕西行都司的辖境,明朝在这一区域设威虏卫、白城子千户所和威远千户所,以“隔绝哈密与蒙古”。明代的军堡是北疆防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18]148河西的防御体系主要是由墩堡、驿站和边墙三部分组成[19]27-38。“弃地”内的毛目城、金塔寺堡、威虏城、威远城、白城子等城堡关隘也曾被明朝短暂控制。黑河自南而北贯穿“弃地”,诸卫所和城堡关墩沿着黑河两岸分布,威远千户所、白城子千户所和威虏卫自备箱男分布,构成以黑河为中心的防御蒙古的纵深防御体系。
永乐时期,西北疆域内缩之后,肃州边外“弃地”成为明朝和蒙古诸部的缓冲区。南北狭长的“弃地”提供了足够的纵深防御距离,在这一地区修建堡寨,有利于明军的预警和战争准备,能够有效地防御蒙古诸部的入侵。在永乐至正德,“弃地”对于河西走廊边防产生了积极效果。
另外,《边政考》详细记载了北方蒙古诸部入侵河西走廊的两条固定进军路线,蒙古诸部的一条重要进军路线就是以黑河为通道进犯河西走廊西部肃州卫、镇夷千户所[12]396。蒙古诸部南下的地点包含亦集乃、黑城、威远、威虏、金塔寺、毛目头墩,上述诸地皆在“弃地”之内,这表明“弃地”是蒙古诸部南下入侵河西走廊的重要行进路线。洪武五年,冯胜自甘肃二州攻略亦集乃城。天顺元年,卢胜等官军在威虏城地方杀贼有功[20]6045,表明晚至天顺初年,“弃地”内仍然存在一条适合军队行进的道路,否则不可能出现上述的军事活动,这条通道无疑就是以黑河为中心的河谷。
此外还有卫所设置,《边政考》提及毛目头墩在镇夷所北一百九十里[12]394,《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卷》陕西行都司图幅将毛目头墩标在黑河的东岸,毛目头墩本是镇夷千户所下辖的一个军事据点,黑河西岸的威虏城等都是肃州卫的下属军堡。那么,可以认为黑河以东的“弃地”归属镇夷千户所管辖,黑河以西的“弃地”归属于肃州卫管理。永乐以前,明朝将“弃地”沿黑河划分东西,且分属两个不同卫所管辖。考虑到肃州卫“三面受敌,通呼吸于一线,惟南北为边塞,其西南北三面皆属夷疆”[21]70边防压力极大,单独一个卫所的有限兵力很难防守宽大正面,且“弃地”范围较大,防守难度较大。因而,明朝迫于边防压力会设置两个军事机构负责“弃地”的防御。
河西走廊肃州卫北部有亦集乃,与黑河相连,白亭海连三岔河,河谷成为北方蒙古诸部入侵的天然通道。黑河贯穿“弃地”,蒙古诸部能够沿着这条通道南下入侵河西西部诸卫。明初在“弃地”设立卫所的举措意在以军事手段控扼交通要道,抵御蒙古南下。
总之,正因为控扼交通孔道,蒙古寇边乃至明军北上才会通过“弃地”。自明朝南退之后,“弃地”之内少有民众居住,故而成为真实的缓冲区。缓冲区减轻了直接接触带来的边防压力,防御纵深提供了足够的反应时间,明军也能提前预警蒙古的寇边行动。
永乐边疆内缩以后,肃州的边外形势相对稳定,直到正嘉年间哈密二种(哈密、赤斤两部族)的内迁,“弃地”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哈密卫是关西七卫之一,在关西七卫的最西端,毗邻土鲁番。成化年间,明朝又与土鲁番争夺哈密卫[22]68。土鲁番屡屡强占哈密,哈密危机爆发,[23]14-22+115哈密走向衰弱。正德、嘉靖两朝,谢亦虎仙之乱导致哈密危机加剧,部分哈密民众逃入河西走廊,。
按照《边政考》的记载,正德十一年,哈密诸部迁居威虏、金塔寺及临城沿边上下古城。[12]617按照《五边典则》的记载,嘉靖七年,哈密诸部再次内迁,甘肃巡抚都御史唐泽将内迁民众安置在威虏旧城及天仓墩、毛目城、白城子等地。[24]472据此可以判断哈密诸部曾两次内迁;一是正德十一年,二是嘉靖七年。再者,第一次安置内迁民众的寄住范围仅限于威虏、金塔寺、上下古城一带,第二次的寄住范围有所扩大。第一次内迁的规模,按《边政考》记载,赤斤部落约有男女一千五百六十口在正德十一年左右内迁上下古城(“弃地”的一部分)。[12]616第二次内迁的规模,按《明史》记载,嘉靖七年,王琼内迁赤斤之众仅千余入。[11]14458那么,哈密诸部相继内迁数千人,实际上哈密诸部内迁的人数可能比历史记载的要多[25]158-161。总之,正德十二年和嘉靖七年,哈密诸部分两次陆续迁入“弃地”,分布范围也从金塔寺、威虏堡等临近诸堡扩大到整个“弃地”。两次内迁的规模约有1万人。[4]33-46+148-149
嘉靖五年时,甘肃都御史陈九畴、兵部尚书金献民对这些哈密诸部内迁的态度是“以安插之,永杜后患[2]1442”。陈九畴等认为将数量较多的哈密诸族安置到“弃地”,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肃州汉人和内迁诸族发生冲突,也是为了防止内迁诸族劫掠肃州,危害地方社会的安全。而且,“弃地”经常遭到河套等部族的劫掠。杨一清将内迁“弃地”的举措视为“又添设一藩篱”,有利于地方的长治久安。[9]1797陈九畴和杨一清是当时明朝的重臣,他们两人的态度表露出明朝的官方倾向——明朝认为内迁民寄住“弃地”可以成为明朝边疆的“藩篱”,隔绝明蒙。嘉靖二十八年,杨博巡抚甘肃,开始修葺“弃地”内的威虏、金塔等古城堡,添设白烟墩等七座城堡,修建墩台十二座,允许内迁之民耕种和放牧。[26]79-82杨博认为“番汉错居”不能做到长治久安,还将肃州视为人体,必须“固本培元”才能“保无虞”。[26]83可见,杨博的理念与陈九畴、杨一清的“藩篱”相类似。事实上,哈密内迁“弃地”作为肃州屏障的观念不仅一脉相承,更是成为河西走廊边疆经略的政治共识。自嘉靖年间后,河西走廊北部边疆形势一直相对稳定,虽北方少数民族时有南寇,但是“弃地”始终发挥中立缓冲区的作用,屏护河西走廊的边疆安全,直至明末农民起义席卷河西,“弃地”才逐渐消失。
总之,明代河西走廊北部的“弃地”存在时间漫长,始终在明朝河西走廊边防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初,弃地”所在区域尚未完全形成,因明朝积极拓边,经营边疆,明军可以通过“弃地”北上进攻蒙古,河西走廊“弃地”所在区域成为明王朝对抗蒙古的桥头堡。自永乐间边防压力骤增,北部疆域内缩,该区域成为蒙古南侵的固定路径,明蒙双方在此地区展开激烈交锋,“弃地”成为明蒙之间的中立缓冲区,缓解了明朝的边防压力。正德嘉靖时,哈密危机导致哈密二种内迁,寄住肃州和边外“弃地”,“弃地”成为了肃州的藩篱,隔绝番汉,维护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因此,“弃地”作为明朝西北边疆的不可或缺部分,不论西北边疆形势如何变化,其始终作为中立缓冲区,隔离明蒙,屏护河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河西的边防压力,保障了河西边疆社会的安全,在明朝西北边疆经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余论
与中立缓冲区这一概念相似的区域很早以前就存在于中国历史中,春秋战国时期的“隙地”、两汉的“瓯脱”、唐代的“闲田”和“闲壤”等都具有中立缓冲区的性质。自永乐时期明朝北方边疆内缩,明朝九边边军时常有出边“烧荒”的军事行动。九边明军一般在秋冬季节有计划的越过长城,焚毁长城以北一定范围内的林木、草场,制造一条漫长的废弃区域阻挡蒙古南下,也利于边军的预警和防御。认为制造出来的“烧荒”区颇有中立缓冲区的性质,值得进一步探究。而且明代河西走廊镇番卫以北还存在一条北方蒙古南下入侵的固定路线,镇番卫以北因疆域南缩也存在类似“弃地”的区域,但限于现存史料的不足,尚不能判断中立缓冲区的存在。因此,明代中立缓冲区的深入研究还需要新史料的发现,也更需要深入、广泛的野外考察。
另外,明代“弃地”记载出现的时间是在正德嘉靖年间,而且有关“弃地”的历史记载较少,其只见于少数大臣的奏疏中。因此,用“弃地”来称呼河西走廊肃州以北、亦集乃以南的这片区域还值得商榷,“弃地”的概念、范围界定、作用尚有探讨的余地。
注释:
①亦集乃蒙古语名哈日浩特,意即黑城,即古代黑水城,亦集乃在城附近。
②马顺平《明代陕西行都司卫所建置考实》一文考证威虏卫、威远千户所的设置时间在洪武二十九年至洪武三十年之间。
③图一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卷》陕西行都司地图自行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