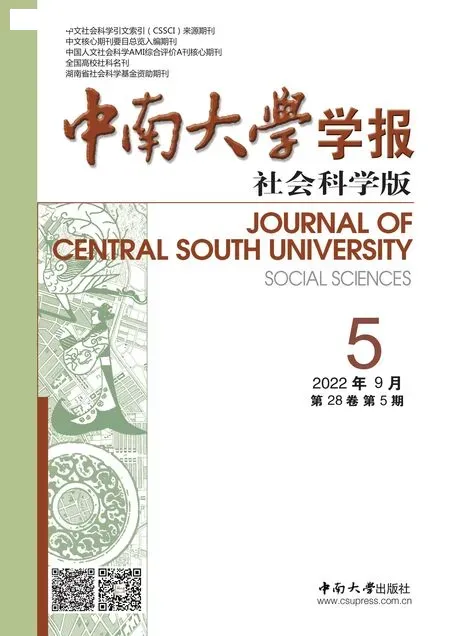朱陆王工夫论的结构差异
2022-12-25傅锡洪
傅锡洪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学者一般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来划分宋明儒学的主要思想流派。在此框架中,王阳明的思想与陆象山的思想一脉相承,合称陆王心学。与之相对的则是程朱理学,尽管学者对这里的“程”究竟是包括了二程兄弟程明道、程伊川,还是仅指弟弟程伊川存在分歧①。且不论二程兄弟,至少朱子堪称理学的代表则是不争的事实。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相对而言的理解框架中,阳明的思想被认为是趋近于象山而远离朱子,并与朱子形成对立的。
这样的认识框架固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存在若干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阳明曾从不同角度批评象山,其中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他批评象山“只是粗些”。虽然这是在高度评价了象山之后做出的批评,亦即越过朱子,认为“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1](104),但是这一批评却仍然可以提示我们在陆王之间存在的微妙分别。且不论阳明自己在朱陆之间有过调停之论,他在正德三年(1508)的龙场悟道的次年,席元山向他求教朱陆异同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讲述了自己在龙场所悟的内容,最终使席元山对此前的提问得出了“朱陆异同,各有得失”[1](1355)的结论。相比于单纯是陆非朱而言,这无疑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看待阳明与朱陆思想的远近关系。
大致来说,阳明的思想介于朱陆之间而相对更接近于陆。传统上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划分无疑有其合理性,只是我们不应该由此忽视陆王之间的差异,以及阳明与朱子的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至于何以得出这一结论,可以从他们对本心的看法说起。从他们对本心的不同看法切入,可以看出他们倡导的工夫的结构差异②。
一、朱子的二元八层非本体工夫
先秦时代的孟子即已提出人都有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此四端之心即是本心。本心实际上是直接发自本性的意念,是不容已要实现的情。一般而言,本心是使人为善去恶,并最终实现成贤成圣目标的重要条件。包括朱子在内的宋明诸儒都承认人皆有本心,不过在怎样对待本心的问题上,他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朱子认为本心是凭借不上的,成就圣贤终究要依靠居敬和穷理。如弟子向他提问:“先生尝说‘仁’字就初处看,只是乍见孺子入井,而怵惕恻隐之心盖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处否?”朱子回答:“恁地靠着他不得。”[2](110)“靠着他不得”即是凭靠、凭借不上的意思,“初处”即是发端、萌芽的意思,“不期然而然”意味着意识发自先天本性而无后天的思虑。在遇到诸儒“乍见孺子入井”的情形时,人会不自觉地产生恻隐之心,这就是本心。孟子之所以要突出“乍”,是要排除后天思虑的渗入,让此时的意识尽可能是完全发自先天本性的。朱子并未正面回答弟子的提问,实际上他并不否认弟子的观点,他只是强调本心是凭借不上的。本心凭借不上可以分两层来讲:一是无法完全凭借本心,由此,工夫并非完全是先天工夫而具有后天工夫的性质;二是进一步讲,本心虽然不是没有作用,但在后天工夫中也是凭借不上的。
第一,不借助后天的努力而完全诉诸先天的本心是行不通的,如果不借助后天的反省、觉察,那么本心是无法保持清明状态的。朱子说:“只为从前不省察了,此端才见,又被物欲汩了。所以秉彝不可磨灭处虽在,而终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2](2846)四端之心固然可以不期然而然地展现出来,但是人如果不加以后天省察的话,这些意念就会混杂并淹没在私欲之中。
由此可见,朱子固然不否认本心的存在③,但他又坚持认为本心是无法完全凭靠的,这就是他对本心的基本态度。基于这一态度,他对象山提出了如下评论:“陆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举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2](2970)朱子认为,象山宣扬本心的诸多论述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象山只是凭借本心而完全忽视了修为存养之类后天努力的作用,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他并不否认本心的存在。
朱子所说的修为存养,最根本的便是居敬和穷理。大致而言,前者指的是保持意识的清醒、警觉状态,后者指的是把握事物之理。居敬与成贤成圣的联系较易理解,即保持清醒、警觉的状态,则私欲不容易产生,即便产生也容易被觉察并加以克除。穷理与成贤成圣的联系则需加以说明。做成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了解与这件事情有关的事物的道理,在此意义上穷理是必要的,但朱子所说的道理不仅包括成事的手段,还包括道理的实现本身,因为他所理解的道理从根本上来说即是圣人致力于实现的生生之意。他说:“圣贤出来抚临万物,各因其性而导之。如昆虫草木,未尝不顺其性,如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当春生时‘不殀夭,不覆巢,不杀胎;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所以能使万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2](256)“天地本来生生之意”即是所穷之理的根本内容,圣人所做的事情无非是在把握了这一天地本来生生之意的道理之后,使其具体实现出来或实现不受干扰而已。
由于人都有恻隐之心,所以原本“不殀夭,不覆巢,不杀胎”之类的道理并不难以理解,那为什么还需要穷理呢?朱子以下说法正可作为解释:“圣贤教人,虽以恭敬持守为先,而于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验今,体会推寻,内外参合。盖必如此,然后见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于世间万事、一切言语,无不洞然了其白黑。”[3](2543)意思是此心此理原本并不难理解,真正需要努力才能做到的是理解“此心之真,此理之正”。“真”与“正”表现在,心并不是可以恻隐可以不恻隐的,生生之理可以实现可以不实现的,不恻隐、不生生也无妨碍。相反,以恻隐的方式实现生生之理具有必然性和迫切性。朱子以“不可易”和“不容已”的形式[3](528)④,明确表达了必然性和迫切性的意思。同时,他认为迫切性更为根本,强调迫切性可以统摄必然性。也就是说,如果感受到了实现生生之理的迫切性,自然会行动,必然性自然也就蕴含在其中;如果仅仅体认到必然性,则未必当下就行动,仍然可能延宕,则必然性最终也将落空。因此,相比必然性,迫切性是更为重要的。总之,穷理最关键的目的是要实现对生生之理的不容已和不可易的体认和确信,有此体认和确信,便能落实人所固有的恻隐之仁,而不至于使之淹没在众多私欲之中⑤。至于居敬,则可充当人做穷理工夫的必要条件,当然穷理反过来也有助于人保持敬的状态,因为人对道理体认得越深,就越不容易被私欲干扰,也就更容易保持清醒、警觉的状态。居敬与穷理又有着各自的内涵而不可相互化约,由此两者构成了朱子工夫论的二元基础。穷理即《大学》八条目中的格物,在穷理的基础上,以及在居敬的保证下,朱子主张以八条目为次序层层推进工夫⑥。
第二,本心在后天工夫中也是凭借不上的,居敬、穷理之类工夫凭借的不是本心。考虑到朱子并不否认本心的存在,那么就有必要追问,他主张的工夫是否有凭借本心。因为居敬之为居敬是保持清醒、警觉的状态,其要点是保持而不间断,而在经过长期工夫修养之前,本心恰恰是暂明暂灭,其呈露是时断时续的,因此总体上可以确定居敬并不凭借本心。他以下所说即体现出居敬存养凭借的不是固有的本心,存养工夫和本心并不是一体的关系:“便是物欲昏蔽之极,也无时不醒觉。只是醒觉了,自放过去,不曾存得耳。”[2](377)本心持续的、稳定的呈现是居敬工夫的结果。朱子并不认为本心是本体,如果要说本体,那么存养工夫就是本体,而不必在存养工夫之外另寻可以自然呈露的本体,因而存养工夫可以成为工夫凭借的本体。他说:“盖操之而存,则只此便是本体,不待别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于义理而不妄动,则所谓寂然者,当不待察识而自呈露矣。”[3](2189)“寂然常感者,固心之本体也。然存者,此心之存也;亡者,此心之亡也。非操舍存亡之外别有心之本体也”[3](2183)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其中“寂然常感”的本体是指与作用相对但又能发用的性。最后是说存养工夫之外别无本体,亦即除了作为实体、本源的性以外,作用层面只有存养工夫本身可以称为本体,不必再去寻找本体。这实际上是排除了本心在存养工夫中的作用。存养之所以可以被称为本体,原因也并不难理解,即存养本身体现了性的要求,使得性在现实中得以落实,所以才可以和性一样称为本体。
至于穷理,从本心为人所固有的角度来说,它应该会给穷理提供帮助,如朱子所说:“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终是遮不得,必有时发见。便教至恶之人,亦时乎有善念之发。学者便当因其明处下工夫,一向明将去。”[2](264)“因其明处”可以成为“下工夫”的条件,不过“一向明将去”才是关键,而不是说已有之明才是关键,否则就错过了本心的发用,其发用就没有意义了。事实上,一方面,理的复杂性是单纯依靠本心难以把握的。人只有通过读书之类的方式,才能对理的内容获得充分了解。由此,读书是朱子实现穷理目标无可替代的主要方式,“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⑦[3](668)。另一方面,从穷理的根本任务是体认到理的必然性和迫切性的角度来说,本心也是无济于事的。很显然,如果本心有帮助的话,朱子根本就没有必要诉诸穷理并为其设定体认和确信理之必然性和迫切性的最终目标。真正有效的是视听之类的知觉以及全身心沉浸式的投入。关于知觉,朱子说:“道理虽极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见闻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别求玄妙于意虑之表,亦已误矣。”[3](1563)“别求玄妙于意虑之表”实即象山等人主张的直接体认本心的工夫主张。朱子认为这是过于玄妙,难以捉摸的,只有视听之类知觉才能使人体认并最终确信理的必然性和迫切性。关于全身心沉浸式投入,朱子说:“人多把这道理作一个悬空底物。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所谓实体,非就事物上见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车以行陆。今试以众人之力共推一舟于陆,必不能行,方见得舟果不能以行陆也,此之谓实体。”[2](288)“实体”是切实、真切地体认、感受的意思。车只能行于陆,舟只能行于水,原本并不难理解,恐怕也不会真有人行车于水、行舟于陆。朱子只是以假设的行车于水、行舟于陆之不可行的显而易见性、确凿无疑性,来比喻全身心地沉浸于一件事情中,从而真切感受到理是必然如此、当下便如此的。此外,若非工夫已达纯熟之境,那么诚意以下各个条目的工夫也是并不凭借本心的。如果以凭借本心的工夫为本体工夫,以并非凭借本心的工夫为非本体工夫,那么总体而言朱子主张的工夫可以说是二元八层非本体工夫。
二、象山的一元一层本体工夫
与朱子本心凭借不上以及工夫不凭借本心的观点相反,象山工夫论的要旨在于基本上完全凭借本心。在象山看来,本心既具充足性,可以使人因应不同情况作出妥善应对,也具直接性,可以自然呈现。象山以下所说就表达了本心兼具充足性与直接性的意思:“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4](455-456)既然本心具有如此作用,那么首先需要做的是了解和把握具有这些作用的本心。象山说:“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贵至厚,自然远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4](440)我所“固有”的便是本心,了解和把握本心的工夫即是格物。不过其含义与朱子理解的注重读书的格物并不相同,朱子注重读书的观点在象山看来是“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4](459)。象山理解的格物的意思在于:“某读书只看古注,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4](441)将精神倾注在文字训诂解释上,结果是阻碍了本心的自然发用,象山倡导的减少负担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让本心可以不受干扰地发挥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在他看来,后天因素不仅不能起到促使先天本心落实的积极作用,反而会有干扰、阻碍的负面影响。由此,真正需要的是自然而然地让先天本心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以自然的方式把握本心。象山说:“深山有宝,无心于宝者得之。”[4](409)这是比喻只有以自然无为的方式才能把握本心,后天的努力反而会起到遮蔽的作用。他所说的“优裕宽平,即所存多,思虑亦正。求索太过,即存少,思虑亦不正”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4](464)。之所以自然无为可以把握本心,是因为本心本可自然呈现,而不待后天的努力。如前所述,象山的这一观点受到朱子“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的批评。象山认为只有自然才能把握本心,后天努力只能起到阻碍作用;朱子则认为没有后天努力的话,本心只能暂明暂灭,其呈现只能时断时续,不足凭借。
其次,基本上完全凭借本心以为善去恶。象山说:“循吾固有而进德,则沛然无他适矣。”[4](416-417)又说:“若立得住,何须把捉?”[4](443)又说:“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会一事时,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个闲闲散散全不理会事底人,不陷事中。”[4](459)都在自己手中的“血脉骨髓”指的是本心,因为完全凭借本心,所以可以沛然无事,可以无须把捉,可以闲闲散散。由此可见,象山虽然讲自然无为,但并非是完全无所作为,而恰恰是凭借本心大有作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并非完全忽视修为存养,只是他依靠的力量基本上完全来自本心。之所以只是说“基本上完全”而不说“完全”,是因为习气对人的负面影响是习焉不察的,需要通过后天的精察才能发现,才能克治⑧。对此,象山指出:“积思勉之功,旧习自除。”[4](454)在象山并非完全排斥后天努力、朱子主张虽不凭借本心但本心也能起到一定作用的意义上,双方的工夫论是有一定交叉性的。
阳明高足王龙溪的一个说法,可以用来概括象山的以上两层主张,即“无形象中真面目,不着纤毫力中大着力”[5](90)。前者是说以自然的方式把握本心,后者是说毫无后天努力、完全凭借本心以为善去恶。
综上所述,因为象山主张的工夫是围绕本心展开的,故为一元工夫;因为本心是本体,所以工夫又是本体工夫;因为自然无为贯穿工夫始终,所以工夫又可说是一层工夫。要言之,象山主张的是一元一层本体工夫,其工夫呈现出简易直接的显著特征。
三、阳明的一元两层本体工夫
阳明认为,本心具有直接性和充足性,人应该凭借本心来做工夫。在这一点上,他和象山是一致的。不过他并不认为后天努力只有负面影响,而认为对于落实本心来说,后天努力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初学阶段更是如此。他倡导的工夫可谓一元两层本体工夫⑨。在肯定后天努力的意义上,他接近于朱子。只是两人所说后天努力的方式不一样,朱子所说的是并不凭借本心的居敬穷理等,阳明则是承接直接发用的本心而使之落实。由此,我们才说阳明的观点介于朱陆两人之间而相对接近于象山。就阳明倡导经由后天进入而最终达到完全先天的为学进路的角度来说,唐君毅先生的说法是恰当的,“阳明之学乃始于朱而归宗于陆。则谓阳明之学为朱陆之通邮,亦未尝不可”[6](132)。不过,他对阳明学的有些看法则又不免有问题,“若其精义所存,则与朱子之别在毫厘间”[6](132)。实则朱、王在后天工夫之所指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其差异便是是否直接凭借本心。
阳明以下说法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其工夫主张:“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刮磨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若驳蚀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尘埃之落,固亦见得,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勿以为难而疑之也。”[1](1358)因为在这里圣人是与常人相对而言的,而常人属于学知力行以下的人,所以可以说圣人实即生知安行者。两层工夫首先指的是生知安行的圣人和学知力行以下的常人的不同工夫。常人即便是从困知勉行出发,最终也可达到“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的状态,这与生知安行的圣人已经没有区别。因此,两层工夫又指常人从困知勉行或学知力行出发,最终达到和生知安行者一样的状态的不同工夫。无论是横向的圣人与常人,还是纵向的从常人到圣人的不同阶段,其主要区别在于是以自然为主还是以勉然为主。
困知勉行的人在起步阶段本心处于遮蔽状态,即阳明所说“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⑩。这种状态下如何开始做工夫呢?可以说有两种力量可以凭借,第一种是本心。即便现实的意识和本心有距离,本心也一点便醒,正如阳明所说:“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1](34)这一被点醒的本心可以在工夫中发挥一定的指引和推动作用,尽管其作用比较微弱,却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种可以凭借的力量是后天努力。刘海滨先生指出,阳明的工夫“一方面是用良知本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遮蔽较厚,良知本身力量尚微弱,就不得不借助意识的助力”[7](39)。值得注意的是“助力”的说法,它表明后天因素并非只是先天因素的流溢,并非只是先天因素在后天的展现以至于是内在于先天因素的,实则后天因素与先天因素是平行、并列的关系。杨国荣先生也指出了阳明心学具有先天、后天两种因素并用的特点:“正如致良知这一命题所表明的那样,肯定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统一,构成了王阳明心学的重要特点。”[8](81)
后天努力从动力方面讲是“着实用意”[1](39)或“着实用功”[1](23),从准则方面讲是“精察克治”[1](1298)。着实代表本心自然发用的力量之外的力量;精察则代表对如何行动才符合良知准则的分辨,故而精察是从准则方面来说的,代表对准则的辨析以及坚守。初学阶段本心受到私欲遮蔽,因此单纯本心的动力和准则不足以支撑为善去恶的工夫,着实用意和精察克治便起到了弥补动力不够充足、准则不够明晰的问题的作用。初学阶段单纯本心不足以指引和推动工夫的完成,这是需要着实用意和精察克治的原因⑪。
有心或者有意,在儒学史上往往受到批评。且不论孔子对“意必固我”的反对,宋代的批评如横渠所说:“有心为之,虽善皆意也。”[9](28)明道也持类似看法,当然他虽然认为有心为善是私欲,不过却也承认一般的学习者难免要经历这一阶段:“论持其志。先生曰:‘只这个也是私。然学者不恁地不得。’”[10](398)前述象山否定有心工夫的观点的源头,便至少可以追溯到张程二人这里。阳明的观点与明道有微妙的区别。“欲也者,非必声色货利外诱也,有心之私皆欲也。”[1](204)并非“有心皆欲也”,只有在不恰当的时候的有心,才是“有心之私”,才是欲。实际上这里暗含了有心有其积极作用,而不是像明道一样认为仅仅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需要注意的是,应该有的着意不是着意让本心呈现,而是让本心落实。二程有关恕心的一个区分也可以用来讨论阳明所说的本心,因为本心也可以和二程所说的恕心一样自然呈现。本心可以自然呈现,所以着意的目标不是呈现本心,而是使本心落实。二程说:“彼谓着心勉而行恕则可,谓着心求恕则不可。盖恕,自有之理,举斯心加诸彼而已,不待求而后得。”[10](9)⑫
后天努力与先天本心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朱子处,居敬与格物是两轮并进、两翼并举的关系,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对于阳明来说,后天努力始终是围绕本心而展开的,两者并非同等并列的结构,即便在初学阶段后天努力提供的动力与定力的分量超过了本心直接好善恶恶的分量,其与本心的好善恶恶也是辅助与中心的结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明的工夫论是一元工夫论,不同于朱子的二元工夫论。
人之所以能做到勉强,是因为立志。阳明说:“夫苟有必为圣人之志,然后能加为己谨独之功。能加为己谨独之功,然后于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于古人论学之得失,孰为支离,孰为空寂,孰为似是而非,孰为似诚而伪,不待辩说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实有诸己也。”[1](1127)可见立志构成了工夫的真正开端。阳明极为重视立志,认为立志之于工夫具有充足作用:“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1](37)“只是立志”的意思是,立志就是充分条件,其后所说的积极进展可以随顺立志而来。既然这些积极进展及从无到有的发生,是完全由立志带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立志是无中生有亦即从无到有的工夫。阳明强调的“信得及”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对这一从无到有之可能性的信得及。而立志之所以能带来从无到有的积极进展,原因就在于人有本心,本心可以使人在为善的道路上动力日益强劲,准则日益明晰。因此,对于立志作用的信得及,实际上就是对本心作用的信得及。信得及的另一重点是本心不容违背,人应该依循本心而行,亦即对落实本心的必要性的信得及,在此不赘。
从反面来说,从无到有的工夫,就是无论知识还是才能,这些相比于本心而言的外在因素都不凭借,只是凭借本心,让本心在意识中升起,取得对意念的主导权。可以说,“无中生有”点出了阳明凭借本心的工夫的自足性。
阳明特别强调学者有必要相信良知作用的充足性。从与朱子观点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这一必要性。朱子认为,通过漫长而艰苦的格物工夫可以激发本心之知,使之稳定发挥作用,而在阳明这里,并无格物工夫的激发。在此情况下,自然状态的本心便只能暂明暂灭,而不能持续发挥作用。此外,一般人都基于朱子的思想,认为只有格物致知才能使人充分了解事物之理,怀疑单纯凭借本心怎么能应对纷繁的事务。这两点使得信得及本心变得异常困难。可是,如果脱离本心做工夫,那就不仅支离而烦难,而且终究无法成功。支离即沉溺于对事物之理的探求,偏离为善去恶的总体方向;烦难即对事物之理的探求是漫长而艰苦的。无法成功的原因则是大量事例没有现成的道理可以参考,只有诉诸本心才能得到善解。正因为本心如此重要,而信得及本心又如此困难,所以阳明特别重视信得及本心。按照阳明弟子薛中离的说法:“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1](132)
工夫虽然分为两层,但很难截然分开,第一层是勉然多而不是完全抛弃自然(本心可以自然呈现),第二层是自然多而不是彻底抛弃勉然。阳明说:“众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圣人分上较多,故‘率性之谓道’属圣人事。圣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贤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谓教’属贤人事。”[1](111)二者虽然没有截然的区分,但因为主导的方面不一样,或勉然或自然,所以两层的区分仍然是有必要的。过渡的标志应该是脱落习染,良知充分发用,由此人便有不容已的动力去为善去恶。阳明说:“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1](1424-1425)又说:“颜子‘欲罢不能’,是真见得道体不息,无可罢时。若功夫有起有倒,尚有可罢时,只是未曾见得道体。”[1](1297)这里说的是一种真的能放下私欲的状态,本心所发之念不息,所以欲罢不能,这无疑已经进入工夫的第二层了。在这种状态中,意志与本心融合为一,本心之外别无意志:“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1](25)“天聪明”即是本心,从本心充分发用的角度来说,这一阶段是有为的;从本心之外别无意志的角度来说,这一阶段又是无为的[11](42-43)。实际上这就是自然好善恶恶的状态。
工夫熟后自然为善,或许可以说就是已经养成德性,拥有美德。因此,第二层的工夫不仅可以从行为,而且可以从美德的角度加以解释。
美德的外在表现主要是使万物得到妥善安顿。人要能自然而然地做到为善去恶,关键就在于人的意识与现实物达到高度协调。因为协调,所以不必刻意、执着,便可自然而然使之得到妥善安顿。使现实物得到妥善安顿即是万物一体。而自然而然使万物得到妥善安顿,即是自然生生,这构成了阳明乃至整个宋明儒学所讲的工夫的最终指向。
要言之,阳明工夫论的要义是先天与后天两种因素的并用,由此区别于基本上完全凭借先天因素的象山和主要凭借后天因素的朱子。可以说,阳明的主张既不同于朱子,也不同于象山,加上注重静坐的陈白沙等人,四者在宋明儒学史上构成四足鼎立的格局。单纯将阳明归为象山的同调、朱子的反调,是不足以全面、准确理解阳明的主张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否定阳明和象山一样同属心学,只是说两人属于不同类型的心学,不能将他们等同视之。
四、从龙溪、阳明之异看象山、阳明之异
象山与阳明的差异,还可以从龙溪与阳明的差异看出来。前已述及,作为阳明最重要弟子之一的龙溪,其主张与象山趋同而不同于阳明。龙溪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阳明后学的走向,甚至可以说他在很大程度上使阳明后学偏离了阳明原本的方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否定龙溪思想自身的价值,而只是一种事实判断而已。他对阳明思想虽有深刻透彻的理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阳明思想的正确理解⑬。与象山和龙溪思想接近的人尚有不少,如北宋的程明道、明代中期阳明的密友湛甘泉以及明末的刘蕺山等。分析龙溪与阳明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阳明与象山的差异以及心学内部复杂性的理解。而无论龙溪与阳明的差异,还是象山与阳明的差异,都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龙溪与阳明的差异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观察。
第一,何谓“第一义工夫”。阳明是从立志、诚意和致良知的角度提及“第一义工夫”的。如他在信中对弟子说:“数年切磋,只得立志辩义利。若于此未有得力处,却是平日所讲尽成虚语,平日所见皆非实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经一蹶者长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为后日之得,但已落第二义。须从第一义上着力,一真一切真。”[1](190)第一义工夫即是依循本心而行的工夫,依循本心而行既包括自然依循本心,也包含勉然依循本心,而勉然依循本心的开端便是立志,并非只有自然依循本心或者完全凭借本心的工夫才是第一义工夫。
龙溪认为从有所刻意、执着入手的勉然工夫“恐未是究竟话头”[1](133),不足以称为第一义工夫。阳明后学对第一义工夫的主流意见受龙溪影响。其内容或可参考黄梨洲所说:“南都一时之论,谓‘工夫只在心上用,才涉意,便已落第二义,故为善去恶工夫,非师门最上乘之教也。’”[12](452)这种对第一义工夫的理解,实际上是以象山、龙溪等人代表的工夫为标准,追求完全凭借先天本体的指引和推动,而否定后天努力的积极作用。从阳明的角度来说,这无疑窄化了第一义工夫的范围。实则只要围绕良知而非绕开良知展开,使良知得以落实的工夫,哪怕包含了后天的努力,也都可以称为第一义工夫⑭。
第二,如何看待“转念”。本心具有直接性,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通过有心的方式使本心落实,已不是直接意识,而具有了反思意识的性质。通过有心的方式落实本心,虽然符合本心的准则,但却不是严格意义的本心,或者说这已经不是“初念”,而是“转念”。阳明弟子龙溪肯定初念而否定转念,阳明通过有心来落实本心的主张也在他否定之列。从阳明的角度来看,龙溪对转念的理解过于狭隘,有心落实本心,对于初学阶段的人来说是具有积极作用而不应否定的。龙溪的观点为:“今人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乃其最初无欲一念,所谓元也。转念则为纳交要誉、恶其声而然,流于欲矣。元者始也,亨通、利遂、贞正,皆本于最初一念,统天也。最初一念,即《易》之所谓复,‘复,其见天地之心’,意、必、固、我有一焉,便与天地不相似。”[5](112)龙溪认为,一念恻隐才是善的,“纳交要誉、恶其声而然”之类转念都是恶的。这本来没有问题,然而转念并不限于“纳交要誉、恶其声而然”,坚持恻隐一念不滑落,使之不受干扰地最终得到落实的念头也是转念,但却是正面的。龙溪似未注意到此处。以下对话便体现了阳明肯定初学阶段转念、有心的积极作用:
问:“近来妄念也觉少,亦觉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实用功,便多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会妥帖。若才下得些功,便说效验,何足为恃?”[1](140)
提问者处于无所着意的状态,阳明认为这一状态不适合他此时的阶段,故在回答中强调“多这些着想也不妨”。可见阳明认为对常人而言第一层工夫不可跳过,不能将第二层以自然为主的工夫扩展到初学阶段,初学阶段应该以勉然为主。这与象山、龙溪面对类似问题时强调宽平、自然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如何看待“无中生有”。阳明所说的无中生有是指以立志开启工夫。无中生有的工夫如果理解为在无所着意的“无”上立根的工夫,那就可能把勉然工夫排除在外。事实上,就如树木出生之时容易抽繁枝一样,人在初学时也往往被各种外在的爱好牵累。此时唯有通过有所着意的工夫,才能实现本心对意念的主导,所以关键在本心对意念的主导,而非是否有所着意。但是从龙溪的角度来看,无中生有恰恰指的是从自然而入,“盖良知原是无中生有,无知而无不知;致良知工夫原为未悟者设,为有欲者设”[5](35)。
龙溪所谓无中生有,指的是在没有任何私欲干扰的条件下,凭借完全发用的良知自然应对万事万物。对他来说,无中生有不是体现了以良知为中心的工夫的自足性,而是体现了工夫的自然性。这是他的主张不同于阳明之处。师徒双方虽然采用了相同的表述方式,但其内涵却是非常不同的。综上所述,牟宗三先生以“调适而上遂”概括龙溪的观点与阳明的关系,是有其洞见的:“王龙溪之颖悟并非无本,他大体是守着阳明底规范而发挥,他可以说是阳明底嫡系;只要去其荡越与疏忽不谛处,他所说的大体皆是阳明所本有;他比当时其他王门任何人较能精熟于阳明之思路,凡阳明所有的主张他皆遵守而不逾,而亦不另立新说,他专注于阳明而不掺杂以其他(此其他可只限于宋儒说);他只在四无上把境界推至其究竟处,表现了他的颖悟,同时亦表现了他的疏阔,然若去其不谛与疏忽,这亦是良知教底调适而上遂,并非是错。”[13](179)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龙溪“上遂”的做法在阳明去世前一年的天泉证道时获得阳明支持,但是,阳明只是允许他以自然的方式自修,而不认为可以以此教人。可以说,龙溪的思路是从阳明平时的思路切换到了象山的思路。因此从他与阳明的差异可以看出象山与阳明的差异,而这正是本节的论旨。由于牟宗三先生对阳明两层工夫的思路未深入关注,没有注意到陆、王的差异,使得他对龙溪继承阳明的一面注意有余,而对其偏离阳明之处则观照不够。同时,龙溪的思路自有其合理处,不能仅仅因为他完全凭借本心,就认为是“疏阔”和“不谛”。实际上,宋明儒学中不同的工夫提升之路是殊途同归的关系,不同道路自有其合理的逻辑和成功的可能,也不乏内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流弊。发掘各自的价值而加以熔铸、创新,或许才是我们今天研究宋明儒学时应采取的态度。
注释:
①如冯友兰先生如下说法便展示了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道学后来发展为‘程朱’、‘陆王’两大派。这个‘程’,传统的说法以为统指二程,其实二程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哲学思想,而程颢的哲学思想,则为‘陆王’所继承、发展。”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三松堂全集》第10 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②笔者曾撰文详细对比阳明的一元两层本体工夫与朱子的二元八层非本体工夫,参见傅锡洪:《朱王工夫论的结构差异——兼谈朱陆之争》,《学术研究》2022年第1期,第41—47页。此外也曾以朱陆之辩为切入点,对比过朱陆工夫及其整体思想的异同,参见傅锡洪:《朱陆之辩再论:理论症结、内在关联与话题选择》,《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 期,第30—40页。本文可说是上述两文工作的延续和深化。
③如所周知,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思想中没有本心。较早摆脱这一观点影响的是蒙培元先生。他对朱子处之本心的内涵有深入阐发,他指出:“朱子有道德本心之说,而最能说明其道德本心说的,莫过于‘心即仁’说。”参见蒙培元:《朱熹哲学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
④曾亦先生指出:“‘不容已’表面上是指理所当然,实际上是情不自已的意思。”所言甚是,不过,其后他并未将对其的体认和确信视为朱子穷理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参见曾亦:《工夫与效验——从程明道论“识仁”看朱子对〈大学〉新本的阐释》,《中国儒学》第十辑,2015年,第82页。
⑤朱子固然重视理是不可易的准则或规范,但也重视其不容已地要实现出来的性质。钱穆先生以下说法似只是注意到了前者:“大抵晦翁讲宇宙方面,思路较完密,但其所谓理,则规范的意味重,推动的力量薄,平铺没气力,落到人生方面,使人感到一种拘检与散漫疲弱无从奋力之感。”参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5)》,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80页。学界广泛讨论在朱子这里知如何导出行的问题,其要害即在对理之必然性和迫切性的体认和确信。
⑥当然不是说只有完成致知才能开始诚意,而是说只有达到知至,才能做到意诚。诸如此类,前一条目的完成是后一条目完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后一条目开始的必要条件。吴震先生从工夫系统和工夫次第的角度对此做了说明:“一则说正心诚意不全在致知格物之后,一则说必等到‘物格知至’,然后才能真正做到正心诚意。朱熹之意似在强调:前者是就工夫系统而言,后者是就工夫次第而言。”参见吴震:《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 期,第21页。
⑦不过朱子也有看似与此相反的言论,如:“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见朱熹:《朱子语类》卷十,第161页。徐复观先生就此指出:“朱子言论,以读书问题为中心,有显系自相矛盾而无以自解者,则系难以否认的事实。故朱、陆异同问题,实即朱子治学上所包含之矛盾问题。”参见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6页。朱子以下所说实际上可以调和上述两方面的观点:“须是存心与读书为一事,方得。”又说:“本心陷溺之久,义理浸灌未透,且宜读书穷理。常不间断,则物欲之心自不能胜,而本心之义理自安且固矣。”分别见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一,第177、176页。这实即他居敬与穷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观点的具体化。应该说,朱子观点自有其可以自洽的内在逻辑。并且他与象山的分歧也与读书、涵养或居敬、穷理之间的关系无关,而与是否依靠居敬、穷理有关。因此,朱陆之间的分歧应该不能归结为朱子自身的矛盾或居敬、穷理的关系。
⑧陈来先生在研究阳明致良知工夫时注意到的习气之于致良知工夫的不利影响,在象山这里同样是适用的:“良知既然是不虑而知,它就有可能被混入其他一些同属不虑而知的情欲和本能,这也是王门后学中实际发展的一种倾向。”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其说甚是。
⑨陈立胜先生如下关于阳明的说法,触及了从朱子两轮一体工夫转向阳明一元工夫的问题:“‘独知’工夫乃是一即省察即涵养、即明即诚、即知即行的端本澄源的一元工夫,而有别于朱子省察与涵养、明与诚、知与行两轮一体的工夫。”参见陈立胜:《王阳明思想中的“独知”概念——兼论王阳明与朱子工夫论之异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 期,第79页。
⑩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似乎是说存在着本体被彻底遮蔽的情况,然而阳明终究认为“觉即蔽去”“一提便醒”,这就意味着本体的作用其实并未彻底中断。
⑪陈来先生注意到了良知未充分发用对工夫的影响:“良知本体人人具足,但现成地表现在意识活动的良知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才要‘致’良知。个体良知的巨大差别性不能替代、反映道德法则的统一性。因而每个人不能仅仅依据尚未‘致极’的良知决定行为准则,否则,道德判断的机制就是不完善的。”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335页。应该说,良知未充分呈现,是需要包括着实用意和精察克治在内的后天努力的原因。现实中难以存在彻底的、完善的良知,只有具体的、有限的良知。人不应脱离这具体的、有限的良知来做工夫。事实上,陈立胜先生说的“省察之心”“以经印心”和“从师亲友”的必要性,也可从现实中良知的有限性角度来理解。参见陈立胜:《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335—354页。
⑫冈田武彦先生如下关于阳明后学中修证派的工夫的论述说的也是这一区分:“修证派的工夫是本体的工夫,而不是与本体相对的工夫。所谓本体的工夫,就是‘用功于本体’上;所谓与本体相对的工夫,可以说就是‘用功而求本体’。”参见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第143—14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在此有必要对法国学者于连(François Jullien,也译作朱利安)先生的一个观点加以辨析。“孟子如此强调条件势化的过程,不过是与中国思想共通的效率观念相连了:人不应该希求直接达到所欲的事实效果(因为直达目的总意味着要强求,而结果也不就会长久),而应该使效果自然而然地,作为结局,从事前准备好的条件情势中顺势而出。”参见于连:《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0—101页。如果按照伊川的说法,“自然”指的是本心的发露或呈现,而不是说充实或落实。要反对的只是勉强地让本心发露,而不是勉强地使本心落实。尽管勉强地让本心落实并非工夫的最高阶段。
⑬如近来张新民先生的研究即揭示出阳明二传弟子孙淮海的工夫论受到龙溪的影响,他们的主张属同一类型。相关研究参见张新民:《孙应鳌及其传世著述考论》,《孔学堂》2021年第1 期,第42—70页。
⑭阳明与阳明后学认为的第一义工夫之间的区别,未受到学者足够重视。林月惠先生以下所说实际上是将阳明所说的本体工夫与阳明后学的第一义工夫等同起来:“阳明之‘本体功夫’,即是阳明后学所言的‘先天之学’,笔者称之为‘第一义工夫’,彭国翔名之为‘究竟工夫’,也相当于牟宗三紧扣‘逆觉体证’所言的‘本质的工夫’(与‘助缘的工夫’相对)。”参见林月惠:《诠释与工夫:宋明理学的超越蕲向与内在辩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第162页。实则阳明这里本体工夫具有广狭二义,只有在狭义的意义上,本体工夫才等同于阳明后学所说的第一义工夫,而在广义的意义上则不能等同。广义的本体工夫等同于阳明所说的第一义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