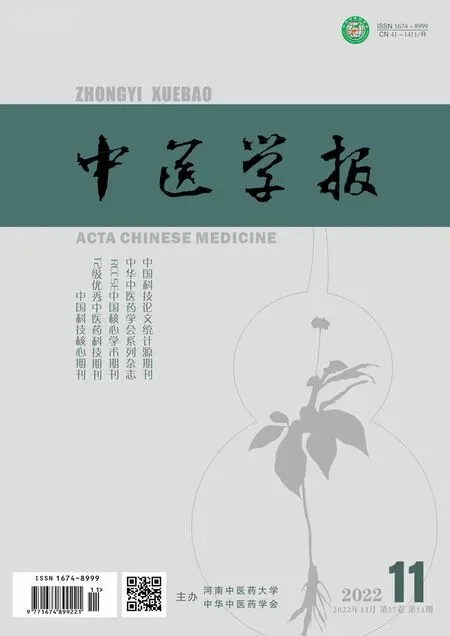《伤寒论》六经病中风法度
2022-12-25田同良马萌
田同良,马萌
1.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4; 2.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201203
营卫学说是《黄帝内经》中论述最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在营卫与气血的关系上,则气血为体、营卫为用[1],这就是经方理法重视营卫之根本原因。仲景基于此,将营卫理论发展到了极致,赋予了中风以病机概念。医圣把包括《汤液经法》在内的许多经验之方打造成为经典之方。《伤寒论》六经统于太阳经,而太阳经又统司营卫,由此可知,营卫实为六经辨证之法眼。桂枝汤作为调和营卫的代表方,因卫行于脉外,而营行于脉中,卫强而营弱、阴虚而阳亢,因此桂枝汤不单纯是一个解表方。《伤寒论》六经中风均在原文中有明确条文,六经皆可中风,不止太阳一经。仲景伤寒学术特点就是以中风法度为中心思想贯穿表里,重视表里观,并以中风体现里病出表、阴病转阳之病解途径。
仲景伤寒六经体系的形成及其中风法度的确立,奠定了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地位,使得六经中风成为《伤寒论》中最核心的病机理论而自成体系。《伤寒论》六经体系中,解表是总则,解表法是汗法,为祛邪而设,这是伤寒经方不可更易之定法。汗法是泄津液以发汗,为常规解表法,而解肌法是在解表的基础上再细辨津液虚实,是为存津液而发汗所设的一种特殊治法。解肌是仲景对表证经方理法的一次创新,完善了经方表证理论体系,使中风法度这一经方最为重要的病机概念,具备了更为完善的治疗方案。桂枝汤作为伤寒六经病第一方,不仅蕴含了经方理法之表里观、津液观和正邪观,而且蕴含了里病出表、阴病转阳的病解法度,而且桂枝汤本身又内涵阳法复脉、阴法解肌的经方理法。
1 《伤寒论》六经中风之阴阳、表里、正邪观
仲景继承扁鹊阴阳、表里二分法并认识到其不足,加入半表半里的病位概念,创立三分法,开创了三阴三阳病论治之先河。以表里分阴阳,即表之阴阳为少阴病、太阳病,里之阴阳为太阴病、阳明病,半表半里之阴阳为厥阴病和少阳病[2]。至此,《伤寒论》六经病辨证体系得以确立。所以六经经方理法就是表里、阴阳,为万病之宗。六经病的治疗总则是解表,表里观是贯穿六经病的一条主线,解肌是医圣对解表法的一次创新。伤寒经方理法首重表里,尤重表证,医圣在阴阳表里之基础上,将表证再拆,分出伤寒与中风,不但给予《伤寒论》中风以特定之含义,而且还赋予了《金匮要略》杂病以丰富内容,使得中风最能代表机体表里合病、里病出表之特点[3]。
《伤寒论》六经中风理论蕴含了津液观、表里观、正邪观,津液观首当其冲。伤寒病虽分六经,但津液本具阴阳,在表即营卫,在里曰胃气。经方理法就是基于“津液观”阐释营卫、阴阳,因此人体津液既含有阳的层面,如阳气、卫阳、卫气;又含有阴的层面,如阴液、营阴、营血,这也是仲景伤寒经方体系独具之概念。津液亏虚不能濡养的同时,亦必然表现出在表不能温煦,从而进一步影响到营卫的交合。伤寒经方理法可谓以解表为第一要义,以存津液为基本宗旨,故表证之中,必以中风法度为核心。对于津液不足而有表证者,仲景立解肌法护津液而解表以治之,补充了解表之麻黄汤与麻桂汤之不足,而让里邪得以出表,阴证得以转阳,使得诸多疑难病症有了针对性的治疗方向。
其次是表里观,仲景对扁鹊表里观推崇备至。《伤寒论》开篇即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伤寒六经体系把表里观推向了极致,在仲景之前的经方体系中,表证是表证,里证是里证,表里关系是割裂的。而医圣把表证拆分出中风法度,打通了疾病的表里关系。《伤寒论》以桂枝汤治中风,而遍见于三阴三阳各篇,所宗乃风无定位,通行六经之义。中风之阳旦法度不但解决了太阳病传变及六经病里病兼表的问题,而且还揭示了六经里病出表、阴病转阳愈病之规律。
《伤寒论》第7条曰:“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前者即为太阳病,后者说的就是少阴病。因此,伤寒大家胡希恕认为,伤寒表证绝非太阳独有,少阴病与太阳病同属表证[4],只不过证有阴阳之别,全在于机体虚实之反应耳,前者是表阴证,后者为表阳证。
最后,《伤寒论》中风理法之正邪观以祛邪为第一要务,主辨虚实,细分胃虚,注重六经病传变与虚热转实病机,用津液的疏布离合来架构疾病的水火、气血的虚实正邪关系。中风经方理法之三观又以津液观为基础,一部《伤寒论》也是一部津液大论,处处体现着保胃气、存津液的观点,从而达到扶正祛邪之目的。
《伤寒论》之中风法度遍及六经病,亦体现了土主四时这一理论内核,而且,凡是冠名“中风”的条文,均为表里同病,而以表证为所急所苦,这就是解读《伤寒论》中风之密码。也就是说,中风营卫不和之卫缓,源于津液的不足。桂枝汤及其类方作为阳旦法度,同时内涵阳法复脉、阴法解肌治病大法,而且还蕴含了伤寒六经病之病传观,以及里病出表之愈病观,绝不能仅局限于太阳病。医圣又以太阴中风病传为内伤杂病之根基,强调了伤寒与杂病并非各自为政,原本就是一脉相承。
《伤寒论》经方理法特点之所以首辨表里、尤重表证,是因为表是邪气的来路,愈病就是要让邪气出表,给邪气以出路。医圣对表证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确立了中风、伤寒、温病为主之表证的不同证治法度。寒性凝滞收引,羁绊百骸而困表,因此只有表证的太阳、少阴有伤寒。而风性开泄善行,洞开腠理而入里,因此六经皆有中风。而中风又最能代表机体表里合病、里病出表之特点。由此,《伤寒论》当里病兼表、表里合病,而以表证为所苦所急时,有一种法度叫中风,即桂枝汤法度。与温病之黄芩汤之阴旦法度相对应,或称为阳旦法度;亦与麻黄汤解表大法相对应,抑可称之为解肌大法。
2 《伤寒论》六经病各兼营卫、皆有其表,六经皆可中风
在《伤寒论》条文中,伤寒只见于太阳病的麻黄汤证,以及少阴病的麻黄附子甘草汤证,而中风则在六经病中均有明确条文。六经之太阳中风、太阴中风、阳明中风、少阳中风、厥阴中风、少阴中风均在仲景原文中有明确指出。因此,六经皆可中风,不止太阳一经,六经皆有表证。医圣在表证中纳入中风病机概念,就是为此而设。由此,前人所认为“三阳为表,三阴为里”的观点,以及认为太阴病就是单纯的里虚寒证等,都是值得商榷的。凡仲景言中风者,均是里病兼表,而以表证为所急所苦,这就是中风的内涵,因此六经病均有中风,不但有表证,还有很多里病也是中风范畴。在《伤寒论》六经本病的基础上,因外邪侵袭导致的营卫不和、津液涣散等病机转化,称为六经中风。六经中风也是贯穿整个《伤寒论》的一条主线,三阴三阳中风在《伤寒论》各篇中均有明确的条文,《伤寒论》以桂枝汤治中风,而遍见于三阴三阳各篇,所宗乃风无定位,通行六经之义。
中风除了解决里病兼表的问题,同时还揭示了六病痊愈之规律。仲景表里体系源于扁鹊,扁鹊认为,邪气由表入里,层层深入。因此,病愈即相反的过程,里邪出表是病愈机转。《伤寒论·辨脉法》曰:“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即阴病见阳脉说明疾病转愈而恢复,而阳病见阴脉是病情加重。又如仲景对三阴中风的论述。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均为阴病阴脉而逐渐出现阳脉浮脉而愈,然必兼发热微恶风寒之候,仲景不言者,以脉言证也。因此,六经中风脉象的沉浮亦决定了疾病的转归和预后。
《伤寒论》六经病皆有中风,而六经中风又是贯穿伤寒六经病的核心病机,这就是仲景之学术体系特点,是对扁鹊阴阳二分法的一次创新,表证再拆,纳入中风概念,打通表里,使表里关系可以非常圆通地体现出来。伤寒表证入里,里病和表证的联系要用中风法度去解析。《伤寒论》六经统于太阳经,而太阳一经,又统司营卫,由此可知,营卫实为六经辨证之法眼。桂枝汤是《伤寒论》开宗明义第一方,柯韵伯谓“此方为仲景群方之冠,乃滋阴和阳,解肌发汗,调和营卫之第一方”,可谓一语中的。
《伤寒论》所列之经方理法,因证而设,非依经而出,是医圣伤寒定法。《伤寒论》第95条曰:“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卫强营弱,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因为卫行于脉外,而营行于脉中,桂枝汤也就不能单纯理解为一个解表方,其实中风已经就是表里合病了[5]。六经病痊愈之规律即为里邪出表、阴病转阳,这就是经方理法强调“首辨表里、尤重表证”之原因。有表证则立足于“表里观”先解表,无表证则立足于“正邪观”创造机会透邪出表。而阴病转阳的本质即是津液一元论在“正邪观”中的体现,所以经方理法是立足于“津液观”的阴阳规律来辨析“正邪观”所统摄的病传病解路径。不但如此,桂枝汤补津液而解表,作为伤寒第一方,还蕴含了阳法复脉、阴法解肌的经方表证理法,若真能领悟《伤寒杂病论》桂枝汤表证经方理法之本义,则仲景伤寒心法,思过半矣。
3 桂枝汤之阳法复脉
《伤寒论》极其重视表里观,伤寒六经就是表里观统摄之下的水火病证论治。桂枝汤源自《汤液经法》阳旦法,蕴含了阳法复脉之桂甘法与阴法解肌之芍甘法两种不同的证治法度,用以燮理阴阳。相对于复脉法的正虚,解肌法又以邪盛为主,医圣在阴法解肌的基础上衍生出阴旦法度的缘由,在于扩充了阴法解肌应用的适应证,并揭示了伤寒六经病之阴阳二旦两种不同的病解途径。
桂枝汤之阳旦法度,出于《汤液经法》,又源于《黄帝内经》虚邪贼风理论及仲景营卫学说,方中内含复脉法与解肌法阴阳相对。复脉法的核心是顾护阳气而救里,解肌法的核心是顾护津液而解表。桂枝阳法复脉,炙甘草和胃。孙思邈《千金要方》炙甘草汤一云复脉汤,而能复脉的炙甘草汤恰恰是桂枝汤去芍药,就是为了不让芍药羁绊,从而更好地发挥桂枝化阳复脉的功效。桂枝为阳法是复脉的,芍药为阴法是解肌的,这就是桂枝汤所蕴含的治病法度。复脉法以正虚为主,若阳气不足,四肢冰冷疼痛,神志昏昧,脉道不利,脉结代或沉微时,经方常用桂枝、附子这样的阳药为主回复阳气,故言阳法复脉。而当机体津液不足,于表里均不能温煦推动,就可以用到复脉法,复阳而救里。此时最忌用茯苓、白术这一类淡渗利湿药更伤津液,以免犯“虚虚实实”之戒。《伤寒论》第29条曰:“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
《伤寒论》体现医圣阳法复脉的代表方剂是桂枝甘草汤。《伤寒论》第64条曰:“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太阳病本用发汗之法,若汗出过多,内伤心阳,心阳虚衰而失其所主功能,则心中悸动不安;胸中阳气不足,心虚则喜按,故其人常叉手按其心胸,以安心悸”。针对这种临床症状,医圣创阳法复脉法度,用桂枝辛甘性温,入心助阳,炙甘草甘温,益气和中。两药相伍,辛甘化阳,则心阳得复。必须清楚的是,真正的复脉法并不只是辛甘化阳或回阳救逆,因为津血的来源和基础是津液,津液不能温煦的同时,亦必不能濡养,从而容易产生燥结。因此,津液不足自然就不能温煦,必须先补足津液,血脉才能畅通,得以发挥防御和温煦之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伤寒六经体系中,阳法复脉是运用解表法的基础,表实证加入麻黄以开泄腠理,表虚证则加用芍药以顾护津液。因此医圣在麻黄汤中配伍桂甘法以辛甘化阳,以加强发汗解表之功;而在桂枝汤中配伍芍药以酸甘化阴,以顾护津液,行解肌之用。阳法复脉之法在临床中应用极其广泛,经方中体现阳法复脉的方剂还有当归四逆汤、炙甘草汤、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千金桂甘磁石附子复脉汤等。
4 桂枝汤之阴法解肌
在伤寒六经理法中,解表是总则,解表法为汗法,这是《伤寒论》不可更易之法度。汗法以泄津液发汗而为常规解表法,而解肌法是在解表的基础上,再细辨津液虚实,是为存津液而发汗之表证的一种特殊、细腻的治法。实者解表、虚者解肌,医圣分别立麻黄汤与桂枝汤对治。解表法适用于伤寒或溢饮水寒病机;解肌法适用于中风或风水水热病机。相对于复脉法的正虚,解肌法又以邪盛为主。当机体津液绝对不足,于表里均不能温煦推动,在复阳而救里的同时,就可以用到解肌法,即补津液而解表。
宋版《伤寒论》谓:“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桂枝本为解肌”实则是指“桂枝汤本为解肌”,比如原句在《玉函经》中就得到了完整的保留。《玉函经》及《千金翼方》皆谓“桂枝汤本为解肌”。许家栋进一步指出,桂枝汤真正发挥解肌作用的是芍药。而阴液不足,四肢挛急疼痛,烦热惊悸,血府不充,脉象缓弱或细数时,经方常用芍药、葛根、知母等这样的阴药去滋养阴液,故言阴法解肌,如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葛根汤等。
曹颖甫《经方实验录》曰:“盖桂枝汤一方,外证治太阳,内证治太阴”。桂枝汤统治表里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调和营卫,振奋脾阳。肌肉层次在表之皮毛之里,内由中焦脾胃所主。而且,桂枝汤营卫不和之病机,同样可以通过平冲降逆来达到调和营卫之目的。可见,桂枝汤也是调节气机升降与出入之枢机方[6]。因此,桂枝汤之解肌,本与其调和营卫作用密切相关,但其临床应用范围早已突破了这一范畴,只要是津液不足,导致筋脉失养的各种肌肉拘挛、疼痛等,都可以应用。
许家栋明确指出,《伤寒论》桂枝汤解肌,实质是指以桂枝汤中之芍药配生姜为代表的补津液而解表之法门,经方的解肌大法及其方阵,使得经方表证理法不但有麻桂方阵之决泄津血者,亦有芍药葛根等生津解肌者,而让里邪得以出表,阴证得以转阳,也使中风法度这一经方最为重要的病机概念,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对治方案。《伤寒论》体现医圣阴法解肌的代表方剂是芍药甘草汤。芍药酸苦微寒,益阴养血,炙甘草甘温,补中缓急,二药合用,酸甘化阴,阴液恢复,筋脉得养,则挛急自伸。阴法解肌在临床中应用极其广泛,尤其是在血液病、肿瘤等疾病如血小板减少症等突出以肌肤表证为所急所苦时。经方中体现阴法解肌的方剂还有当归芍药散、《千金》诸解肌汤等。医圣在阴法解肌的基础上衍生出阴旦法度的缘由,在于扩充了阴法解肌应用的六经格局。
5 《伤寒论》六经中风病机及病传病解
仲景创立了中风病机概念,打通了疾病的表里关系,使表里不再孤立,也使疾病传变观得以确立。而临床中,《伤寒论》三阴三阳病证各自相对独立,病理上并非有必然的联系,但又不可分割,而临床更多见的是本病经内之传变。因此,伤寒表里传变,不但存在于伤寒六经之间,更是体现于各自的三阴三阳病之中,而并不一定存在各经先后规律性的问题。因此,六经中风才是病传核心,伤寒六经病传立足于津液的输布离合,愈病规律是使里病出表、阴病转阳。中风之阳旦法度不但解决了太阳病病传及六经病里病兼表的问题,而且还揭示了六经里病出表愈病之规律。
伤寒六经病传并非外邪一路传下去,而是受邪之经气变成邪气侵害下一经腑。医圣立半表半里概念的依据是正邪相争的病位,而非阴阳病性,因此伤寒六经病传依次应为太阳、少阳、阳明,然后传太阴、少阴、厥阴,而后循环往复。寒邪入里,首先为皮毛至肺脏本体,再往里就是脾家所主之筋肉,病在此处仍属太阳病。若再往里传便是肝脏,肝脏伤寒,则胆腑燥淫,此病在少阳也。少阳为病,未必有肝胆病症,但胆腑燥淫,可以客犯三焦,致胃腑与脉腑发病。因此,所谓太阳传阳明,往往是少阳传阳明而不自知。《伤寒论》之太阳多寒、阳明多热、少阳则寒热并作,正如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曰:“邪在表则多寒,邪在里则多热,邪在半表半里,则寒热亦半矣”。
《伤寒论》之少阳病诸证,既有本经之胆火上炎、经气不利诸证,又有太阳病之头痛、发热、微恶寒、头汗出,以及阳明病之默默不欲饮食、阳微结、口渴等症状。因此,少阳病的症状,既有太阳之表证,又有阳明之里证,其定位理应当在太阳病与阳明病之间。《黄帝内经》曰:“厥阴之表,名曰少阳”,以此知少阳与厥阴亦并非纯粹之病传关系,厥阴病本应包含少阳在内。因此,不同于少阳为三阳病之半表半里,厥阴乃六经病三阴三阳之半表半里。
然而,临床中的三阴病传又有所不同,因为有伤寒病为直中少阴而发,只因少阴肾经易虚故也。因此,胡希恕又称少阴病为表阴证,其病传规律则依次为少阴、厥阴至太阴,以太阴为至阴故也。与阳病入阴的病传规律不同,阴病传至太阴则为不治。所谓不治乃不太平也,即太阴为杂病之薮、太阴中风为杂病之机。伤寒六经以上二种病传途径依次对应于由伤脾及伤肾引起的传变规律。与仲景所处的时代不同,现代疾病传变多倾向于后者,尤其是绝大部分的血液病、肿瘤等复杂病种,因此,肿瘤血液病的三阴论治或许是突破其辨证论治瓶颈之正确的打开方式。而伤精的概念在《伤寒论》中几乎是空白的,好在医圣在《金匮要略》中予以了必要的补充。桂枝汤本为太阳病调和营卫之代表方,内含酸甘化阴、辛甘化阳配伍,因此又是调和阴阳第一方。而营卫均源于中焦,由此可知,桂枝汤从发汗解肌至调和阴阳这一过程之转化中,太阴中风占中枢地位。因此,医圣用营卫统言气血阴阳,调和营卫就是调和脾胃、调和气血、调和阴阳。
6 结语
《伤寒论》六经体系来源于《汤液经法》而非《黄帝内经》,这就是经方派与医经派各自的渊源[7]。《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对医经与经方分别做了明确的划分。医圣完善了伤寒六经理论,赋予了许多经验之方以理法的高度。伊尹阴阳二旦为经方理法主线,在《汤液经法》中属于中土剂,以此二方和胃气、扶脾阴,以升降阴阳[8]。张仲景继承了这一思路,又与天之六气学说相融合,将阴土剂与阳土剂分别委以主温病与中风之任,迎合其开阴启阳之本义。而且阳旦法度中蕴含阴旦法,揭示了医圣六经病经方理法之重视表里观、津液观、正邪观这一伤寒定理。
迄名医辈出的魏晋南北朝以降,《伤寒杂病论》几经沉浮,蒙尘民间数百年。《千金要方》开篇即引用张湛之语“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孙真人由此发出“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而不传”之叹。经方浩如烟海,其理法之精深,若无医圣伤寒六经体系以及包括中风法度在内的诸多经方理法以统摄,后学者自是难以驾驭。《伤寒论》之魅力,就在于其所建立的六经格局和所蕴含的经方理法可以容纳后来的一切病证,且历久弥新。仲景《伤寒论》不轻易使用合方,这是因为医圣重在昭示经方中蕴含的证治法度,用伤寒经方理法架构疾病不同层面,并非医圣不提倡后学者使用合方。而且《伤寒杂病论》中凡是有明确意义之合方,又皆逃不脱桂枝汤的影子,这就是医圣应用合方之定律,其独到之处,值得后学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