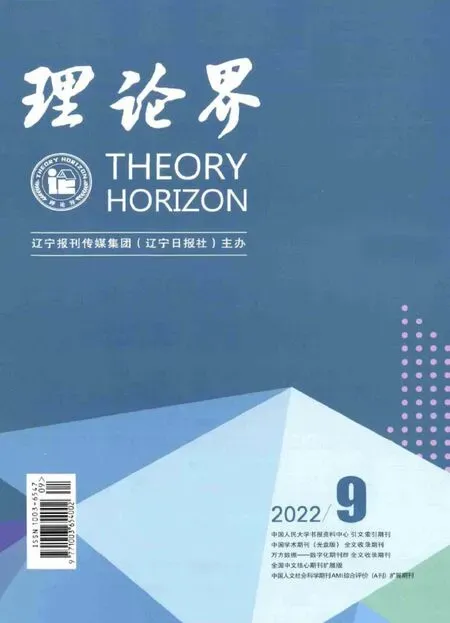杨绳武《文章鼻祖》与早期钟山书院的文学教育
2022-12-24田雨露
田雨露
书院是清代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学者将清代书院分为四个类别:讲求理学为主、博习经史辞章为主、以考课为主、学习西学为主,〔1〕最后一种晚清才出现,清代前中期以前三者为主,其中又以专攻考课者占据绝对地位。博习经史辞章的书院,一般以钟山书院为最早,以晚清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最为典型。
雍正元年(1723),官方“命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教授以广文教”,〔2〕次年两江总督查弼纳于江宁创立钟山书院,雍正手书匾额“敦宠实学”,初步规定了钟山书院的教学方针。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下诏于各省省城创建书院,“各赐帑金千两为营建之费”,〔3〕乾隆元年(1736)规定“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4〕乾隆二年(1737)杨绳武到书院,十四年(1749)离职,在院十三年,以经史训士,奠定了早期钟山书院的教学风格。
一、杨绳武及早期钟山书院的教育理念
杨绳武,字文叔,江苏吴县人,晚明复社领袖杨廷枢之孙,有《古柏轩文集》《文章鼻祖》传世。杨绳武受家风影响,自少能文,又“游尧峰汪钝翁之门,与其仲兄各以文相雄长。”〔5〕同时兼长经学。中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殿试二甲第一名,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居京师,惟汲引士类,一言之善,必扬之”。〔6〕后丁父艰归,遂不出。先主讲浙江敷文书院,乾隆元年(1736)“两江制府庆公欲振兴钟山书院,闻其名,凡三聘,始至江宁”。〔7〕
之所以延聘杨绳武为钟山书院院长,是因其学术观念及教学理念与雍正以来钟山书院的办学风格极为契合。李果称杨绳武:
文叔自少时即寝食六经、《左》《国》《史》《汉》诸书,理与识并到,其发之古文也,闳邃坚苍,抑扬操纵,不可忖度。既成进士,入翰林,郊庙应制及大著作,必推文叔。而又亲见国典庙谟,学益博,才益老,为文益深醇严密,有汉京之风。〔8〕
其学以经史为基,为文追慕两汉。同时杨绳武任教敷文书院时,以实学训士,教学理念与钟山书院契合。袁枚云:“苏州杨文叔先生,掌教吾乡敷文书院,以实学教人。余年十九,即及门焉。”〔9〕时在雍正末。杨绳武有《论文四则》,是在敷文书院的教学记录,其论八股文写作,主张通经为主:
八股者,说经之文也。故义必根经,而取材亦以经为上。此不但习句读、通传注而已,当熟复注疏,旁参经解诸书,会通焉以折其衷,乃为通经,通经而后可以说经也。〔10〕
首先以说经之文定义八股,强调八股文的学术品位,不以功利之具视之;其次,阅读范围大为扩展,不再以程朱传注为限,而是汉唐注疏、宋元经解并重,原则上打破了以程朱为至尊的风习;最后学子当以通经为向,八股文只是通经之后的自然流露,不是最终目的。
杨绳武并非主张放弃宋儒之学,在具体的教学设计上,亦仿照朱子之法。刚入钟山书院时,两江总督庆复问其治理书院之法,杨绳武曰:“上谕备矣!规制则仿《白鹿洞》,读书则仿《分年课程》,肄业则举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而推广上意,使学者近而可循,则自励志、立本、勤学、慎业、交游及经史、诗赋、古今文之源流派别,一一别白而指示之,约十有余条,重以广置书籍、加重膏火数事。”〔11〕所谓“上谕”,指乾隆元年(1736)上谕,指出“书院之制,所以导引人才,广学校所不及。”〔12〕“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从游之士亦必立品勤学,争自濯磨,俾相观而善,庶人材成就,足备朝廷任使,不负教育之意。若仅攻举业,已为儒者末务,况藉为声气之资、游扬之具,内无益于身心,外无补于民物。即降而求文章成名,足希古之立言者,亦不多得,宁养士之初旨耶?”〔13〕故而要求书院的课程设置与日常教学“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也。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14〕
可见,杨绳武的教育理念是对乾隆书院教育思想的贯彻实施,落实到日常的人才教育与课程设置上,就是《钟山书院规约》所云先立志、务品节、穷经学、通史学、论古文源流、论诗赋派别、论制义得失、戒抄袭倩代等八条,兼顾了道德教育、经史教育与文学教育。可以说《钟山书院规约》既是对官方书院教育理念的响应与实施,同时也与杨绳武本人一贯的治学、教学宗旨相契,又与钟山书院的教学传统相合,故而塑造了钟山书院的学术风气,在此指导下,培养了大批人才。
《钟山书院规约》“论古文源流”条云:“今人读《尚书》知尊之为经,而不敢目之为文,愚恐数典而忘祖,故为推原其所自,详则俟与诸生细论焉。”〔15〕“论诗赋派别”条云:“此皆愚之蠡见,俟暇日与诸生细质之。”〔16〕则理念有待于应用到具体的教学之中,《文章鼻祖》就是与学子细论、细质的记录,是杨绳武教育理念的具体实践。
《文章鼻祖》六卷,选文十四篇,包括《尚书》中的《尧典》《禹贡》《洪范》,《国语·齐语》,《左传》中《战于城濮》《战于邲》《战于鄢陵》,《史记》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封禅书》《平准书》,《汉书》中《霍光金日磾传》,《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序》及庾信《哀江南赋并序》,既包括经史著作,又有诗赋,反而没有普通意义上的古文。
如此选目,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量。首先,正如《文章鼻祖》书名所示,所选之书皆文字之祖,这是由发生学角度将所有书写溯源到所选诸书。杨绳武云:“《尚书》,经之祖;《左》《国》,传之祖;《史》《汉》,史之祖。而其中又自有祖之祖,则兹编所标举是也。”〔17〕以《尚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分别为经、传、史之祖,首先是出于时间上的考量。唐代以后五经的排序是《易经》在前,《尚书》次之,因为传统上认为《易经》成于伏羲、文王、孔子之手。但杨绳武认为伏羲所作只是卦画而没有文字,《十翼》虽然是文字著述,但时间上远远晚于《尚书》的《尧典》,因此,选《尚书》而不选《周易》。《左传》《国语》并称内外传,被认为是解释《春秋》的传,其作者传统上认为是孔子同时人左丘明,时间上早于公羊、榖梁。而《史记》《汉书》确立了纪传体史书的基本形式,以后历代正史体例皆效仿二书,故而被认为是史书之祖。因此,所谓“祖”,不仅有时间起源的意义,还有著述形式确立的典范上的考量。而诸子是外编,唐宋八家乃经史之苗裔,故均不入选。
其次,从创作成就着眼,杨绳武曰:“大抵文章之道,未论妍媸,先别高下。”〔18〕分别高下,则据成就最高者进行评价。而“凡人虽善属文,必不能每篇斤两悉称,必有其一生极得意之笔为全力所贯注者。视其全力贯注之处而称等其斤两,然后其人之本领、身分、高下乃定”。〔19〕作者倾注全力的就是创作成就最高者,因此,论文须以作者全力贯注的作品为评价对象。杨绳武认为所选各篇皆作者用心之作,值得仔细分析揣摩。
再次,杨绳武认为“文字有大小,笔力有高下,气味有厚薄”,学者当取法乎上。“所标举皆千古来第一种大文字,笔力最高、气味最厚者,其经营意匠,重规叠矩,千汇万状,犹泰山乔岳之观而建章承明之制也。”〔20〕则其所选之文皆集大成之作,学子得其一点,即受用无穷。
但是,杨绳武所设立的几种选文标准并不能涵盖所有选文,即就诗赋而言,诗自然起源于《诗经》,而不选《诗经》,则不符合起源标准;杨绳武虽然谓《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序》“笔力最高,气味最厚”,但作者不明,很难说是作者心力贯注之作。而在具体的阐释中,杨绳武也并没有阐发出此诗作为集大成之作的典范意义与泽被后人的影响,则视为诗歌之祖,恐不能服众。
《文章鼻祖》包括经传、史书、诗赋,这种设置也是杨绳武入主之前,钟山书院已有的教学课目。沈起元为《文章鼻祖》所作序云:“昔余主钟山书院讲席,以经传、《史》《汉》、诗赋训诸生,刊一日程,各令填注。贵专不贵博,贵少不贵多,以讲明透彻为主,非谓经传、《史》《汉》、诗赋不为遍览遐搜、恰闻广见也。”〔21〕沈起元,字子大,江苏太仓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光禄寺卿,著有《周易孔义集说》等,传见《清史列传》《清史稿》。沈起元雍正十三年(1735)入主钟山书院,乾隆元年(1736)二月离开,在院时间不长,杨绳武继其后掌院。沈起元谓以经传、《史》《汉》、诗赋训士,与《文章鼻祖》的选目正合,可见此书的编著一定意义上是钟山书院的集体结晶,只是与杨绳武本人的文章观念恰好契合。
二、作为万事之祖的《尚书》
南宋以来,通代古文选本层出不穷,明清达到鼎盛,选本呈井喷之势。宋末真德秀《文章正宗》已经初步奠定了基本的选目格局,一般上起《左传》,下至宋代,基本呈现先秦两汉与唐宋八家并重的格局。先秦两汉文一般来源于《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明人评经风气大盛,产生了众多经书评点著作,因此,通代古文选本中又常选入《檀弓》《考工记》。这是明清通代古文选本的一般情况。
《文章鼻祖》完全排除了八家文与历代的单篇独行文章,经史著作之文占据绝对的篇幅,而在经书的选择上,凸显了《尚书》的地位,在《尚书》中更对《尧典》推崇备至,甚而论断说“《尧典》一书,不惟千古文字之祖,实为万理万事万物之祖欤”,可谓石破天惊之论,其详曰:
“克明俊德”节,包罗一部《大学》;“乃命”六节,该贯历代《天官》;“类帝”四段,曲台、两戴之根柢;“询岳”十一段,《周官》六职所权舆;封山浚川,《地理志》之祖;象刑钦恤,《刑法志》之宗;“寅清”者,制《礼》之本;依永和声,作《诗》作《乐》之指要;而“钦”之一字,又为千古帝王治法道法之所由开,而后世儒者讲学主敬之所根本也。〔22〕
首先,杨绳武认为《尧典》是众经之首,同时包罗众经,更是众经之祖。“克明俊德”节由亲睦九族推广到平章百姓,再向外推及万邦,最后达到天下黎民时雍,这种由内而外的结构与《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相似,故杨绳武以为“包罗一部《大学》”。“类帝”四段写各类祭祀,则后仓、戴德、戴圣《礼》记载各类祭典礼节本于此。“询岳”十一段讲设官分职,故谓之“《周官》六职所权舆”。“寅清”指“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言官员日夜敬服其职,乃《礼》之本。“声依永,律和声”一段论文学艺术之起源,《诗》《乐》皆本于内心情志,故谓“作《诗》作《乐》之指要”。又谓书尧舜事而以纪年书之,乃编年体的《春秋》之祖。则《尧典》总三《礼》、《诗》《乐》《春秋》众经,乃众经之祖。
其次,杨绳武认为《尧典》也是史书之所出。以纪年书尧舜事,乃编年体史书之祖。“曰若稽古”先书人再纪事,则后世本纪、列传本于此。“乃命羲和”等述历法节令,为《天官书》之祖;“肇十有二州”叙述地理疆域,乃《地理志》之祖;“象以典刑”以下叙刑罚,则《刑法志》之祖。后《洪范》篇又论“肃时雨若”,乃“历代史家《五行志》俱从此出”。〔23〕在杨绳武看来《尚书》已包含了后世纪事、编年、书、志等史书的各种著述体例与形式。
再次,经史著作中所使用的具体笔法,在杨绳武看来,也是起源于《尧典》。如“文钦安安”用叠字,杨绳武认为《周易》之《卦辞》《系辞》《诗·文王》等经书中用叠字皆本于此。“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四段采用扇对形式,杨绳武认为《礼记·月令》《豳风·七月》逐段相对的体制特征由此而来。
《尧典》亦有史书之笔法,如史书称名之法,《史记·高祖本纪》先书刘季,起事后称沛公,封王后称汉王,即皇帝位后称上,本于《尧典》《舜典》中舜即位前称舜,即位后书帝之法。又如史书合传两人之间过渡转下的写法,亦本于《尧典》《舜典》转接换头之法。
此外,杨绳武还观察到后世集部文章取法于《尧典》者,如“汤汤洪水”用叠字形容水势,后世《海赋》《江赋》《上林》《两都》等赋描写水势用叠字本于此。“命官”一节,“举其名,称其官,或一人专一职,或数人共一官,或论其职业,或奖其劳绩,皆书帝命临之”,这一写法,韩愈《平淮西碑》写分遣诸将,亦仿此。则经、史、集的笔法皆仿效《尧典》。
对《尧典》的分析中,杨绳武指出“钦”字乃通篇骨子,通篇皆以“钦”字为核心,而统合敬、恭、寅、让,皆表示内心的恭敬、庄重,故而认为其“为千古帝王治法道法之所由开,而后世儒者讲学主敬之所根本也”,则进一步统合了内圣、外王之道,故而总结说《尧典》“不惟千古文字之祖,实为万理万事万物之祖”。
从先秦起,历代虽然将五经视为一个相济为用的整体,但又从内容、功能、风格上对各经进行区分。《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24〕这是由内容区分。《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25〕内容与功能皆不相同。韩愈曰:“《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26〕这是从风格进行区分。柳宗元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27〕主张学习六经各有针对性,背后的预设是五经各不相同,所以从中所得亦有异。李翱亦曰:“六经之文不相师。”从表达方式与风格上进行了区分。
宋人有对此反驳者,如陈骙《文则》曰:“六经之道,既曰同归;六经之文,容无异体。《诗》文似《书》,《书》文似《礼》。”〔28〕指出六经文字风格上的相似之处。同时又谓六经创意相师,举《诗·小旻》师《洪范》、《诗·楚茨》师《仪礼·少牢》为例。前者指出六经之文相似,后者指出六经之意相师,所谓“相”,就表示双向的关系,并没有一家压倒其他的倾向。
杨绳武一方面出于推尊经书的意图,建构经为史、文之祖的脉络,同时又极力抬高《尧典》一篇的地位,以之笼罩群经,营造出祖中之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杨绳武的论证,有些具有一定合理性。如谓韩愈《平淮西碑》学习《尧典》,这一点唐人李商隐就已经谈到过。韩愈本人具有强烈的宗经观念,“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对儒家经典的模仿是有意识的,故而建构《尧典》与《平淮西碑》之间的源流关系,有史可据。但是其他的承继关系,比如其他经书对《尧典》的师法,除了局部内容与写作技法的相似之外,其基础建立在时间先后的逻辑上。但《尧典》《舜典》所载之事与其写作年代的先后并无必然关系,更何况《舜典》本身就有后人伪托之处,这就使得依赖《舜典》总结的体式与技法的有效性彻底落空了,那么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师承关系也就无从谈起。
三、以文说经与以文为本的教育体系
上文提到杨绳武论《史记》合传过渡之法,在以《史记》相关篇目为例说明其具体操作之后,有一段方法论介绍:
余多援史例以证经,或疑非说经之体,况《廉颇》《魏其》等传,岂可上例《尧典》?拟非其伦。然余所论者,文也。文章之道,千古一脉,无论大小。〔29〕
杨绳武以《史记》之例来论证《尧典》中由尧事转入舜事的过渡之法,在逻辑上固然可以说是《尧典》影响了《史记》,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是由后以例前,由后世史书、文章中总结出来的体例、技法来反观《尚书》。表述上是由源及流,实际上是由流溯源。这在方法论上产生一种危险,即在价值等级上,经书高于史书,经是永恒的标准,史却有权有变,能够以经证经,以经证史,但不可以史证经。杨绳武对此的回答是:“余所论者,文也。文章之道,千古一脉,无论大小。”〔30〕将经、史一概视为文,那么作为文章,本身就并无大小高低的等次。这里杨绳武剥离了经史作为价值承载的一面,等同为文章,那么意味着经史著作皆可以文来看待。
实际上,《文章鼻祖》的基本批评方法都是文学性的,即以《尧典》为例:
篇中叙述二帝事,处处应照,亦处处分别,繁简相错,长短相间,分合互用,整散兼行,开后人文字详略、起伏、照应、变换无数法门。〔31〕
致力于寻找文章通篇的照应关系和对称结构,特别是对繁简、散整、详略、总分等相反属性的搭配津津乐道,体现鲜明的骈偶思维。
对《禹贡》的评论也首先着眼于通篇章法,“‘禹敷土’三句,一篇纲领,以下逐段照应”,又云“篇首‘禹’字提起,篇末‘禹锡玄圭’,两‘禹’字相为呼应,所谓‘禹贡’也”,因此,赞叹说:“古人文字切题,章法缜密如此。”〔32〕指出本篇章法有两重照应关系,故而缜密。对本篇总体评价说:
自《左》《国》《史》《汉》以来,文章之道未有能出其范围者也。至其中句法、字法,典古奥阃,浓纤雅淡,无不备具……所以为千古文字之祖欤?〔33〕
完全当作一篇古文来读,全部着眼于形式分析,而不及其内容,与汉学家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对《禹贡》的注释解说迥异。
以文评经,明代风气极盛,以孙矿最为有名,有《孙月峰评经》十六卷,四库馆臣颇多批评:“经本不可以文论,苏洵评《孟子》,本属伪书;谢枋得批点《檀弓》,亦非古义。矿乃竟用评阅时文之式,一一标举其字句之法,词意纤仄。钟谭流派,此已兆其先声矣。今以其无门目可归,姑附之《五经总义类》焉。”〔34〕批评集中于两点,一是混淆门类,将经当作文来评论;二是以使用评阅时文之法,标举字法、句法、章法,流于纤佻。《四库全书总目》中对以文评经的著作都由这两个角度提出批评,论郭正域《批点考工记》“是编取《考工记》之文,圈点批评,惟论其章法句法字法,每节后所附注释亦颇浅略,盖为论文而作,不为诂经而作也”,〔35〕论贺贻孙《诗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36〕钱谦益对这种风气的批评态度更为激烈:“侮经之缪,诃《虞书》为俳偶,摘《雅》《颂》为重复,非圣无法,则余姚孙氏矿为之魁。”〔37〕针对的是孙矿对经书的批评,所谓“诃《虞书》为俳偶”指孙矿评《尚书·大禹谟》“儆戒无虞……任贤勿贰”为“亦渐俳”。钱谦益所反对的是居高临下批评经书的态度,非圣侮法,破坏了经书至高无上的形象。
杨绳武评《尚书》与孙矿有类似之处,比如孙矿也认为《尚书》文字最古:“六经之古莫先《易》,然是直庸羲轩画称古尔,其卦爻彖象传文字,自文、周、孔。有文字之古莫《书》若。”〔38〕也极为推崇《尧典》:“前此无文字,有之自此篇始。然篇章句字法皆备,平正奇峭靡不有。”〔39〕杨绳武对自己以文说经的方法具有清醒的自觉,他曾为金沙徐遹言《初学准绳》作序说:
或曰:“圣人之经,圣人之道也,以文章求之,此特识其小耳。”夫文与道岂有二哉?《论语》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集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不曰道而曰文,文即道也。然则徐子之以文说经,徐子之由文见道也,而焉得小之?〔40〕
他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将表示礼教制度的文来代替文章之文,从而赋予文章本身以独立价值,肯定因文见道的正当性。所以虽然主张通经读史,但落脚点还是在文上:
古人穷经,不专为文章,而文章之道亦非经不可。韩子曰:“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柳子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变,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合二子之论文,可以知文章之道非原本于经不可矣。〔41〕
虽然穷经不专为文章,但在杨绳武的设计中,穷经主要是为了文章,而且主要是为了八股文。他论近二十年来文章之病曰:“槁其面目,钝置其心思,开卷索然,了无意味,假先辈之病也;臃肿其支体,痴肥其肠胃,卷卷茫然,不知何语,烂时文之病也。”〔42〕而救治之方在于“培其本而澄其原”,即多读书。“多读书以为根柢,则熟于古人之义理,娴礼古人之法度,而有以得古人之议论,识见、气味、骨力亦因之日出。”〔43〕“有原本,弸中彪外,笃实光辉,乃能矫陋矢靡,以造于清真雅正之域”。〔44〕
所以,杨绳武虽然重视经史,但并不能视为汉学家,其学术宗旨仍是以程朱为依归,他论经学方法曰:“大抵汉儒之学主训诂,宋儒之学主义理,晋、唐以来都承汉学,元、明以后尤尊宋学,博综历代诸家之说,而以宋程、朱诸大儒所尝论定者折衷之,庶不囿乎一隅,亦无疑于歧路。”〔45〕宗旨鲜明。那么,所谓以实学训士并不代表提倡汉学方法,其课程设置的重点与归宿,还是在于科举写作。但这种科举训练并不仅包括八股文,还考虑到了以后学子成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主要表现在诗赋的写作训练上。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科举改革,二场试试帖诗,对于杨绳武任教钟山书院时期的科举考试生态而言,诗赋并非必备的要求。但是杨绳武本人应该比较擅长作赋,李果《杨编修古柏轩集序》谓之“既成进士,入翰林,郊庙应制及大著作,必推文叔。”〔46〕可见其长于此类写作。《长洲县志》又谓其所训士“多入馆阁”,可见其兼顾诗赋的课程设置,确实培养了学生应对馆阁写作的能力,说明了其课程设置确实是以文学教育为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