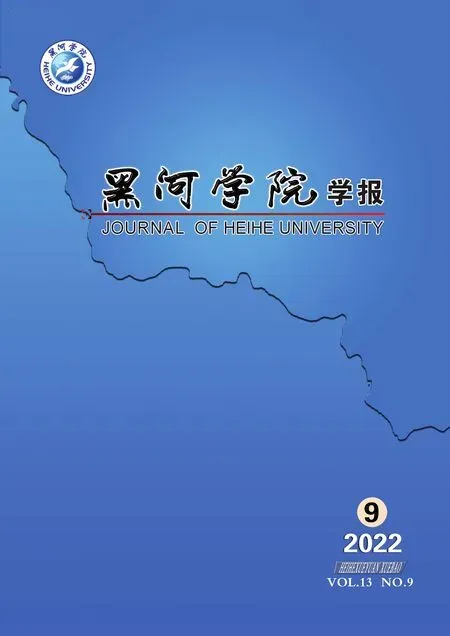“虚假意识”概念再探析
——以社会存在本体论为基点
2022-12-22王向志
王向志 罗 华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对一种思想的在场性进行历时态还原,并不意味着这种还原后的思想就不具备现实的时效性与当代性。一颗糖果经过一层又一层的糖纸包裹,并不意味着揭开它的层层包裹时,它就不再是同一颗糖果了。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问题一经进入人们的视野,就一直是一条极度复杂又无法回避的“鸿沟”,将人类的“观念”与“科学”看上去遥不可及般隔开。难怪英国学者大卫·麦克里兰面对意识形态自经诞生就一直处于“厮杀的战场”中“不可自拔”的情景而感慨道:“意识形态是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最难以掌握的概念。”[1]而在一代又一代不同立场、不同身份的各式各样的理论家对“虚假意识”这一糖果进行包裹之后,处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在世界大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之下的我们,耐心地去揭开糖纸,回到“虚假意识”概念的历史发生学语境中,重探“虚假意识”神秘面纱之下的原貌,就成了理所当然又必不可少的步骤了。
一、“虚假意识”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使用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概念时,多以形容词或词组形式出现,很少直接使用“意识形态”这一名词。虽然这一术语与概念的形式与内容的差别并不妨碍我们对马克思“虚假意识”概念内涵的理解,但就如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社会研究方法时所说过的那样:“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2]在论述马克思的“虚假意识”概念之前,对马克思之后的学者于“虚假意识”概念的思考进行梳理,并非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学理。国内外学者对于“虚假意识”概念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虚假意识”是意识形态的代称,意识形态也就是指“虚假意识”。意识形态家们对思维独立性的崇拜是“虚假意识”产生的来源,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这种现象根植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方式之中。如在前期阿尔都塞的著作那里,一方面,他明确断定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一旦阶级被消灭了,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也就消失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意识形态是意识和无意识的形式,它再现了个人与其生存条件的想象性关系,是一种物质性的客观存在[3]。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从人本主义角度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使人觉得只要需要出现就得被满足的假象和幻想,根源于一种同样虚假的意识。”[4]这种“虚假意识”是真实和虚假的混合物,并不断从精神层面上再生产自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恶的不合理性反而合理、合法地成为了“文化标准”。从这个角度,阿多诺不无悲观地断言,意识形态是“必然的虚假意识”(“notwendig falsches Bewußtsein”)[5]。第二种观点认为,“虚假意识”不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马克思视阈中的“虚假意识”概念有其具体的文本背景与历史、逻辑指向。有学者指出,不能由《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引申出马克思贬斥意识形态的结论。马克思在文中所说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主要是指其“颠倒性”,“虚假意识”的“假”是溯源性的关系概念,而不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评价型概念,颠倒的“虚假意识”是颠倒的经济结构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颠倒的意识其实是对现实社会真实的反应[6]。
可以看到,仅仅只是极其简要地回顾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概念理解史的片段,就已经可以初窥“虚假意识”概念理解的不易。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对“虚假意识”和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溯源,明晰其历史发生学真正内涵,就具有了相当程度上的必要性。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以卢卡奇晚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为基点,尝试探析“虚假意识”概念的发生及其内涵。
晚年卢卡奇在其遗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从发生学与功能论两个角度对意识形态概念作了规定:一是意识形态的产生具有现实直接性。它“首先是人们对现实进行思想加工的形式。”[7]世界上没有脱离“存在”而产生的所谓纯粹的“观念”。归根究底,意识形态是“从那些在社会中采取社会性的行动的人们的此时此地的社会存在中直接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7]二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它的社会职能性。卢卡奇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斗争手段,体现着人类“史前史”阶段的每个社会的社会特征,它在不同社会中具有着职能上的差异,而这也是导致意识形态在历史上出现褒义与贬义两种大相径庭评价的原因所在。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既不因为它是某个个人的思维产物(无论其是否有价值或反价值),也不在于某个思想是否得到普遍传播,而在于某种思想或思想整体是否在社会发展与变革中“执行某种规定得非常确切的社会职能”[7]。
二、“虚假意识”概念理解史再反思
美籍奥地利学者威尔海姆·赖希曾就意识形态问题提出过一个饶有趣味同时引人深思的“意识形态追问”,即在意识形态研究中“需要解释的不是饥饿的人为什么会去偷窃或者罢工;而是需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饥饿的人不去偷窃或者罢工。”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按照常见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解释:这是统治阶级利用其经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炮制出一种“意识”,通过这种“意识”或者说“意识形态”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精神层面的奴役,同时将自己的特殊利益伪装成全部人的普遍利益,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所导致的“虚假意识”。但只是简单地从认识论与功能论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如此的复合定义,难免会落入“独断论”的窠臼,在学理上至少会产生以下问题:首先,既然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在“观念”上的伪装与误导,那么是否可以说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呢?如果不是,那“虚假意识”与科学的、正确的意识或意识形态是否有区别呢?甚至,是否可以就如著名的“曼海姆悖论”一样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某种思想在批判另一种思想观念是意识形态的时候,实质上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意识形态了,因为它代表着一定社会集团和阶级的利益诉求,且缺乏自反性?其次,既然大多数被统治阶级没有起来反抗,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赖希的追问反映了大多数被统治阶级缺乏对共同利益的共同认识,他们可能不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认同),但他们终究没有进行反抗,这说明他们没有形成属于自己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他们的阶级意识。
那么,是否可以就此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在职能作用的过程中具有某种可利用的中立性成分呢?在这一点上,与晚年不同,青年卢卡奇在其成名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高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其作为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部分,而不是首先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他撒下“福音”:无产阶级那具有“虚假意识”可能性的意识形态经过辩证法这一中介环节,可能也必然地上升为科学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在青年卢卡奇那里,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可能虚假也可能不虚假,但“无关紧要”,因为“虚假意识”一经辩证法的改造,必然地就科学化、革命化了。
显然,青年卢卡奇视阈中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中立性,是作为形而上体系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总体意识的那一部分而言的,这在实际上仍然是先验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构图,“物化意识”上升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这一“现有”到“应有”的历史的过程,不是仅仅通过“观念上的改造”就能完成的。从这一角度看,青年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论极易使人误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独断论的成分。某种程度上来说,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丹尼尔·贝尔和雷蒙·阿隆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是滥觞于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曲解之中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固然有其反第二国际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诉求,使他着重强调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法部分,但这一时期他本质上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尤其是他黑格尔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使当时的他不懂得实践的本质——不仅仅是在“观念”或“头脑”的“实践”中,而根本的是在活生生的现实的实践中。意识形态在青年卢卡奇的认知中是一种虚假的、但有用的阶级意识,却往往使人容易得出他视阈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中性的这一结论。在他的笔下,作为“虚假意识”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凭空地”在观念上改造过后就上升为了科学的革命意识,无疑是重新退回到了启蒙主义,退回到了“观念”决定“存在”的“绝对精神”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退回到马克思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那里去了。仿佛受到“虚假意识”压迫的无产阶级一经辩证法的“洗礼”,就顿悟般走向了科学的意识。列宁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丹尼尔·贝尔戏谑地称呼他为“弃暗投明的灰衣主教”,不正是看到了他天才的思想里唯心且独断的成分吗?对此,卢卡奇晚年也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第二版序言”等文本中对他早年的思想作了较为诚恳的学术自我批评,这里不再赘述。但可以看到的是,卢卡奇晚年坚持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提出的“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论断,与他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看到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历史发生根源却仍然将意识形态的功能性置于意识形态概念理解的核心一样,是有他的目的设定在其中的,这也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最为人所诟病之处。
因此,笔者认为,单从认识论上对“虚假意识”概念进行理解,容易走向“独断论”的窠臼;单从功能论与目的论设定上对“虚假意识”概念进行分析,则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抛弃“虚假意识”概念内含的阶级差异性,单独从某一阶级出发先验地寻找其普遍性与合法性的“西西弗斯式陷阱”。二是过度强调意识形态固有的否定性环节和阶级意识、革命意识发生的内在关联,重走历史唯心主义老路,将已经由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解蔽的“虚假意识”的本质重新遮蔽起来,在历史上再次成为一种同义反复的形而上体系。
三、结语
马克思曾对“意识”这个概念做过一个重要的规定:“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人与他的环境的关系决定了人的意识的诞生与发展,人对人的自然环境的关系决定了他最初的自在的意识。而在人的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在人的自为的中介过程中,亦即在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与生产关系进一步扩大的过程中,意识在历史上经过了多次“自在—自为”的否定之否定的环节,自为的意识重新获得自在的外在形式,成为了自在自为的意识。但由于历史已经过去、一定历史时期的认识主体无法直接面对认识客体,自在自为的意识的原初发生在历史上就被遮蔽了,成了谜一样的现象。历史的、自在自为的意识中人为的成分被极度淡化以至近乎消失不见,只留下了形而上的自在的成分。
“虚假意识”不外乎是意识诸形式的一种,人的意识是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存在的产物,“虚假意识”同样如此。在理解“虚假意识”概念时,不应对“虚假意识”概念进行孤立地研究和把握,而是需要将“虚假意识”这一历史现象放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总过程、尤其是放在当下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运行过程中去理解。我们认为,理清“虚假意识”,至少要在“虚假意识”概念界定中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从本体论角度,“虚假意识”来源于人类的一定的社会现实与生活的实践及其决定下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具有溯源意义上的本真性,这也是马克思“虚假意识”批判的根本前提之所在,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与社会关系存在本体论。
其二,从世界观与认识论角度,“虚假意识”狭义上是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家”因各式各样的原因而产生的对社会现实颠倒的、错误的认识,是与科学认识对立的谬误,“虚假意识”也是在这一点上被人们等质于意识形态;从广义上来讲,“虚假意识”既包括作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也包括日常生活意义上的一般的个人的错误的、虚假的认识,以及人类科学认识进程当中被逐渐扬弃的成分等等[8]。而马克思视阈中所指的“虚假意识”概念显然指的是前一种,即阶级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
其三,从功能论与目的论设定角度,在阶级社会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虚假意识”既不停地自我推翻与自我否定,又同时不停地自我维护与自我革新;“虚假意识”既受到支配,它没有历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竖立在其经济基础之上,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并日益实体化的此时此地的发挥其作用,侵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意味着“虚假意识”在功能论与目的论设定的角度上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复杂性,甚至迷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