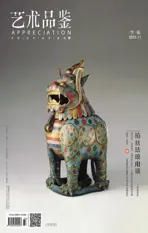从《华山图册》看王履的山水写生观
2022-12-19仪骐嘉湖北美术学院
仪骐嘉(湖北美术学院)
元末明初画家王履以“屏去旧习,意匠就天出之”等全新的观念在生活中实践,他提出“法在华山”的鲜明响亮的写生理论,并以《华山图册》的创作,重新诠释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古老理论的现实意义。王履对于明初的绘画发展,特别是其后不久的浙派绘画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以其旗帜鲜明的写生观与独特的对待前辈传统的态度引导着文人画家的创作。本文将从分析王履《华山图》的风格与特点入手,探讨王履的艺术思想及其艺术史价值与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一、王履与元末明初画坛
“昌黎曾到不能画,摩诘能画不曾到。万秀千奇不出山,秘作深深鬼神奥。海滨野客一何幸,直抵峰尖问苍昊。笑呼二子看我盘于其间,石剑泉绅积翠连天。无乃未了此山之真妙,何如野客负匮揭匣担囊趋,一任山英指为盗,贫儿暴富喜难说,时借长歌写幽抱……”(《图成戏作此自庆》)。
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王履完成《华山图》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写诗庆祝。诗中提及的韩愈(字昌黎)、王维(字摩诘)都是名重千古的文学大家:前者是唐宋古文运动领袖,青年时曾登临华山,华山至今仍有“韩愈投书处”;后者与华山并无关联,但作为“诗画一体”的代表被刻意提出来,显然是别有用心。强调韩愈的“不能画”、王维的“不曾到”,是惋惜,却又在惋惜中带着些得意:惋惜是人之常情,得意则让人们看到了王履的自命不凡。
王履,字安道,号奇翁,别号畸叟、抱独老人,江苏昆山人。大约生于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卒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约六十。《无声诗史》称其“学医于丹溪朱彦修,博极群书,为诗文皆精诣有法,画师夏圭”;《明史》说他“工诗文,兼善绘事”。
元朝享国祚虽只百年,但其山水画坛却因着技法的臻善,而呈现出风格流派林立的局面。依照董其昌的审美观,大抵由提倡书写性线条的以“元四家”为代表的“南宗”一派,和李成、郭熙传派以及南宋院体一派延续而来的“北宗”共分天下。事实上,元初北方直接继承了金代的“李郭”派审美趣味,同时“李郭”派山水因其山重水复的丰富画面及其有着伦理喻示、宾主关系分明的全景构图而深得皇室贵族喜爱,赵孟頫所提倡的“书画本同”“援书入画”的观念至元代后期才形成势不可挡的滔滔洪流。尽管没有非此即彼的强制选择,但是,对当时的画家来说,面对卓有成效的历史遗产,显然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因此,“宗”与“不宗”,不仅是每一位后来者必须要做出的选择,更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困境。在追寻历史渊源的过程中,王履选择了以马远、夏圭为代表的南宋院体。正是这一选择,使得原本拥有文人画家修养的王履,也兼而具备了院体画家的技法。因而可以说,王履是一位以行医为生,具有文人修养的业余画家。
王履对南宋院体的画风有着独到的认识,他在《画楷序》中说:
“余壮年好画,好故求,求故蓄,蓄故多。多而不厌,犹未足也,复摹之习之,以充其所愿欲者……夫画多种也,而山水之画为余珍,画家多人也,而马远、马逵、马麟及二夏珪之作为余珍。何也?以言山水欤,则天文、地理、人事与夫禽虫、草木、器用之属之不能无形者,皆于此乎具,以此事诸画风,斯在下矣。以言五子之作欤,则粗也,而不失于俗,细也,而不流于媚,有清旷超凡之远韵,无猥暗蒙尘之鄙格,图不盈咫,而穷幽极遐之胜已充然矣。”由此可见,王履将马、夏视为绘画的标准有多种原因:首先,王履的绘画风格是通过对马、夏作品长时间的收藏与临摹建立起来的。收藏是附庸风雅的形式之一,附庸风雅是通向绘画之门的快速通道;临摹则是王履登堂入室的安全密钥。其次,通过临摹马、夏作品,王履认识到马、夏有着“粗也不流于俗,细也不流于媚”的高格雅调,在粗细之间能够随心所欲、畅心达意。再次,学习马、夏不仅要有气韵高清的格调,还要拥有以“咫尺之图”表现“穷幽极遐之胜”的高超技术。王履清楚地认识到要超越马、夏,仅凭借摹拟远远不够,还需要“胸储万千丘壑”。恰在此时,历史给了王履一个机会。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七月,王履去关陕一带采药,途经华山。“工诗文、善绘事”的王履不畏艰险,亲身实践了“行万里路”的古训,并“以纸笔自随,遇胜则貌”。在知命之年登临西岳绝顶,面对天下名山、太华奇景,王履不仅用图画来表现,更以文、诗来赞颂。所以,我们今天不仅可以看到根据写生创作的40 幅《华山图》,还有15 首诗及序、记、跋十数篇:通过图册我们可以看到王履的艺术风格、特点;通过诗文则可以了解王履的艺术观念。
二、王履《华山图》的创作
《华山图》以册页的形式绘成,共40 幅,纵34.5cm,横50.5cm,纸本设色。图册深得马、夏“图不盈咫,而穷幽极遐之胜”的妙处。图册的每一幅都描绘华山一处胜景,有奇峰峻岭、灵泉古洞、幽谷险道、祠庙宫观,重在表现华山的峭拔奇险之势,整体呈现出雄健、厚重的风格。
王履完成《华山图册》后,交由其弟立道和侄子绪留存,后归太仓武氏所有,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分别收藏。这套册页在明代便得到画史著录。徐沁《明画录》记载王履:“洪武中登华山绝顶,图其景,尽得天外三峰高奇旷奥之胜。”《无声诗史》评《华山图》“极高奇旷奥之胜”。周天球在《华山图跋语》中称“披图按迹,恍如华山飞堕几上”,可知此画在后世之影响。
《华山图》描绘华山的几十个景点,有奇峰峻岭,如《上方峰》《西峰顶》;有灵泉古洞,如《贺师避静处》;有幽谷险道,如《百尺撞》《千尺撞》《苍龙岭顶》;有祠庙宫观,如《玉泉院》《真武祠》。全套作品意境各殊,丰富多彩,系作者在登攀华山途中写生而成,取法自然,理法咸备,可谓“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以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用笔上,山石、树木轮廓多以富有粗细变化的中锋线条勾勒,或沉着,或圆转,或方折,或凝重,或劲健,或爽利。王履通过笔锋的提按顿挫将山石体积、树干结构表现得很到位,显示出娴熟的技巧。山石的皴法类似范宽的雨点皴、小斧劈皴,少有马、夏的大斧劈皴法,山石转折衔接处加以洒落的苔点统一画面。用墨上,山石、树木轮廓皆以浓重的墨线为主,山石的体面以稀疏且较淡的笔触皴出,山凹处及远处山石则根据画面需要以淡墨皴染出层次。
近景山石留出的大片空白,与繁密的松树形成强烈的疏密虚实对比。用色多以水墨为主,少量作品以青绿完成。青绿是在水墨稿的基础上,以赭石色打底,山石顶部施石青,色彩层次分明,用色沉稳而不失变化。构图虽然带有马、夏“一角、半边”之景的特点,但多数作品偏重于表现近景、中景,且多是对山体局部的描绘,带给观者的是“身在此山中”的感受。细节的描绘如人物、房屋建筑、溪流、道路等描绘亦颇为精彩。画家以秀雅淡逸的江南气格与雄浑峻厚的“关陕之风”相结合,营造出“茂密而不繁”、厚重而不失清润的风格。可以说,王履既准确地把握住华山奇险、秀绝的特点,又得华山雄浑大气的天然意态。
从《华山图》整体来看,王履将马、夏的笔墨改造为更具有厚重雄浑的味道的风格,从而使作品的风格趣味在整体上有类于北宋的范宽。对此,台湾学者石守谦认为:“《华山图》中除了明显的使用来自马、夏的方劲笔法构成的形象外,整体营造的却是类似范宽雄浑峻厚山体的气势,而造成与马、夏完全不同的表现力量。《华山图》与南宋渊源之间的差异,当然多少与华山本身的奇险有关,但更重要的似乎在于他意识到将范宽风格掺入表现的需要。……他所说的'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实亦出自范宽'与其师人不若师其造化'的名句,此即透露出其以范宽之雄峻表现来改换马、夏山水风格的意图。”
王履对外在之“形”与内含之“意”的思考,可以从他的《重为华山图序》中看到:“画虽状形,主乎意。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虽然,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画物欲似物,岂可不识其面?古之人名世果得于暗中摸索耶?彼务于转摹者,多以纸素之识是足,而不之外,故愈远愈讹,形尚失之,况意?苟非识华山之形,我岂能图耶?即图矣,意犹未满,由是存乎静室,存乎行路,存乎床枕……怵然而作曰:得之矣夫……但知法在华山。”
在王履看来,绘画不仅仅要描绘事物之表象,更要表现事物的内在精神,亦即“寓意于物”。“留意于物”仅仅是关注物象外在形体,“寓意于物”则是将“我”与物象融为一体,物象要为“我”服务。所以“状形”的目的是得己“意”——借助华山之形表达自己。犹如重生的哪吒借助莲藕化身成形,肉身虽是莲藕,灵魂却还是哪吒自己的。苦苦思索之后的王履悟到“法在华山”,或者说华山之于王履就是依据,这种依据不仅在技法上为王履提供支援,也是王履创作灵感的不竭之源。王履找到了可以承载其绘画灵魂的肉身,这肉身便是以华山为依托成形的。当然,这种依据是很宽泛的,唐诗、宋词、元曲、书法、音乐……同属于一个文脉的任何分支或是滋养文化成长的任何土壤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画家创作的依据。而处于“宗与不宗”尴尬境地中的王履寻到了华山。
将自然造化作为山水画创作的起点,使绘画中对“形”与“意”的追求落实在华山,即自然造化之中,而不是在古人的“家数”里。古人不正是由“造化”所得的“心源”吗?所以,师“造化”乃是历代大师成功的催化剂。
三、王履的山水写生观
晚明黄汝亨给姚元素《黄山记》作序:“我辈看名山,如看美人,颦笑不同情,修约不同体,坐卧徙倚不同境,其状千变。”
从晚唐开始,山水画中的“写生”渐成潮流。首先,“写生”一词在绘画的文言语境中是作为花鸟画的别称而存在的,其含义有三:一是写物象之生机、生意;二是在纵横交错的点线中见出画者的精神状态;三即本土既有且流行当代的西方式对景、对物写生。苏轼《书鄢陵王方薄所画折枝二首》中有“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之句,在此,苏轼用“写生”与“传神”二词来称赞边鸾、赵昌两位花鸟画家的长处,可见,写生与传神是对等的,或曰:写生是为传神,写生即目的。宋人花鸟作品中多有某某画家“写生”的款识。“写生”的内涵不独为花鸟画所有,以山水为首的绘画大宗更是难逃“写生”的统摄。至宋元,“写生”成为山水画家创作的必要手段和途径。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看山要远取其势,近取其质,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画山要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郭氏以“如笑”“如滴”“如妆”“如睡”等种种欣赏美人的要求来看四季山川之美,人即是山,山即是人,可谓得“写生”真髓。荆浩在太行山携笔写就了数万本松树方得其“真”。黄公望“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摹写记之”。王履“以纸笔自随,遇胜则貌”。画史上卓有成就的大家无不因“造化”而得“心源”。
“写生”不只是得“心源”的一种手段,亦是画家观照自我、追求与天地齐一的终极目的。
画家的艺术演变历程总有主、客两方面的作用,王履亦不例外。主观上,王履拥有三十年的摹古功底,长期的临摹使王履掌握了较为娴熟、高超的技巧,而扎实的技巧又使王履可以在古人与自然之间自由穿梭,写生,便成了王履在古人和自然之间探究的别一番境地。王履不仅取法马远、夏圭,还上追北宋范宽、郭熙诸家,集众人所长。从客观上来看,他随身携带纸笔,见有奇景就以写生的方式记录下来,为他创作《华山图》积累了大量素材;另外,马、夏苍劲、秀润的斧劈皴法与华山的爽利、刚硬的岩石有着外在形似的关联,王履在华山找到了古人技法的来源。在学画的三十年中,王履把主要精力放在临摹古人上,对于自然造化不甚关注。所以,登太华后,就被它的奇秀之美深深感染:“余学画余三十年,不过纸绢者辗转相承,指为某家数,剽其一二以袭夫画者之名,安知纸绢之外有神化如此者。”
登太华之前,王履所见多是烟波微茫、浩渺无边的湖山景致,江南山川多平远,少见奇险峭拔,华山给以王履“极视听之娱”的感官刺激。在审美趣味上,王履崇尚大气磅礴之美,雄健有力的马、夏风格成为首选,体现在他的画面上,是豪爽、劲健、遒美。当这种审美落实到现实当中——以华山作为依据及表现对象就不难理解,有了现实依据,大胆扬弃马、夏技法中浮薄的大斧劈皴法,采用点皴来强调山石结构,留出大片空白使山石变得整体统一。因此,王履依据华山创造出更精准的绘画语言,构图立意强调现场感自然变得顺理成章。他后来感叹说:“尝见石刻本华山图,以为形似不过如此,及既登而还重见于姜月心家(石刻本)不觉失笑。”
当然凭借“目师华山”是不足以“尽其形、尽其色”的,还需要“心师华山”:把握华山内在精神。在由“造化”得“心源”这一层面上,王履的“法在华山”和前辈赵孟頫的“到处云山是我师”、后辈董其昌的“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至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的箴言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已经“立于前人之外”的王履,对于揶揄他不合“家数”的人,自谦地说,“只可自怡,不堪持赠”。
王履将精湛的技巧与自然造化完美融合,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华山图》。
华山不仅是王履从中悟出全新绘画理念的依据,也是整合“博极群书”后的修养、三十年的临摹功底,及“以天地为师”理论观念的依据,身临其境的深切体会,使得王履的华山之行收获了40 幅绘画作品及上百篇诗文,以至于不免有“贫儿暴富”一般等惊喜。
唯其如此,认为自己的绘画有“天出之妙或不为诸家畦径所束”的王履,才能自信地去惋惜韩愈的“不能画”,王维的“不曾到”,敢于“笑呼二子看我盘于其间”。
四、结语
王履以一个业余文人画家的身份旁观元末明初的画坛时势,以非职业画家的心态看待前代的一个个“家数”。借助华山认识到“摹拟”与“写生”都不过是学习的手段:有了前者可以获得古人技法,通过后者可以找到完整的自己。有了这二者,王履才可在“安敢故背前人”与“不能不立于前人之外”的矛盾中创立自己的“家数”。《华山图》为我们呈现出元明之交独特的绘画风貌,开启了明初新的绘画风格之门。王履以“法在华山”重新诠释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古老理论的现实意义,成为一位在创作与理论上均有很高建树的画家。作为依据之所在的华山,对王履来说,是“法”亦是“道”,是“手段”亦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