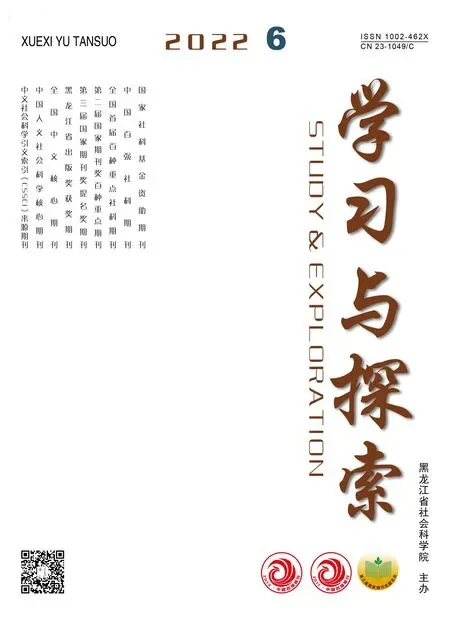近代英文报刊上的“中国觉醒论”
2022-12-18童杰,胡刚
童 杰,胡 刚
(1.宁波大学 浙东文化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211;2.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 教研部,杭州 311121)
今天,在西方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威胁论”。这种论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世纪后期英文报刊上开始出现的“中国觉醒论”。“中国觉醒论”在近代(1840—1911)英文报刊上的一再重现,不仅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折射出近代中国艰难坎坷的历史进程。
一、英国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与“中国觉醒论”的出现
英国是大西洋北部的岛国,一直处于古代欧洲文明的边缘。中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等人曾在中国长期生活过,并且在著作中盛赞中国的繁荣、富饶[1]。而英国人则根据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在想象中漫游中国。1357年左右,一个自称生长于英国圣奥尔本(St. Albans)的“曼德维尔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在游记中说曾到过“美丽富庶、商贾云集、伟大强盛”的中国,并且加入了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交战[2]。由此可见,这个“曼德维尔爵士”并不知道此时元朝(1271—1368)早已完成了统一大业,而依然以为中国还处于元与南宋的对峙之中。因此,这部《曼德维尔爵士游记》是根据其他资料编造出来的,其作者根本没有到过中国。更加重要的是,现代多数学者认为,所谓的“曼德维尔爵士”是虚构出来的,此书作者应该不是英国人。(1)① 参见I. M. Higgins, Writing East: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虽然《曼德维尔爵士游记》并非真实的历史著作,但却是一部文学佳作,18世纪被誉为“英国散文之父”,20世纪中后期被定位为“幻想文学”(Imaginative Literature)的代表作[3],在英国被广泛阅读。《曼德维尔爵士游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的向往之情。
16世纪后,葡萄牙人率先经由绕过非洲的新航路到达中国沿海。1553年,葡萄牙人获得中国政府的允许,入居澳门。随后,来自欧洲大陆的天主教传教士通过澳门陆续进入中国,并且将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回欧洲。英国在16世纪前半期进行了宗教改革,脱离了罗马天主教,改奉新教。其结果是,在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中,几乎没有英国人。这样,英国“总体上一直通过邻国辗转获得的材料与信息了解中国的情况”[4]。虽然英国人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资料都是间接的,但这也使他们有机会对这些资料进行比较冷静、严肃的审视,并且不时地发出一些对中国的批判之声。17—18世纪,欧洲各国刮起了推崇中国的“中国风”。在英国,“第一个受到孔子思想影响的英国文人”[5]就是政治家约翰·坦普尔(William Temple,1628—1699),他称赞孔子是“最博学、最睿智、最高尚的中国人”[6]。不过,“中国风”在英国延续的时间较短,17世纪后期是高潮,随后就衰落了。而且与欧洲大陆相比,即使在高潮时期,也不乏批评之声。针对约翰·坦普尔的尊孔言论,英国语言学家威廉·诺顿(William Wotton, 1666—1727)在1694年出版的著作中就认为,孔子学说“只不过是汇集了一些语无伦次的道德说教,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稍具生活经验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些道理”[7]。英国作家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在1719年出版的名作《鲁滨逊漂流记》中写道:“尽管中国人吹嘘自己非常勤劳,但实际上,那里农业凋敝,经济落后,生活悲惨”,“中国人无比自傲,当然,能够超越这种自傲的,就是他们的贫穷了,此外就是他们的惨状了”[8]。
16世纪末,英国人试图与中国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17世纪初,一些英国人经由日本、东南亚、印度,在中国沿海活动过[9]。1637年,由威德尔船长(John Weddell)率领的船队从英国来到广东沿海,这是最早从英国直接抵达中国沿海的英国船只。威德尔在虎门和明朝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样,中英两国的首次官方交往就无果而终,并使后来的中英关系蒙上了阴影[10]。此后,虽然英国人一再努力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但由于葡萄牙人的阻挠以及中国明清鼎革的动荡,英国人的对华贸易一直不顺。直到1715年,才开始在广州设立固定的商馆[11]。从此开始,英国对华贸易逐渐兴旺起来。
17世纪后期,英国打败荷兰。1754—1763年,英国又在“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成为海上霸主。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历史大幕。快速崛起的英国,迫切需要打开中国的市场。而清政府则从1757年开始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不仅指定英国人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而且还越来越严格地限制他们的活动。为了扩大在中国的贸易,英国政府先后派出马戛尔尼使团(1793)、阿美士德使团(1816)出使中国,但都无功而返。阿美士德使团回国时,途经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拜访了被流放的拿破仑[12]463。据说,拿破仑就是在会见这批使团成员时,讲述了如下这段名言:“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就让它沉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撼世界。”[13]26拿破仑这段话的本意是提醒英国人不要轻易对中国发动军事侵略。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通过在中国内地的广泛旅行,得出中国文明正在退步的总体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蒙古征服中国之前,“中国文明达到了顶峰,当时的中国人无疑比蒙古征服者及同时代的欧洲人更为文明,但自从被满人征服之后,中国在过去的150年里并没有什么进步,相反,还出现了退步”[14]。1800年前后,英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可谓好坏参半。1816年来华的阿美士德使团,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个使团的第三号人物埃利斯(Henry Ellis)在出使中国的日记中写道:使团成员中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应被归入像欧洲那样的文明国家”,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属于同一类型”[12]197。并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的”“落后的”“半开化的”国家[15]。既然中国长期停滞不前,那么就要设法将其“唤醒”。这样,“中国觉醒论”就呼之欲出了。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7月29日,美国出版的《普罗维登斯晚间先驱报》(ProvidenceEveningHerald)写道,这场战争将使中国“从几百年的沉睡中觉醒过来”[13]26。这样,“唤醒中国”(或“使中国觉醒”)就成了英国对华侵略的美妙托辞。1842年,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1844年,英国侵略军首领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返回英国,他于12月在曼彻斯特演讲时说道:“中国人妄自尊大、傲迈自满,而且一直沉睡于这样的迷梦之中不可自拔,因此,我早就认为,而且始终坚信,要使中国人从这样的迷梦中觉醒过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战争,而不是争辩、说理。看看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就会知道战争是完全值得的。”[16]美国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认为,“中国觉醒论”是由曾纪泽“于1887年在伦敦首次被表达出来”的[17]。现在看来,费约翰并不正确。至少在1844年,璞鼎查已经在伦敦出版的《泰晤士报》上使用这个词汇了。
清政府虽然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但并没有痛定思痛,更不愿意直面全球化的猛烈冲击,而是闭目塞听,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幻觉中,“大有雨过忘雷之意”[18]。这样,西方人所期待的“中国觉醒”并没有发生。因此,当太平天国运动于1851年爆发之后,西方人就将希望寄托在太平军身上。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大有推翻清朝之势。1853年11月,英国伦敦出版的《旁观者》(Spectator)杂志刊发了一篇关于中国问题的长文,文中写道:明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王朝,清朝则是一个封闭排外的王朝,现在太平军正在不断取得胜利,因此,“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中华帝国正从长期的深睡中觉醒过来。中国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定将成为地球上众多商业王国中的重要一员”[19]。
不幸的是,太平天国并不像西方人所渴望的那样是个基督教政权,更加重要的是,1864年,这个政权就被镇压了。这样,西方人寄托在太平军身上的“中国觉醒论”也就成了泡影。但太平天国灭亡后20多年,“中国觉醒”又重新出现在英国的报刊上。所不同的是,这次的“中国觉醒”并不是由西方人一厢情愿提出来的,而是由中国人以充满自信的笔墨亲自表达出来的。
二、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及其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中国的内乱外患不断加剧,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朝廷重臣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再继续因循守旧、拒绝变革,那么中国就会面临“败亡灭绝”之危险[20],于是,决心“自图振兴”[21]。从1861年开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兴起。1887年1月,清朝外交官、一等侯爵曾纪泽(1839—1890)以“曾侯”(Marquis Tseng)之名,在英国伦敦的《亚洲季刊》(AsiaticQuarterly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theSleepandtheAwakening)的文章。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30多岁“试取泰西字母切音之法,辨其出入而观其会通”[22],开始自学英语,1878年奉旨出使英国和法国。对于《中国先睡后醒论》的写作时间及缘起,《亚洲季刊》的创始人迪米特维斯·鲍尔吉(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1853—1928)有过这样的记载:1886年,曾纪泽奉命回国,“在离开伦敦之前,曾纪泽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就中国问题写篇文章,以此来表达对英国的惜别之情。这对我来说,是非常荣幸的。他让马格里先生根据他的意思,起草了恢宏之作《中国先睡后醒论》”[23]431。这里所说的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是英国人,与1793年来到中国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是同一个家族。马格里本来是个医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随英军来到中国,与太平军交战过,又参与洋务运动,后因受李鸿章赏识而被推荐到中国驻英国使馆工作。由此可知,《中国先睡后醒论》是马格里起草的。曾纪泽本人于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九日(1886年3月24日)获知转补兵部左侍郎,随后启程赴各国告别,8月27日从德国回到伦敦,9月8日离开英国,取道法国,11月回到上海[24]。迪米特维斯·鲍尔吉说,《中国先睡后醒论》是曾纪泽“在离开伦敦之前”撰写的,可见,此文的写作时间应是在1886年8月27日至9月8日之间。但曾纪泽本人在日记中并没有记载此事。
《中国先睡后醒论》于1887年1月在伦敦刊出时,曾纪泽刚回到北京。大概两个月后,曾纪泽收到由马格里寄来的这一期《亚洲季刊》。1887年3月3日,曾纪泽在北京用英文给马格里写信说:“已经收到了《亚洲季刊》,以及《泰晤士报》的剪报”,并且为《中国先睡后醒论》深受读者关注而感到高兴。曾纪泽接着写道:“此文措辞经过了仔细的斟酌推敲,思想表达既简洁又有说服力。这篇文章以如此优美的文采被刊登出来,这使我非常高兴”,“我注意到,《泰晤士报》的评论认为,此文反映了我离开伦敦前往北京期间的观点。你使读者认为,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是我个人的观点。你这样做非常正确。我还注意到,许多英国的主流报刊都引导读者去关注这个问题,而且,这篇文章还要被译成法文和德文。我从你的来信中获悉,这篇文章在伦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23]由此可见,《中国先睡后醒论》是由马格里润笔修饰的。曾纪泽提到的“《泰晤士报》的剪报”,无疑是指《泰晤士报》1886年12月29日发表的文章《曾侯向欧洲道别》(TheMarquisTseng’sFarewelltoEurope),因为文章中有这样的内容:“曾侯在撰写此文时,已卸下驻英公使等官职,同时还没有抵达中国接任新官职”,因此,“曾侯在从伦敦前往中国的途中,无官一身轻,以私人身份撰写了此文,文章只表达他个人观点”[25]5。《曾侯向欧洲道别》一文没有署名,但根据曾纪泽的信件,该文作者应当就是马格里。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汉译全文在国内的最早传播,则已是20世纪初的事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上海《格致新报》馆铅印出版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全本,其初编《曾论书后》之后,附有汉译《中国先睡后醒论》全文,译述者署为‘古沪颜咏经口译、娄东袁竹一笔述’”[26]。但考诸史实,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上海出版的《申报》在1887年6月14日和15日就连载刊发了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中译文,而且,翻译者同样署为“古沪颜咏经口译,娄东袁竹一笔述”。
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的中文标题,其实是颜咏经、袁竹一翻译的。尽管译者强调他们在翻译时“以悉遵本文意义、不加改窜为主”[27],但实际上,如果与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英文原文进行比较的话,则可发现,颜咏经和袁竹一的这篇译作不仅文采不足,甚至还有许多误译,因此,该译文并不能完全反映曾纪泽的思想,更不能代表曾纪泽的写作水平。有鉴于此,本文仅引用其中准确无误的译文。
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写道,在欧洲人看来,由于“中国古昔之盛,与近今之衰,判若霄壤”,因而“遽谓中国即一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而曾纪泽则认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更加重要的是,曾纪泽还自豪地向西方人宣告:中国已经“觉醒”!他接着分析了中国从酣睡到觉醒的具体过程。曾纪泽认为,中国过去确实曾自我满足,固步不前,“沉酣入梦”。但鸦片战争“略已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只不过此时的中国依然未能“全醒”。在曾纪泽看来,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焦及眉毛”,于是“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于是“忽然觉醒”。曾纪泽介绍了由李鸿章等人领导的洋务运动,包括“用其全力,整顿海防”,并且还将准备建立工厂、开采矿藏、引进铁路,等等。曾纪泽因此信心十足地写道,现在的中国“固与五年前大相悬殊也”,“今如他国再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之祸”!颜咏经等人所译的“庚申之祸”,在曾纪泽的原文中是eventful year,指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事件。
曾纪泽坚信中国已经醒来,因此,他在文中非常认真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时俱醒”的中国人,会不会凭借“觉醒”之后的巨大力量去向西方列强复仇?颜咏经等人将这段话译为:“中国有三万万人,如一时俱醒,而自负其力,其作事得无碍无中西之和局否?或记昔时之屡败,今骤得大力,得无侵伐他国否?”曾纪泽的回答是:“决无其事!”他的理由是:“盖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有史书可证。嗣后亦决无借端挑衅、拓土域外之思。”[28]34接着,曾纪泽以大段文字来论证“觉醒”后的中国是不会“侵伐他国”的。
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刊登在1887年1月出版的《亚洲季刊》上。《亚洲季刊》主编迪米特维斯·鲍尔吉对曾纪泽的这篇文章显然非常重视,并且进行了一些前期宣传策划。因为在这一期的《亚洲季刊》问世之前,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就已经在其他报刊上披露出来了。1886年12月29日,曾纪泽的好友马格里在《泰晤士报》上匿名发表了《曾侯向欧洲道别》一文。虽然马格里在这篇文章中强调说,《中国先睡后醒论》是曾纪泽在“无官一身轻”的背景下“以私人身份撰写”的,但他同时也指出,由于“中国是亚洲的三个大国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的大国之一”,而曾纪泽又将在中国身居要职,所以,“此文值得研究外国政治的学者仔细研读”[25]5。次日出版的《每日电讯报》(TheDailyTelegraph)也刊登了曾纪泽的文章[29]。《曼彻斯特卫报》(TheManchesterGuardian)还就此发表了一篇社评,指出:曾纪泽并没有说《中国先睡后醒论》是一篇清朝政府的正式文告,“但实际上它就是政府文告”[30]。这样,在曾纪泽的这篇文章刊出之前,许多人就已翘首以待了。《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后,英国的《伦敦与中国快报》(LondonandChinaExpress)等报刊进行了转载或介绍。娱乐杂志《大众滑稽》(FunnyFolks)还以“中国先睡后醒论”为标题,以系列漫画的形式,描绘了在中国出现的一些西方新事物[31]。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曾纪泽的文章也受到了重视。《纽约时报》在1887年2月18日发表的文章说,曾纪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将对中国的未来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位中国重臣所表达的观点、所发表的意见,应当受到美国的关注”;曾纪泽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未来目标及政策的宣言”,文中所涉及的问题,都与美国息息相关[32]。1887年3月8日,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特地给远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柏夏(Thomas F. Bayard)写了一封信,不仅概括了曾纪泽这篇文章的要点,而且还抄录了全文。同年5月3日,柏夏给田贝回信说,他因为曾纪泽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中美关系而感到“非常鼓舞”[33]196-197,211。
在中国,尽管曾纪泽主持翻译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文版没有在社会上流传,但是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却很快出现在中国沿海外国人创办的一些报刊上。“《香港德臣报》(DailyPressofHongkong)和《孖剌报》(TheChinaMail)、上海的《北华捷报》(TheNorthChinaHerald),天津的《中国时报》(TheChinaTimes)相继转载,在旅华的外人间,传诵一时,争以先睹为快。”(2)李恩涵:《外交家曾纪泽1839—1890》,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页。不过,李恩涵所说的香港报纸名称有误。The China Mail的中文名称是《德臣报》《德臣西报》或《德臣西字报》,1845年创刊。Hong Kong Daily Press的中文名字是《孖剌西报》,1857年开始发行。我们在香港公共图书馆所保存的Hong Kong Daily Press上,就可以看到汉字《孖剌西报》。还可参见陈鸣:《香港报业史稿(1841—1911)》,香港:华光报业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8、48页。其中,最早转载曾纪泽英文原文的是《德臣西字报》(TheChinaMail),时间是1887年2月8日。2月16日,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这样,那些能够阅读英文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因此而“先睹为快”了[28]37。
对于曾纪泽的这篇文章,英文报刊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高度认同曾纪泽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觉醒”。英国《旁观者》的一篇文章甚至说:“曾纪泽此文优雅的魅力,正是中国复兴的标志。”[34]《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位通讯记者写道:“总的来说,中国人是非常敏捷、机智、聪明的,同时,中国的统治者也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教训,深知过去的排外行为,不仅是无益的,而且还会对当今产生危害。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中国走上了进步之路,因此,中国屹立于世界各国之林,也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中国的进步可能不快,但中国必将进步”[35]。一个署名为“北京居民”(a resident in Peking)的作者,还在伦敦出版的《当代评论》(TheContemporary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此文对清王朝大加褒扬,并且多次引述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文章在分析了亚洲几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后写道:“也许,‘先睡后醒’一词用来指日本可能比用来指中国更加适合。但是,中国也正在觉醒。”文章同时向西方人指出,为了适应“觉醒”的中国,“西方政治家有责任去熟悉中国的悠久历史及丰富资源”[36]。
当然,也有许多人并不认同曾纪泽的观点。《北华捷报》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中国先睡后醒论》宣称:中国开始了迈向进步的航程,中国已经强大,并且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强大。如果此文作者真的是曾纪泽的话,那么,他的这番言论,显然是有其政治目的的。”[37]一位匿名的通讯记者,对曾纪泽关于圆明园被烧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这些论述表明,“曾侯没有思考过圆明园被烧的教训是什么”。同时,这个作者也不认可曾纪泽关于中国从来不侵略别国的说法[38]。针对曾纪泽的这篇文章,《北华捷报》的一篇评论尖锐地指出:“中国目前吏治腐败,海陆防务堪忧,正在遭受诸多天灾人祸的折磨,而且,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还将继续遭受这种折磨。但在曾侯看来,他的国家似乎是一个重获生机、革新去弊的泱泱大国。曾侯的宏论,其实只不过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自吹自擂,在当今这个时代的最新表现形式而已”;“如果曾侯真的陶醉于他在文章中所宣称的那种幻觉之中的话,那么,这对于他本人以及他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坏事。”[39]
曾纪泽的文章发表在《亚洲季刊》1887年第1期上。在随后出版的该刊第2期上,刊发了两篇长文,都对曾纪泽关于中国已经“觉醒”的论断提出相反意见。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曾经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的英国外交官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他虽然觉得曾纪泽的文章“非常值得重视”,但并不认为中国真的像曾纪泽所说的那样已经从过去的失败中获取了教训。阿礼国写道:“曾侯以为,在僵尸般的中华帝国的枯骨里,现在已经焕发出激荡的活力,而且,这种强大、旺盛的活力,必将足以使政府恢复元气、再度振作,并且获得自强不息的灵魂;对于中国来说,为了应对目前这种巨大的变局,这种自强不息的灵魂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中国的现状,真的如曾侯所说的那样吗?”“中国真的已经觉醒了吗?”[40]另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在中国已生活多年”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雒魏林(Willaim Lockhart,1811—1896)。(3)李恩涵在《外交家曾纪泽1839—1890》中(第275页),将Willaim Lockhart的名字音译为“罗克赫特”。其实,此人的中文名字是“雒魏林”。参见龚缨晏:《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125页。雒魏林指出,“曾侯承认中国政府犯过许多错误,但曾侯并没有认识到这样的事实:中国所遭遇的诸多祸难,并不是仅仅由于‘沉睡’造成的,而是由于它的狂妄自大”[41]。
除了一些西方人外,也有一些中国人对曾纪泽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广东启蒙思想家何启(字沃生,1858—1914)。他在《德臣西字报》上读到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的英文原文后,以Sinensis(意为“中国人”,胡礼垣将其译为“华士”)为笔名,投书《德臣西字报》,认为曾纪泽的这篇文章“完全是因果颠倒,混淆本末”[42]。1887年3月21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写信给美国国务卿柏夏,专门介绍了这篇署名Sinensis的英文文章,并且认为,在批评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的诸多文章中,“这是最重要的一篇”[33]203-205。同年农历五月,另一位广东启蒙思想家胡礼垣(字翼南,1847—1916)将何启的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并且“阐发之,间亦添以己意,涉以喻言”[43]70,此译文即著名的《曾论书后》。由于《曾论书后》是经何启本人审阅过的,所以这篇译文代表了何启本人的思想及文字。
曾纪泽认为中国已经觉醒。何启则反问:“中国果醒矣乎?”曾纪泽列举出洋务派“整顿海防”之类的举措,作为中国已经“觉醒”的证据。但何启认为,这些举措其实是“以后为先,以本为末”。他写道:“以今日中国之所为也如此,而其所欲也则又如彼,是无异睡中之梦,梦中之梦也。侯固曰中国而今既明明奋发有为矣,既明明实力举行矣。吾以此等奋发举行者,如酣睡之人,或被魔而梦里张拳,或托大而梦中伸脚耳。”更加重要的是,何启根本不同意用“睡”或“醒”来比喻国家,因为“今夫人睡已则醒,醒已则睡,非睡则醒,非醒则睡,如阴阳之倚伏,若寒暑之代更。而国则不然,有一睡而不能复醒者,有一醒而不致复睡者”,因此,“睡与醒之喻,决不足以明一国也。”[43]69-102
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在英国发表后,在西方报刊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部分人赞同曾纪泽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觉醒”。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觉醒”。当然,要证明两种观点孰对孰错,不能靠笔墨,而只能靠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此,曾纪泽也非常清楚。他在写给马格里的私人信件中说道:“正如你所说的,我也注意到,在西方,对于中国的良好评价正在形成。我希望中国能够不断进步,这样,西方人的这些良好评价就可以得到证明了。”[23]435不幸的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曾纪泽过于乐观了。《中国先睡后醒论》问世后,清朝不仅没有像曾纪泽所期盼的那样“不断进步”,而是快速走向了灭亡。
三、清末“新政”与“中国觉醒”
在1887年发表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曾纪泽满怀自信地宣称:现在的中国“固与五年前大相悬殊也”,“今如他国再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之祸”!但《中国先睡后醒论》刊出后7年,甲午战争(1894)爆发,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于次年签订《马关条约》。从此,自古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而岛国日本则成为世界强国。1898年,以变法自强为目的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随后,举国上下掀起了狂热的排外热潮。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人依然热衷于鼓吹“中国觉醒论”。最典型的是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外事秘书史密斯(Judson Smith)[44]。他在中国实地考察了一年之后,于1899年在美国发表了一篇长文。他写道,在世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一个国家获得新的生命,“现在,我们看到,经过几个世纪的沉睡之后,中国正在觉醒,中国的统治者们已经激发起新的生命,一种全新的力量正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制度及文化教育制度”,“中国的觉醒,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史密斯看来,促使中国觉醒的力量,正是甲午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对于日本来说,胜利是如此的辉煌,对于中国来说,失败是如此的耻辱、如此的震惊,中国人深深感到,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他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如果再不接受新的观念、新的力量、新的生活方式,那么,就要亡国了”,所以,甲午战争“迫使中国的统治者去探究日本获胜的原因,迫使他们去学习西方的艺术及科学”,于是,中国被唤醒了[45]。
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还提出,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使中国“忽然觉醒”。但在曾纪泽的宏论发表13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因义和团而侵占北京。这次劫难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宣告中国并没有像曾纪泽所宣称的那样已经“觉醒”。不过,一些西方人坚信清朝政府一定会改弦更张、锐意革新,正如《中国丛报》(TheChineseRecorder)在1901年的新年献辞中写道:“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且再也不会倒退回去了。”[46]
确实,《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为了挽救已经奄奄一息的政权,在不影响自身统治地位的前提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就是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内容包括鼓励工商、编练“新军”、改革官制、废除科举,等等。在西方人看来,这些“新政”,正是中国觉醒的标志。于是,西方报刊为清政府的“新政”而热情地齐声欢呼。比较典型的是英国伦敦的《每日邮报》(DailyMail),从1906年10月到12月,连续发表了以“中国巨人的觉醒”(“TheArousingoftheChineseGiant”)为主标题的系列文章,共计15篇。《每日邮报》编辑部在该系列文章前面特地加上了一段按语,其中写道:“中国正在前进,在难以计数的中国人之中,正在进行一场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47]
《每日邮报》这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是《四亿三千万人的觉醒》(FourHundredandThirtyMillionsofMenAwakening)。该文开篇写道:“经过几个世纪的沉睡之后,中国终于觉醒了。中国是东方最大的帝国,同时也是地球上历史最久、人口最多、组织程度最高的帝国,它就要启动现代化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个龙的国度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傲慢而排外,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无动于衷。几年前,英国人用枪炮迫使中国开放了几个口岸进行通商,但无法使中国人的思想也对西方开放。”因此,“面对西方的影响,如果说日本是蜡的话,那么,中国则是大理石”;但在1900年之后,中国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中国的巨大变化,无论对于东方来说,还是对于西方来说,其影响都要远远超过亚历山大东征或拿破仑征战”,因为“龙的国度如此庞大,能够推动它前进的力量,一定也能影响整个地球”[48]6。
长期在中国生活、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对清政府的“新政”更是赞美有加,他在1907年出版的《中国的觉醒》(TheAwakeningofChina)中写道:“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为伟大的运动,正在中国这个舞台上上演。”他还热情洋溢地说:“倘若中国人依然像半个世纪之前那样呆滞僵化的话,我也许会对他们的未来感到绝望。但今天中国人,正在齐心协力地竭力告别过去,力图通过采纳西方文明的精华而寻找新的生活。当我看到这些时,我觉得,我对他们未来的希望,已经实现了一大半。我很高兴,我能够用我的笔墨及声音来帮助他们的事业。”[49]近代日本著名记者河上清在美国发表的英文文章中,同样认为清朝的新政措施“准确无误地表明,中国经过长期的昏睡之后,现在终于觉醒了”。不过,河上清还审慎地写道:“中国几乎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几个世纪中,中国一直处于僵化呆滞的状态,要指望这样一个国家在一天之内就能摆脱此种状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经过几代的人努力,中国才能脱胎换骨。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开始脱胎换骨了。”[50]
清政府“新政”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重要特色的科举制度,采纳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对此,西方报刊予以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写道:“中国正在觉醒,旧的秩序正在逝去”,而中国的未来,则取决于教育,因此,西式教育在中国的引入及推广,“犹如黑暗中的一束亮光,象征着中国的未来将有美好的希望”[51]。现代化的另一项重要标志就是铁路。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完工。《每日邮报》在报道中写道:“一直以来,不断有人向世界发出‘中国觉醒’的警讯,而且,‘中国觉醒’被认为会带来咄咄逼人的威胁,可事实上,世界几乎看不到中国觉醒的证据,结果,许多人认为,这种警讯其实是虚假无据的。”现在,中国人“既没有依靠欧洲的技术人员,也没有利用欧洲的资金”,“自己设计、建造”了京张铁路,所以,“这条铁路向世界表明,中国正在觉醒”。驻北京的英国公使甚至认为,“京张铁路的建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52]。
由于坚信中国已经觉醒,所以一些西方人就开始思考中国觉醒后所产生的影响。发表在《每日邮报》上的那篇《四亿三千万人的觉醒》直接发问:“中国的觉醒,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几个世纪的时间中,用泪水、祈祷、奋斗,建立起了我们的欧洲文明。中国的觉醒,会对欧洲文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人的到来,是福?是祸?中国会使我们的未来蒙上邪恶凶险的滚滚乌云吗?几百万手持武器的亚洲人,黑压压地前来攻打我们,就像哥特人攻打古代罗马一样,这样的‘黄祸’恶梦是否真的会变成事实?或者,中国的觉醒,是一个全新的因素,将使我们古老的地球进入一个诗人们所梦求的幸福时代?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48]6一个驻印度的英国记者认为,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正在觉醒,这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因为“亚洲的觉醒,甚至比欧洲最近几个世纪的所有事件(包括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都要伟大”。这样,“我们再也不能将黄色人种及棕色人种视为比我们低劣的人种”。这位记者强调,“中国和日本正在不断强大,面对着这样的事实,英国必须把来自亚洲的移民问题视为本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并且采取一些实际的措施,否则就会陷于巨大的麻烦之中。”[53]有个英国人还专门给《曼彻斯特卫报》写信,认为“在近几年的世界历史中,最大的事件,大概要数继日本之后中国的觉醒了”。这位作者接着写道:“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停滞不前。只有无情的战争,才能唤起它去思考自己的未来。中国已经觉醒,现在,对于中国、西方、甚至全人类来说,需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将沿着什么样的路线前进,我们怎样才能对中国产生最好的影响?”特别是,由于“中国将日本视为改革的先驱、成功的榜样”,所以,“大量的日本教师正在努力进入中国”。这样,如果要想在中国建立起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教育体系,英国传教士就必须行动起来,争取掌握中国教育的主导权,而不能让它落入日本人的手中[54]。另一个英国人则写信给《每日邮报》,讲述了俄国人对中国觉醒的看法。信中写道:“俄国人认为,中国人总有一天会重新称霸世界”,“俄国人经常担心中国人会向西伯利亚扩张,因为西伯利亚有着丰富的资源”,所以,圣彼得堡的一名俄国军官曾向此文作者建议:“英国人和俄国人应当团结起来去对付中国人。”[55]
1887年初,卸下驻英公使之职的曾纪泽从英国返回北京时,伦敦的《亚洲季刊》发表了他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文中宣告中国已经觉醒。巧合的是,1910年7月,卸去驻美公使等职的伍廷芳(1842—1922)刚回到中国时,美国的一份杂志也发表了伍廷芳的《中国觉醒的意义》(TheSignificanceoftheAwakeningofChina)。在这篇文章中,伍廷芳同样宣称中国已经觉醒。他写道:“中国人认为,过去几千年行之有效的制度,一定是优良的制度,并将世代永存。但是,经过许多次惨痛的教训之后,中国官员及其他人都开始认识到,虽然中国古代文明及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即使不是优于西方文明的话,至少也是与西方文明同样优秀的,不过,由于时代的变化,中国必须改变政策,并且要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一些知识。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全国上下都已经觉醒,并且行动起来了。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在进行了重要的变化与变革,那些一直被认为是有效、优越的制度,现在看来已经无法应对当今的需求了。”[56]
虽然伍廷芳在美国的杂志上满怀信心地宣告中国“全国上下都已经觉醒”,但这篇文章发表时,他已经对清政府“失望乃至绝望”了,因为他回国后痛苦地发现,“清政府宛如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只是稍微伸了一下懒腰,又打着一连串的呵欠呼呼大睡过去。此时的它已是病入膏肓,纵然华佗再世,扁鹊显灵,也难以让其起死回生。”[57]1910年8月,伍廷芳称病请假,结束了长达28年的官宦生活,寓居上海。此时,他的《中国觉醒的意义》在美国刚刚发表一个月。伍廷芳的归隐,表明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所宣称的中国已经觉醒。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这样,在《中国觉醒的意义》问世后一年,清朝不仅没有“觉醒”,反而灭亡了。
四、余论
武昌起义爆发后,西方人觉得“中国觉醒”的时代终于真正来到了。1911年11月2日,革命军正与清军交战之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中国人’一词,一直以来都被当作停滞、僵化的代名词。但是,现今已完全不同了。中国,曾经被认为是僵尸文明的典型代表,是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怪异遗骸,就像是某种厚皮类动物一样。而今天,我们再也不能以这种眼光看待中国了。中国正作为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以全新的姿态兴起。中国就像一个精神重振的巨人,正在觉醒,并且展示出青春的热情和活力。这是近代历史上最为震撼的事实。它的巨大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广泛、如此剧烈的觉醒”[58]。就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1912年,孙中山的老师、好友英国人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1—1926)出版了《孙中山与中国的觉醒》(SunYatSenandtheawakeningofChina)一书。书中这样写道:“世界总是鄙视中国,将其视为怠惰陈腐的巨人。现在,世界不得不意识到,中国的觉醒,将产生出奇异的、无可估量的巨大力量,而且,世界必须面对这样的力量。”[59]214但历史最后还是无情地粉碎了康德黎的良好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人在提出“中国觉醒论”的同时,还在讨论“中国觉醒”对西方、对世界的影响。清朝“新政”期间,《四亿三千万人的觉醒》就问道:“中国的觉醒,会对欧洲文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人的到来,是福?是祸?”民国建立后,康德黎也问道:中国觉醒后,“会对远东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后果?”[59]214在有些西方人看来,中国的觉醒,将对欧美直接构成威胁。特别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使西方人感到,“觉醒”后的中国人会变得“非常野蛮、残忍、反文明”[60],“美国漫画家们就将义和团画成是挣脱铁链的巨人,或者是从沉睡中觉醒过来的巨人”[61]。一些俄国人甚至认为,“中国人总有一天会重新称霸世界”。这些言论,就是“中国威胁论”的前身。或者说,“中国威胁论”是从“中国觉醒论”中派生、演变而来的。
当近代中国拖着沉重的脚步踉跄前行时,英文报刊上一次又一次地发出“中国觉醒”的欢呼声。有学者统计过,仅仅在美国,“从1890年到1940年,有60多篇文章的标题、30多部著作的书名,都是‘中国(或者巨人、巨龙)已经觉醒(或者正在觉醒、正在奋起、正在崛起、正在巨变、浴火重生’之类的)”[62]。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为了追求现代文明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更加重要的是,这一事实还表明,尽管屡遭重挫,中国人依然以惊人的毅力不屈不挠地追求着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