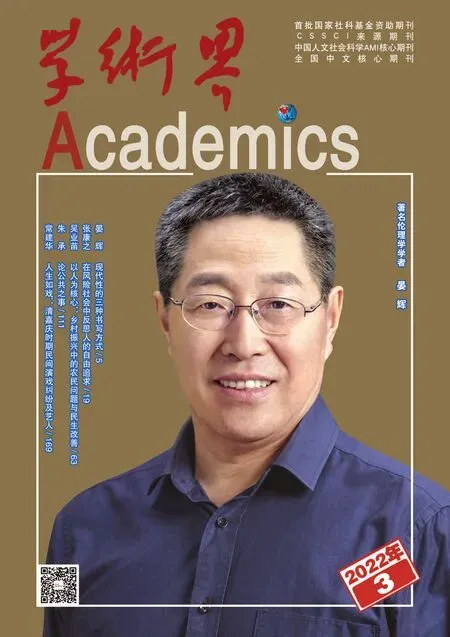晚清朱子学者对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批评〔*〕
——以夏炘、朱一新为中心
2022-12-15乐爱国
乐爱国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戴震的学术在现代得以兴盛,与胡适的大力推崇有很大的关系。1924年,胡适在《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中说:“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是朱子,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戴东原。”〔1〕然而,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下半部分述“戴学的反响”,不仅讨论了“凌廷堪、焦循、阮元,这三个人号称戴学的传人”,而且还叙述了“姚鼐、程晋芳、方东树一班顽固的反动派”,〔2〕包括清中期对戴震作出批评的一些学者。事实上,对于戴震的批评一直持续到晚清,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朱子学者夏炘、朱一新对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批评,但至今尚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
一、夏炘《与友人论〈孟子字义疏证〉书》
夏炘(1789—1871),字心伯,一字弢甫,安徽当涂人。“心伯学兼汉、宋,尤尊紫阳,粹然儒者。”“在婺源十八年,与生徒讲学,惟以诵法朱子相勖。”〔3〕他于清咸丰二年(1852)所刊行的《述朱质疑》中说:“炘幼读朱子之书,长好朱子之学,老官朱子之乡,高山仰止,欲从未由。……数载以来,讲习讨论;凡关涉朱子之学术著述、师友出处者,随笔疏记,积久成帙,共得如千篇,厘为十有六卷,以未敢自信,名之曰《述朱质疑》。”〔4〕夏炘《述朱质疑》推崇程朱之学,说:“夫程朱之释经,虽不敢谓其字字句句尽得圣人之意,然其大者固得之矣。……又程朱虽未能便是圣人,然皆颜曾之侣,王佐之才,使其得位行政,皆可以制礼作乐,复三代之盛。”〔5〕《述朱质疑》中有《与友人论〈孟子字义疏证〉书》一篇,约计2359字,针对友人“盛称《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为近今之巨制”而提出质疑,进而对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论“理”、论“性”章进行了批评。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讲“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并由此认为宋儒“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是把人之意见当作理。〔6〕对此,夏炘强调“理也者,万事万物当然之则”,并且说:“《疏证》以自然者为欲,必然者为理,而不肯言当然。夫欲任自然,则无所不至矣。理曰必然,则鲜不以意见当之者。惟求其当然,则知之明而处之当。”又说:“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则具之于心亦明矣。理之在事物者,撒著之理也;理之在一心者,体统之理也。必以理属事物而不属之心,是告子‘外义’之学也。”〔7〕在夏炘看来,程朱讲的“理”,并非戴震就“必然”而言,而是就“当然”而言,因而并非意见,而是要“知之明而处之当”;同时,具体事物之理,存在于事物之中,而总合之理,存在于心中,这是孟子的思想,否则,以为“理属事物而不属之心”,乃属告子之学。为此,夏炘还说:“‘如有物焉’,乃老庄之说。……程朱无是言。加于得天、具心之上,张冠李戴,不亦诬乎?”“以意见为理,程朱之所深恶,故‘格物’之训,‘致知’之‘补传’,覶缕言之,而谓程朱即其人,真辜负先贤之苦心矣!”〔8〕在夏炘看来,戴震认为宋儒讲“如有物焉”,实际上“乃老庄之说”,“程朱无是言”,是张冠李戴,所以戴震所谓宋儒“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是不能成立的;而且,程朱讲格物致知,就是要反对以意见为理。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论“性”,讲人与物之“血气心知”,他说:“古人言性,但以气禀言,未尝明言理义为性。”〔9〕反对程朱言“性即理”以及“气质之性”。他说:“创立名目曰‘气质之性’,而以理当孟子所谓善者为生物之本,……是谓性即理,于孟子且不可通矣。”〔10〕又说:“孟子言人无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无有不恶,……宋儒立说,似同于孟子而实异,似异于荀子而实同。”〔11〕还说:“其所谓性,非孔孟之所谓性,其所谓气质之性,乃荀扬之所谓性。”〔12〕对此,夏炘说:“程子‘性即理也’之说,发挥孔孟性善之旨,颠扑不破。不知《疏证》何独恶此‘理’字,以为性不可以‘理’言也?后人之‘理’字,即仁、义、礼、智之谓也;赋于人为仁、义、礼、智,本于天为元、亨、利、贞。《中庸》‘天命之谓性’,即孔子‘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也;虽一言‘性’即有‘气’,然此句终属于‘理’。孟子之以‘四端’言性,实渊源于此;其云‘性善’,即‘继善成性’、‘各正性命’之谓也。程朱之以理诠‘性善’,与孔孟吻合无间。……自程张‘论性不论气,不备’之说出,而后拨云雾而见青天。张子‘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者,即孟子‘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之性’也。《疏证》独取先儒之不以为性者,而必辗转以申其说,不知已落佛氏之窠臼。而反以程朱与荀卿合,不亦诬乎!”〔13〕在夏炘看来,程朱言“性即理”是对孔孟性善说的发挥,而“孟子之以‘四端’言性”,实际上源于“理”,即仁、义、礼、智,本于元、亨、利、贞,就是《中庸》“天命之谓性”和《易传》解“元亨利贞”,而且程朱讲“气质之性”,也来自孟子所谓“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之性”,而并非荀子之性。
对于戴震说“理者存乎欲”,“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并指程朱不过“就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者转之以言夫理”,夏炘说:“人欲者,在人为耳目口鼻;接乎物则为声色臭味。欲纵有不必尽邪者,未有理而不正者也。老、释之‘真宰’‘真空’,指虚无寂灭而言;程朱所谓理,指真实无妄而言。……判若天渊,而谓转彼以言此,是文致之法也。”〔14〕认为程朱讲天理人欲,就是要以天理正人欲,讲的是理的真实无妄,根本不是老、释的虚无寂灭。
至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将程朱理欲之辨与“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15〕对立起来,夏炘说:“欲有根于秉彝者,如欲仁、欲立、欲达之类是也;欲有出于形体者,如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四肢之欲安佚是也;欲有流于偏私者,如‘其欲逐逐’、‘克伐怨欲’之类是也。……程朱理欲之辨,安得与体民之情、达民之欲并论?”〔16〕夏炘认为,程朱理欲之辨,是要反对私欲,而不是要排斥人的正常欲望,不可与“体民之情、达民之欲”相互对立。他还说:“程朱所著之书,发挥王道,纤悉具备,无非达民之欲、体民之情。朱子外任九载,漳州之经畍,浙东之荒政,何一非体情、达欲善政?而谓自宋儒辨理欲遂为祸于天下,此似非仁人之所忍言也。”〔17〕认为程朱理欲之辨,在于克除私欲,“无非达民之欲、体民之情”。
由此可见,夏炘《与友人论〈孟子字义疏证〉书》对于戴震的批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就戴震认为宋儒以意见为理,夏炘明确认为程朱不仅没有以意见为理,而且“以意见为理,程朱之所深恶”;其二,就戴震将程朱理欲之辨与“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对立起来,夏炘明确认为程朱理欲之辨不仅没有排斥人的正常欲望,而且正是要“达民之欲、体民之情”;其三,就戴震以“血气心知之性”反对程朱言“性即理”以及“气质之性”,夏炘明确认为程朱言“性即理”以及“气质之性”来自孟子。
夏炘《与友人论〈孟子字义疏证〉书》最后说:“《疏证》一书,专与程朱为仇。知名物制度不足以难程朱也,遂进而难以性命;知道德崇隆不能以毁程朱也,遂进而毁其学术。程朱之学术,莫大于辨理、辨欲、辨气质之当变化。一切皆不便于己,于是扫而空之。以理责我者,以为是乃程朱意见之理也;以欲责我者,以为欲乃人生之所不可无,圣人无无欲之说也;以变化气质绳我者,以为气质即天命之性,主敬存理皆宋儒之认本来面目也。”认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对于程朱的批评,就是要“专与程朱为仇”,排斥异己,有意作对。
二、朱一新对戴震人欲论的批评
朱一新(1846—1894),字蓉生,号鼎甫,浙江义乌人。他推崇朱子学,说:“程、朱之学历元、明数百年而无弊,即弊,亦不过迂拘弇陋而已。”〔18〕他还曾推崇明代章枫山所言:“浙中多事功,有末而无本;江西多主静,有本而无末。惟朱子本末兼尽,其论‘居敬’,则自谓于专一上见功夫;论‘穷理’,则自谓于精义处得力。”〔19〕他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写成的《无邪堂答问》对戴震多有批评,指出:“乾、嘉诸儒,东原、竹汀(钱大昕)为巨擘。……然戴氏之《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绪言》三书则谬甚。”〔20〕
朱一新认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之谬在于“以人欲为天理”,说:“古书凡言欲者,有善有恶,程、朱语录亦然。其教人遏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纵,故专举恶者言之,乌可以辞害意?东原乃以欲为本然,中正动静胥得。无论古书多不可通,率天下而祸仁义者必此言矣。”〔21〕他还说:“戴氏《疏证》,语多支离,谬不胜纠。大率以人欲为性之本然,当顺而导之,不当逆而制之。此惟‘圣人所欲不踰矩’者乃可,岂中人以下之欲皆能如是乎?”〔22〕在朱一新看来,人欲有善有恶,程朱“专举恶者言之”,讲“遏欲存理”,更多的是看到人欲之恶;与此不同,戴震“以欲为本然”,“以人欲为性之本然”,必然会导致人欲横流,祸害仁义道德,“虽使人欲横流,皆自以为合于天理,是尊情以灭性,而并可以废学,东原其殆未之思耶?”〔23〕
朱一新特别强调程朱的“理”与“礼”的一致,说:“先王本理以制礼,以禁慝也。有礼斯有乐,以导和也。古乐既亡,礼亦为文饰之具。宋儒因亟以理明之,又恐人矜持拘苦,而屡以从容乐易导之。今读其遗书,以理为教,实多以礼为教。”〔24〕对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既说“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25〕又说“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朱一新说:“夫圣贤正恐人之误于意见,故有穷理之功。东原乃认意见为理,何其言理之粗?体民情固也。遂民欲而亦谓之理,何其言理之悖?欲仁,欲也;欲利,亦欲也。使徒求遂其欲而不以理义为闲,将人皆纵其欲而滔滔不返,不几于率兽食人乎!”〔26〕在朱一新看来,程朱以理为教,是继先王“本理以制礼”,是以礼为教,“正恐人之误于意见”,因而是要通过格物致知,即物而穷理,同时,人之欲,有欲仁和欲利之分,不能只讲“遂民之欲”,而不讲理义,否则就是纵其欲。朱一新还针对戴震所言“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27〕说:“苟以此为教,恐五季之祸,其不复见于今者几希。诚不意儒者日治三礼,而竟不求诸制礼之本原也。”〔28〕认为戴震斥责程朱理学“以理杀人”,是忽视制礼之本原在于“本理以制礼”。
朱一新特别强调“欲本兼善恶言”,说:“欲本兼善恶言,宋儒曷尝谓欲有恶而无善?特‘理’、‘欲’对言,则理为善,而欲为恶。故《乐记》言‘天理’、‘人欲’,《易》言‘惩忿’、‘窒欲’,《论语》言‘克伐怨欲’,经典中此类甚多,东原概置之,而但援‘欲立’、‘欲达’以为说,不知《说文》欲训贪欲。贪之为义,恶多而善少,东原精揅训诂,岂独不明乎此?第欲伸私说以攻宋儒,遂于本明者而转昧之,此即‘欲’也,而不当遏之乎?天之赋人有食色之欲,未尝有贪淫之欲,其有之者,人自纵之也。东原乃谓‘食色之性,人不可无’,此何待言?愚人知之,宋儒不知耶?”〔29〕朱一新认为,欲,既有善,也有恶,而且恶多而善少;程朱较多看到欲之恶,而戴震较多看到欲之善;但他们都知道“欲本兼善恶言”,既有“天之赋人有食色之欲”,也有因放纵而有“贪淫之欲”。朱一新还说:“《疏证》有云:‘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是东原未尝不知欲中有恶也。既知有恶,而又禁人存理遏欲,诚不知其何说也?《朱子语类》‘……若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凡东原之所辨,朱子已早言之矣。”〔30〕在朱一新看来,戴震肯定“天之赋人有食色之欲”,又不否定欲中有恶,与程朱讲“存理遏欲”,遏止欲中之恶,同时又不否定“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并非相互对立。
对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讲“血气心知之性”,反对朱熹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别,朱一新说:“夫仁义礼智天所与我,而皆于四端之心见之,苟非‘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何以能应万事?〔31〕《诗·蒸民篇》郑笺:‘天之生众民,其性有物象,谓五行,仁义礼智信也。’《乾凿度》:‘五常以之行。’郑注:‘天地气合,而化生五物。’郑君以‘五物’训‘五常’,非‘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谓耶?……推其致误之由,盖以‘血气、心知为性’,而不知以‘义理气质为性’。血气、心知未尝非性。然此但言‘气质之性’而未及义理。”〔32〕在朱一新看来,戴震讲“血气心知之性”,只是朱熹所谓“气质之性”,〔33〕而且还应当有如郑玄所说,由天之生众民而有五常之性,即“天命之性”。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说:“欲者,血气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不悦理义者,未能尽得理合义耳。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理义;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34〕显然,戴震是由“血气心知之性”而言性善。对此,朱一新说:“夫孟子谓:‘心之所同然者,为理义。’未尝谓心之所发者,皆合于理义也。心统性情,故理义具于心。其具于心者,性之所固有也。所谓性善也,其动而不必皆合者,情之有善有恶也,所谓其情可以为善也。可以为善,亦可以为不善也。……才情气质,虽有善有不善,而人皆有此秉彝之性,故皆可以为善。是则性相近也,是乃所谓性善也。若以是归诸心知之自然,则心知有恻隐矣,亦知有残忍也;心知有辞让矣,亦知有争夺也。而以为尽合理义,不亦诬乎?”〔35〕在朱一新看来,朱熹讲“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由“天命之性”而言性善,与此不同,戴震是由“血气心知之性”而言性善。
应当说,朱一新站在朱子学的立场,对戴震“以人欲为性之本然”以及由“血气心知之性”而言性善作了批评,但是,这样的批评似乎又包含了试图调和戴震之学与程朱之学的意味。通过比较程朱讲“存理遏欲”与戴震对程朱的批评,朱一新认为,程朱讲“存理遏欲”,只是要遏止人的“贪淫之欲”,并不是要排斥“天之赋人有食色之欲”,而戴震讲“以人欲为性之本然”,肯定“人欲”,并非指人的“贪淫之欲”,就此而言,戴震与程朱是一致的。同样,戴震反对朱熹讲“天命之性”,而讲“血气心知之性”,实际上只是讲朱熹所谓“气质之性”,差别只在于戴震讲“血气心知之性”为善,而朱熹讲“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二者虽有差别但并非截然对立。
此外,朱一新还就朱熹讲“格物”与戴震作比较,说:“朱子《补传》‘在即物而穷其理,一‘即’字已吃紧,教人非谓只格一物,便可贯通,亦非谓必穷尽天下之理,只积累多后,自然见去。’戴东原《孟子疏证》谓:‘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亦岂足以穷其知?’案东原之说,正与朱子《补传》意同。”〔36〕显然,朱一新对戴震的批评,更多地思考戴震之学与朱熹之学的相通之处。
朱一新为学,主“汉宋兼采”,说:“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乾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空疏之弊。”〔37〕又说:“汉学家以汉儒专言训诂,此浅陋之说,不足信也;以宋儒为不讲训诂,此矫诬之说,尤不足信也。汉宋诸儒,无不学贯天人,门径不同,及其成功则一。”〔38〕因此,他批评乾嘉汉学,说:“乾嘉诸老,逐末忘本,曼衍支离,甚且恣肆无忌者,诚为经学之蠹。”〔39〕同时又说:“程、朱之学,所以可贵者,以其本末兼尽也。小小抵牾,岂能尽免?后人虚心以订之,可也;肆口以诋之,不可也。”〔40〕既表明他的程朱理学之立场,又不否认程朱理学有其不足之处。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戴震的学术,既予以批评,又试图与程朱的学术调和起来。
三、余 论
如上所述,戴震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其《孟子字义疏证》还说:“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着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41〕戴震把程朱的“理”等同于酷吏所谓“法”,并认为“后儒以理杀人”更甚于“酷吏以法杀人”,“死于理”更甚于“死于法”,较多地讲程朱理学对于社会生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包含了对当时清廷统治的批评,当然,其中也涉及对于程朱理学的不同解读,而当时朱子学者对戴震的反驳,则主要是试图从学理上纠正戴震对于程朱理学的误读。
从以上安徽当涂的夏炘和浙江义乌的朱一新对戴震的批评来看,他们所批评的主要不是戴震的理欲观,而是戴震对于程朱理学的误解。戴震认为宋儒以意见为理,对此,夏炘认为程朱不仅没有以意见为理,而且反对以意见为理,朱一新也认为程朱以理为教,“正恐人之误于意见,故有穷理之功”;也就是说,在夏炘、朱一新看来,无论戴震或是程朱,都反对以意见为理。戴震斥责程朱理学“以理杀人”,并认为圣人之王道在于“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对此,夏炘认为程朱理欲之辨并没有排斥人的正常欲望,而是要克除私欲,“无非达民之欲、体民之情”,朱一新也认为,程朱要遏止的“人欲”,只是“贪淫之欲”,戴震肯定“人欲”,同样要排斥“贪淫之欲”,同时,讲“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还必须讲理义;也就是说,在夏炘、朱一新看来,无论戴震或是程朱,他们都反对“贪淫之欲”,都讲“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实际上二者是一致的,只是夏炘、朱一新更为强调“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必须要克除私欲,应当讲理义,更为接近朱熹,而与戴震既有相同亦有不同。此外,戴震讲“血气心知之性”,实际上只是讲朱熹所谓“气质之性”,二者亦有相通之处。尤为重要的是,夏炘、朱一新在批评戴震的同时,也承认程朱并非“字字句句尽得圣人之意”,不否认有其不足之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戴震的批评,更多的是就戴震理欲观与程朱理欲观进行比较,论述二者的一致与相通,既是对程朱理欲观的肯定,也是对戴震理欲观的肯定。这样的研究,无疑与当时讲“汉宋兼采”的学术趋向有密切关系。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
钱穆说:“近儒首尊东原者自太炎。”〔42〕余英时也说过:“戴震‘以理杀人’之说,在近代首先是由章炳麟发现的,到了‘五四’时代更自然而然地和‘吃人礼教’的口号合流了。”〔43〕需要指出的是,章太炎推崇戴震,并非由此而完全否定程朱理学。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中论及戴震及其对宋代理学的批评,说:“他虽专讲儒教,却是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这位东原先生,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硃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册子,他的书上,并没有明骂满洲,但看见他这本书,没有不深恨满洲。”〔44〕在这里,章太炎显然认为戴震是借批评宋儒而批评清廷帝王以理学之名任意杀人。1910年,章太炎发表的《释戴》,说:“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迾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衋伤深。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愬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究极其义,及于性命之本,情欲之流,为数万言。夫言欲不可绝,欲当即为理者,斯固政之言,非饬身之典矣。辞有枝叶,乃往往轶出阈外,以诋洛、闽。……洛、闽所言,本以饬身,不以政,震所诃又非也。”〔45〕由此可以看出,章太炎对戴震批评程朱“以理杀人”,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观点:其一,章太炎特别强调戴震讲程朱理学“以理杀人”,是要批评清廷帝王不是依据法律而是借着理学的言辞任意杀人,是就清廷帝王“以理杀人”而言,而且“以理杀人”更甚于“以法杀人”;其二,程朱的理欲之辨,“本以饬身,不以政”,戴震所讲理欲,要求“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是“政之言”;其三,由于程朱讲理欲属于修身,而戴震讲理欲属于治国之道,戴震斥责程朱理学“以理杀人”,如果是指向程朱理学,是不对的。章太炎《释戴》还说:“极震所议,与孙卿若合符。”〔46〕认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所言,虽“资名于孟子”,但“以欲当为理”,而与荀子相符。事实上,正如夏炘所说“程朱所著之书,发挥王道,纤悉具备,无非达民之欲、体民之情”,程朱理学在修身上讲理欲之辨,讲“存理遏欲”,而在治国之道上则讲王道,讲“仁者散财以得民”,“君子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47〕重视百姓之财利,“无非达民之欲、体民之情”,并非“以理杀人”。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晚清朱子学者对戴震的批评,还是清末民初章太炎对戴震的推崇,他们都不是要将戴震之学与程朱之学对立起来,或推崇程朱而批评戴震,或推崇戴震而打压程朱。他们既肯定程朱讲“存理遏欲”,又认为戴震对于人欲的肯定,与程朱的理欲观并不相矛盾。至于后来,随着戴震学术的兴盛,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戴震对于人欲的肯定,反对程朱讲“存理遏欲”,将戴震学术与程朱学术对立起来,比如胡适认为,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排斥人欲的哲学在七八百年中逐渐造成了一个不近人情、冷酷残忍的礼教,戴震是反抗这种排斥人欲的礼教的第一个人”。〔48〕这一说法,认为戴震是要反抗朱熹排斥人欲,明显背离了最初章太炎推崇戴震时的初衷,更是远离了晚清朱子学者对于戴震的批评。当然,胡适也说过:“戴学实在是程朱的嫡派,又是程朱的诤友。”〔49〕但最终敌不过后来把戴震与朱熹对立起来,抬高戴震打压朱熹的学术思潮。
注释:
〔1〕胡适:《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胡适全集》(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6页。
〔2〕〔48〕〔49〕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全集》(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2、386、471页。
〔3〕徐世昌等:《清儒学案》(6)卷155《心伯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023页。
〔4〕〔清〕夏炘:《述朱质疑序》,《续修四库全书》(95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5〕〔7〕〔8〕〔13〕〔14〕〔16〕〔17〕〔清〕夏炘:《述朱质疑》,《续修四库全书》(95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9-100、102、102、103、102、103、103-104页。
〔6〕〔9〕〔10〕〔11〕〔12〕〔15〕〔25〕〔34〕〔41〕〔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6、26、34、37、9-10、169、18、9-10页。
〔18〕〔20〕〔21〕〔22〕〔23〕〔24〕〔26〕〔28〕〔29〕〔30〕〔32〕〔35〕〔36〕〔40〕〔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8、3、3、122、122、29、29、29、122、122、122-123、123、148、83页。
〔19〕〔清〕朱一新:《佩弦斋文存》卷上,《拙庵丛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288页。
〔27〕〔清〕戴震:《戴东原先生文·与某书》,《戴震全书》(6),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496页。
〔31〕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无邪堂答问》(吕鸿儒、张长法点校),该句为:“苟非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何以能应万事?”
〔33〕“戴氏说血气心知是性,这正是宋儒所谓气质之性。他却直认不讳。”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全集》(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3页。
〔37〕〔清〕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76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19页。
〔38〕〔39〕〔清〕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76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55、648页。
〔4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96页。
〔43〕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5页。
〔44〕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章太炎全集》(1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2页。
〔45〕〔46〕章太炎:《释戴》,《章太炎全集》(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2、124页。
〔4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