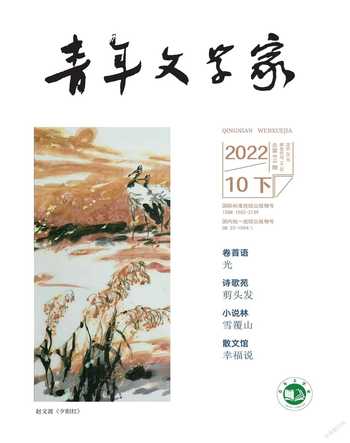光影交叠里的女性悲剧
2022-12-14王虹媛
王虹媛

虽然都为“五四”潮流后诞生,张爱玲的作品与几乎同期的左翼文学潮流有着一定的区分,她不将自己的作品服务于社会的显性斗争,而是纯熟地运用纷繁的色彩与多样化的意象等手法,转而关注摩登都市中新旧个体微小的精神体验。而在其中,她对世俗人生中女性的刻画尤为显著。张爱玲创造的这种“五四”后的“小传统”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性的文学形态,不但与“五四”基本精神不冲突,而且与之大传统所形成的现代性构成了互补,推动着“五四”文学的进一步延伸。
正如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中,她多处运用了光影的意象,在明与暗的融合与变幻中刻画了曹七巧、长安、芝寿等典型的新旧交替时代封建家庭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在长期的宗法父权意识形态下面对多种错位的生存困境与心理异化,隐喻了一个时代多数女性的普遍悲剧命运。
一、主人公挣扎与绝望的写照
《金锁记》这部小说被傅雷称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也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就是由于张爱玲以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和人性关怀,真实地再现了曹七巧这样一个身世悲惨的女性,在抱怨与挣扎无效的绝望之中人格分裂至癫狂,成为一个迫害子女与他人的恶魔的演变过程。在此期间,自然或非自然的光影伴随着她们的命运,成为女性在压抑下掙扎与绝望的写照。
曹七巧本来是一个青春洋溢、小家碧玉的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她勤劳、开朗、渴望爱情,却被她的兄长卖到望族姜家,在姜家老太太的一念之差下成了姜家的二少奶奶,服侍她那位瘫痪在床,“看上去还没有那三岁的孩子高”的丈夫。她的悲剧命运就此开始,便再没有任何希望。于是,对待姜家的老少,她也是牢骚满腹、苦衷满腔。在向老太太请安之前,对曹七巧和众人的对话中,张爱玲插入了一段这样的光影描写:“敝旧的太阳弥漫在空气里像金的灰尘,微微呛人的金灰,揉进眼睛里去,昏昏的。街上小贩遥遥摇着拨浪鼓,那懵懂的‘不楞登……不楞登里面有着无数老去的孩子们的回忆。”“敝旧的太阳”投射在众人身上的光是一种“金的灰尘”,它是“昏昏的”,光照下的人却无法逃避,隐喻着权威的、封闭的家庭对这群女性,尤其是对曹七巧这样一位悲剧女性的精神迫害,是一种让人难以呼吸的压抑。在丈夫和老太太相继去世,曹七巧分得家产后,她欲望寄托的对象姜季泽假托爱情来哄骗曹七巧的钱财,她“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此处的出现的光伴随着不可言明的心理情感的流露,又照见了她一直压抑的爱情与欲望的苏醒。但曹七巧立即侦破了姜季泽的谎言,把姜季泽连骂带打地赶走,却也意识到她无法再拥有幻想中的爱情。
从此以后,她的精神逐渐向更加畸形与变态的方向发展,残存的人性也逐渐消解,人格的分裂一发而不可收。她因为内心变态的怀疑赶走了长安的表哥,然后在“屋里暗昏昏的,拉上了丝绒窗帘……除此只有灯和烧红的火炉的微光”的环境下,“灯的火焰住下一挫,七巧脸上的影子仿佛更深了一层”。在昏暗、微光的室内封闭环境下,曹七巧劝说长安远离男人,还说服她裹脚,以她大家长的身份在身体与心灵上控制自己的女儿。光与影的交叠、闪动不仅预示着曹七巧的复杂情感交织中的变态心理开始作祟,长安的人生也自此走向了深不见底的黑暗。
在亲手毁掉了女儿长安的爱情,逼死了儿媳妇芝寿、娟姑娘,儿子长白也不敢再娶后,门庭里仅剩下这么几个半死不活的人时,曹七巧回忆着她三十年的来人生:“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张爱玲写了她青春时的回忆,写了她的死亡。在小说的最后,张爱玲用了她文章中频繁出现的月光:“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同时也呼应了小说开头的月光,凄迷、冷寂的光辉也是作者的眼睛,代替她目睹了不仅仅是曹七巧一个人的三十年,也是几千年中国无数女性人生里的三十年,无数个不同又相似的悲剧。同时,张爱玲笔下的这块“黄金锁”,也不仅仅是曹七巧一人金钱和欲望的象征,更是长期以来女性无法摆脱的心理阴影和悲剧的枷锁。黄金锁下,月光下女性的悲剧永远在接续上演,没有终点。
二、意象与主体异化的对应关系
在《金锁记》这部小说中,光与影的意象产生了新的隐喻意义。传统诗词当中也存在着许多的光影意象,比如日光象征着热烈、希望,以及黄昏即将过去迎来黑夜的迟暮怅惘;月光、月影象征着独身或客居的清冷静谧、寥落孤独,以及随月相变化实现团圆与否的温存、陪伴与思念;还有非自然的烛光、火光,人影、灯影等,多去传达与夫妻、亲友间的感情,也与这些自然光影有着相似相近的意味。
在《金锁记》中,光与影的这些传统意蕴仍然未被张爱玲抛弃,被她纯熟地运用在文章中,这与她对传统文学作品的喜爱与研究是分不开的。譬如,小说里对长安的刻画中,当七巧去长安的学校闹事,让她没有脸面再读书那天,半夜里,“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长安又吹起口琴来”。黑夜里的月亮和淡淡的灯光,是长安对希望失去的怆然心境。而当长安经长馨的介绍认识了童世舫,“玻璃窗上面,没来由开了小小的一朵霓虹灯的花—对过一家店面里反映过来的,绿心红瓣,是尼罗河祀神的莲花,又是法国王室的百合徽章”,这里的霓虹灯光,是她在家庭中受母亲压抑已久后,面对爱情到来的心灵颤动,这让她体会到了少女的情感,这是在她身上多年未发生过的,长安缺失的精神得到了填补。进一步发展恋爱,在订了婚后,长安与世舫偶尔几次单独出去,“晒着秋天的太阳……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身边的阑干,阑干把他们与众人隔开了”。“有时在公园里遇着了雨,长安撑起了伞,世舫为她擎着。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烂的车窗上,汽车驰过了红灯、绿灯,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秋日的阳光温暖,闪着光的彩色雨珠充满奇幻和想象,都是一个女子在恋爱中烂漫的沉浸心理,同时,面对爱情恢复出的渴望,也是主体意识的精神复苏。
但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金锁记》中更有许多光影的意象是与传统文学作品大相径庭的。光影似乎更多地在张爱玲笔下被异化,正如《金锁记》开篇所说,“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月亮是迷糊的、晕染的,像用眼睛透着云雾和水汽去看,月色光影中充满了虚幻和不真实。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敝旧的太阳”带来的是“金的灰尘”,而非光明与希望;“灯的火焰”和“烧红的火炉的微光”带来给长安的不是冬日的温暖,而是曹七巧变态心理造就的不幸命运,都产生了异化的表征。
曹七巧也是如此,丈夫软骨病早亡,儿子毫无男性的责任与心志,十三四岁时却瘦弱的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成年后散漫颓废只知享乐,曹七巧成了家中唯一的家长,她顶替了男性的位置。在小说中,在曹七巧身上的异常的光反复出现,对应着她心理状态的异化和这个家中疯狂错乱的关系。光影象征意味的异化成为主体精神异化的隐喻,在童世舫与曹七巧见面的场景中尤为突出,仅靠明暗光影就让童世舫感受到曹七巧精神气质中的疯狂,让人更觉阴森恐怖。
三、男性身份的隐而复现
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提到:“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身为女性作家,她也在诸多作品中展现出较强的女性意识。其中一方面就是男性角色成为权力去势者,女性家长则取代了男性家长的位置。张爱玲将传统父权从男性主体身上剥夺下来,让他们成为女性统治的家庭中被压抑的一方。
在《金锁记》中,这些男性人物具体表现为得了软骨病毫无人气的姜二爷,只知道吃喝嫖赌的姜季泽和瘦小纤弱、贪图玩乐的姜长白,他们有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残疾,羸弱、无能、昏庸、麻木。而在这样一个男性主体普遍去势的家庭中,同时姜二爷和姜老太太去世,曹七巧就自然而然地由被统治的家庭成员成了女性家长,以女性个体的身份成了父权的载体,长安、芝寿等则成了被统治的女性家庭成员。笼罩在长安和芝寿身上挥之不去的恐怖的、阴森的、异样的、死寂的、狰狞的光与影,也是在男性缺失下,曹七巧拥有女性身份却掌握父权的这种异化力量的隐喻。此时,男性主体的力量即父权,是一种寄托在女性身上的隐性力量。由于作为有夫之妇,却因丈夫缺位长久无法释放压抑的欲望,加之成为女性家长后,主体自身“妾妇之道”的固有心理意识与被赋予的父权无法相融合,造成了曹七巧自我认知的混乱,进而导致其精神的异化与癫狂,她反过来去控制自己的儿子、女儿、儿媳,使他们经受自己曾经承受过的压抑、绝望。
虽然围绕在这个家庭中的男人都是非正常的,甚至女性化的形象,但在父权的控制下,身为女性家长的曹七巧面对家庭周围仍然存在的男性时,存在着权力转移的精神忧惧,这是历时以来父权争夺的必然的精神产物,拥有权力的主体会想尽办法去迫害潜在的权力争夺者。所以,在曹七巧赶走了可能利用残余的爱情与欲望“争夺父权”的姜季泽后,作为这个家中唯一的男人,长白这一弱化了的男性主体同时承载着芝寿身为妻子的正常欲望和曹七巧变态的欲望,由于曹七巧变态的权力笼罩,他无法在精神上给予妻子一个丈夫的支柱与责任感,转而成了身为母亲的曹七巧满足精神欲望的工具。
然而,对同为女性的长安、芝寿等,曹七巧也并未手软,这是女性竞争心理作祟的必然产物,导致了曹七巧母性的缺失,在精神疯狂中受雌竞的原始本能的心理主导下,用附加的父权力量去伤害同性。儿媳妇芝寿由于本身存在于父权与男性的精神主体相契合的家庭中,在嫁给了长白之后,也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权力主体和精神主体搭配异常的环境,导致她看到月亮就像“黑漆的天上一个白太阳”,是“反常的明月”。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太阳力量的月亮”,芝寿作为正常的女性主体无法理解和忍受非正常的異化环境,承受着无法破解的精神上的压力。所以,在惨白的月光中无限惊惧地死亡,是芝寿必然的结局。
而长安这一角色,是自小处在具有父权力量的母亲的掌控下的,被要求裹脚,进行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阉割”,被母亲逼退学,虽然她在过程中都进行了挣扎与反抗,但始终处在掌控下的她无法造成颠覆性的反抗力量,都是一种微乎其微的、温和的心理波动。而童世舫的出现使她产生了一个较大的转变。他是一个正常的男性主体,按照规律进入家庭会成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正常拥有父权和使用父权的男性。此时男性身份的出现使得长安第一次被赋予了真正的女性的身份,可以对男性产生渴望、欲望,可以正常地履行“妾妇之道”,她长期受压抑的心理上产生了较大的波动。在长安与童世舫相处的过程中,童世舫带来的男性精神力量让她周身的光影都成了正常的:两人一起约会时,“秋天的太阳”是温和的、暖人的。
但此时的曹七巧,是一个父权在精神疯狂与分裂中逐渐站稳了脚跟的主体,她逐渐意识到父权被争夺的潜在危险,所以便要求长安不要与童世舫继续进行下去。长安在母亲和父权双重的压抑中无法反抗,她“攀起了她的皮包遮住了脸上的阳光”,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得到这种“阳光”,这种男性给予她的安全感等精神力量时,面对童世舫,她泪如雨下;而当童世舫见到曹七巧,男性的主体意识使他对这个异化了的权力主体感到“那是个疯子”“毛骨悚然”,并听说了长安这个中国女性、大家闺秀竟然抽鸦片,童世舫选择离开这个家庭。长安望着他,“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儿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迟暮之后迎来的是黑暗,她的命运在这样一个男性主体的离开后再也无法挽回,仅剩下一点儿不多的回忆。光影的变化,也隐喻着正常的男性主体身份的缺失与复现,再到消失,同时也是女性人物的焦虑、歇斯底里、疯狂的另一种复本,隐喻着女性在男性、父权中心社会为生存而痛苦挣扎的生命轨迹。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以人性观察为角度对女性心理痼疾的书写,实际上也是将“五四”以来国民性的批判发展到女性个体微观的心理领域当中,通过独特的光影描写手段,用曹七巧的精神疯癫、人格分裂,以及对家庭成员的迫害构成主要的故事内容,传达了她对女性人格悲剧的深切关注和极度忧虑。同时,张爱玲利用光影传统隐喻的异化和明暗交叠中男性身份隐而复现的象征,既体现了她深厚的文学功底,又蕴含着她对历时已久的女性问题所具有的独特思考和深刻关切,从中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女性意识和根植于心的反父权意图,不仅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当下社会问题和女性心理发展的考量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