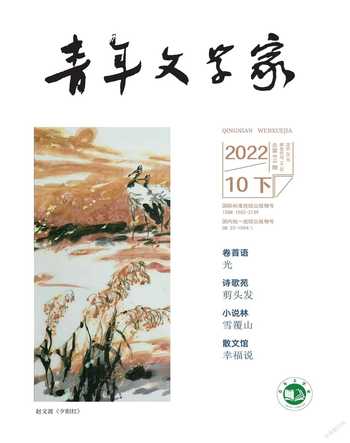用诗歌探测生命的温度和深度
2022-12-14杜源
杜源

在《忽冷忽热》的“编后小记”中,梁平提到某个年事已高却仍然写诗的诗人,称赞他“这是诗人的气质,这是一种永远的激情,永远的写作状态”,实际上梁平自己也是这种诗人。梁平说过“生命就是我的一首诗”,他将诗拔高到与自己生命同等的高度,凸显了诗歌对他的重要性,诗与生命同在,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写诗,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写诗,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写诗,写诗贯穿他的生活,也成为他的生活,他用诗歌探测生命的深度和温度。梁平从生活里各种风光与事物中得到思考,反映在自己的诗歌里,在《忽冷忽热》里,可以读出他从任何外部事与物里牵扯出的诗意,这种诗意是自然风光、社会事件投射出的,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现实倒影。
一、城市地理的温馨记忆
作家的写作总是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在梁平的诗歌中,我们经常能找到重庆与成都这两座城市的影子。在《回家》里,他写道:“成渝高速/是我唯一不能感受飞翔的速度/横卧在成都与重庆之间/混淆我的故土。”梁平作为在重庆出生成长的诗人,二十一世纪初从重庆转场到四川,在成都开始写诗,主持诗刊,两地辗转,因此他继续写道:“和别人不一样/我在两者之间无法取舍/从成都到重庆说的是回去/从重庆到成都说的也是回去……/我现在的身份比雾模糊。”“乡愁”是想家的愁思,诗人将对家的情感投入在重庆与成都两座城市里,一个是他的成长记忆所在地,一个是他的事业立足地,两地对他而言都意义重大,不管他从两地哪方出发都可以称为“回家”,两地都能使他在“一个不陌生、识旧的、原有的地方从容安息”(江弱水《诗的八堂课》),因此他通过诗歌与两座城市进行心灵沟通与对话。家不再局限于城市的房子里,而在于城市中他留存的记忆与感觉。
卷一中几篇有关重庆与成都两座城市的诗歌都从城市里的一条街、一个景点展开。城市的街道,只要是存在触动了他心灵的一景一物,他都在诗歌中有所呈现,因此他的诗构筑城市的特性框架,专注于城市风光与文化的诗性书写,从中挖掘出诗意。卷一开篇三首诗是对成都自然风光的书写,龙泉山上的桃花引起诗人想象,“龙泉山第三十朵桃花/揭秘她的三生三世”。“我在树下等待那年的承诺/等候了三十年/从娉娉袅袅到风姿绰约/只有一首诗的距离。”(《又见桃花》)诗人从盛开的桃花想到女子,女子也是桃花,桃花绽放是为了在春天守约,漫山的桃花落下花瓣雨,诗人又因为如雨飘落的花瓣牵动自己的内心,对桃花、对自然、对美好万物的爱浸润着诗人。在景观中,也有诗人心境的流露,“花好不在名贵,在于赏花人的心境”(《花岛渡》)。花在自然中孕育,正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能否欣赏到花,在于人的心境,诗人“闻香识岛,岛上一次深睡眠/醒来就是陶渊明”(《花岛渡》)。这种淡泊宁静的状态正是诗人所追求的,在花岛,他得以实现这种文人理想。成都的雪带给诗人的欢乐与欣喜在于“奢侈更多时候不是过分享受/而是求之不得,而得”(《成都的雪》)。不常见的雪花每一粒都是珍贵难得的,下雪带给人不常见的欣喜和快乐,这种快乐荡漾在城市里成为“豪华的抒情”。诗人的诗给现在的成都找回久远的历史记忆,找到存在于成都以外的人文符号,使读者从诗中能真切地感受到成都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
关于重庆,诗人则更偏向于一种回忆,记忆中的农田与荒野这些平坦之处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重庆印象是此起彼伏的爬坡上坎,心境的袒露在于“面对任何一条路,只要心平气和/都是坦途”(《重庆》)。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交通便利,“嘉陵江凌空的索道/高楼大厦穿堂而过的轻轨/不可思议之后,优雅平铺直叙”(《重庆》)。重庆在诗人不在的日子里迅速发展,诗人写过关于重庆的《重庆书》,但对于重庆的变化诗人也不得不承认“其实我对重庆也陌生了,上清寺/沧白路的光怪陆离,软埋了旧年时光”(《重庆》)。这种几十年带来的变化使得一些回忆的发生变得措手不及,诗人论今从谈古开始,“北郊一个普通的山梁/名字很好,梁上飘飞的书香/在百年前那间茅屋里的油灯下/弥漫多年以后/从那根羊肠子的道上/走出一个秀才”(《读书梁》)。读书梁这个地名让诗人赋予它一种文化内涵,成为崭新的文化符号,然而城市化后的城市容纳不了更多的人,于是房地产开发到读书梁,商业化将文化气息冲淡。开始谈到重庆也是家,乡愁是诗人对逝去的美好事物的追忆,但日新月异带给诗人不同于以往的感受,城市化带来的变异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距离,人与城市也有着无法填平的时间缝隙,诗人在诗里穿过钢筋混凝土筑造的森林去找到它被遗忘的过去,在城市化进程中寻找丧失的传统与记忆,以及诗意栖居的家园。
二、社会现实的冷静观照
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带来一些社会问题,梁平作为一个有平民情怀的诗人,并不只是将自己的创作视野放在自然、人文景观中。正如江弱水所说:“诗的主要功能是抒情,但它还需要叙述,也需要思想。”梁平认为,写诗就是要对自己負责,对得起自己,因为这是写作者的良知,自我的表达,表达诗人对当今社会的看法。他的诗歌用词不算激烈,但总能直指出社会问题的痛处,从单纯描摹事件升华到事件带来的感受与反思。
对于现代社会中一些真假难辨的声音,梁平用“我确定应该还有星期八,人神验证”来表达他的态度,“不然装神的大行其道,忽悠方圆/真伪难辨,越来越含混”(《星期八》)。诗人嘲讽地提出一周少了一天星期八,因为前七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充满一切美好、光明的事物,而星期八是混乱无序的,就像社会中各种流言蜚语,这样的对比用以剖开社会虚伪的一面。同样讽刺这种虚伪的还有《知水暖》,诗人借用苏轼的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为依据,用现代人的眼光进行了批判,认为鸭子下水只是本能,投映到现代社会里就是“假借和暗示习惯了/越来越觉得自己聪明”。诗句简单明了地描述出人自以为是和故作姿态的扭捏。
梁平关注社会生活,对新兴的社会现象有自己独特细致的观察。在短诗《画像》中,“画像”指的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评价,即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样子,这接近于创作中的“人设”一词。网络的发达让每个人都拥有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因此“人设”已成为抛开现实生活后网络社交的一个重要元素,网上所见不一定为真实。在诗里,通过“画像”这个比喻,梁平对这种现象加入了自己的审视:“根本没有时间自我辨别,那些画/无论蒙别人还是自己/反正都轻车熟路,信手拈来。”人们为了相互的利益选择说假话,为他人“画像”也为自己“画像”,从别人口中了解到的都不是真实的自己,自己也永远不会反思,但是在直面真实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镜子里看见有白色颜料打翻/溅在鼻梁上,好有喜感”这种自欺欺人的丑陋。现代社交软件的发达,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便利与紧密,但是,生活节奏的加快也增大了人内心的空虚,“漂流瓶”等交友功能的出现和兴起正依托于此。诗人认为匿名的交友是“寂寞与寂寞的互动”(《漂流瓶》),由此带来的纠纷刚好印证了“寂寞都是诱饵,各种诱/一不小心就拽你沉入海底”(《漂流瓶》),体现出梁平对复杂网络环境下人际交往的警示。
梁平将对现代社会的冷静观照转化成诗,从中寻找与建构人类的精神家园,抚慰现代人饱经沧桑的心灵。诗人对社会的审视绝不是消极的,他没有使自己那颗真诚的诗心消逝,而是将所观所闻的万事万物的内在意蕴从诗中解放,转化成为一种冷静平和的力量,轉化为绽放在精神上的花朵。
三、生命本质的诗意探寻
梁平曾说过:“我把诗歌的形式和技巧置于我的写作目的之后,我更看重诗歌与社会的链接,与生命的链接,与心灵的链接。”他的诗歌中虽然存在想象,但诗歌内容本质上还是描摹日常生活和现实社会的写实之作。《忽冷忽热》中的不少诗作,就是通过对现实人生的诗意素描,来体现诗人倡导的文学创作与当下生活、真实生命和内在心灵相互链接、相互影响并发生作用的诗学理念。
梁平写过一些记录和描述自己日常生活的诗,通过这些诗歌剪影,我们拾起诗人的日常生活碎片,拼凑出诗人的生活状态,如《端午节的某个细节》:“诗人都在过自己的节日/我在堆满诗歌的办公桌上/把烟头塞满烟缸,把烟丝排成行/一行一行地数落自己/数到第五行的时候,被迫打住/刚更换的靠椅显得格外生硬。”作为诗人和诗歌编辑,阅读和修改诗稿应该是他最基本的工作了,这首诗交代的正是诗人梁平的工作常态。在《桌上江湖》与《老兄弟》里,梁平描述了生活中与朋友的交往最自然的状态:“我喜欢满屋子荡漾的快活/喜欢桌上没大没小没规矩。”以及在兄弟面前“想说的话口无遮拦,想做的事说做就做”。这些都是梁平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生动描画,但他从来不满足于将诗歌放在只是简单叙述生活这样一种浅层次上,而是从平凡生活的细节出发,以小博大,积极思索生命的本质与意义,于个人思考中总结出一些哲理穿插在诗歌字里行间,引起读者共鸣。《端午节的某个细节》最后一节写道:“窗台看出去的街上,堵得一塌糊涂/我和城市同时胸闷、感到心慌/我们都不愿意声张/粽子、黄酒以及府南河上的龙舟赛/与我们没有关系。还是那个城市/我在等待另一个城市的电话。尽量保持/节前的那种安静。端午节应该肃穆/一个诗人的忌日,所有的人都快乐无比。”梁平将“一个诗人的忌日”与端午节“所有的人都快乐无比”加以对比,写出了这个节日中存在的不合常理的悖论,一个人的牺牲在后世变成了一个节日,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诗集《忽冷忽热》不仅呈现诗人的平凡日常生活,还可以看到诗人在诗歌里“向内转”的自我剖析。梁平作为诗人是真诚勇敢的,这不只体现在他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批判上,还在于他通过诗歌展示了他自我的孤独与寂寞这类一般人难以向大众言说的情感上,因此他从写诗中挖掘更深层的自我。孤独、寂寞是渗透在梁平诗歌中的一种感受和体验,这种感受与体验给梁平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痛苦,他才会写出一些“向内转”的心灵诗篇。在《寂寞红颜》里,梁平指出:“但我知道寂寞是我的红颜/与我相依为命。”这首诗就像戴望舒的《我的记忆》一样,把一种心境拟人化、具象化,把寂寞比拟成亲密的红颜知己—只有她与自己形影不离,也只有她能分享自己的秘密。这样的寂寞又体现在亲人、朋友离世上,如在《一个无法面对的日子》里,“突如其来,突如其来/一句没有任何铺垫的应答,比子弹/更迅疾地击中我的牵挂”。诗人连用两个“突如其来”克制自己的情感,面对父亲的突然去世,梁平陷入痛苦的自责之中,“我无法面对这一天,手指犯贱/拨出一个不该拨打的电话”。他认为是自己不同寻常的拨出电话导致父亲的去世,再见面是面对父亲的墓碑。整首诗里没有一个词在明说痛苦,但读下来全是自责、遗憾与痛苦,是诗人的一种克制带来的情感体验。
然而,梁平不是一个面对痛苦就懦弱与逃避的诗人,在《人眼猫眼》里,“我”与俯卧翻转的猫对视,“我和猫在对视中的颠倒/猫可以顺势倒下,而我不能/决不”。在陌生的、颠倒的世界里,诗人不愿意妥协,他要做一个坚守原则,一个倔强的人。他甚至喜欢通过伤痛去体会生命的真实与快乐,“我从来不吃没有刺的鱼/就好像,我不喜欢/没有伤痛的快乐”(《鱼刺》)。面对死亡这一沉重话题,梁平却很旷达与平静,“之所以为人,只有生前的事/清清爽爽,死后才干干净净/不求视死如归,但愿了无牵挂”(《说说死吧》),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存在异曲同工之处。可以发现,梁平诗歌中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寻觅总是伴随着生命体验本就存在的艰难。梁平的勇敢和真诚之处在于,他通过诗歌展示了他的脆弱、痛苦以及面对这些的勇气和力量,而生命中无法避免的磨难变成了诗意,这种诗意让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发现希望,享受生活。
梁平以简洁又饱含情感的话语探寻城市历史与记忆,向外透过现代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剖析人性、观照底层,向内直面自我生命的痛苦与欢乐,追求最真实的生命体验,由此达到用诗歌探测生命的温度和深度的高度。将个人感受与外部世界融合在诗里,这种内外相结合所生发出的感受构成了他的诗意,也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和艺术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