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杨绛的文学与人生
2022-12-07李金涛
◆文/李金涛
本书结合杨绛的文学作品、学术成果、相关传记等一手文献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以“身份”为视点,从文化人格、性别身份、学者身份、作家身份等方面对杨绛的“为人”与“为文”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书中将杨绛的文学风格视为作家主体人格的外化,对杨绛的创作精神与审美趣味进行了阐发,并对杨绛之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意义进行了整体性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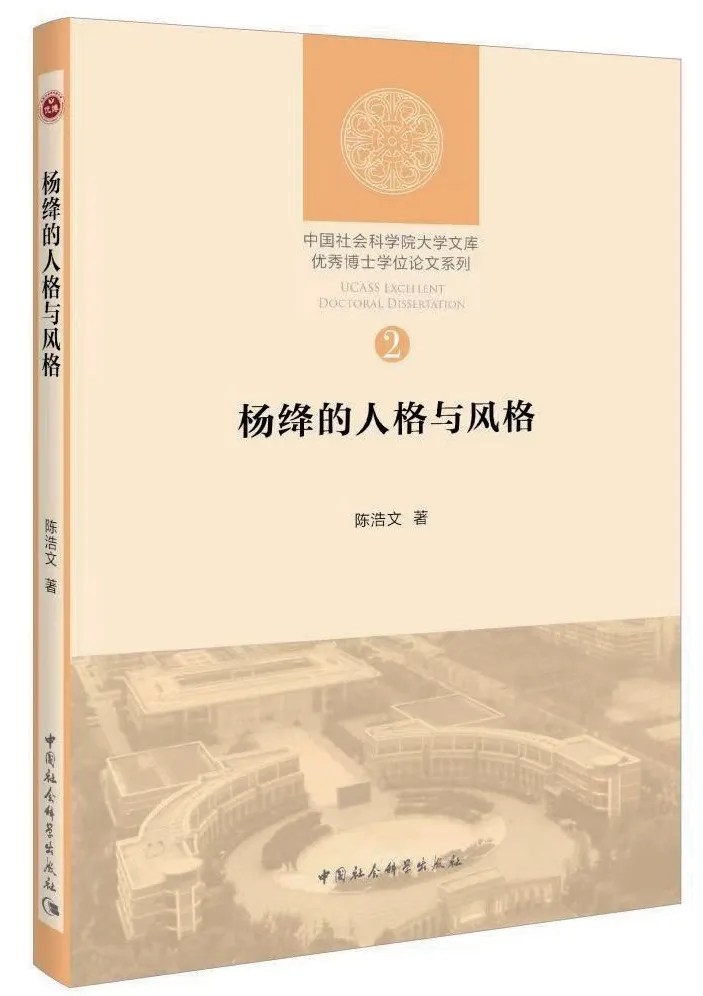
《杨绛的人格与风格》陈浩文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7/98.00元
陈浩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后,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若干论文,独立主持并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8批面上资助项目“杨绛与英国文学的关系研究”。
除了作为钱钟书的夫人之外,杨绛何以能被称为“先生”?这是许多读者面对关于杨绛诸多传闻时容易产生的疑惑。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随之而来的是网络上形形色色不知真假的名言金句。在“碎片化”阅读时代,由于普通文学读者缺乏系统的文学阅读训练,有时会不自觉地将文化名人“神话化”,而文学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专业的考证和阐释,尽可能地为读者还原真实客观的历史,展示经典作家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之所在。
杨绛龟鹤遐龄,她的文学生活贯穿了民国和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但总结起来,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成果在数量上都不算太多。她在坊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似乎都是与钱钟书才子佳人、珠联璧合的爱情故事。作为女性,杨绛为钱钟书付出良多。钱钟书能够心无旁骛地治学、创作,离不开杨绛对家庭的精心照顾。作为作家、学者、翻译家,杨绛却一直隐藏在钱钟书这位国宝级学者的光环之下。对杨绛的这种“隐身”,不少学者引为憾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研究所的董衡巽、薛鸿时两位老先生与钱、杨有过师生之谊,薛鸿时曾在他的文章中回忆自己与董衡巽结伴探望两位老师的往事。董衡巽在钱、杨两位先生家作客时,忍不住为杨绛抱不平,直言“其实杨先生才华卓绝,可惜被钱先生overshadowed(遮蔽住)了”。年轻弟子口无遮拦,钱钟书倒也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别人能这么欣赏自己的妻子。钱、杨两位先生如此相互爱护、相互欣赏,确实是知识分子夫妻中少有的模范,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杨绛“被遮蔽”,很大一部分原因与她为家庭作出的牺牲有关。


在杨绛逝世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审视杨绛的生平和作品,理解她的为人与为文,一方面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我们越来越需要一种值得追慕的生活,一段与我们当下生活有距离的、充满历史想象的文化记忆来安放当代人紧张、惶然、焦虑的灵魂;另一方面,作为从“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作家,杨绛的旧学根基、西学素养让她的写作、研究与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学者、作家有巨大的差异。以钱、杨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汉语语言上沟通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圆融和精深,是当代学者、作家很难达到的高度。
可惜的是,目前研究杨绛的论文有很多,专著却很少。在陈浩文的《杨绛的人格与风格》一书出版之前,国内杨绛研究领域的专著仅有于慈江的《杨绛,走在小说边上》、吕约的《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和火源的《智慧的张力:从哲学到风格——关于杨绛的多向度思考》三部。这些专著或以小见大,对杨绛的小说翻译与小说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专门而深入地阐释;或从审美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杨绛的小说、散文、戏剧分门别类地进行文本细读;或以整体宏观的视野,对杨绛的文学创作与不同时期文学史之间的联系进行考察。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从不同角度为杨绛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方法,但是这些学者对杨绛研究的重心基本都放到了对其文学作品的解读上。
作为近十年来杨绛研究领域的佼佼者,陈浩文与前辈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使她看到了杨绛身份上的复杂性,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搜集和对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为读者展示了杨绛身为作家、学者、翻译家和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此外,还有作为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如何看待这一身份;作为女性,婚姻家庭生活与杨绛其他身份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这些问题在陈浩文的研究中都得到了比较有趣的回答。
文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相比,特殊之处就在于其不仅需要学者具备严谨、务实的态度,还需要具备比一般文学读者敏锐许多的艺术感受力。只有把研究的理性和创作的感性圆融地结合在一起时,文学研究学者的学问才会充满生命的灵动。尽管从学术履历来看,陈浩文作为一位毕业不久的年轻学者,在许多方面与本专业领域的前辈学人相比尚显稚嫩,但年轻也意味着一颗种子的萌芽,一种尚未受到世俗生活过分干扰的、对学术纯粹的热情和天真。本书在陈浩文博士期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丰富,不仅增加了对杨绛生平唯一悲剧剧作《风絮》的文本分析,还将“风格”等范畴放在中西方文论的不同体系之下,进行了更加具有理论深度地阐发。这样的修改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内容,也使这本书在最后定稿时具备了相当的深度。
在编校书稿的过程中,笔者与陈浩文进行了多次沟通,历时近两年,经过八轮编校,终于使这本书能够比较完善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陈浩文在博士阶段的学习成果,《杨绛的人格与风格》从整体上用畅达而诚恳的语言为读者展示了一位青年学者良好的学术资质,分别从杨绛的文化人格、女性叙事、女性形象、主体间性思维、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创作与学术的关系、文学风格等方面对杨绛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而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与一般性普及读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学者需要向读者说明他的研究基础,也就是他所研究的问题是从本领域研究的哪个空白点“接着说”。陈浩文对海内外杨绛研究资料进行了集中梳理之后,发现以往的杨绛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记忆书写、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艺术风格、创作精神等问题上。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以往学术界对杨绛的定位首先是一位作家,然后才是学者和翻译家。这些研究成果在凸显杨绛作家身份的同时,忽视了杨绛作为学院学者作家与职业作家的差异;在以文本为中心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忽略了作家个体经验的复杂性。这些未解决的问题就是本书的阐释起点。

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场域对民国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趋于扁平化和流俗化。杨绛去世之后,自媒体炮制的所谓“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等名人名言将杨绛变成了一位心灵鸡汤写手,这种宣传不仅过分地美化了民国,消解了中国百年动荡的民族苦难,还将一位思想复杂的知识分子塑造成一个庸俗而甜软的小资“才女”,无疑是有损杨绛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
针对这些问题,陈浩文通过对杨绛从民国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文学作品的通读,从历史、伦理、个人生活经历三个方面考察了杨绛的文化人格与现代中国社会风气、学术思潮之间的联系。她指出清华“会通东西”的治学理念、京派文学的文化观念及审美趣味对青年杨绛在文化立场的选择上有所影响,使她偏向于成为一个自由的旁观者。20世纪40年代,复杂的婚姻家庭生活和艰苦的抗战生活使杨绛从个体生存的感悟中进一步拉开了与时代主流思潮的距离,形成了一套以“含忍”与“自由”辩证法为核心的生存哲学。杨绛的这套生存哲学在国难当头的年月既有家庭伦理层面的意义,又有公共道德的意义。1938年,钱钟书与杨绛二人归国,此时钱、杨两家均已避难至上海,为生存生计,钱钟书远赴外地,照顾一大家子的重担就此落在杨绛一人身上。这一时期,杨绛不仅要带着女儿对长辈尽孝,还要冲破钱家旧式家庭的规矩,想办法出去工作、补贴家用。杨绛在抗战时期曾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女士之邀帮助筹备分校,此事曾在钱、杨两家家长之间引出了一点亲家之间的矛盾。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位有些古板的老先生,不大喜欢儿媳妇在外抛头露面;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则是民国早期的“海归”,鼓励女儿独立,因此对亲家的观点很有意见。在新旧家庭的纠纷下,杨绛拿出“含忍”的姿态调和了外部的矛盾,同时也没有失去内心的自由。
这种“含忍”在公共道德层面体现为她的喜剧创作。杨绛在抗战时期没有直接参与左翼作家群体的抗战文学创作,但是她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喜剧作品为长夜漫漫下的沦陷区人民带来了笑声和自信。这种“笑声”如杨绛所言,是在艰苦的生活中“保持乐观的精神”,这正是中华民族能够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杨绛的“含忍”不同于传统士大夫对“仁”道的维护,也不同于“五四”之后部分知识分子的玩世和颓废。杨绛的“含忍”是基于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怀疑,一种主动下沉的“市隐”姿态,所指向的自由是一种调和了传统与现代、极具中庸色彩的自由。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含忍”与“自由”的辩证法在杨绛晚年时期形成了充满西方人文主义痕迹和变通的儒家“守死善道”精神的审美趣味。从杨绛晚年发表的《窗帘》《隐身衣》等散文来看,这样的审美趣味包含了三层内容:一是在积极的入世姿态中进行的道德自我超越;二是回归民间智慧的古典喜剧精神;三是在冷眼旁观中保存的天真趣味。这三层内容都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对杨绛人格塑造的影响力。
对一般读者来说,杨绛出名主要是和她圆满的婚姻生活有关。在部分文学研究者看来,杨绛研究的热潮根本就是搭上了“钱钟书热”的顺风车。这些印象有意无意地将杨绛变成了钱钟书的附属符号,消解了她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独立性。而陈浩文通过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问题的历史化梳理,指出要从性别视域对杨绛的为人与为文进行价值重估,并对杨绛进行目的层面的价值解读,也就是说,在进入杨绛的文学生活时,不仅需要看到杨绛塑造的两性形象,更要看到杨绛在创作这些形象时是如何看待自己作品中女性与男性的生存境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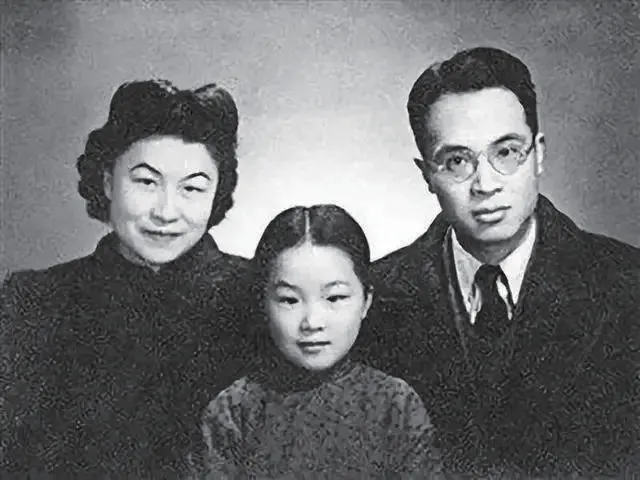


从女性身份对杨绛的创作与生活进行阐释,还意味着要重新去审视杨绛作为“钱钟书夫人”的这个身份。基于此,陈浩文对杨绛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叙事、女性形象以及主体间性思维等问题进行了缜密地分析,指出杨绛不同于同时代女性作家如冰心、陈衡哲、张爱玲、萧红等人在女性身份认知上的复杂性。从杨绛文学创作的整体状况来看,她并没有像同时期的女性作家群体一样建构出一个需要被打倒的父权世界,用同情的目光来看待庸常的世俗生活中男女皆不得自由的生命状态是杨绛在文学创作中的基本态度。比如杨绛在《我们仨》中塑造的钱钟书形象,一般读者对钱钟书天真、痴气形象的认知基本上都来自于杨绛的文学塑造。杨绛对钱钟书的这种塑造方式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动机。一方面,杨绛作为妻子、朋友,十分欣赏钱钟书在学术上的纯粹,不自觉地放大了他的优点。另一方面,杨绛也深刻地理解钱钟书作为旧式家庭中的儿子,他在父亲钱基博面前是怎样一个“未长大”的形象。《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一文被部分读者看作杨绛不尊敬自家长辈,不懂得为尊者讳,随意贬低老先生的一个证据。但如果从女性的视角看,杨绛对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历史公案做出这样的辩护是完全解释得通的。在这篇散文中,杨绛不是以儿媳、妻子的身份在为钱氏父子任何一方断案,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女性在审视旧式家庭中的父子关系问题。对处于旧式伦理秩序中的男性生存状态的审视,不仅是杨绛在散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她在小说创作中的一个聚焦点。这种审视的姿态在陈浩文看来,有利于让研究者回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去考察女性文学面貌的复杂性。
此外,作为文学学者,杨绛在学术研究上的成绩曾经长时间被人忽视,陈浩文在书中也对杨绛的菲尔丁研究、李渔研究等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她指出杨绛的学术研究虽然起步晚,论文数量不多,但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杨绛学贯中西的学术积累。以杨绛的菲尔丁研究为例,陈浩文认为杨绛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将菲尔丁作为她的研究中心,虽然从历史表象上看是受制于当时的学界风气和学术要求,但是杨绛这种“戴着脚镣跳舞”的研究方式是以她对英国文学发展精神脉络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杨绛的翻译同样能显示出她的深厚学养,陈浩文根据杨绛“借尸还魂”和“一仆二主”的翻译理念及翻译策略,指出杨绛的翻译活动贯彻了她的文学创作精神。翻译被杨绛视为文学创作的变形,这也就决定了她的翻译活动偏重从实践中获得经验而较少谈及纯理论问题。
杨绛作为一个学院学者作家,不像职业作家一样把文学视为一项事业,她的文学创作具有业余性和自娱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以往的杨绛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因此在本书的第五章《杨绛创作与学术之关系》中,陈浩文集中讨论了杨绛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互动的情况,通过对杨绛求学经历、阅读经验与文学创作经历等方面的历史材料的考察,揭示了杨绛文学创作中题材的选择、审美的偏向、结构故事的方式都受到了她的读书生活的影响。文学知识和理论上的丰富储备让杨绛在创作上具备了不同于一般职业作家的理性、智性之特征,而学院生活的限制也不可避免地让杨绛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存在题材反复和人物形象同质化的问题。
然而“风格”这个概念在中西方文论中的指涉虽然有很多差异,但是在作品意义及价值层面上存在共通之处,也就是说,作家的道德人格不能等同于作品的风格,而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也不可以完全脱离作家人格而论。据此,陈浩文在第六章《杨绛的文学风格》中指出,作为一位现代女性学者作家,杨绛的学者身份、女性身份对她文学创作生涯产生的影响使杨绛的“为人”与“为文”存在很多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杨绛文学创作中探索人性时流露出的宽容和同情,在情感表达上的节制和冷静,在语言形式上的和谐雅正,无一不是她人格精神具象化的表现。
在本书的结语中,陈浩文还对杨绛之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意义作出了一个整体性的判断。她认为从文学成绩来看,虽然杨绛未必能够跻身一流作家的队列,但是她的为人与为文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作家乃至普通读者来说,都有值得借鉴和追慕的地方:其一是杨绛作为知识分子,面对人性困境作出的无愧于知识分子气节的选择;其二是杨绛作为现代知识女性,悦纳自我的自尊与自信;其三是杨绛亲切可学的汉语写作之章法,让人看到她作为一位历经百年风云的现代女性学者作家的人文价值。这种判断是陈浩文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杨绛的深入理解。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对于杨绛何以能被称为“先生”这个问题,一定可以获得一个颇具启发性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