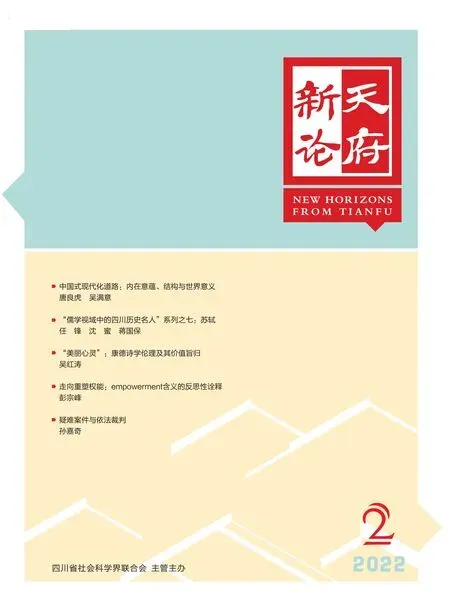民族认同的历史建构:徐则臣《北上》的拯救叙事
2022-12-07高志
高 志
徐则臣的《北上》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彰显其独特的小说想象与另类的历史建构,“带有个人体温的历史,一个人的听说见闻,一个人的思想和发现,一个人的疑难和追问,一个人的绝望之望和无用之用”(1)徐则臣:《徐则臣的获奖演说:历史、乌托邦和文学新人》,《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作者以具体的物理实存——京杭大运河为纽带,从现实和历史两个维度凭借文学形式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历史链条。作者不断填充民间历史空白点,将缺位的民间生活、人事、风俗呈现在笔触之下,虽然小说情节的链接点多为偶然和巧合因素,但作者的着重点并不在民间历史的建构上,而在于如何处理传统与现在、中外、历史和未来、政治和民间、战争和个体、人的内心和行为的关系,徐则臣“试图给出属于自己的理解和阐释”(2)张艳梅:《“70 后”作家的历史意识》,《上海文学》2017年第5期。。
在小说中,冲突、矛盾、战争、仇杀、械斗、河盗等多元语境糅合,生产出复杂文本,也反映出现实存在实景:人与人、中外、政府和民间、江湖和外在力量、异信仰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作者的创作旨归并不是带领读者去历险和创造传奇,也不是盛赞运河文物连城的价值与运河人家一脉相承的家风,徐则臣重点表述人与人之间隔阂的消除与和谐关系的创生,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沟通和真情存留。因此,小说传达出拯救的信息,中国人和外国人、义和拳成员和外国人、邻里之间、家庭成员、男女恋人、父子关系由对立到和谐,其改变历程、轨迹与运河时空密不可分。运河不仅是触媒,更是一个“活”的流动的建构物,永远在路上。从这一层面上说,拯救叙事在时空的伸延中获取价值。
河流超越了政治、种族、语言和战争,具有弥合纷争和矛盾的自然功能:缝合创伤、促成婚恋、繁殖生产、加强中外交流。河流不仅是想象的空间表达,更是河流自然功能的缩影。运河的废流终止了河流的拯救功能,而申遗成功则表明拯救意识的复苏和拯救实体的转型,这是后现代操作。运河历史的变迁凸显了河流对民间生活、中外关系、传统和现代、历史和文化的持重。徐则臣如何在运河和历史之间搭建桥梁的呢?在小说中,作者拯救了什么?如何拯救?文本内外存在怎样的关联?本文将对此做出探究。
一、拯救什么:运河、历史抑或文学
小说《北上》是一个复杂文本,它既关涉运河本身的兴衰变迁,又与历史文化和民间生活密切相连,更与文学想象密不可分。那么,作者到底在表达什么?作者又是如何处理地理标志、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的呢?
运河“活着”生产历史,“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3)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466页。历史包括正史和野史。小说《北上》以文学虚构的方式还原野史,将民间生活、家族史和个人史通过自然媒介呈现出来,这个自然媒介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已经废止100多年,运输功能也已经荒废,运河的“死”将鲜活的历史埋藏起来。作者崇尚“动”,在小说中安排两个行动元来让运河动起来:一个是迪马克兄弟的中国运河行,一个是谢望和拍摄《大河谭》。迪马克兄弟的运河行由南朝北,串联了运河的各种要素,如地理标志、运河景观、运河民众、漕帮、殖民者、外国观光者、教会人员、大刀会、政府衙门、妓院、义和拳等。谢望和借助拍摄运河纪录片唤醒运河的历史以及两岸民众,以家族史的方式串联起五家运河子民,并以影像这一现代方式重新发掘潜在的运河文化,即以现代方式唤醒运河。其中,周海阔在运河岸边的连锁客栈和沧州等地的运河景观带设置,是运河产业转型的表征,运河的文化通过新的方式仍然存留和凸显。两种行动元的设置使运河动起来,历史和当下衔接,中外因素勾连,流动的运河与国家、平民和外国人士的命运纠缠在一起。
小说既有运河的详细资料,又对运河景观、两岸风土人情进行勾勒,更与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勾连,一条运河就是活着的过去的中国。从国家层面上讲,运河于1906年废止,而对运河时代的人民而言,运河已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潜移默化地操控着他们的生活。作者书写运河,意图将运河与各阶层联系起来,以串联的方式,以主河—支流的结构方式来审视家族史和河流的关系。运河不仅是载体,还是本体,作者强调运河的自我净化功能。历史上的运河生态良好,河民以运河为生,而今天的运河生态遭到破坏。运河除了自然功能外,还具有审美功能。保罗·迪马克一路上欣赏运河风光,并在行进中深深地爱上了运河,将自己的生命与运河融合在一起。他的运河旅行、埋葬于运河边以及其弟真正扎根运河边的事实,象征和隐喻老运河的人格建构功能。归根结底,这是作者的文学建构。
运河只有活起来,才能完成人物及人际关系的建构,才能够在行进中透视人与运河的关系。小说借鉴游记探险和拍摄纪录片《大河谭》的形式使运河“活”起来。自大运河废止后,济宁以南还在使用,而济宁以北(德州、沧州)则荒废,河道渐隐渐现。运河自隋开凿以来一直是漕运的重要通道,尤其明清以来成为京城物资的重要支撑,沿河两岸的百姓也以水为生,纤夫、运输船、船民、码头、漕帮、旅店酒馆、修船厂,这些名词与运河口唇相依。运河的衰落影响到两岸民众的生活、职业和习惯。如河运业不景气,邵星池坚持上岸,筹办修船厂,但河运业冷清导致修船生意难以维持。运河还成为外国势力侵入的焦点地区,“利益均沾”,各国列强相机操纵运河生意,且拥有免税特权而集聚大量财富。保罗·迪马克的船只过闸时,挂上外国旗帜,就可以优先免税通过。运河成为权力博弈和表征的物理空间,小说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和它的现代性”(4)杨庆祥:《〈北上〉:大运河作为镜像和方法》,《鸭绿江》 (下半月版)2019年第2期。。
当然,运河两岸也是传教士较早登陆的地方,运河为他们提供了便利通畅的通道。小说描述扬州、沧州、济宁、天津等地的教堂和教会医院。作者书写教堂及教会人士,并没有将它们污名化或丑化,而是以理性的态度视之,区别对待。孙过程老家的圣言会帮助教民与大刀会对抗,教会以群体利益为主的帮派意识有殖民的嫌疑,但个别教会为当地民众提供教育、医疗和物质帮助,深得人心,他们与当地民众形成和谐的共生关系。与征收重税、不顾人民死活的天朝政府比起来,外国传教士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所以当教堂将要被焚烧时,当地民众愤而维护教堂利益。在这里,作者没有美化传教士,而是还原传教士存在的真实状况,作者不认同对传教士一概污名化、丑化和妖魔化,从创作的层面看,徐则臣“寻求历史叙事的变异”(5)江飞:《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与形式意识——徐则臣论》,《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1期。,展开另类历史叙事。
作者采用双线叙述:一条是北上,另一条是南下。北上包括保罗·迪马克的北行以及费德尔·迪马克从天津到北京的婚恋和运河生活,本线索以传奇、历险形式建构民间历史;南下则是对当下运河的历史发掘,旨归在唤醒和重建运河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北上中,运河的自然、审美、文化功能展现出来;在南下中,作者梳理了历史和当下一脉相承的纹理,以对家族史追溯的方式复活运河。“家族史又往往与地方志相杂糅。 ”(6)郭冰茹:《家族史书写中的 “历史真实”》,《山花》2018年第6期。无锡、扬州、高邮、淮安、济宁、天津、北京,地理空间的往复移动,复活了时间,建构了民间的生活史,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展布了历史的褶皱。
运河自然功能的衰退或终止,并不能遮蔽其文化和审美功能的存留,申遗、纪录片、文物发掘以及沿河风景带的建设,正是运河现代转型的表征。马可波罗、小波罗运河行和申遗是运河内引、外联的象征。运河超越种族、国别,具有人类学考察的意义。作者旨在对运河进行终极思考:运河的生与死、存与逝。运河归根结底是河流与人的关系。
作者不仅交代生态问题,更主要的是书写了政治和文化问题,并最终超越了单一的政治、经济、国族、信仰和文化视角,从人类学的角度反思历史。徐则臣带着“70后”理解和温和的态度,审视河流、外国人、传教士、船民、义和拳、大刀会和战争。“70后作家是富有宽容度和富有弹性的,他们与社会和世界的关系是善意的和和解的,他们具有仁爱和温和的美德。”(7)张莉:《关于70后小说家的写作难局》,《文学自由谈》2011年第4期。通过对运河人民共同感的发掘和梳理,凸显了运河的凝聚力、召唤力和生命力,作者将这一流动的自然景观人性化,体现了作者的人类学视野和博大的文学理想。
那么,作者具体怎样讲故事,又讲了哪些故事?
二、如何拯救:考古、拍摄抑或讲故事
徐则臣传达拯救意识,采用考古、拍摄和讲故事相结合的方式。“只有经过形式,我们才能进入真正的艺术领域,进入从客体到形象的转化过程之中。”(8)马里奥·佩尔尼奥拉:《当代美学》,裴亚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7页。小说先以龚自珍《己亥杂诗(八十三)》和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名句导入。龚自珍的选诗记录其行走运河时由景寄情对故乡的思念与深情,运河成为龚自珍回溯历史和地域的载体。加莱亚诺的“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近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交代了作者的创作内旨——过去和现在密不可分。作者从感情和哲学的高度点明创作的主线,它处理的是运河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过去和现在是小说的两个时间维度。
小说以运河申遗前夕运河济宁段出土大量文物和日常船上生活用品为背景,从考古报告和发掘的信件入手,考古报告以丰富的文物勾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再加上本世纪初的文物热、盗墓文学热,为小说预热。一封意大利人的家信将运河与历史贯通起来,这是小波罗的弟弟费德尔·迪马克的战地信,陈述了自己抱着对运河的喜欢来到中国,却被迫参与战争,“当年的我的大偶像,马可·波罗先生,就沿着运河从大都到了中国南方”(9)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页,第335页,第336页,第413页。。作者通过信件结构故事,将运河与外国人的关系延伸到历史中去。马可·波罗游记将中国介绍给西方,中国的辉煌形象吸引西方人到东方探险,掀起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的序幕。依照蝴蝶效应理论,运河间接催生了现代世界的诞生。作者重启这起事件,以仿拟的模式演绎新时段的运河效应,期望发掘运河的多重功能。
徐则臣依据信件设置人物、结构情节、布展故事。故事发生在过去和现在两个维度。过去包括两个故事:一个是费德尔·迪马克的战争经历和恋爱生活经历,他以运河为始终;另一个是以其哥哥保罗·迪马克为中心,旁涉谢平遥(河衙翻译)、邵常来(挑夫、厨子)、周义彦(船员)、孙过程(护卫)等人。这两个故事都将中国的历史大事牵扯其中,故事、河流、政治和文化纠缠在一起。现在维度上以拍摄运河纪录片为主线,将邵家、谢家、周家、孙家和胡家(费德尔·迪马克的后代)汇合起来,最后在“小博物馆客栈”汇合,以大团圆的结局与北上故事人物群形成呼应和循环结构。小说吸取中外游记文学、传奇、侦探小说的优长,揣摩读者的接受心理,采用类似说书人(花开两朵,先表一枝)的讲述方式,传统和现代糅合,古典和时尚并行,在现代形式下复活了运河。而在现代社会,现代运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高速度,而河运行业无法达到现代运输的需求,成为“夕阳产业”。但作者从非经济学的角度,赞赏河运行业的慢,将之视为一种风景。从思辨的角度看,它又是“快”,它带有不可复制的传统文化的光晕,成为标准化现代社会的后现代风景。济宁以北的运河废止,而沿河的运河风景观光带建设不仅带有文化凭吊韵味,而且功能更变适应了现代社会对城市人文景观的需求。从这些层面上看,运河没有脱离人们的视线,只是改变了存在的形式,它仍在发挥审美、文化和休闲功能。孙宴临拍摄的邵家船民生活和结婚场面的照片,谢望和的纪录片,周海阔的运河客栈,它们既是对古老运河的凭吊,又是对现代运河的建构。
运河除运输、凝聚、审美和文化休闲功能外,它还促使人的认知和世界观的改变。小波罗起始并不是来中国寻找马可·波罗足迹和体验运河文化的,其真实目的是寻找先前到中国的弟弟。他也并不真正喜欢运河,但当他从无锡出发,与运河以及中国民众朝夕相处后,在天津临终时,吐露真言,深深地爱上运河及中国人民,“我的呼吸更与这条河保持了相同的节奏,我感受到了这条大河激昂澎湃的生命”(10)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页,第335页,第336页,第413页。。运河还促使费德尔·迪马克的认知发生了改变,“它用连绵不绝的涛声跟我说:该来就来,该去就去。就像这条大河里上上下下的水,顺水,逆水,起起落落,随风流转,因势赋形。”(11)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页,第335页,第336页,第413页。
费德尔·迪马克逃离战争,运河为他提供了遮蔽所,更为他与秦如玉相见、相恋提供了场地和惊险的经历。费德尔·迪马克目睹战争惨状,逃离战争。他喜欢中国年画艺术和中文,并改名马福德,最终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并与秦如玉生活在运河岸边,以渡人为生。他最初因运河而来,最终超越了时空局限,“我一直以为马可·波罗很重要,运河很重要,后来我发现,跟如玉比,一切都不重要”(12)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页,第335页,第336页,第413页。。在马福德的最终启悟中,运河只是载体,是他爱情、亲情的媒介,而没有像小波罗那样从中寻出人生哲理。但在马福德的生命中,运河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运河,就不会遇见秦如玉,所以,他叮嘱儿子自己死后葬在与秦如玉相遇的地方(运河边的风起淀)。
徐则臣从考古发现中找寻线索,并进行文学虚构,在现存的物体之间搭建桥梁,如拐杖、信、笔记本、罗盘、相机、意大利挂饰、运河文物,通过物将人联系起来。遗物传递的信息,不仅仅是感情和价值,更重要的是文化。在小说中,遗物超越时空,在家族史中起着决定方向的作用。遗物发散着旧时代独一无二的光晕,家族的人在神圣故事的引导下,不断地向它及其文化靠拢,家族职业、生活、习惯和志趣趋向一致。周义彦得到小波罗的意大利语笔记本,他的子孙通过出国或自学获得较高的意大利语言能力;周海阔更在运河两岸开设连锁客栈,搜集运河文物;邵常来得到小波罗的罗盘,邵家世代为船民;谢平遥作为知识分子(翻译专家)陪小波罗北上,获得与运河相关的书籍和资料,其孙谢仰止一直希望沿着运河到北京体验祖先的荣光,其玄孙谢望和拍摄《大河谭》;孙家被赠与相机,改武习艺,后代执着于绘画和摄影。与其说物和人之间存在权力关系,不如说是文化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更深层面上讲,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物将运河、遗物和人链接起来,这一链条结构了线性的同类故事。
故事是小说的内容,遗物成为故事的原点,它结构了几个不同职业的家庭,但他们的情感倾向和信仰具有共同点,即共同沐浴在与运河相关的祖先荣光中。共同情感的小集体是结构故事的基点,但也会产生文学上的缺陷,家族史的单一化影响了文学的丰富性,同时遮蔽了家庭小单位的丰富性。在这一层面上,可以看出小说的单调和贫乏。
但不可否认的是,运河内在的凝聚精神,尤其是活起来的运河更加有力。运河上的喜怒哀乐、创伤和荣光,都会烙印在文化之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三、情感共同体:发现民众
在小说中,情感共同体的形成为战乱、贫穷、语言隔阂和孤立无援的民众提供了共鸣和支撑的平台。作者交代了多组情感共同体。这些情感共同体与运河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同类别的情感共同体使所属民众有了归属感,它们共同维护和保持成员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在这些情感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成员进行自我归类。 “当人们需要与某一群体产生共同联系以获得某种归属感或话语权的时候,群内个体或群体在重要的维度上会放大自身群体与别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并且根据类别成员的共同特征知觉自己或他人,形成刻板性知觉。”(13)钟媛:《代际意识与徐则臣的小说创作》,《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6期。在小说中,存在大刀会、漕帮、圣言会等情感共同体,共同体内部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且对他者共同体有明显的排外情绪。圣言会与大刀会对峙,漕帮与官府泾渭分明,而义和拳与外国人之间存在刻板的认知局限。通过阅读,我们看到中国民间情感共同体的存在,运河将他们串联起来,成为民间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体。
上文论述了北上五家形成了情感共同体,他们情感的最终所指就是京杭大运河。家族的光荣与耻辱,职业与兴趣都与运河密切相关。运河运输业成为“夕阳产业”,邵秉义仍然坚持不离船,保持船上的生活习惯和风俗。运河不仅赋予祖上荣光,他的个人成长也离不开运河。虽然大儿子葬身运河,但并不能改变他对运河的深情。邵星池卖掉了祖传罗盘(船业象征),邵秉义倾其所有不惜一切代价将其赎回。邵星池后悔欲赎回罗盘,彰显了家族情感的根深蒂固。周海阔在听到邵星池尤其邵秉义对赎回罗盘的解释后,运河情结产生共鸣,他们祖先都有辅佐一位外国人北上的经历,主动退还遗物,甚至不再要求退钱。情感共同体将他们黏结在一起。谢望和请求孙宴临参加运河纪录片拍摄,孙宴临严词拒绝。但当谢望和讲述其家族史后,她深受感动,并最终与谢望和走到一起。谢望和的父亲和堂伯谢仰止由于当年推荐大学生的矛盾拒绝认亲,谢仰止纠结的不是上大学后的待遇和出路问题,而是纠结于再也不能像祖先一样顺运河北上,重走运河路。运河的情结是揭开他们兄弟误会的钥匙。
谢家、邵家、周家、孙家和胡家在运河的感召下,重新聚集成一个情感共同体,共同投入《大河谭》的拍摄,重新复活100年前祖先结成的情感共同体。他们的祖先形成的共同体(费德尔·迪马克除外),不是一开始就存在情感共鸣,而是在共同历险的过程中形成的。北上伊始,小波罗(外国人身份)具有财势双重优点,谢平遥受朋友托付,邵常来、老夏船长及徒弟(包括周义彦)为了丰厚的报酬,旅途中老夏船长及徒弟惧险退出,加入了老陈夫妇和孙过程。可以说,在北上中,他们是命运共同体:谢平遥常常将中国人对小波罗的咒骂翻译成赞语,不断化解矛盾,以语言的遮蔽和有意的误译缓解敌意;小波罗对谢平遥很大方,平等对待;参加过义和拳的孙过程起始对小波罗充满敌意,在接触过程中,外国人被妖魔化、污名化的形象得到澄清,发现“传说中凶神恶煞,抽中国人的筋,扒中国人的皮的家伙竟能如此亲和”(14)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84页,第184页。。小波罗在与大家平等相处、共患难的旅途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去世前夕,将身上财物分给大家。旅途终结,命运共同体结晶为情感共同体,“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支出缔造了一个情感共同体”(15)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84页,第184页。。共同体形成的同时,小波罗也与运河真正融合在了一起。
费德尔·迪马克与大卫同为厌弃战争者,他们共同沉浸在运河的年画艺术中。对中国民众的勇敢、善良和艺术充满崇敬和赞赏之情,尤其是费德尔以马可·波罗为偶像,从内心崇拜运河和东方艺术。他与秦如玉结成连理,学着改变自己,改名马福德,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与中国人的“差异在无限地缩小”。“家庭首先应该是一个情感共同体,是人们生活的最基本的归宿和港湾。”(16)秦前红:《新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马福德的孙女取名“马思艺”,重孙“胡念之”,是对马福德的追念。马福德还为了秦如玉枪杀多名日本兵,并嘱咐儿子将其埋在运河边上。马福德家族与运河的关系凸显了政治之外的情感共鸣点。中外抑或东西的对立是建构的对立物,对二者的概指和统一化标称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妖魔化处理更是极端行为,如义和拳将西方一概而论,从而抹杀了个体特征,小波罗丧命与此有关。
小说中多处写到教会与民众的关系。如圣言会帮助信教群众出头对付大刀会、山东“巨野教案”等,教会成了邪恶魔鬼的代名词。作者并没有随声附和,追随教材概念化的定论,而是通过查史料和田野调查,发现并不是所有教会人士都怀有邪恶之心。如沧州二道湾教堂,孙过路按照义和拳上级命令进行烧杀,教会人士戴尔定自杀,尸体被烧。方圆近百号百姓号啕大哭,跳圈凭吊戴尔定。从他的遗信可知,他不远万里,到中国帮助贫苦民众,帮他们重建信仰,他与周围民众形成了情感共同体。
徐则臣发现了100年前运河边上复杂背景下情感共同体的存在,这是作者跳出教科书上刻板的历史窠臼,与民间共情而得到的成果。“作家只有放下姿态,把自己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与大众水乳交融的情感共同体,真正在思想上、情感上融入这个群体,他的笔下才会流淌出带着他们情感温度的浓情和诗意。”(17)马忠:《忠言忠说》,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2页。小说从而呈现他种历史风貌。
作者揭开运河表面的遮蔽物,发掘运河传统和现代的价值与意义,研究民间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机制,绘制运河疗治自然和战争创伤、消除种族隔阂和超越狭隘民族观的拯救路线图。那么,作者的拯救思想从何而来?它又是如何成型的呢?
四、拯救来源:文本内外
徐则臣是“70后”作家,身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语境,社会相对较为开放,有丰富的创作资源可资借鉴,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潮流及经典著作成为他模仿的对象。徐则臣最早创作的“花街”系列,如《花街》《镜子和刀子》《石码头》《梅雨》《水边书》《人间烟火》《失声》等,是对苏童的“枫杨树故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棣花街”个人写作标签的仿作。不同的是, “花街”不是他的故乡,只是求学的地方。他对“花街”没有莫言他们对血地那种痛彻心扉的情感。所以,徐则臣早期的创作焦点放在对淮安景观、风俗、遗迹以及理性的思考上,死亡和出走是两大主题。而在随后的以北京为地理空间的小说中,如《啊,北京》《天上人间》《伪证制造者》《跑步穿过中关村》《耶路撒冷》《王城如海》,作者求学、北漂多年,挣扎于社会底层,将其切身感触记录下来,善于书写底层边缘者的失败和困境及社会荒谬,但又不仅仅沉浸在苦难的书写中,而是带着嘲谑、幽默的态度以“含泪的微笑”书写人与城市的关系,且探寻人物的内心力量,发现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如《耶路撒冷》思考如何重建人生信仰问题,如何在重新认识世界中认识自我,“到世界去,归根到底是为了回到自己的世界;当然,这一去一来,你的世界肯定跟之前不一样了,因为你由此发现了更多的新东西,重新认识之后的你的世界可能才是世界的真相”(18)徐则臣,张艳梅:《我们对自身的疑虑如此凶猛——张艳梅对话徐则臣》,《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6期。。
小说《北上》联结历史和当下、中外、民众与政治、现代与传统,作者寻找人类存在的情感共同体,且重新审视运河、历史、政治、战争和人性,以拍摄纪录片和重走运河路双线来发现存在的意义。这与《耶路撒冷》中的双线设置、人物结构和思想内涵有类似之处。《耶路撒冷》 “主线基本遵循传统故事的惯例,按时间顺序纵向展开情节序列,但在各个事件的安排上又以‘景天赐’及其自杀为焦点,围绕此焦点分述以五位主人公为核心的次要事件,从而在情节链上形成焦点凸出、前后对称又彼此咬合的‘齿轮’结构;副线则以初平阳为《京华晚报》撰写的‘我们这一代’十篇专栏为主体,使情节又如蜘蛛网般蔓延开来。”(19)江飞:《〈耶路撒冷〉:重建精神信仰的“冒犯”之书》,《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可以说,这完全是《北上》结构的翻版。《北上》采用两条线索,没有主副线之别,双线交替进行,两条线索互相印证。第一条线索以小波罗北上集结五个家族的先祖(马福德虽然单独由天津到北京,可视为小波罗北上的分支);第二条线索以拍摄运河纪录片汇集五个家族的后人,情节比第一条线索散漫。这两条线索在历史和现实层面激活运河,并在运河苏醒中,发现民间情感共同体的形成轨迹,由外在的文学建构转为内在的人类学问题,跨越国别、政治和战争的局限,探索人类共存的心理情感机制和超越性意义。
徐则臣重写历史,是以非虚构为基点的。在《北上》写作过程中,作者实地勘察大运河。“这一路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改变了我对运河的很多想法。确是‘绝知此事要躬行’。……它还给了我另一个想象世界的维度,那就是时间。”(20)李婧璇:《徐则臣:河流堪称我文学意义上的原乡》,《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8月23日。徐则臣在田野调查和实地勘察的基础上,展开想象,渗透思想,既考虑运河的空间和历史,又想打开历史的褶皱处,发掘和填充历史的空白。当然,这种发掘和填充是有一定的思想预设的。思想的生产建立在庞大的资料收集和材料积累上,也是作家人生体验和知识升华的结晶,而非突发奇想的另类创新,是脚踏实地的民间发现和被遮蔽的小历史。如对义和拳、教堂人士、外国人、战争的理解,作者超越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悬置了正义的战争和死亡”(21)徐则臣:《徐则臣的获奖演说:历史、乌托邦和文学新人》,《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站在人类学的高度,思考人在战争、复杂社会环境下的困境和处理方式。如在孙过路家与赵满桌家因沟渠灌溉问题出现矛盾时,赵满桌老婆动用哥哥所在的圣言会,而圣言会并不想参与群殴,但为了更好地树立和维护圣言会形象,无奈参加,并警戒持枪者不得擅自发射。实质上,圣言会遵循的是民间互换实用伦理。而孙家召唤的大刀会基于义气和排外心理参加,最终由于误射导致孙过路父亲去世。孙家兄弟愤怒报仇。然而,当看到赵满桌女儿那种可怜的穷苦相时,共同的命运感油然而生,他们最终放弃复仇。这是民间历史,也是处在庙堂之远人的发现。 “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是个‘现代性’的问题,如果你不去质疑和反思,不去探寻和追究,永远不会深入到人物内心。”(22)徐则臣,张艳梅:《我们对自身的疑虑如此凶猛——张艳梅对话徐则臣》,《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6期。徐则臣从问题意识入手,发现他者历史,即民间历史,“不管是关于历史的叙事还是现实的表现,都是深处当下的人所意识到的问题”(23)陈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徐则臣书写历史,继承新历史小说,但没有踏上老路,而是另辟蹊径。新历史写作是对旧历史写作进行反驳,注重个人视野下的历史重构。先锋派率先开启新历史小说的大门,他们“远离历史与现实,以形式主义实验来叙述他们并不真切的历史,与经典历史叙事构成明显对立”(24)陈晓明:《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8页。。格非的《欲望旗帜》《青舟》等采取有限的个人视角,且以“空缺”“留白”构建历史迷宫。苏童的《红粉》《妻妾成群》《帝王生涯》等新历史小说以个人虚构为核心,多采取第一人称,在历史的氛围下,书写个人在权力争斗中的心理、语言和行动,彰显个人的历史困境。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等小说从民间个人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历史,将战争、酷刑、运动等正义问题摒除在外,探寻底层民众、边缘人群生存的策略和路径。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将乡村存在史揭露为权力的变迁史,权力争斗围绕个体利益展开,作者将乡土还原为赤裸裸的个人利益争斗场。乔良的《灵旗》以非虚构的史料入手,书写湘江之战,将红军残酷的被杀戮场面、血淋淋的现实展示出来,祛除了乐观英雄主义浪漫色彩的遮蔽,以一个个残杀红军的小事件为点通过青果老爹串联起来,更加凸显红军当时处境的艰险,乔良将焦点放在现实的真实基点之上。徐则臣的《北上》既非五四启蒙叙事和田园牧歌叙事,也非共和国文学中的阶级斗争叙事。
作者在历史和文学虚构中搭建一座桥梁,想象成为建构小说的关键部件,但其想象建立在实地勘察、地方史志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纪实的是这条大河,虚构的也是这条大河。……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25)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464页。徐则臣的文学观并不拘泥于事实或虚构,而是巧妙地将两者结合起来。当然,作为“70后”作家,徐则臣无形中带有代际烙印,具有浪漫主义的文学理想,是“最后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了”(26)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作者对河流的书写,是“文学意义上的原乡。”(27)李婧璇:《徐则臣:河流堪称我文学意义上的原乡》,《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8月23日。徐则臣青年时期生活在淮安(运河重要码头),对运河遗迹和文化涉猎较深。他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思考运河如何影响人民生活以及人民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这一方运河岸边的人是如何走到了现在,又为什么只能走成现在的模样”(28)李婧璇:《徐则臣:河流堪称我文学意义上的原乡》,《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8月23日。。
徐则臣的思考不是对运河价值及其子民生存意义的盖棺定论,而是发掘和激活运河,寻找内在的文化承传,对行走着的中国人感兴趣,“对走在半路上的中国人感兴趣”(29)徐则臣:《别用假嗓子说话》,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08页。。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小镇青年敦煌、子午,他们北漂,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矛盾、彷徨又有个人的内在坚持。秦福小在外遍览祖国山河后,回归故乡,发现故乡。厌倦北京生活的初平阳,前往耶路撒冷寻找人生的信仰。易长安逃离山沟中的教书工作,作为北漂,办假证,最终在返乡途中进入监牢。杨杰驰骋于商海,永不停息。这些小说人物,无论是在乡镇还是在城市中,他们都是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们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撑。徐则臣的《北上》以行走在运河上的人(中国人和外国人)为中心,插叙历史背景,追溯行走着的人的情感共鸣,寻找他们及其子孙生存下去的动力和精神支撑。可以说,徐则臣发掘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依据。
徐则臣的《北上》是一部新历史小说,没有从战争的正义性质入手,而是着重书写战争中个人的逃离和转变,并且将不同种族的人放置在同一时空,在时空行进中,完成的是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河流成了这种建构不可或缺的载体和文化基因。徐则臣以河流、遗迹、考古为材料,以文学虚构为工具,建构了他者历史,这是“去历史化的历史写作”(30)曹霞:《“70 后”:去历史化的历史写作》,《北京日报》2016年6月16日。。因此,历史并没有远去,而是以另一种姿态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