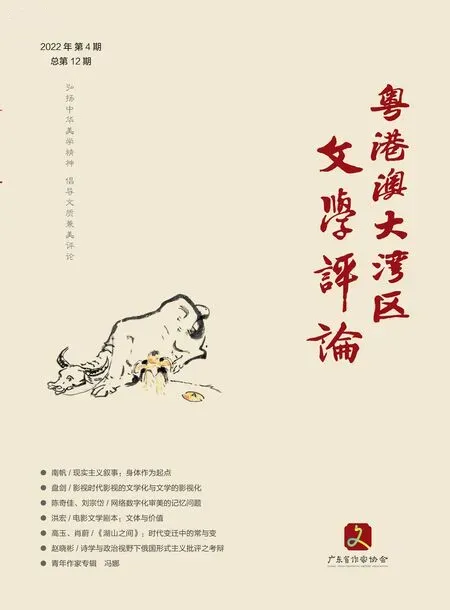秦兆阳文学编辑思想与实践初探
——以大型文学期刊《当代》为观察对象
2022-12-07梁向阳
梁向阳 张 瑶
《当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创刊于1979年6月。秦兆阳为第一任主编,至1994年10月在主编任上病逝,他主持工作长达15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带领《当代》编辑部尊重文艺规律,以正大严肃的现实主义品格反映时代风貌,发掘并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促进了新时期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其文学编辑思想与编辑实践对繁荣新时代文学仍有深刻的启示。
一、坚守现实主义的办刊理念
1979年,我国的文艺事业百废待兴,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了大型文学刊物《当代》。这一年,彻底平反后的秦兆阳来到由老延安文艺工作者严文井与韦君宜共同主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审工作。《当代》创刊前,该社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屠岸曾提议:“这本刊物应该有一位在全国文学界很有威望,压的住台的主编,就是秦兆阳同志”[1];韦君宜则明确告诉他已敲定就是秦兆阳。秦兆阳1938年奔赴延安,是陕北公学分校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生,他的青春年华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度过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文艺报》执行编委、《人民文学》副主编。尤其在1955年冬至1957年上半年,秦兆阳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期间,推出了一系列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力作,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新时期之初,《当代》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应运而生,众望所归的秦兆阳被任命为主编。
创刊之初,“全社办《当代》”[2],各编辑部组极力在编前会上拿出最好的稿件,1980年6月人文社领导决定成立《当代》编辑组专门处理日益增加的来稿和编务,再至1981年上半年成立《当代》编辑室,这份刊物的承载愈加厚重。“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历史的真实,事物的逻辑”[3],是秦兆阳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核心要素,也成为《当代》编选作品的重要内在标准。正如纳博科夫所言,“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衡量一部小说的质量如何,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4]。秦兆阳认为生活本身存在其规律性,在作品中表现为形象与情节发展的必然性。当文艺创作通过表现具体事物演进的逻辑触及历史与时代的大真实时,其思想性也就此生成。因此,生活的逻辑性不仅是衡量艺术真实性的重要尺度,也成为影响作品深刻性的关紧。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打通“胜利前进的航道”[5]以来,肃清“四人帮”流毒、澄清思想、培育新人、推动改革、推进“四个现代化”势在必行,《当代》力图贴近现实,表现时代风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景观,秦兆阳认为“文学入口处是设在人民的生活里面,而时代的大的局势,生活的真实和真理……必须用自己全部的血肉去探究去追求。”[6]因此,《当代》呼吁文艺创作者将艺术感受力的测深锤探入现实生活内部,解读其深层逻辑并将之表出来。历史为现实生活提供来处,秦兆阳认为不可偏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去抽象地表现历史。诚如托尔斯泰所言,“艺术家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想象历史人物和事件,但应像历史学家一样以历史材料为指导。”[7]对于历史文献无法精准还原的历史现场,创作者要思考历史事件的内在规律,以文学真实抵达历史的精神真实。在秦兆阳看来,表现生活的真实不意味着就事论事,像自然主义那样“照相”,他注重作品的“格调”的表现,认为“它可以使作品闪烁着智慧、才能(能力)、品德的光彩,使作品非同凡俗。”[8]格调的形成除了“有来自生活和来自思索的较厚实、较新鲜、较深刻的真材实料”[9],还要求独特的文字风格和高妙的艺术处理,更立足于作者“高度自觉的、既宽阔又深邃的历史洞察能力”[10]和高度的哲学思辨能力。这就要求创作者不能满足于一时一地一人的狭窄表现,而要以博大的襟怀去观照时代发展与人民生活,表现出时代要求与人民愿望,使作品立足于现实而升华出辽阔深沉的审美空间,指引历史前进的方向。
“对时代负责,对人民负责,要帮助推动现实的进步”[11],是秦兆阳办刊的崇高追求。他审时度势地提出“五气”(志气、骨气、才气、朝气、正气)办刊主张,力求《当代》在历史上站得住。
秦兆阳主编下的《当代》注重刊发具有思想道德价值与社会意义的作品。“写真实”固然意味着拒绝向壁虚构,但并不代表着一味地控诉苦难、揭露阴暗,秦兆阳认为要高瞻远瞩地看见历史总是向前发展这一最大的真实。他说,“在我们时代,对文艺总的要求,文艺应是启蒙的工具,能引人思索的工具……文学作品表现苦难的时候,不能老是哀叹、牢骚、呻吟、哭泣……真正的批判要有健全的头脑。我们批判是为了他好,而不是为了发泄气愤。要给人以自信心,民族的自信心”[12]。
为了更直接地反映现实,秦兆阳要求《当代》要敏感时事,跟上形势,注重报告文学的发展与深化。事实上,秦兆阳在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时期,报告文学和特写就占了该刊较大的登载比重。他认为“这是一个转变的时代,许多新的事物在涌现,许多矛盾在起作用,小说、诗歌不可能那么快地来反映这些生活内容,必须同时提倡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翼,使得文学创作领域更加宽广,对现实反映更快,更充分,以满足广大读者需要。”[13]《当代》1979年第2期,即以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为重点。1980年8月,秦兆阳从报纸上读到一条关于中共河南省委紧抓改革的报道,觉得应该抓住这个大题目,这就有了后来张锲的《热流》。1981年,秦兆阳约刘真赶一篇关于葛洲坝的报告文学,甚至急切到朝刘真作揖。从1979年的《她有多少孩子》(理由)、《命运》(杨匡满、郭宝臣)、《爱的奇迹》(从维熙)……到1980年代的《热流 》(张锲)、《励精图治》(程树榛)、《战马的风骨》(杨旭)、《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中国姑娘》(鲁光)、《强国梦》(赵瑜)……再到1990年代《天地人心》(正言、爱民)、《希望之海》(孟可)、《澳星风险发射》(李鸣生)……这些作品堪称时代风向标和晴雨表,从一个个鲜活的侧面及时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引领人民积极向上,而《当代》热心刊发报告文学的传统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章合为时而著”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一开始就很自觉地将创建新文学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的目标紧密联系起来”[14],并且认识到“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的发展路径,借重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助力思想革命。秦兆阳在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期间,推崇忠于生活、思想深刻的现实主义文学,宣称要把该刊“办成像19世纪俄罗斯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那样的一流的文学杂志……”[15]新时期,秦兆阳承继并丰富了传统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内涵以主持《当代》编辑工作。《当代》强调现实主义,绝非以之为独尊,而是“力求席面上有好的营养丰富的主菜,同时摆出各种不同风味的冷拼和热炒,调以甜咸酸辣,配以红白青黄,尽可能适应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口味的读者的需要。”[16]创刊号即登出了外国文学作品约翰·契佛的小说《乡下丈夫》和蒂图斯·波波维奇的剧本《权利与真理》,这一传统延续到人文社《外国文学季刊》成立及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恢复。《当代》忠于现实,提倡艺术风格异彩纷呈的办刊特色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反响。创刊号发行7万份,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外媒曾将之作为中国文坛的新动向加以报道。《当代》以季刊形式发行7期后改为双月刊,发行量最高达到了55万份(1981年第1期),后来回落稳定在二三十万,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秦兆阳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渗透下的编辑主张与一些作家的创作理念形成背反。王朔回忆道:“……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动笔时就不知道,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他当时说的话好像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17]这意味着秦兆阳所代表的严肃主流文化观念被一些自我意识高涨的作家视为颠覆的对象。1991年,秦兆阳认为《九月寓言》偏离了生活真实,作者以片面认识“抹煞了农民要求出路的阶级本性”,“在假托性和寓意性两方面都经不住审视和思索”[18],要求《当代》编辑汪兆骞处理退稿事宜。然而一些观点却认为,张炜这部“偏离此前的基本的写实风格,代之以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和哲理内涵的‘诗化’叙述方式”[19]的作品“体现了不是现实却比现实更为真实的原则”[20]。观照秦兆阳195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其核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却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和命运。即使秦兆阳在评析《九月寓言》时,出于自身经验而忧虑写作者在社会转型期对历史持轻率态度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忧虑,然而,在1990年代科技进步、自我发展打开的文学景深里,秦兆阳无疑显得保守了。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曾言,艺术家的“第一个时期是真情实感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墨守成法与衰退的时期”,“一切宗派,我认为没有例外,都是在忘掉正确的模仿,抛弃活的模型的时候衰落的”[21]。现实主义这条广阔的道路,在新的时代话语下亦当在连续的异质冲击中不断延伸。
总体观之,《当代》创刊几十年一贯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现实主义火热时,它为其呐喊助威;现实主义不受待见时,它仍为现实主义作品提供园地;现实主义再热时,它进一步促进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这一秦兆阳主编《当代》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展现了一份刊物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持久坚守,彰显了文学不躲避现实的责任担当。
二、着重新人新作的发掘培育
编辑这一角色,作为理解和接受作品的第一人,其对大量原始形态的精神产品的汰选与提炼工作成为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作家与编辑的有效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助力了文学作品的生成与到位,推动了文学史进程。秦兆阳主编《当代》,团结、照顾老作家、名作家理所当然,而重视对新人新作的扶植亦是其编辑实践的显著特征。
秦兆阳早在1956年的1月拟定的《“人民文学”全年计划概要》,对新人的扶植与培育就有明确要求:“1. 小说组一年内帮助二十个作者,成为作家者五人。2.诗歌组十二——三人3.评论组十二人——三人。4. 召开新作者座谈会一至二次。5. 全年培养少数民族作家至少一人。6. 各组应总结来稿中的问题,全年至少两次,并写成文章。7. 各组应经常拟出联系重点作者的名单,以加强与作者的联系,了解其生活和创作的范围与创作计划。8. 调查少数民族作家与翻译家,二月底完成。9.年底前在北京的工厂农村中建立读者小组两个。10. 编辑部内部争取在下半年建立通联组……”[22]秦兆阳认为在我国实行“四化”的这个伟大时代,文艺上百花齐放,扶植新作家的意义更重大。因之,《当代》发刊词即言明“我们希望多发表新作家的新作品”[23]而每期亦必推出新人新作。
从1950年代秦兆阳主持《人民文学》工作期间推出的《在桥梁工地上》(刘宾雁)、《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雪天》(林斤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到1980、1990年代《当代》刊发的《将军吟》(莫应丰)、《赤橙黄绿青蓝紫》(蒋子龙)、《河的子孙》(张贤亮)、《啊,故土》(李小巴)、《秋天的愤怒》(张炜)、《钟鼓楼》(刘心武)、《芙蓉镇》(古华)、《白鹿原》(陈忠实)等有重要影响的作品,正是在秦兆阳现实主义主张的影响和编辑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显耀出当代文学的光辉。
秦兆阳曾强调“要寄希望于没有出名的有生活的作者”[24],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文学之路就离不开秦兆阳关键性的帮助。路遥于1978年完成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时投稿了众多大型刊物后皆被婉拒,最后他托朋友将稿件投给《当代》,就在他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秦兆阳对该小说做出热情肯定。路遥赴京改稿后,该小说刊载于1980年《当代》第3期,并在秦兆阳的推举下,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次成功树立了路遥文学路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并显示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此后,中篇小说《人生》和长篇力作《平凡的世界》分别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贺抒玉认为:“这次成功对路遥在文学创作上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犹如一个水手,在大海中游向彼岸过程中疲惫不堪的时候遇上了一艘快艇。此后,路遥的写作便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5]。秦兆阳写于1981年12月30日、并于1982年3月25日刊发在《中国青年报》的《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一信中,热情评价《惊心动魄的一幕》,认为年轻的路遥创作的这篇以独特方式反映“文革”的小说是难能可贵的。他称赞道:“……路遥同志,你被所熟悉的这件真事所感动,经过加工把它写出来,而且许多细节写得非常真切,文字又很朴素,毫无华而不实的意味,实在是难得。这说明你虽然年轻,思想感情却能够跟我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相通相联,说明你有一种感受生活中朴素而又深沉的美的气质。这,好得很……”[26]信末,秦兆阳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对小说提出中肯建议并谦诚地勉励路遥在此基础上达到“更深沉、更宏大、更美妙”[27]。路遥在1982年的致信中以恳挚恭敬的言辞对秦兆阳发抒了深深的敬意并表示自己将继续求索以不负秦兆阳的厚望,在写给何启治的几封信件中亦不止一次提到并感激秦兆阳和《当代》对自己的关怀与帮助,如1991年元月致信中,路遥谈道:“我对《当代》,尤其是我最尊敬的老师秦兆阳同志有极其不一般的感情,没有秦兆阳同志和《当代》,也许我现在仍然成不了任何较为重要的事……”[28]路遥视柳青与秦兆阳作自己的文学“教父”,更说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29],是他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自己走入文学的队伍。作家陈世旭亦深深感怀秦兆阳对他的热情扶助。1984年秦兆阳致信陈世旭,信中将后者引为同调并鼓励创作。陈世旭意外又惊喜地回信表示秦兆阳“这种无私、真诚的关心,对一个在艰难中摸索的人,是多么温暖”[30],并随信寄出两稿,秦兆阳在认真审读后回信提供参考意见。蒋子龙、叶文玲等众多后来在当代文坛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家都曾受到“文坛伯乐”秦兆阳的扶掖,而每一颗成熟的果实,都会怀念这位辛勤的园丁。
秦兆阳主编下,《当代》刊发的每一部作品后面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故事,它们形成了编辑、作品、作者之间的情感纽带。1979年,史铁生在《当代》崭露头角,当年的第2期刊发了其创作《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原名《之死》),后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选播,这个文本就是当时孟伟哉在北京市崇文区文化馆内部刊物《春雨》上发掘来的,打响名声后的史铁生又推出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等优秀作品。王朔、柯云路等众多作家正是在《当代》编辑部同仁的帮助下享誉文坛,新时期“晋军”作家的名号也自《当代》响亮地打出来。《当代》亦吸引了众多优秀来稿。美国作家山姆·奥克兰主动投稿《从前,某时某地》,秦兆阳回信作者通知此稿将刊于1980年第3期。许多作者对《当代》心向往之,愿意把他们最好的作品交给这份杂志。1992年陈忠实致信编辑部表示,在《当代》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表态之前,他不会把《白鹿原》这部他很看重的小说交给别的杂志社。
秦兆阳主编以来,《当代》以“不薄名人爱新人”的办刊特色助力了众多作家迈入空前繁荣的新时期文艺百花园,成为至今登载获“茅盾文学奖”作品最多的刊物,并着力在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新的辉煌。
三、践行严谨负责的编辑作风
秦兆阳有作家、文艺理论家等多重身份,他却说,“如果一个人非要有个头衔的话,我倒觉得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31]。秦兆阳何以历经磨难而对党的文艺事业始终丹心不改,恒以一腔赤诚专注于编辑事业?回首当年,或可为此问做一个注解。童年与少年时期,贫苦的幼年秦兆阳受教师父亲感染,爱好绘画,性格里带着板性和呆气。青春时期,傲视金钱,不通世故,有着传统知识分子式的清高,此为后来遭受不公批判埋下命运的伏线。见闻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热河沦陷、何梅协定、西安事变 ……秦兆阳深感于祖国和人民的苦难与愤慨,不安于无所作为的他决定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1938年8月,秦兆阳来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的陕北公学分校,后又被允许去延安鲁艺学习一月有余,1939年7月随军出发参加革命工作并于1941年入党。期间,他以木刻、贴画等方式宣传革命;到了1943年,他被地区党委分配到《黎明报》当编辑,负责收译延安解放社的电讯。随军深入战地,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温情与奉献,秦兆阳回忆说:“我不停地记‘战地笔记’,我惊奇于人们叙事情、 讲故事、 表感情时语言和形式的生动性。 我总是尽力按照讲述者讲述的口气韵味来记。于是我明白了:将来如果不把这样的生活写出来,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子孙后代。美术是不能表现这样生活的,只有文学,只有小说。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放弃美术专业, 要走文学写作的路!”[32]战争年代与人民共进退的生活感受和将之反映的愿望,推动秦兆阳走上文学道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昭其以光明和真理,引导秦兆阳走进了胜利以后新的中国,使他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和内心的寄托。1955年12月秦兆阳被作协党组调去《人民文学》任副主编,1956年9月,他在“干预生活”思潮和“鸣放”背景下发表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触犯了当时的政治规约,加之其主持工作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被批评、不愿参加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等事件,刚直不阿的他于1958年7月被当权错划为右派,留在了广西。从1962年开始追求重新入党,1979年秦兆阳终于走出痛苦的沟壑,再度从事编辑事业。初心不改的他珍惜散失的时间,始终以对家国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全力关怀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发展,把自己的编辑工作当做一项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事业来对待。秦兆阳的性格与经历与塑成其苦难与坚守,为国家和人民努力做一把铺路的泥土,是他一生不倦的追求。
新时期创办的《当代》,受文学制度规约变小并不意味着其与政治完全无涉,相反,它仍属于国家体制之内。《当代》发刊词即言:“文学事业是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33]。严文井说:“我们创办的 《当代》杂志,是一个供作家们战斗的阵地,欢迎同志们创造出像生活那样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创造出具有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作品,使人民群众感奋起来,团结战斗,推动历史车轮前进,以期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34]。可见《当代》自创刊起就自觉助力政治建设。秦兆阳主编的《当代》,既以家国情怀融入集体、认同体制,又借重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人格坚守文学自律。
秦兆阳曾言:“编刊物比编书锻炼人,因为接触现实生活更紧密,社会的各种反映逼着你。我们不能出问题,出一个问题影响大。大问题影响整个文艺运动,小问题也影响我们的刊物。这就逼着我们要慎重从事。”[35]他主张严肃工作,力求对作者、作品、读者、社会与时代负责。面对浩如烟海的来稿,秦兆阳经常亲自审阅。朱盛昌回忆说:“上午秦兆阳来,在老孟处谈稿子。孟拿了两个中篇叫我看,他以为秦忙不会看,不料秦听了立马要了一个去。说起短篇,我说有个写彭德怀的,丛培香和老丁都认为有基础,孟叫我先看看,也被秦要了去。他这种一心想尽早抓到好稿子的精神,令人钦佩”。[36]在审读柯云路的小说《衰与荣》时,秦兆阳担忧书中关于上层生活和人物的书写会给刊物造成一定麻烦。他说:“对我个人, 麻烦是无所谓的,我年纪大了,无官无欲,怕的是给刊物和编辑部惹来麻烦。我们有一个好的阵地很不容易,要好好地保护,不要因为一些本可以避免的原因而被停刊……我不欣赏匹夫之勇, 要的是大智大勇。”[37]诚然,秦兆阳生活简朴平和,淡泊名利,这“保护”的目的是更好的“战斗”,希望刊物能够有力地推动历史前进。听完作者的陈述和解答后,为了更稳妥,秦兆阳还召集编辑部全体谈论对《衰与荣》的意见,在获得大多数支持意见后,秦兆阳郑重决定在当年的最后一期和次年的第一期《当代》全文发表该作品,并说“既然决定发表了,我是主编,出了问题我负责任。”[38]某次编务会上,秦兆阳针对莫应丰的新作《在水碾房旧址》中存在的问题,提了满满六张纸的修改意见,进而又担忧一些青年作者看生活不够透彻影响文学事业发展,提出了七点具体意见[39]。
秦兆阳要求编辑工作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视工作为畏途,以看稿为负担。个人写作第一,编辑工作扯淡。提意见隔靴搔痒,笼统含糊;编稿子照收照发,免得费事”[40],是秦兆阳眼中的编辑工作者大忌;“磨稿亿万言,多少悲欢泪,休云编者痴,我解其中味”[41],正是他忠实的自况。在修改李国凯的小说《代价》时,秦兆阳说:“……稿子还是要改,不能叫读者觉得我们发的东西太粗糙。我们改了,作者如果不同意,可以讨论,甚至可以把原稿和改稿同时对照发表”[42]。在共商作品时,秦兆阳常主张首先明确作者的写作缘起,以求提出正当合理的修改建议。
秦兆阳鼓励《当代》的编辑工作者不但要去了解时代和生活以便更有把握地处理稿件,还要善于勤于思考来稿的情况,从做中学,教学相长。他说,“看稿也是学习。除极差的稿子外,每一篇稿子都会给我们一个小的生活侧面,一种艺术手法,编辑可以从中认识生活,分清什么真什么假,又可以认识艺术规律。我们不要把看稿当成负担,来稿比任何书本更复杂、广泛。通过看稿,可以学习理论,学习艺术。我自己就从看稿中得到好处。我的理论是从稿件的实际中来的,只有在需要时才去找马恩列。我写《农村散记》,就是因为看稿中觉得不能那么写才写的……”[43]早在1950年代,秦兆阳就针对来稿中过分注重配合政策宣传的急功近利之作和耍花架子的浮浅创作风,发表《概念化公式化剖析》《形象与感受》等理论文章鞭辟入里地指出症结并引导改善,一反当时进行过火批评、乱扣帽子的评论文风。
在秦兆阳严谨负责的工作表率下,《当代》的编辑工作者们以诚朴端庄的敬业精神在新时期以来的商业浪潮中寻找到张力空间,既把握市场动向和读者心理需求又不遮蔽文学的价值,成就了一本响亮的刊物,也成就了几代作家。
结语
“文章千古事,荣辱百年身。风雨长征路,丹心永不泯。”[44]秦兆阳几十年来写文章、办刊物的一切言行,都以发自内心的真诚忠于时代、党和人民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其之人生浮沉彰显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经岁月磨砺而毫无动摇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人格。秦兆阳以自己的思想底色点亮了《当代》的光辉,使《当代》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把握现实与时代的脉动,形成的正大严肃的美学风貌,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秦兆阳主编《当代》期间所展现的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息息相通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及其注重新人新作发掘与培育的编辑实践、严谨负责的编辑作风对繁荣新时代文艺事业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注释]
[1]孔令燕:《记忆,在叙述中重显——纪念〈当代〉创刊二十周年往事回顾座谈会》,《当代》,1999年第3期。
[2]朱盛昌:《全社办〈当代〉》,《当代》,2009年第4期。
[3][6][8][9][10][18][22][26][27][40][41]秦兆阳:《秦兆阳文集·5·文学评论》,武汉出版社2016年版。
[4][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页。
[5]《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10月7日。
[7]钱中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页。
[11][13][36]朱盛昌:《秦兆阳在《当代》(日记摘录)》,《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12][24][35][38][39][42][43]朱盛昌:《秦兆阳在〈当代〉(日记摘录·续一)》,《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1期。
[14]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15]王培元:《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灵魂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65页。
[16]朱盛昌:《〈当代〉七年》,《当代》,1986年第4期。
[17]王朔、老霞:《美人赠我蒙汗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1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
[20]王安忆:《我们在做什么》,《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4期。
[21][法]丹纳:《艺术哲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页。
[23][33]《发刊的几句话》,《当代》,1979年第1期。
[25]詹歆睿:《关于路遥小说的编辑案例及其启示——兼论编辑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态度》,《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9期。
[28]路遥:《人生》,《路遥全集(典藏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页。
[29]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30]陈世旭:《迟到的悼念——怀念秦兆阳老师》,《中国编辑》,2005年第1期。
[31]李频:《磨稿亿万字 多少悲欢泪:缅怀秦兆阳先生》,《出版广角》,1997年第2期。
[32]秦兆阳:《回首当年[四]》,《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
[34]严文井:《文学,应当象生活那样丰富多彩》,《当代》,1979年第1期。
[37][38]柯云路、秦兆阳:《我不赞成“匹夫之勇”》,《同舟共进》,2008年第10期。
[44]屠岸:《风雨长征路,丹心永不泯——沉痛悼念秦兆阳同志》,《当代》,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