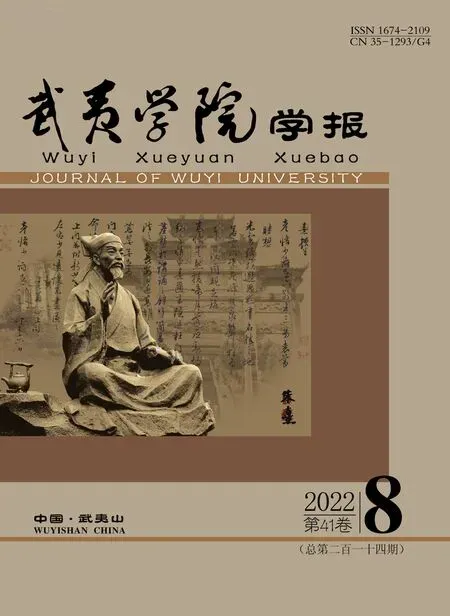我国华南地区“壮侗-南岛语”人群的蛇崇拜辨析
2022-12-07苏巧莹范志泉
苏巧莹,范志泉,3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福建师范大学 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7;3.厦门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考古学、民族学研究表明“壮侗-南岛语”人群的先民在新石器时期便已居住在中国华南地区,他们共同组成以环南中国海为中心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在其他异文化相继移植之前,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土著文化共同体体系[1]。语言学者认为南岛语与壮侗语、汉语方言(粤语、闽语、吴语等)这两类不“同构”的语言存在着一批具有“同源关系”或“底层关系”的基本词汇。如壮侗语人群的先民操的是原始南岛语,原始南岛语的原乡在古百越文化区[2],而“南方汉语保存了古南岛语底层”[3]。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遗传学材料的支持,其最新研究成果已发表在Science、Nature 等国际顶级权威刊物上,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华南沿海人群与现今广泛分布于我国台湾海峡、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南部岛屿的南岛语人群有着非常密切的遗传联系[4-6]。
既然“壮侗-南岛语”人群先民作为我国新石器时期华南地区的一大族群,那么必然有着一些共同的民族性特征与文化现象。由此,本文主要从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成果出发,对这一人群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征之一的蛇崇拜研究进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语言学材料,提出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新思考。目前,学者们依据不同的研究理论、方法以及材料,在关于华南族群蛇崇拜的研究上取得了诸多成果,大抵可归纳为以下两类:1)华南族群以蛇为崇拜对象;2)质疑华南地区的崇蛇现象。
一、华南族群以蛇为图腾崇拜对象
认为华南族群以蛇为图腾崇拜对象的学者,几乎均引用古书文献的相关记载作为依据,以《说文解字》注“南蛮,蛇种。从虫,亦声”及“闽,东南越,蛇种”为多,以此认为我国南方人民早期被称为“蛇种”,从而具有悠久的蛇崇拜历史。
此后,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加,考古工作在南方区域文化中具有丰富且独特的研究。其中,南岛语族文化起源是包括闽台考古在内的东南考古的核心问题,可以从中探索两岸考古遗存背后的土著民族关系、民族迁徙[7]。而“反映南方土著早期崇拜蛇形式的材料主要是岩画和几何印纹陶片,这些材料分布在古代百越族活动的大部分地区,如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台湾等”[8]。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大量文物古迹发现,在印纹陶、青铜器、岩画等确切地刻有众多蛇纹饰、蛇图案,这些蛇图案与纹饰预示着我国南方土著民族确实与动物“蛇”存在某些文化上的联系[9]。陈文华通过考察多种几何印纹陶,将蛇图腾崇拜与印纹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认为随着民族变迁而带来的文化融合使得土著民族的蛇崇拜意识淡化,从而导致印纹陶的蛇纹刻画艺术逐渐被冲淡[10]。杨建芳根据考古发现,一些陶、石工具、漆木器、青铜器和玉器等文物刻有大量纹饰:两湖地区出土的楚国陶敦、陶壶、陶盒、陶鼎中有盘踞状或“S”形蛇图像;良渚文化陶器上的云雷纹、回字纹、重圈纹;江苏金坛三星村M248 新时器时代陶豆的爬行动物简化造型……这些均是抽象蛇纹的产物,并按起源与传播的演变指出南方流行的云雷纹是当地先民对蛇崇拜的反映[11]。郑岩将诸多蛇文化题材在古代艺术品中所表现的蛇形象进行归纳,探索先人有关蛇的宗教与艺术的观念,认为人们在“敬、畏、惧”之间的不断转化产生了对蛇的尊膜崇拜[12-13]。此外,高业荣等人利用周边环境、考古资料进行考察,发现岩画点之一的“孤巴察娥”(KTM1),蛇形象比人物形象更为突出,圆涡纹、蛇形曲线等抽象的几何图形在岩画上轮廓分明;而在另一岩画点“大扎拉乌”的TKM4-1、3、4、5、7 岩刻处同样出现了大量的蛇形象或抽象蛇纹的痕迹,他们认为万山岩雕的制作族群应该是与高山族鲁凯人和排湾人具有同源性文化的族群,制作岩雕的目的则与农耕及宗教信仰有关[14]。
另一方面是有关“蛇”的传说故事,《山海经》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原始神话传说丰富的上古奇书,“蛇”在书中大量出现,特别是对上古神形象的描述,诸如伏羲、女娲、共工、后土、九婴均是人首蛇身的形象,可见先民们将“蛇”与创世繁衍的能力联结起来。如今民间依旧存有的崇蛇传说是这一联结的延续,几乎有蛇崇拜的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故事流传至今,其中以始祖传说为多。陈维刚以民族学资料为考察,描述了广西侗族当地的崇蛇风俗、蛇始祖传说,认为侗族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便产生图腾崇拜,并把它当作自己民族的起源及保护者,尊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15]。梅伟兰通过对黎族的始祖传说“勾花的传说”“五妹与蝻蛇”等故事进行考察,表明黎族人认为他们的祖先“黎母”是一蛇卵在山中所生而来,蛇图腾崇拜在黎族所有支系中都普遍地存在,人们视其为始祖或是祖先死后变生的灵魂[16]。吉成名则通过对黎族、壮族、高山族、疍民等越族族群内部流传的始祖传说进行分析,认为各地所崇拜的蛇分为有毒蛇与无毒蛇,并且有的属于图腾崇拜,有的不属于图腾崇拜,各地越族崇蛇习俗的性质和内容并不相同[17]。李海林在对高山族蛇图腾的起源、现象、特点分析中发现,高山族蛇图腾文化和大陆同根同源,是古越蛇图腾文化的深化和发展。高山族的“蛇生说”“太阳卵生说”等神话传说,揭示台湾土著雕刻与绘画的各种图腾纹饰的起源应与百步蛇有密切关系,并以百步蛇的三角形斑纹为蓝本进而演变为各种花纹,如曲折线纹、网纹、菱形纹等[18]。
最后,一些学者基于现今还保留的“蛇节”“蛇庙”“蛇像”等民俗节庆对崇蛇文化进行探讨。如:林蔚文是较早对福建地区的崇蛇现象展开讨论的学者之一。他将视角置于闽地,在对福建民间动物神灵信仰的研究基础上对南平樟湖坂的“连公爷”、漳州平和等地的“侍者公”、闽东地区的“九使蛇神”等各地崇蛇信仰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探讨闽越古地各类“蛇神”“蛇妖”的文化内涵[19-22]。另外,郭志超以闽台地区的“蛇”宗庙、“蛇”神像以及“蛇”节庆为例,指出闽台崇蛇风俗从同一个角度显示古代闽台两地文化底层具有相似性,皆属百越文化系统,反映了自古以来海峡两岸文化的一体性[23]。吴春明则运用文化类型学描述华南地区“正面”蛇神、“反面”蛇妖或镇蛇之神、“改造”蛇神三类现象,说明以“蛇”为核心因素的宗教文化内涵与形态各不相同,认为南方蛇神呈现多样性态与中原文化、土著文化相融合有关[24]。
纵观前人研究,大抵立足于地域、族群等视角,从史书文献、蛇纹图案、民族传说、风俗节庆等方面,对崇蛇现象进行讨论。
二、质疑华南地区的崇蛇现象
诚如支持华南地区的蛇崇拜现象一样,对其提出质疑的学者虽然比较少,但大抵也是从前文几个方面出发进行反驳。陈剩勇通过对《吴越春秋》《说文解字》等古书文献进行文本解读,认为资料记载的古越人“杀蛇”“食蛇”的行为与图腾崇拜的意义产生了冲突,蛇图腾崇拜说从根本上忽视了原始社会图腾信仰的基本内涵及其本质特征,而仅仅是依据东汉以后的一些野史传说穿凿附会而成[25]。王圣宝认为将几何印纹陶纹饰笼统地归为蛇纹是错误的观点,他以对陈文华《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 一文的批驳为基础,提出古人对于蛇的厌恶以及对扬子鳄的青睐,并认为几何印纹陶的起源物不是单一物而是综合物的反映与抽象,如果非要说是单一物,则不应是蛇,而是扬子鳄[26]。陈国威则通过对“图腾”一词进行概念阐释,认为图腾所具有的功能迷惑了人们对“蛇”的情感体验,产生错误的图腾崇拜,并指出在巫术盛行的古代南方社会,蛇作为一种神秘的媒介,充当了原始文化中赋予神性的象征符号,因此才被人们尊崇,而长期以来的“崇蛇论”忽视了最重要的所述内容的时代背景,同时对百越民族发展的脉络也欠考虑,造成无法对一个族群的信仰文化进行客观考定[27]。更有学者认为将“闽”“蛮”“它种”与崇蛇联系起来缺乏合理性描述和完整证据链,对“闽人崇蛇”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福建是因为崇蛇才简称为‘闽’”的提法予以质疑,“闽人崇蛇”应该是人们对“闽巫操蛇”现象的曲解[28]。
对于反对“崇蛇论”观点的学者来说,蛇是一种凶猛恶毒的动物,《说文解字(卷十三)》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凡它之属皆从它。蛇,它或从虫。”[29]早期先民在社会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饱受蛇害的苦恼,怎会对其产生信仰崇拜一说呢?质疑者认为如果说因为南方多虫蛇便以蛇为崇拜,那么北方多事游猎便以犬、豸为崇拜;西方多牧羊为生便以羊为崇拜……[26]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往认为华南族群具有蛇崇拜均是后人掺杂自己的主观臆想所产生的误解。例如对“闽,东南越,蛇种”而言,“闽”这一称呼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见于文献了,那么,为什么“闽”这个带“虫”字形体的简单汉字,竟会长期以顽强的思维定势让人生出其必定与崇蛇有关的望文生义的文化成见呢?[26]“闽”“蛮”是古代汉族文人鄙视南方少数民族的贬称,许慎释“闽”为“东南越”无疑是对的,但是后面的“蛇种”显然是穿凿附会,因为目前为止考古学的发现并没有为“蛇图腾说”提供可资证明的材料[25]。于是认为,该地区之所以出现相关的“蛇”现象,是因为古代南方社会好巫的风气,蛇作为一种巫术道具经常被使用。现如今可见的出土文物中,操蛇、饰蛇、践蛇、戏蛇等图案都是对古代巫术进行时的刻画,具有神性与权力的象征,象征天与神授的政治权威与合法性、交通天人的灵力、对自然力与社群的有效控制[30]。东周以后,不仅在中原铜器上有较多的蛇纹,而且在南方的吴越文化、楚文化、滇文化中,也出现了装饰蛇纹的铜器、漆木器,其内容复杂多样:有双蛇组成的神祗、有积蛇形象的蟠虺纹、有《山海经》中常见的操蛇之神、人首蛇身之神,以及蛇食蛙、蛇鸟组合等多种题材,盛极一时[9]。另外,在民间故事中也有与巫术相关的制蛇、斩蛇、镇蛇的例子。《搜神记》中“李寄斩蛇”发生于闽中地区,岭西北山洞有一大蛇有时托梦于人,有时下告巫祝,说要食用十二三岁的少女,接连多年已断送了九女之命,李寄闻此便在八月初祭那天带上宝剑,利用糍粑引蛇出洞杀之,为民除害,“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其歌谣至今存焉。”在江南水乡苏州,据《吴地记》记载:“西阊、胥二门,南盘、蛇二门,东娄、匠二门,北齐、平二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在说到此事时解析到“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越国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吴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蛇门是苏州最早八座城门之一,当时的吴王在城西南的盘门城楼上挂着一条蟠龙,蛇门上还悬挂了一条木蛇,凭借蛇这一巫术因子所具备的神秘功能对敌国进行制衡,具有征服越人之意。
可见,蛇被当做连结自然神力的巫术道具受到推崇,自然成为一种世代沿袭的文化象征,由此也容易被误解为是一种历来的崇拜现象,这是反对“崇蛇论”者所认同的南方地区相关“蛇”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所在,而非从古至今就有的原始信仰或者图腾崇拜。
最后,通观这些文章的论说,可见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反“崇蛇论”中认为的人们对蛇的尊崇敬畏心理,而是抓住古人对蛇这一不祥之物的厌恶进行推测,认为现存的一些崇蛇习俗与物象是因为巫术文化在土著民族精神信仰、宗教观念等方面的反映,而并非是对成为图腾的蛇崇拜进行传承。
三、对现有蛇崇拜现象的评述
学者们对于蛇崇拜现象虽有不同意见,但是对其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观点:一是适宜的地理环境;二是认知水平的问题。
首先,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适宜的生存条件,这种环境十分适合动植物生长繁殖,我国蛇类基本分布于南方地区,以云南、广西、福建等地分布最多,人与蛇打交道的机会也相应较多。因此,可以推断在人与蛇长期共处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对蛇这一动物逐渐了解并习以为常。其次,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认知能力受限,对于凶残恶毒的蛇所带来的祸与福不能准确地认识并以科学有效的方法解决,于是便将这些现象描绘成大自然对人所施加的神力,将蛇视为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等互通的媒介,具有通灵的功能,由此形成了对蛇的信仰崇拜。例如,生活在海南岛的黎族先民,这里森林密布,毒蛇猛兽成群,他们认为蟒蛇性格温厚、体型巨大、力量惊人并且是一种无毒蛇,拥有掌管众生的法力,便将其视为蛇王,尊奉其为自己的祖先。黎族人幻想着人、蛇同族,以期得到蛇王的保护,而免受蛇类和其它猛兽的伤害,从而使自己的氏族能够繁荣和兴旺[15]。再如,现在的江苏宜兴人的崇蛇习俗主要沿袭了古代土著越人的有关习俗,他们将蛇分为家蛇和野蛇两大类,分别称为“里蛮”和“外蛮”,并且十分崇拜家蛇,民间流传有“家蛇吃鼠”“家蛇运米”的说法。因为家蛇是一种无毒蛇,又能够帮助人们灭鼠、运米,由此,先民们不禁对自然神力充满联想,将家蛇视为吉祥物,对家蛇产生了信仰崇拜,称呼其为“蛮家”,并形成祭祀习俗,称为“请蛮家”或“斋蛮家”。
目前,福建南平樟湖坂是汉语方言区内蛇崇拜民俗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该地每逢农历七月初七便举行盛大的蛇节活动,村民们在这天游蛇神、放生蛇、拜蛇王庙。该地崇蛇传说中,“蛇王”连公是一只蟒蛇精,不但从无害于乡里,而且是本地的水上保护神,为百姓消灾祛难,凡事有求必应,由此深受民众崇祀[22]。这样的民间传说与习俗大量地成为支持“崇蛇论”观点的引证,尤其在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壮族的龙母传说、侗族的“大花蛇始祖”、白族的“蛇日祭”习俗、高山族的百步蛇传说等。
然而,虽说华南各地均拥有大量崇蛇传说存在,但各地的崇蛇信仰并不完全一致,其中存在着些许差异,主要表现为崇拜体系上的不同。在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上,民间信仰主要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等崇拜体系,随着早期中原汉人的南移,土著民族与其不断融合,在汉族发达的佛、道教的宗教氛围中,蛇的崇拜体系不断发展演变,并带有人格化的偶像形式[17][31]。南方地区于唐末五代两宋时期出现大量的造神运动,就是主要体现为动物神崇拜的降格和人格神崇拜的兴起,这是源于巫文化与佛道文化相融合的现象[32]。正如福建闽北樟湖坂的崇蛇文化,中原汉人的南迁将该地原有的“蛇”自然崇拜融合了“儒释道”汉文化,将动物“蛇”进行了神灵化、人格化处理,由此呈现出现今的“蛇神”“蛇王”“蛇妖”等形象。经过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认知的进步,所崇拜的蛇形象从原始蛇图腾到蛇神、蛇妖,有了一个转型的时期,大致路径为史前上古到周末秦汉再到唐宋明以后[19]。整个崇蛇文化史的转变,可以说是南方土著民族的变迁史。相关的蛇神传说可以窥探出在本地土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汉文化的影响,土著蛇神经过“改造”变得多样化,带有更多“中原正统”的特色。正如《白蛇传》降蛇的叙事模式便体现出正统观念对蛇妖的镇压与改造,侧面反映了六朝时期制度化的宗教文化开始试图征服江南地区的民间崇拜,通过降蛇将蛇妖蜕变成庙宇正神[33]。这是封建社会阶级制度下所产生的神灵崇拜,在江浙、闽越地区民间所流传的蛇神、蛇妖故事及蛇王庙、蛇神庙,甚至于蛇节习俗均属于这一崇拜体系,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在形成神灵崇拜之前,蛇信仰更多的是图腾崇拜,并且图腾崇拜大多与始祖、祖先崇拜连结在一起。“番人因拜蛇之故常雕蛇形,以表敬意,其后此种蛇形渐成为艺术上之模样,而应用于装饰”[34]。20 世纪以来,林惠祥、凌纯声、铃木质等学者在对台湾高山族崇蛇文化进行研究后发现,他们基本将蛇作为祖灵信仰为主,蛇具有创生与庇护的神力,因此在他们的房屋、祭祀用品、木雕艺术、生活器物等方面均刻有大量蛇图案符号[34]。台湾高山族的崇蛇习俗以鲁凯人和排湾人最为重视,他们自认自己的祖先是百步蛇,族内流传有“百步蛇、青花蛇孵卵繁衍先民”的传说。由于高山族没有文字系统,这些传说只能通过语言或图案符号记录下来,蛇图腾也由此形成。另外,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高山族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台湾东部山区,受外部影响程度较小,所以能够较好地保留住原始的图腾崇拜。
往更早的时间推进,崇蛇现象表现为一种自然崇拜。人们认为自然界中的动物“蛇”会带来某些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于是对蛇进行信仰崇拜,便是原始信仰的最初形式。前文所述宜兴人对家蛇的崇拜也应是自然崇拜的一种,他们认为看见了家蛇出现在自己家中就会有好运并做出相应的祭祀,如果对家蛇进行捕杀或是破坏某些禁令就会遭到惩罚。这种自然崇拜同样在黎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中有类似的尊崇与禁忌之俗。归根到底,蛇崇拜主要来自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正是因为南方优越的生存条件,蛇类众多,所以人们遇到蛇的机会大大增加,而认知水平有限的早期先民面对神秘莫测的蛇难免会产生相应的惧怕、敬畏、尊崇的心理,从而形成对动物“蛇”最初简单的自然崇拜这一形态。
从上述可知,我国华南族群的崇蛇现象内涵并非一概相同。以蛇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为主的崇蛇现象,是一种单纯的土著民族的蛇崇拜,大多存在于诸如山区、山地等一些相对封闭、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的地区,几乎没有遭到其他文化的消解或融合。而神灵崇拜究竟是否是一种单纯的崇蛇现象需要依照具体的、内在的文化内涵所定,正如质疑者们所认定的相关的“蛇”现象可能是一种巫术文化的反映,蛇被作为巫术道具遗留下来,“闽人崇蛇”的说法应该是人们对“闽巫操蛇”现象的曲解[26]。此外,将动物改造成神妖的信仰变异,其中夹杂了许多文化因素,民族志上南方各族大量存在的蛇神、蛇王等崇拜以及被汉人“文化改造”的诸多涉蛇神话传说,操蛇、斩蛇、饰蛇、镇蛇等行为,充分反映土著蛇文化的传承、积淀与变迁以及土、客文化之间强烈的对立、冲突与融合[9][18]。人们因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对蛇产生复杂矛盾的心态,形成对蛇双重特性的认知心理,即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从而积淀厚重的文化蕴涵与审美基础[35]。
总的来说,一分为二客观地对蛇崇拜进行辨析显得十分必要。尽管有些证据对于解释华南族群是崇蛇一族来说缺少合理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确实存在有部分族群具有崇蛇现象,只是它们所表现的崇拜体系有所差异。将所有南方土著民族与“蛇”衍生文化一律割舍开来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因此,在进行考察时需要因地制宜,立足于各地区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以历史唯物的视野看待各族群的崇蛇习俗与物象。
四、小结与思考
“壮侗-南岛语”人群的先民在新石器时期便已居住在我国华南地区,他们共同组成以环南中国海为中心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蛇崇拜”现象作为我国古代南方“壮侗-南岛语”人群先民的民族特征,是华南族群在原始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种精神寄托,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由于受环境因素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影响,这些人群的早期先民对于“蛇”这一动物所带有的敬畏、惧怕、禁忌等心理,经过不断地创造与被加工从而呈现出各种各样形式,进一步表现为不同的蛇崇拜体系,衍生出丰富多彩的崇蛇习俗与物象,最终成为一种特色的原始崇拜,至今在各地还留有大量的崇蛇遗存。
此外,蛇崇拜在语言材料上同样有着另一番有趣的体现,如:原始南岛语*SulaR“蛇”,原始鲁凯语*so-La?a,万山鲁凯语’olra’a,卑南语unan,阿美语’oner;原始马波语*hulaR,马来语ular,伊班语ular,巽他语oray,巴厘语ula,莫肯语olan,占语群嘉莱语ala,回辉语la33,原始黎语*ilaB,黎语za2,壮语?a:i6“(虫子)爬”,布依语za:i6“(虫子)爬”,临高话l??8“(虫子)爬”,仫佬语la6“(虫子)爬”,水语la5“(虫子)爬”,毛南语la:i5“(虫子)爬”,南平松溪ia2,南平建瓯y?4。李方桂为上古汉语“蛇”构拟*diar>djz?a,白一平、沙加尔2014 年则构拟为*C?.lAj。两者的构拟与南岛语“蛇”第二个音节以及壮侗语较为一致,南方汉语同样保存了古南岛语底层。从上述语言材料可知,蛇在华南族群(南方汉人、壮侗语族、高山族)的语言中体现出了明显的同源关系,也显示出蛇在这些人群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便反映出为何华南地区普遍存在蛇崇拜现象。这些语言材料填补了长久以来欧美等学者以“今”南岛语重建的原始南岛语所缺乏的华南地区的语言材料,同时也弥补了部分语言学者所认为的今日之中国大陆上已无任何南岛语言遗留的空白。
长久以来,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南岛语人群起源于台湾,并以台湾为中心向东南亚、太平洋群岛等地扩散。在包括我国高山族在内的南岛语人群及其语言的演化历史研究中,以欧美、澳洲等地区学者为主导的国际南岛语人群研究学界似乎有意或刻意忽视来自中国大陆华南地区(如南方汉语方言、壮侗语等)的语言学证据与材料,在相关论著中较少讨论或甚至完全不提及。一些台湾地区学者也极力否认包括我国高山族在内的南岛语人群及其语言与东亚大陆华南地区人群及其语言的早期密切关系。然而,从本文所阐释的“蛇”崇拜文化现象以及蛇一词在华南族群语言中的演化来看,南岛语人群与华南地区人群(特别是壮侗语人群)的早期考古文化遗存之间的显著一体性、彼此语言之间的晚近亲缘关系、在遗传学上的直接同源关系等,或可为南岛语人群(包括高山族)起源于亚洲大陆地区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解读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