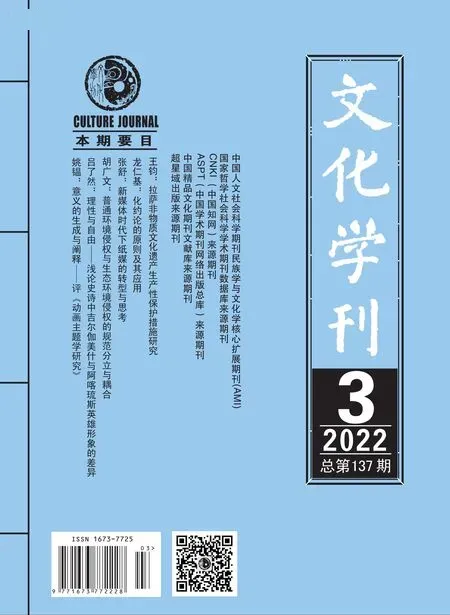汉语的意义:从语言到文学,从民族到世界的大语言观
2022-12-07杜玺娜赵媛媛
杜玺娜 李 娟 赵媛媛
一、引言
语言作为人类沟通交流的方式,它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自诞生之日起,语言就承载着人类认识世界及自身的重要使命,人类使用语言表达和创造生命体验,可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文化价值的人类特有属性。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正如赫尔德所言,“语言是一座人类思想的宝库,藏有每一个人以自身方式做出的贡献;它也是一切人类心灵持续活动的总和。”[1]语言表达着人类思想,展现着人类文化,是一切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
从两希源头开始,西方文化的变迁就与语言问题相伴相生,“从文化进化与语言学发展的角度追寻,西方文化所经历的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均对语言学产生了震撼。”[2]随着西方认识世界的开始,汉语作为他者必然被纳入到西方视野,成为认识东方的途径,也开启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西方对于汉语的研究始于明末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不论其目的如何,这些对汉语的学习和研究使得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从器物转向了思想领域,也为19世纪初汉学研究进入西方的近代学术体系打下了基础。不仅如此,“从16世纪到晚清的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历史以及对汉语的深入研究,构成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前史。”[3]
国内对于西方汉学中的汉语研究,大多聚焦于语言学上的探讨,张西平教授的《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2011)和《近代西方汉语研究论集》(2013)即是此方面的成果。此外,也有个别学者或依托国别,或依托年代,或依托某位汉学家做出研究探讨,但鲜有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特别是中西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大背景下做出研究,童庆生教授的《汉语的意义》即是此方面的开拓性成果。该书重点通过对西方汉语观形成的历史语境的考察,将西方学术思想界对汉语的认识与现代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联系在一起,考察西方现代理念和现代知识体系中一些带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现代知识发展的影响。总体而言,该书以“以小见大”的研究视角,在研究视野上进行跨民族间的横向比较,在研究焦点上进行历史的纵向延展,在研究范围上进行跨领域的辐射观照,为此后相关研究打开了思路。
二、研究视角的以小见大
《汉语的意义》副标题为“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相信不阅读此书的读者定会迷惑,何以这三者并置?三者在此书中的关系又是如何?书的第一章为“语文学、世界文学和人文科学”,可以说是奠定了整本书的研究基调,即对西方汉语观的讨论并不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之内,而是使用语文学的研究范式,通过对汉语观形成与发展的西方思想文化背景的解读,探究世界文学的存在及可能,展现人文学科的精神意义。
何为语文学?
语文学(philology)源于拉丁文philologia,由Philo(热爱)和Logia(词、文字、语言)两部分组成,在意义上与哲学philosophy相对:前者为“爱语言”,后者为“爱智慧”。“语文学的兴起是近代人文学科赖以突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建立起各自独立、规范和科学的学术领域的基础和标志。”[4]现代语文学的奠基人是意大利思想家维柯,他确定了语文学的任务是考察和研究“意识”,即可以确认的历史中的人物、事件和现象;语文学精神传统的另一个来源是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他把语言的产生归结为人的“悟性”,使语言与人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何以语文学?
作者在绪论部分就表达了研究材料的浩瀚使得人文学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方法论上的,而20世纪伟大的语文学家埃里奇·奥尔巴赫的世界文学研究路径恰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奥尔巴赫[5]在其著名的论文《世界文学的语文学》(PhilologyofWeltliteratur)中指出,“为了完成重大的综合性研究,选择一个起点是必需的,它就好像是主体可以掌控的手柄。起点必须选自一系列有清晰界限、容易辨识的现象,而对这些现象的阐释就是现象自身的辐射,这种辐射涉及并控制比现象自身更大的一个区域。”很显然,《汉语的意义》采用的即是奥尔巴赫所描述的语文学的研究路径,以西方汉语观为“手柄”(handle),对这种观念形成的历史作出阐释,并以此辐射比这种观念更大的区域,即世界文学,以此反思人文学科研究的意义。
西方人关于汉语的研究材料极为丰富,拥有这些材料不是难事,但有效利用才是重点。我们需要一个有利的切入点来发掘材料背后的文化意涵,并以此反观西方思想史与汉语观之间的张力,凸显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该书很好地抓住了语言的文化属性,利用语言探究思想、观照文化,使我们对汉语的认识更加深刻。
三、研究视野的横向比较
西方汉语观,顾名思义,即西方人关于汉语的观点和思想,显然,西方人对汉语的论述即是西方汉语观研究的起点,但却不应是终点,因为汉语观是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对汉语的总体认识,更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社会和历史的总体想象中的核心内容,对汉语观做本体探讨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至少在该书中,作者并没有梳理西方汉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也没有对汉学家的观点进行分门别类的考究,而是把汉语观与西方现代理念和现代知识体系中一些带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对照,以揭示历史事件背后暗藏的思想关联。
语言上的变化从来都不是独立发生的,它和社会各方面息息相关,相互影响。欧洲现代民族语言的形成过程就是欧洲语言去拉丁化过程,即语言由统一走向分裂,此过程标志着欧洲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整个欧洲现代化的开始,但后拉丁时代语言的碎片化也给欧洲内部的交流带来了隔阂,在欧洲的文化中留下始终无法弥合的分裂感。同时,从宗教体系走来的西方文化,普世主义价值观始终存在,致使西方认为自己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放之四海而皆准,始终从自身角度出发,认识东方,解读东方。
被分裂感困扰并追求普世价值,西方开始了世界通用语运动,一是寻找在巴别塔丢失的“原始语言”,二是依照理性原则和“科学”的方法再造世界通用语。正是在此背景下,汉语进入到欧洲学人的视野。部分学人认为汉语历史悠久,存在于巴别塔出现之前,因此是原始语言;另一些学人则认为汉字的表意特性使之超越了不同口语间的差异,可为再造世界通用语提供最佳方案。但随着研究深入,西方汉语观逐渐偏离语言技术层面而转向社会文化各方面,形成了一套固定僵化、充满偏见的话语体系,这套体系被不断复述、挪用、误读和想象,影响到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同时也影响到中国对自身的认识,即西方的“东方主义”和东方的“自我东方主义”。
18世纪理性主义在语言上的一个表现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通过对梵语与拉丁语、希腊语进行比较,语言学家发现了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印欧假说”上的印欧语系。印欧语系存在的一个前提是——不同语言存在同宗同源,这可被视为欧洲普世主义价值观在语言研究上的另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另有学者却认为与其去研究无法被证实的语言起源的假设,不如横向比较语言之间的同质性。汉语,这种与欧洲语言异质的语言,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的他者,由于其没有屈折变化的语法机制,被认为是“有机”的印欧语系之外的“无机”的语言。这种认为汉语是“无生命的”“不自然的”观点被转嫁到“中国观”上,影响着西方,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知识分子为改造国家、拯救民族而提供的“药方”。
四、研究焦点的纵向延展
文化上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西方汉语观同样如此。作为一种文化互动的结果,西方汉语观从东方生发,被西方接受、言说、传播,必定会在空间上再次转入东方,产生反响。因此,仅仅停留在西方语境下讨论西方汉语观显然是片面的,只有连上东方的一环方能形成文化互动的完整例证。《汉语的意义》所展现的广阔的视野,把西方汉语观放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下进行考量,以欧洲典型语言事件为纽带,展现了观念的形成过程。而作者的目的非常明确,对西方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所以该书的焦点在于阐释西方汉语观对于中国自身的影响,何时发生?何种影响?对于这一焦点的追问,作者进行了纵向历史的考察,展现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的求索之路。
中国社会进入晚清,民族自信崩塌,国势衰微,民族、国家挣扎于生死存亡之间,内忧外患的困局使国人体察到文化层面的困境。在变中求生存,成为晚清社会有志之士共同的呐喊,因此,晚清社会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剧痛,也呈现出社会方方面面的巨变。此时,文化层面变革的核心在于语言文字的改革,主要包含三个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部分:一是追求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二是追求汉字拼音化的“切音简字运动”,三是追求语同音的“国语统一运动”。简言之,中国近现代语言文字变革力求以“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以及注音的字母化”改造汉语。作者在书中指出,这些变革基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汉语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在西方传教士、比较语文学家的影响下进行的,至少也是在其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中国语文改革运动其实是世界语文现代性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之后在该书中,作者梳理了清末民初我国学人提出的语言文字改革的不同路径,并阐释了这些不同路径与西方汉语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作者点出不同路径的两点实质:一是废弃文言,走白话道路,统一书面文字和口语的句式、语法和表达形式;二是废除汉字,走拼音文字的道路,统一书面语和口语的发音,使书写系统准确反映口语的语音。前者恰是12世纪前后欧洲语言去拉丁化,形成罗曼语过程的再现,并且传教士以方言翻译《圣经》的实践也助推了口语进入书写系统的过程;后者与西方思想家和语文学家对象形文字的贬抑,对单音节汉字数量“庞大”的批评有关,认为汉字“难学”“难记”,同时传教士注音汉字的实践也给予中国学人以启发。
五、 研究范围的跨领域辐射
《汉语的意义》的研究路径是奥尔巴赫所描述的语文学的研究路径。奥尔巴赫之所以提倡语文学,是因为他深信语文学的思想方法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方向,要走向世界文学的未来必须重返维柯开创的传统,以“为世界而爱”的精神解读人类总体经验和历史进程,以思考改进此时此地的生存和文化条件。该书不但遵循了语文学的研究路径,还秉承了语文学的精神,把个别性的分析和一般性的综合统一起来,以民族性的事例反观世界性的进程。因此,作者在全书最后,立足中国晚清社会的语言变革,描绘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路径,从而达到辐射世界文学的目的,从语言文字跨越到民族文学,再到世界文学。
首先,从语言文字到民族文学是一条明线,因为显而易见的是,现代文学是白话文学,是以白话为媒介的。作者基于对欧洲语言变革和晚清中国语言变革的研究得出结论: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段、不同历史空间的语言改革运动表述了相同或相似的诉求和期待,都希望通过改革语言达到改进人的生存状况和条件的目的,例如欧洲的罗曼语运动和晚清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都是试图通过建设和发展适合本土语言社群的现代白话,建构现代意识,催生现代文化,促进现代民族文学的成长。
其次,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则是一条暗线,因为虽然现代文学的主要内容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但主要形式和体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和文学评论都并非如此,而是世界性的,“世界文学”概念本身所蕴含的普适性在各国的现代文学进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作者总结道:欧洲现代文学的道路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学与欧洲民族文学成长的经历是一致的,正是在此基础上,世界文学是可描述的,并且是有意义的。
六、结语
《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以汉语为切入点,按照语文学的研究路径,考察了现代知识体系下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并重点讨论西方汉语观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交织,之后,本着语文学的“为世界而爱”的人文主义精神,阐发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为解读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该书以小见大的研究视角,凸显了研究视野的横向比较、研究焦点的纵向延展和研究范围的跨领域辐射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