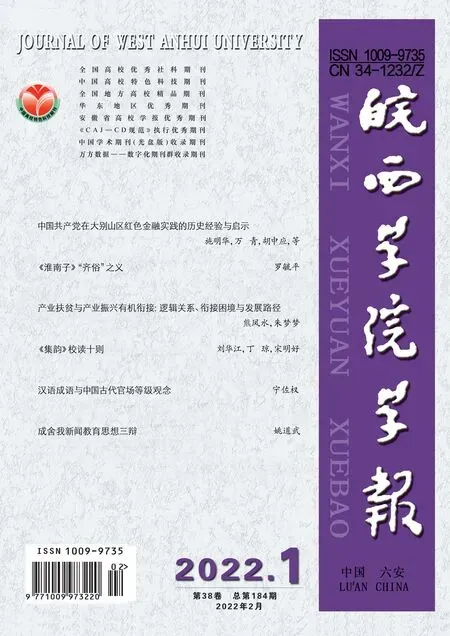成舍我新闻教育思想三辩
2022-12-07姚道武
姚道武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成舍我(1898—1991)(以下统称成先生)倾其一生办报,在报界摸爬滚打了77年,是民国时期卓有成就的报人之一。无论是践行其创业理想的“世界”报系(《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还是进一步推动报纸大众化的《民生报》《立报》等,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在那个极其动荡的年代,能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着实不易。不仅如此,他还热心于新闻教育事业,创办新闻学校,是民国时期“以个人力量从事新闻教育,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成绩最突出的卓越的新闻教育家”[1](P251)。
成先生办报乃至办学所取得的业绩是业界和学界有目共睹的,也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然而,学界对成先生在新闻教育上的某些探索也有不同的声音。梳理一下历年关于成先生新闻教育研究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在办学宗旨、办学目的和育才观等方面,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成先生办学是为了所谓的“问政”,为了实质性的“赢利”,甚至因其重视技能教育而直言其不可能培养出新闻界的“大师”。果真如此吗?下面我们就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谈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讨教于方家。
一、办学宗旨:“问政”与“问民”
成先生创办学校,从事新闻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是“问政”。这里所谓的“问政”,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问政”,它是有其特殊含义的,即主要是指为了“对抗强大的”军阀集团,通过干预腐朽的政府行为而达到最终目的[2]。如果说成先生创办新闻教育意在培养关心时局的学子,那是没错的,因为新闻工作者本来就是社会的监测者、守望者。在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成先生特别反对欺世盗名,痛恨腐朽反动,并期望通过报纸予以揭露、批驳。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新闻监督”,就是“舆论引导”。但如果要是说成先生办学就是为了培养问政,甚至是为了问政而问政的人才,那无疑是片面的、不客观的,显然是有违成先生的办学宗旨的。
不可否认,成先生办报和办学都特别重视新闻人应该自律守正,弘扬公平,匡扶正义,反对报纸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主张报纸要善于揭短,敢于抗腐。早在1925年,他就在《世界日报》的发刊词中明确强调新闻人应该“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但我们只要认真看一看成先生的新闻作品以及他对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的相关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之所以从事新闻教育,其着力点和他办报一样,不仅仅在于通常意义上的“问政”,即关心时事,曝暗揭短,更在于“问民生”“问社情”。他特别反感报纸刊载不良官员娱乐化方面的信息,竭力主张并践行培养学生关注社会情势、关心民生疾苦,要求学生将来要通过有价值的新闻引导社会去化解矛盾、解决民生疾苦。就是说,他要求新闻学子走上社会后,要更多地把目光锁定在百姓身上,并要放眼社会。成先生的办报实践很好地诠释了他的教育宗旨。他所创办的报纸很好地践行了拉斯韦尔所说的大众传播的“协调社会矛盾”的功能。他特别提醒报界同仁,报纸应该传播“大家要说的话”,应该“以国民的意见为意见”。他还在《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中揭示当时的报纸大都“只是特殊阶级的读物,而不是社会大众的读物”[3](P69),其传播的信息内容偏向于官场要人娱乐化的言行举止、作风做派。他举例说当时的报纸基本都是把重要人物的交往、官场的沉浮,作为重点关注的内容,不遗余力地去报道,并置于重要版面,甚至将某些要人的园游会放到报纸的头条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而社会上的那些人们普遍专注的严重事件,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件,反倒很难见诸报端,或在报纸上被弱化处理,比如他曾提到某报将刚毕业的大学生迫于生活压力而投江自杀的新闻仅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里。抗战爆发后,他进一步强调报纸应该关注广大社会,将底层人们的生存状况纳入媒体人的视野,呼吁报纸多刊载大众特别关心的、迫切需要了解的信息。可见,成先生办报和办学不仅仅是要“问政”,而是更在乎“问民生”“问社情”。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成先生不主张新闻学子关心时事,他只是反对报纸被私用,被利用,反对信息传播娱乐化,特别反对猎奇少数官场要人的风流轶事。成先生本身其实是特别关心时局的,他自然也会要求学生关心时局。成先生尤其痛恨腐朽反动,欺世盗名,主张通过报纸予以揭露和批判,并竭尽全力呼吁充分发挥新闻传播的监督功能和价值引导功能。无论是北洋军阀代表之一的张宗昌,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汪精卫,成先生都秉持“坚定立场,言论公正”的原则,坚守底线,不惧强暴,拒绝贿赂,始终坚持揭发腐朽,彰显正义。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问政”理解为抨击欺世盗名、揭露腐朽,揭示社会阴暗面,那么,成先生则意在培养既“问政”,又“问民”“问社情”的新闻传播人才。即要求培养出来的新闻学子走出校门后要坚守民族大义、站稳立场,不畏强暴,激浊扬清,挞伐腐朽反动,弘扬公平正义。同时,又要以民生的视角去关注社会情势,了解大众疾苦,始终为劳苦大众发声。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去理解,那么,在成先生的新闻教育理念中,“问政”和“问民”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二者的统一充分说明了成先生是要造就自觉关注社情民生,自始至终尽职尽责的新闻学子,要求这些学子离校后能尽到一个报人应尽的社会责任。
二、办学目的:“赢利”与“共赢”
学界有种观点认为,作为民办报业创业者和经营者的成先生,其办报初衷不同于“政治家”型报人,他的初衷很明显,就是为了“赢利”,并认为“赢利”也是他“开办新闻学校的又一考虑”[2]。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成先生办学和他办报一样,其目的也是为了“赢利”。但在我们看来,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成先生作为报业实业家,经营“世界”报系及《民生报》《立报》等,其初衷当然是为了赢利,这是所有企业家的创业目标,无可厚非。但如果片面地说成先生办学也仅仅是为了“赢利”,那就有点不厚道了。我们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成先生有关办学的相关论述和办学实践,就不难发现他的办学初衷是要将国外的先进办报经验与当时中国的报业实际结合起来,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优秀报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其人才培养目标是“德智兼修”“手脑并用”,其目的是想通过这样的人才来改革报业,促进报业发展,推动“报纸向民间去”,实现报业大众化,这才是他办学的最高理想和追求。从这样的追求看,成先生的办学是肩负了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诚如他所说:“要实验我们的理想,非有根本彻底的办法不可。而人才的准备尤为重要。”[3](P71)看来,成先生是要通过举办新闻教育这个根本彻底的办法来实验新闻理想,他创办学校意在探索当时情境下中国的新闻教育之路,岂能仅仅用赢利来说明他的办学动机呢?显然,赢利并不是他创办新闻学校的初衷。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他的办学在客观上对其报业赢利是起了间接作用的,因为通过办学培养的各级新闻人才,大部分进入他的报社,这在客观上无疑能够促进其报业的发展。
更有甚者,有种观点毫不掩饰地说成先生早期的新闻教育实践“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他们的理由是成先生“前堂后坊”的手工作坊培养模式,意在为自己报纸培养人才,将“实用性目的置于首要乃至唯一的地位”[4]。这话乍听似有道理,可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其实是有失公允的。成先生新闻学校的学员到他所办的报社实习、为报社做事不假,所培养的学员大多到了自己的报社也是事实,但要因此说他办学带着强烈的“功利性”,认为“实用性”是他办学的首要目的,那未免不够格局。实际上,换个角度思考,这恰恰体现了他的办学特色,彰显了他在新闻教育上的探索。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成先生是在探讨“学”和“做”如何结合,如何相互促进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学不做是不会学有所成的。所以,成先生是在拿自己的学校和报社当试验田,意图改革新闻教育模式,探索新的新闻人才培养方法,为当时中国落后的新闻教育寻找出路,从而推动报业改革,实现报业大众化,推动“报纸向民间去”。
当然,在探索新的教育方式的过程中,学生边学边做,服务于报社,为报社减少了一定的用工开支,报社得点小利,这是事实,但如果因此说成先生办学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报业,功利性太强,那未免太看低了他的格局。我们知道,成先生采用的“前堂后坊”式的办学模式,一方面,学生实务于“后坊”,确实能给成先生的报社节省点劳力,减少一些开支,但另一方面,报社每年都要拿出一定的资金反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同时,成先生所办的初级职业班和高级职业班,以及在新专开办的报业管理夜班、无线电特班等均免收学费,所以有人说他创办的学校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免费私立学校”[5]。实际上,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实习,理论与实践结合,无须花钱,无须自己寻找实习场所,就能很快提高动手能力,这对学生来说,无疑也是得利的。何况,学生服务于“后坊”,还能解决食宿问题,这对那些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差但又十分好学上进的学子来说,是不是一种机会呢?至于“自产自销”“为自己报纸培养人才”一说,那也是极其片面的。因为,成先生招生时,就在简章中明确说明了学生毕业后的三条出路:一是自愿升学的,初级班毕业后可逐级深造;二是自愿服务的,由学校派赴进入成先生的报系;三是前二者都不愿意的,听其自由,学校不加干涉[6]。可见,学生进入成先生的报系是以自愿为原则的。换个角度看,成先生其实是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的。学生毕业后进入成先生的报系能够驾轻就熟,很快进入角色,所以不少学生原意选择留下。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当下,这种机会恐怕也是广大新闻学子求之不得的。
所以说,成先生的这种探索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用现代流行的话来说,成先生探索的这个办学模式是个“双赢”的模式,即既有利于办学者,又有利于受教者,这有何不好?我们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办学,讲究一些回馈和经济效益,本无可厚非,何况还是“双赢”的局面呢?
三、育才观:“大师”与“一专多能”
有学者认为成先生太过看重“实务和实习”,过于重视“获取和编制新闻技巧的传授”。教育教学过程中,“工业化、实践化气息太浓”,导致“理想和道德教育缺失”,以致“很难走出一位真正的报业大师”[2]。不难看出,其言下之意是成先生办学秉持实用主义,偏重于技巧的传授,讲究实务,更多的是一种学徒式培养,而忽视系统的理论传授,缺少“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感”“道德品性”等优秀人文素养教育,最多只能培养出“匠人”,不可能培养出有理论、有思想、有深度的“大师”级人才。
然而,这种观点极其片面,既不合逻辑,也缺乏学理基础,因为无论怎么看重实务和实习,都不可能成为削弱优秀人文素养培养的必然原因,何况实务和实习过程中,人文素养教育是不会缺位的呢?相反,实践教学也是实施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有效的人文素养教育往往是蕴含于一切课程教学的始终,当然不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当下所强调的“课程思政”,或者说“思政进课堂”,是要求把思想品德教育贯穿于所有课程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显然,动手能力的培养并不影响“课程思政”的实施,相反,还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实际上,我们只要对成先生的办学宗旨和办学过程有个系统的了解,就会知道成先生恰恰是特别重视人文素养的教育培养的。凭着办报阅历和长期的新闻活动,他充分认识到当时的新闻记者,尤其是外勤记者,普遍存在的最危险的问题,就是不能“忠于职守”[3](P64),他深知当时有不少新闻记者道德素养缺失。对此,他感到非常焦虑和痛心。所以,在新闻教育的学理方面,成先生第一强调的就是“新闻道德对于社会之影响”[3](P68)。他特别强调办新闻学校,培养新闻人才,不仅要加强技能训练,提高动手能力,而且要高度重视人格品德教育。他“后坊”门上的一副对联“莫刮他人脂膏,要滴自身血汗”就是有力的证明。其实,成先生对学生进行人格品德教育,是贯穿于从招生到毕业的始终的。招生时,他就勉励说:“秀才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毕业时,他也不忘在学生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新闻记者拿红包,罪恶甚于贪官污吏。”而在整个求学过程中,学生常常会听到成先生这样的谆谆告诫:记者手握的一支笔,就像战士肩扛的一杆枪,是用来维护正义,惩恶扬善的。
系统性理论知识的学习,成先生也是特别重视的。夯实“理论素养”,以及绝不忽视“品德陶冶”,都是他的一贯追求,即成先生恰恰是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理论传授、品质熏陶和道德感化的。为此,他还曾公开表示要“聘请最好的老师”[7](P110)。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开课清单看,学科课程,高级班开有新闻学、报业管理等。为扩大视野,增加知识涵养,还设置了社会科学大意、自然科学大意、国文等课程。在教员的聘用上,成先生特别注重专业素养和道德品行这两个条件。办学之初,他就很用心地聘请了学界名流,比如张友渔、左笑鸿、萨空了、赵家骅等。这些德艺双馨的教员凭着自己的深厚学养和优秀品行,自己编写教学讲义,不仅教给学生理论知识、专业技能,还在课堂上随时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在将来做一个有品位的记者。同时,还通过他们平时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令人敬佩的是,成先生本人也是高素质教员队伍中的重要一员。
至于“培养不出大师”一说,就更加没有意义了。虽然说“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但是我们总不能把培养“大师”作为当元帅的标准,当然也不能以所谓“大师”这个标准去衡量办学的质量。新闻学校关键要看是不是能够培养出符合时代特点,适应社会需要,受新闻媒体欢迎的新闻专业人才。况且成先生的学校办学时间短,尚处于探索之中,本科尚未开办,加之时局动荡,这种情况下,能坚持办学,及时为社会输送急需人才,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岂能用培养“大师”去苛求于他?相反,如果不是生逢“国之大,竟无安放一张课桌之地”的动荡年代,如果能依据“逐级培养”“因材施教”的策略,按计划完成本科教育,“大师”不敢说,但培养出能胜任报业工作的“一专多能”的优秀新闻人才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实际上,培养出“一专多能”的新闻学子才是成先生孜孜以求的培养目标,也是他的办学宗旨。
由此看来,成先生从事新闻教育不只是为了所谓的“问政”,还在于“问民”“问社情”,即培育出来的学生要能够敏锐观察时事、细心关注社会、热心关心民生;不单单是图自己“赢利”,而在于追求“双赢”,即办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得利,而且相互促进;不奢求培养所谓“大师”,而在于应社会之需,解媒体之急而探索培养不同层次的、实用的“一专多能”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