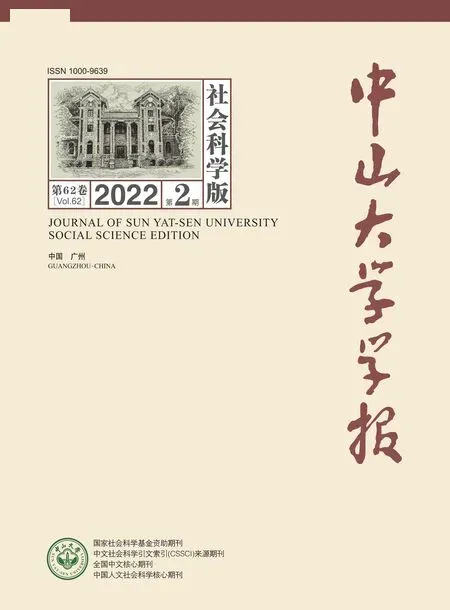“运动”的另一种轨迹*
——作为“白话小说”的《一日》
2022-12-07李扬
李 扬
引言:被追认的“第一”
1928年4月,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适在为之撰写的序言中,将作者发表于1917年6月的小说《一日》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提并论,隐约涉及“第一篇白话小说”的相关问题:“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时有意做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①胡适:《胡序》,陈衡哲:《小雨点》,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第6页。胡适以《狂人日记》为基准,将“第一”的刻度前移,于发表时间上为《一日》寻求历史定位,主要包孕着将《一日》纳入文学革命语言变革的环节并将其经典化的意图,不啻为对“运动”发端的一种建构。事实上,无论“白话”还是“小说”之于《一日》而言,均非不言自明的预设物。这篇小说不仅没有完全脱离文言的痕迹,而且陈衡哲日后也发觉,根据文学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标准,它亦无法完全纳入“小说”的范畴。
现代白话小说作为一种全新的体式,经由文学革命的发酵区别于传统白话叙事文学,但它不存在天然的定义,而是通过不断地辩驳与实践,在“运动”中成型的。因此,被整合进文学革命的历史叙事与参与“白话文学”的理论建构之前,《一日》究竟表现为何种文体特征?我们又该如何审视其文学史意义?这些问题理应放回它所诞生的语境中加以阐明。
众所周知,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以进化论为基本依据。陈衡哲日后将《一日》追认为“同情”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提出的白话文学主张①陈衡哲:《改版自序》,《小雨点》,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页。,这种说法遮蔽了以下事实:陈衡哲试图通过白话小说处理个人的情感经验,而不是站在新/旧文学对立的角度,强调“白话”之于文学革命的工具属性,因此胡适作白话诗“自古成功在尝试”的抱负无法套用在陈衡哲小说创作的动机之上②胡适:《尝试篇有序》,《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第4卷第2号。。当我们跳出胡适对《一日》之于文学革命发生史意义的建构,便会发现,这一诞生于异域的小说提供了考察文学革命发生史的独特视角,其中许多无法糅杂进整饬历史叙事的部分,有待我们进一步清理。
一、白话之“白”:“游戏”还是严正?
《一日》初刊于1917年6月《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2期,内容分别以“早晨”“课室中”“午刻”“下午”“晚上”等9个小标题统摄。小说以人物对话为主体,记叙了美国一女子大学学生一天的日常生活,各情节之间联系不大,结构松散。以文学革命以后逐渐建构起来的标准评价,这篇小说的文学质量不算上乘,学界在论及它时也大多一带而过。《一日》之所以引人注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将其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劼人的《儿时影》等作品并置,就孰为“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争执不休③较早指认《一日》为“第一”的学者是夏志清(见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 年,第125 页);随后又有蔡辉振等学者持此观点(见蔡辉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为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万平近、李西亭、文贵良等学者则否认这种观点(万平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还是〈一日〉》,鲁迅研究学会:《鲁迅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35—254页;李西亭:《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大公子〉——从陈衡哲的〈一日〉谈起》,《中国文化》2002年第19、20期;文贵良:《语言否定性与〈狂人日记〉的诞生》,《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8期)。。然而,无论结论如何,这些研究都未真正从语言层面关照该文本的“白话”特质。
《一日》未脱文言痕迹,呈现出汉语书写转型期的特质,但并不妨碍小说语言的透明性,导致很难从中读出什么“深意”。对研究者而言,如果仅从语言的表层现象入手,作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分析,似乎无法真正触着“白话”背后潜藏的精神空间。但是,如果稍稍将视线打开,将其放置在陈衡哲所处留美学生圈文学革命的白话论域里,便会释放出更多的历史线索。
陈衡哲日后谈及这篇小说时说道:“那时在留美学生中,正当白话与文言之争达到最激烈的时候。我因自己在幼时所受教育的经验,同情是趋向于白话的;不过因为两方面都有朋友,便不愿加入那个有声有色的战争了。”④陈衡哲:《改版自序》,《小雨点》,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页。陈衡哲这里所谓“有声有色的战争”起源于胡适、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等人1915 年夏天开始的你来我往的打油诗。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这样描述这场“战争”的文学史意义:“‘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⑤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6页。
尽管陈衡哲不曾公开发表打油诗,事后将自己置身事外,佯作旁观,但事实上,她不仅在私下身体力行地参与了创作,而且《一日》诞生的语境和对话对象也离不开打油诗及其创作主体。回到《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2号的文章编排上,与《一日》同时刊出的,不仅有胡适的打油诗《新大陆之笔墨官司》与“诗八首”,任鸿隽的《月》(二首),还有陈衡哲使用浅近文言书写的《记某军官之言》和两首旧体诗《寒月》《西风》。此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业已在《新青年》上发表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号。,而留美学界却未感受到太大的波澜,甚至《季报》后来遭遇小说“稿荒”,只好转载《新青年》的稿件⑦[俄]泰来夏甫著,胡适译:《决斗》,《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第4卷第3号。,《季报》的文学图景仍“半新不旧”。此时胡适任《季报》总编,陈衡哲位列本期“编辑员”首位①自1916年第3卷第1号起,陈衡哲开始担任《季报》编辑。,胡、任、陈“三个朋友”的文章同时刊出,并不令人意外。有趣的是,从作品的完成时间上看,以上篇目编织出的事件之网别具深意。其中,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几首有关“月”的诗公开发表,更类似于为未完事件匆匆画上的句点。无法用新/旧、中/西、雅/俗等话语简单地进行阐释,更不能用“轶事”之类的说法勉强搪塞,而是应该看到,作者们的笔端之下掩映着语言观念的较量。
关于这一事件,江淼的《陈衡哲传》一书中有较为详尽的梳理,在此仅作概述。“三个朋友”纸上建交后,任鸿隽对陈衡哲渐生情愫,1916 年11 月5 日作三首“月”诗,寄给胡适。胡适看破任鸿隽的相思之意,便用打油诗改任诗第三首末两句“安得驾蟾蜍,东西只转轮”为“可惜此时情,那人不知道”,并将此透露给陈衡哲,成为矛盾的激发点。其后杨杏佛、胡适又都围绕“月”作诗,更升级了“月”这一意象暧昧不清的意味,成为一场“事件”②江淼:《陈衡哲传》,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第44—59页。。
胡适谈及打油诗的作用时说道:“打油诗何足记乎?曰,以记友朋之乐,一也,以写吾辈性情之轻率一方面,二也。人生那能日日作庄语?其日日作庄语者,非大奸,则至愚耳。”③1916 年10 月23 日胡适日记,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 册(1915—191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2页。陈衡哲虽不曾以打油诗为实,直接参与白话文学的论争,但与梅光迪等人的“刻板”面孔不同,她在与胡适的通信中,借助打油诗毫无忌惮地开玩笑,连口才甚佳的胡适也甘拜下风,在回信中的打油诗里写道:“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④1916年11月3日胡适日记,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1915—1917),第499页。。在信件来往中以白话袒露自我,直接承袭了陈衡哲幼年时期以白话写家书的经验⑤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2页。,呼应了打油诗能写“性情之轻率”的特征。然而,如果说胡适以不登大雅之堂的打油诗申称自己的文学主张、进行诗歌“实验”,引起梅光迪、任鸿隽等朋友的反对,还属于文学观念的探讨,那么打油诗朝向日常生活或者释放自我性情的一面,一旦被摆在公开的位置上,则可能更有争议。它所处理的是书面白话如何公开表达现代人真实情感的问题。可惜的是,这一点并未在当事人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得到充分讨论,而是以系列“月”诗的发表作以了结。
打油诗半开玩笑的态度在胡适的朋友圈里本来心照不宣,然而这种“俚俗”渗透进私人情感领域⑥1916 年12 月21 日胡适日记,胡适引《升庵外集》,称“诗之俚俗者曰‘打油诗’”(见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1915—1917),第515页)。,违背了“发乎情止乎礼义”,显得“越界”。胡适在任鸿隽和陈衡哲之间制造的暧昧氛围令任鸿隽陷入窘迫,而陈衡哲对这种玩笑的态度也十分严肃,不仅向任鸿隽陈说了一大篇“庄重语”⑦1916 年11 月11 日任鸿隽致胡适,胡适著,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 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32页。,并称胡适是“胡闹”⑧1916年11月25日任鸿隽致胡适,胡适著,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第244页。。可以说,打油诗的语言之“白”缺乏蕴蓄的特征,即便在胡适的小圈子里也暴露了它的缺点。胡适改任诗本是玩笑,却被任鸿隽称作“vulgarity(猥亵、庸俗)”⑨1916年11月23日任鸿隽致胡适,胡适著,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第243页。。任鸿隽一改对胡适的打油诗“文章革命标题大,白话功夫试验精”的评语①任鸿隽为胡适拟出“白话之集”的题诗(见1916 年12 月20 日胡适日记,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1915—1917),第515页)。,也暂时偏离了“文言白话之争”这一论争中的矛盾焦点②“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就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1916年11月24日任鸿隽致胡适信,胡适著,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第189页。),引申出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借打油诗发表白话文学主张尚有可讨论的余地,那么,打油诗这一体式天然的“游戏”特征如何与复杂的情感议题对接?白话文学实验能否依托其他文体推进,倘若可行,该文体是否能更加妥帖地处理个人生活题材?倘若遭遇阻碍,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白话能够在“小圈子”以外,含蓄而顺畅地书写私人化的生活经验与情感?
回到《一日》的语言,它符合胡适“释白话之义”中的主张,俗化、明白、干干净净,显得颇为清爽③胡适、钱玄同:《通讯:论小说及白话韵文》,《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1号。,从这一面讲,确为声援胡适之举。但是,在历史的现场中,《一日》与打油诗共时存在,应当考虑陈衡哲力图以一种严正的书面白话与胡适的打油诗形成对话的可能。
胡适曾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将近代取材于“留学生女学生”的小说归入“下流”之列,与“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一类选材相提并论④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针对“女学生”这一形象在晚清民初的小说中被脸谱化甚至负面化的现象⑤黄湘金:《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4页。,《一日》某种程度上带有重塑自我形象的目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白话展现真实校园生活,特别是女大学生的私人活动,使之摆脱“厌女”的符号?如何在公开发表中凸显白话通俗平易的优势,规避它过于直露的缺点?如何协调口语与白话的不对称性,使其不失口语的明白晓畅同时又不流于鄙俗?综观《一日》,可见陈衡哲对形式与内容的思考糅杂在一起,以白话为女学生以及自我“正名”。这主要通过人物口语的书面化实现:一方面,人物对话中出现“谢天谢地,一天又已过去了”“我要饿死了”“我的天呀”“几乎把我吓死”等一系列感叹句,展现女学生鲜活天真的一面;另一方面,对话中又掺杂着“请”“谢谢”等敬词,摹拟学生之间彬彬有礼的态度⑥陈衡哲:《一日》,《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第4卷第2号。。用白话的好处之一在于“记实”,“适如其人之言有好处,是逼真”⑦张中行:《文言和白话》,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0页。。这种以自我正名为目的的“逼真”,摒弃打油诗的“游戏”之义,走上了严正的道路。当然,相比打油诗的泼辣与“俗”,严正而重“文”的姿态也不失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自我收束。1915年陈衡哲应任鸿隽之邀加入科学社。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月刊使用文言书写,赵元任将其称之为“严肃的写作”⑧赵元任:《赵元任早年自传》,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第108页。。1917 年6 月《科学》月刊第3 卷第7 期发表陈衡哲的《论行星轨道》一文⑨陈衡哲:《论行星轨道》,《科学》1917年,第3卷第7期。,几乎与《一日》同时发表。陈衡哲以“严正”的白话对话“游戏诗”,亦可见“科学”精神对“文”的恣肆造成的压力⑩参见袁一丹:《新大陆的旧文苑——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
专家共识推荐:NMIBC患者行电切术后应常规行膀胱灌注化疗或免疫治疗,以减少肿瘤复发和进展的几率。即刻灌注则仅能使用化疗药物,并在没有膀胱穿孔或严重出血的前提下,术后尽早完成。
总之,“白话”并不是静态的文本,它也连带出一个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动态空间,一个对话的场所。它提示我们,落实在纸面上的观点交锋固然重要,更不能忽视语境的重要性。作者选取何种语言进行书写,最终还要回到语言的对话、沟通本质。过于强调打油诗之于白话诗发生的重要性,也消解了文学革命的白话实践背后不同的发言姿态。
二、“一日”体的小说化
在1928 年出版的小说集《小雨点》中,陈衡哲自称《一天》只是“白描”,“不能算小说”①陈衡哲:《自序》,《小雨点》,第17页。,此一判断也得到任鸿隽的认同②任鸿隽:《任序》,陈衡哲:《小雨点》,第11页。。倪墨炎也有类似的说法:“整个作品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也没有较为集中描写的人物。它显然是一篇记事而不是小说。”③倪墨炎:《现代文坛偶拾》,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年,第10页。《一日》发表时标“记实小说”,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上述判断与“记实小说”的分类方式?
事实上,以一天为时间单位,按照时序记录见闻的方式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与《留美学生季报》等留美学生主办的刊物上并不鲜见。这一体式类似新闻报道,在较短的篇幅内勾勒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与以客观立场为旨归的通讯报道不同,它们常常夹带着作者的个人情感与强烈的身份认同,姑且将其命名为“一日”体。《一日》的“记实”因素还需放在彼时留美学生刊物上流行的“一日”体中进行考察。
创刊于1905 年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是留美学生发表议论的主要园地,以留学生身份关注中国时事与世界局势,集中反映该学术群体中西交融的世界视野。其中当然不乏以“一日”为题材记录事件、表达思想的文章。司徒月兰的《博览会上的中国学生日》可视作典型的“一日”体,此文按照早—中—晚的时间顺序,记叙1915 年8 月4 日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的“中国学生日”。作者卒章显志道:“像‘中国学生日’这样的场合让其他人知道了我们的目标和宗旨,我们的希望和恐惧。它不仅提升了我们自己的理想,也提升了我们对他人的评价。”④Miss Nettie Soo-Hoo,“Chinese Students'Day at the Exposi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11(1),1915.这份刊物采用全英文印刷,以对内团结、对外宣传为宗旨,目标读者显然不仅面向留美学人圈,也面向西方世界,肩负着中美两国交流及展示中国留学生形象的任务。因此,“我们”一词的强烈代入感,回荡着作者“学生和使者”的身份变奏。
与《月报》旨在引导留美学界舆论与增强留学生凝聚力有所不同,《留美学生季报》“非留美学生会机关报”⑤《本报凡例》,《留美学生季报》1914年,第1年春期。,因此既可丢掉英文这一“拐杖”,也无需拘泥于费尽心思展示留美学生的“共同体”面貌,反而更有益于思想争鸣与抒发留学生的个体经验。尽管《月报》亦属“公共言论机关”⑥《本报编辑部启事》,《留美学生季报》1915年,第2年春季第1号。,但其中的“一日”体选取记叙的事件相对更“小”,更日常与琐碎,甚至还出现了连载的个人“日记”⑦如唐庆诒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暑假游览南美的足迹(见唐庆诒:《南游日记》,《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5卷第2号;唐庆诒:《南游日记》(续七年夏季本报),《留美学生季报》1919年第6卷第1号)。。署名“君毅”的《华尔街中之一日生活》,以第一人称口吻记录了华尔街一天的生活,试图引发读者思考种族主义问题:“人谓美国乃各种人类之洪炉,信然。然移民人口,独排斥异视东亚人种,实非理之所宜出耳。”⑧君毅:《华尔街中之一日生活》,《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5卷第2号。作者揭下中美“和平使者”的温情面纱,带出强烈的民族情感。我们发现,在有限篇幅内勾勒事件的来龙去脉并非难事,但作者的本意在于,通过“流水账”式的记录,以小见大地管窥宏大的社会与文化命题,继而阐明自己的立场。由此可见,留美学生刊物上的“一日”体,其“记实”性与“说理”性相互渗透。在此意义上,陈衡哲发表于上的《记藩萨火灾》,虽不以“一日”直接命名,但以某一具体事件为切入口反思本国问题,也可视作“一日”体的衍生品。文章亦以时间为轴,记叙她就读的瓦沙(Vassar)大学的一次夜间火灾事件。当晚火灾发生后,学校的教学、生活在短短数小时内便恢复如常,治校手段令人叹服。陈衡哲此文以“告吾国之司教育者”①陈衡哲:《记藩萨火灾》,《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5卷第2号。,表明她有意介绍西方教育理念与方法,推进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
《一日》的“实”首先来源于取材的真实,将《一日》置于留美学生“记实”系列文章中加以考察,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以“我”之眼捕捉当下日常生活片段,某种程度上带有“新闻”“速写”的特征。但这里之所以认为《一日》是“一日”体的文学变形,就在于它一方面存在“一日”体中普遍的“写实”“说理”意图,另一方面,又有意将其进行文学化处理。这些无法“坐实”或曰虚构的成分中,勾连着作者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设计与想象。
“你们在家吃些什么?有鸡蛋么?”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姑母在中国传教,你认得她吗?”
“我昨晚读一本书,讲的是中国的风俗,说中国人喜欢吃死老鼠。可是真的?”
“中国的房子是怎样的?也有桌子吗?我听见人说中国人吃饭、睡觉、读书、写字,都在地上的确吗?”②陈衡哲:《一日》,《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第4卷第2号。
1914 年8 月,清华学校首派10 名女生作为庚款生留美。1915 年秋,陈衡哲与杨毓英二人正式进入瓦沙大学就读,消息很快在留美学界传播开来③《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公布了陈衡哲和杨毓英进入瓦沙大学的消息。Personal Note,The Chinese Writen Language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Masse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11(2),1915.。1915 年11 月,杨毓英在一则英文通讯消息中写到,入学后许多老师和同学时常向她投来“善良而好奇的目光”(good natured curiosity)④“Club news:Vassar”,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11(1),1915.。寓意相反的“目光”则出现在陈衡哲的《致某女士书》中。陈衡哲观察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大多“半开化”“脑垂长尾”“卑陋无识”⑤陈衡哲:《致某女士书》,《留美学生季报》1915年,第2年春季第1号。,她对此表现出强烈的耻辱感。而在上述引文中,作为被同学审视的“他者”,“张女士”则表现得十分淡然,针对提问一一作答,反倒是美国同学密集的提问显得荒诞、滑稽。
陈衡哲通过塑造“张女士”这一形象,将现实中观看的主体与被观看的客体的地位有意倒置。择取、转化时事为“小说”的做法可以上溯至晚清的“时评”体,但《一日》的目标读者与之不同,后者已经由广大而同质的读者“共同体”⑥张丽华:《〈时报〉与清末“评”体短篇小说》,《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收缩为留美学生圈以及国内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因此在小说中,如何文学地折射西方人的“中国想象”,并对此作出回应,才是作者的着眼之处。陈衡哲有关小说的思考正体现在《一日》中传达的异域体验以及“一日”体依托的读写“圈子”中,通过调试自己与目标读者、对话对象的位置而体现出来。
此时胡适的小说观一方面还建立在晚清“时评”小说的认识基础上,主要关注小说主题与时事的关系;另一方面,阅读经验扮演了胡适小说观念形成的重要角色。就后者而言,胡适依循的是自晚清以来以题材为分类标准提炼小说类型的方法,比如将《红楼梦》视作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将《七侠五义》视作侦探小说⑦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7页。。那么,作为“记实小说”的《一日》则摆脱了晚清小说所提供给读者的现成分类方式。这里的“记实”更贴合于一种现实之“感”的表达,在实践的层面突破了胡适的小说观。尽管如此,精英意识主导下的白话小说写作,在单维度地择取生活日常、表达政治理性的同时,如何承载人更复杂的情绪与情感,仍构成一个重要问题。
三、从《一日》到《狂人日记》
事实上,作为一种现代文体,“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是在文学革命场域内各种声音的相互辩难中建构起来的。《一日》虽游离在辩难场之外,但是,将其置于一种“正在形成”的空间中,不失为一个重新进入这场“运动”的视角,以此考察现代白话小说成型的内在脉络与逻辑。
《一日》一再被后来的文学史视为胡适留美时期白话文实践的“敲边鼓”之作,但是实际上,以胡适为中心的留美学人群对白话/文言的探讨,主要围绕诗歌语言的合法性展开,白话小说并不独立地作为一个“问题”被质疑和讨论。梅光迪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任鸿隽也说:“白话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①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8页。而胡适则直接从吴趼人、李伯元、刘鹗等人的小说中寻求“活文学”的语言资源。②1916年4月5日胡适日记,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1915—1917),第356页。胡适等人对白话之于小说的可行性不加怀疑,是以明清小说以及晚清吴趼人等小说家的白话小说为参照系的,因此,《一日》之于“白话小说”的特殊性未曾得到讨论。
胡适用白话翻译的都德的《割地》(即《最后一课》),发表在1915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上,标“短篇小说”,但其译后记以文言写成,形式更接近传统的小说评点,内容则触及短篇小说的谋篇布局问题:
此篇佳处,在于设想之奇……全篇所写,是一蒙学堂中琐屑之事,计时不过半日……真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此短篇小说之上乘也。③[法]都德著,胡适译:《割地》,《留美学生季报》1915年,第2年春季第1号。
而后,在译作《百愁门》的“译者识”中,胡适将短篇小说分为两类:第一类以都德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为代表,“以布局胜”;第二类则以《百愁门》为代表,“以状物写生胜”④[英]吉百龄著,胡适译:《百愁门》,《留美学生季报》1915年,第2年第3号。。如此标准之下,《一日》虽未标“短篇小说”,但篇制短小,与《最后一课》一样,将故事凝结在一天之内,叙事结构具有胡适日后所说的“横截面”特点⑤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号。,形式上更接近重视“布局”的短篇小说。但问题是,胡适译后记所谈到的“布局”,是否是西方小说意义上的情节结构呢?将都德小说的叙事效果比作“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其目的正为突出一个“奇”字。“奇”是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审美范畴,从魏晋志怪小说开始,直至唐传奇、明清白话小说,“奇”的表现对象逐渐从神怪下沉到日常生活。陈衡哲多借助西方戏剧技巧,在小说有限篇幅内制造情节转折⑥这一点夏志清、张丽华都有提及,但未展开说明。(见夏志清:《小论陈衡哲》,《新文学的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93页;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248页)。。无论数次使用“噹”这一拟声词,以起到类似戏剧中“转场”的效果,还是在小说中插入“舞台说明”,提示人物动作,都使小说带有明显的戏剧特征,以区别于传统小说之“奇”。小说对美国女子大学生活祛魅式的书写以及追求人物语言、神情的惟妙惟肖,也使得它与“说部”意义上的“奇”拉开了距离。
但有了戏剧、写实等元素的引入,是否就意味着《一日》可以不假思索地归入现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呢?这需要进一步的辨析。1928 年《小雨点》出版时,陈衡哲称《一日》为自己“初次的人情描写”⑦陈衡哲:《一日》,《小雨点》,第17页。。此时陈衡哲对小说描写的再定义,已经受到新文化运动创制出的各种“话语”的规约,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多方面的予以界定。
如果将目光稍作偏离,便会发现,同为晚清“新小说”忠实读者的钱玄同⑧查钱玄同留日期间的日记,白话小说既不是摹写对象,也不构成白话资源,而是能排遣忧虑、陶冶性情的文学作品。,不仅对白话小说有着不同于胡适的见地,而且随着他对小说中“人情”认识的深入,直接促成了现代白话小说的新局面。1917年1月,钱玄同在“美文”的意义上将吴趼人、李伯元的小说与吴汝纶的文章作比,同意陈独秀认为吴、李二人小说的文学价值高于吴汝纶的观点。他进一步以吴汝纶“搭起架子作无病呻吟之丑文”为对立面①1917 年1 月23 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著,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4页。,申说自己的白话文学观。而在实践层面,他认为胡适的《尝试集》仍太“文”,并提出“宁失之俗,毋失之文”的建议②1917年10月22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著,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24页。。但钱玄同显然不满足于此,他很快跳出了胡适语言工具论的视野,将吴趼人、李伯元等人的白话小说置于“现世纪新文学”的标准下,指出《红楼梦》比李伯元、吴趼人、李涵秋等人的小说和《留东外史》,反而更“新”③1917年10月8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著,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21页。。陈独秀谈及章太炎论《红楼梦》擅写“人情”,随后钱玄同在日记中再提及“人情”之语④1917年4月14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著,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14页。。在他看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因无法达到写“人情”的高度,仅称得上“描写黑暗腐败之社会”的作品⑤1917年1月27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著,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06页。。因此,沿着这一思路,以下问题亟待解决:所谓“现世纪新文学”标准下的现代人的“人情”,如何区别于传统小说的“人情”?如何用白话表现现代人的“人情”?对于彼时的小说创作者而言,仅仅把“白话”与“人情”捏合在一起,就真正构成解决之道了吗?综合起来看,这里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以表现现代人“人情”为基本特征的“白话小说”,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才可被称为“现代文学”。终于,在1918年2 月《新青年》的“通信”栏中,他彻底放弃了在旧有白话小说中找药方的希望,指出中国的小说“没有一部应该读的”,并建议将对白话小说的关注点转向“译”与“新做”,亦即建立新的标准⑥胡适、钱玄同:《通讯:论小说及白话韵文》,《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1号。。钱玄同在提出“新做”小说这一主张的同时,开始频繁造访周氏兄弟⑦参见陈子善:《钱玄同日记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文汇报》2015年3月6日。,可见他急切地寻求建立一种适用于现代小说的白话规范。两个月后,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⑧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号。。
巧合的是,《狂人日记》正文的故事时间也被压缩在“一日”内,但与《一日》的最大不同,也与“日记体”本身构成悖论的是,整饬的时间秩序被彻底打破,有限的时间框架根本无法圈定“狂人”的思考空间。在这一意义上,《狂人日记》颠覆了《一日》所建构的日常生活情境以及生活感受,也质疑了形成这些感受的文化基础。陈衡哲剪裁生活片段,以展现美国女校学生形象,实际上是作者在中西两种身份认同之间寻求平衡的产物,这种以白话呈现出的精英化的“一日”,恰恰囊括在“狂人”疑惧的对象当中。《狂人日记》对整饬时间秩序的破除亦即对历史、文化整体性的怀疑,它高度象征性地指向“吃人”这一主题。因此,与陈衡哲基于文化精英立场的“人情”描写相比,鲁迅对“人情”的把握来自他真实却充满虚妄的生命体验,是反日常、反精英的。《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更展现或曰加剧了这种生存的不稳定性。在两个割裂的文本世界中,我们看到白话与文言互相搏斗的痕迹,而这也体现了现代白话小说艰难诞生的过程。对比可见,只有“向内”地探索形式与思想的统一,才能真正释放隐藏在社会历史深处“人”与“情”的因素,从而打开现代白话小说内蕴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