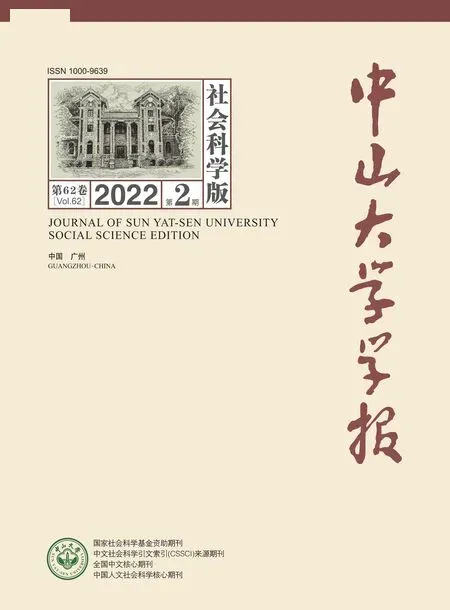形式、语言与情感: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三个维度*
2022-12-07赵静
赵 静
关于孰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仍然聚讼纷纭。而我们一般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卷之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指出《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页。。但近来关于孰为第一篇中国白话小说,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是陈衡哲的小说《一日》,也有说是李劼人的小说《游园会》、刘韵琴的小说《大公子》。从发表时间来看,陈衡哲、李劼人的小说确实早于《狂人日记》,可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文学史界都默认《狂人日记》的“开端”地位。有研究者指出,鲁迅在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时或许没有看到陈衡哲的小说作品,故而未将《一日》列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而在赵家璧关于鲁迅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回忆中也曾谈到,之所以会着手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系列丛书,主要是为了留住“‘五四’时代许多重要作品和代表性刊物”②赵家璧:《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对审查会的斗争》,《编辑生涯忆鲁迅》,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2页。;且在赵家璧看来,最先想到邀请鲁迅执掌小说卷“其他文学团体和作家”部分,原因之一是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奠基的丰碑《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的作者”③赵家璧:《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对审查会的斗争》,《编辑生涯忆鲁迅》,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4页。。换言之,《新文学大系》辑录的是五四时期的作品,借以展现五四新文化思潮,所以没把陈衡哲、李劼人和刘韵琴的小说视作白话小说的第一篇,也许与这些小说本身的“五四”感不强有关。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未将其视作开篇,大概是因为它们还算不上“现代体式”,也不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观看”范围。
一、形式的不“现代”
谈起《一日》的创作缘起,陈衡哲说这“是我最初的试作,是在一九一七年写的。那时在留美学生界中,正当白话与文言之争达到最激烈的时候。我因为自己在幼时所受的教育的经验,同情是趋向于白话的;不过因为两方面都有朋友,便不愿加入那个有声有色的战争了。这白话文的实际试用,乃是我用来表示我同情倾向的唯一风针”①陈衡哲:《改版自序》,《小雨点》,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这场文白之争的当事人胡适也说陈衡哲“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②胡适:《胡序》,陈衡哲:《小雨点》,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第6页。《一日》发表于1917年《留美学生季报》,从时间上确实早于鲁迅创作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后来收录于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的陈衡哲小说集《小雨点》,胡适、任鸿隽均为其作序,陈衡哲也写了自序。陈、任在序言里都谈到小说的形式问题。陈衡哲说,《一日》“既无结构,亦无目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白描,不能算为小说”③陈衡哲:《小雨点》,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第17页。。任鸿隽则说:“这篇东西,叙的是学校里一天的生活,不过略具轮廓,几乎不能算是小说。”④任鸿隽:《任序》,陈衡哲:《小雨点》,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第11页。
陈衡哲将其视作“白描”,而任鸿隽说其“略具轮廓”,《一日》能否视作小说,二人大体将其归为类小说而又非小说。在《一日》中,陈衡哲以“早晨”“午刻”“下午”“晚上”“课室中”等时间和地点作为分界线,将场景和时空片段化地予以割裂并相互转换。夏志清评论这种结构类似于“独幕剧”,并认为,胡适在《留学日记》中提到过爱尔兰剧作家约翰·辛的独幕剧,且在《论短篇小说》中说“写情短诗”“独幕剧”“短篇小说”这三项可以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势”。基于此,夏志清判断胡适应对独幕剧极为熟悉,而陈衡哲在美国留学期间所修的课程与胡适相仿,故而她也许也曾接触过独幕剧。甚至于,在夏志清看来,《一日》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在结构上代表了“两种创新的短篇小说体裁”⑤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93—94页。。其实夏志清的猜测不无道理,在陈衡哲留学期间确实有过较多的戏剧体验,她在《记藩萨女子大学》中提到了不少戏剧社团。可陈衡哲有过戏剧体验不假,但能否就此断定她的小说《一日》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同属于“两种创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显然,这在当时提倡白话文的“新青年”的眼中并不成立。
在提倡白话文的“新青年”看来,戏剧与小说本为独立的两种文体,故而,林纾将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小说,刘半农嘲讽他不通外语,文体不分。这些“新青年”接受的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的文体分类,而深谙古典文学之道的林纾则无此明晰的概念。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小说、戏曲本就源出同宗,在传统小说观念中,戏曲和小说都可被划归为“说部”。严复、夏曾佑都曾把《三国演义》《长生殿》《西厢记》《水浒传》《临川四梦》归于“小说”⑥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等著:《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12页。,梁启超也认为《西厢记》是小说的代表⑦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曾将小说视为改良国民性的利器,他列举的小说包括《西厢记》。。而林纾不分文体也是事实,在他的众多翻译中,无论是《亨利第四》《雷差得纪》还是《群鬼》都被改译成小说。以林纾的知识体系和接受范围来说,西方的“戏剧”不是独立的文体,他基本上将其等同于中国说部中的传统戏曲。在他看来,西方的戏剧与小说并无二致,亦或由于他不通外语,在对助手翻译的再“翻译”中,隐藏了戏剧与小说体例二分的信息也未可知。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戏剧与小说融合,甚至相互替代,本就是古已有之的尝试。以此来看,陈衡哲的小说《一日》整体上近似于戏剧,虽然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却又陷落在“戏剧”与“小说”混淆的窠臼中,算不上具有新鲜感,且“有意识”突破传统表达习惯的格式创造,甚至与林纾的逻辑有混为一谈之嫌。
而与《一日》不同,鲁迅的《狂人日记》采用的是“日记体”。陈平原指出“在接触西洋小说以前,中国作家不曾以日记体、书信体创作小说”①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5页。。不过有趣的是,林纾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就曾因加入了茶花女缠绵悱恻的“日记”而轰动一时②1901 年邱炜萲意识到《茶花女》“末附茶花女临殁扶病日记数页”。转引自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第331页;原载于邱炜萲:《挥尘拾遗·〈茶花女遗事〉》。,甚至有学者因此将其视作中国“日记体”小说的起点。夏志清也说自诩为“东方小仲马”的徐枕亚的《玉梨魂》模仿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日记体”。然而,林纾翻译小说、徐枕亚《玉梨魂》中的日记、自述都与五四时期的“日记体”小说有着极大区别。在陈平原看来,徐枕亚、包天笑等“新小说”家们虽倾向于用“日记体”或“书信体”来表达政见、讲述故事,可没有“坦率真诚地抒发情感”,“五四作家”用的得心应手的“日记体”和“书信体”,在这些“新小说”家手中总有些“别别扭扭”③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1页。。普遍意义上,我们认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④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文集》第6 卷《文论》,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3 年,第261 页。。而“日记体”小说的出现恰体现了“人”的发现。现代日记将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情绪变化推向了显性的表达层面,有其新颖性和日常感。五四作家们不是以“日记”来作小说,而是将其作为小说的一种“格式”,绝非只在小说中穿插“日记”而已,“日记体”的形式本身就有着明显的五四标识和现代意义。
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时深受果戈里写于1843年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影响。在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中,时间是分裂的、跳跃的、混沌的,其开篇是主人公波普里希钦写于十月三日的第一篇日记,接下来则是十月四日的日记,十月的日记结束之后,便是“十一月六日”“十一月八日”“九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六则日记;进入十二月后,也只有“三日”“五日”“八日”3篇日记,再后则是2000年的日记了,时间并不连贯。而鲁迅《狂人日记》的时间意识也较为稀薄,甚至连日期都没有标注,只用“月光”“晚上”“早上”表达一天的时间转移。而当狂人发狂时,小说中的时间就旋转进狂人的情绪宣泄和思维转换中了。可以说,两篇小说都是借助“日记”的“形”,以极度跨越的时间或“月亮”“太阳”等特定符号、意象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体现叙事的隐喻性和象征性。我们常说《狂人日记》有着“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格式的特别”是说它包含了新的形式,而这一新形式对“表现的深切”出力颇多。“日记”让狂人的疯言疯语合情合理,以“格式的特别”唤起了“表现的深切”,很好地表达了五四的启蒙主题。相比之下,陈衡哲的《一日》就少了这一份“格式的特别”,它的类“独幕剧”结构在突破传统文体方面没有多大的进展,也没有形成“有意味”的现代白话“小说体”。
二、语言的不“现代”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3章附录将陈衡哲的小说《一日》列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小说年表的第一篇,而将鲁迅的《狂人日记》视为“现代白话小说开山之作”⑤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45页。。后来的许多文学史也基本延续了这一观点。“开山”意为新开新立,可“白话”早已有之,并非始于《狂人日记》。因此,这里的“开山”是强调现代语言的“开山”,即语言的“现代化”。
古代文学的文言与白话虽然是并立而存的,但没有出现白话的自觉意识,也没有人发出白话取代文言的“有意识的鼓吹”。但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注意到了民间的白话小说,并认为白话小说是影响力最广的文学形式。但他也指出此种白话是无意识、不经济的白话,直到文学革命,白话才衍生出一种有意识的主张①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第17828期,1922年10月10日。。胡适肯定白话的逻辑起点是它“易于教授”,因此他开始与一些留美学生构想新的语言系统,陈衡哲便是其中的一位“同志”。陈衡哲的白话小说《一日》带有留学生的语言表达习惯,使用的白话混杂着英语与文言。陈衡哲在《改版自序》中说她创作的10 篇小说,有9 篇是完全用白话写的,“只有《一日》中仍时时有文言的痕迹存在”②陈衡哲:《小雨点》,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这些文言基本上保留在一些零碎的用词中,如亚娜与贝田贪睡差点误了钟点,写成“贝田不答,反身向壁而睡”,又写亚娜匆匆梳洗,“闪入”餐堂。“反身向壁而睡”“闪入”都留有古文的痕迹。小说中也多处出现“是……的”现代汉语结构,如“若是她向来很用功的”“中国的房子是怎么样的”。亚娜问贝田时间写为“亚娜在床上欠伸说,‘贝田,这是几点钟?’”“这是几点钟”也不是现代汉语,它脱胎于英文中的“what is time”。关于中文混杂英文的情况,《美洲问题六种》一文也有过说明:“有闽粤人焉,有江浙人焉,有燕齐人焉。我所以通情达意者,转操外邦语言,否则视为同路人,情意隔绝,不相闻问。”③朱进:《美国之欧教风俗:美洲问题六种》,《留美学生季报》1911年第1期。为了沟通方便,美东中国留学生每年的夏季年会规定使用英语,“英语这门外语反而可以超越地方差异”,“有助于留美学生形成对中国的民族认同”④季剑青:《留美学生围绕语言改革的讨论及实践与文学革命的发生》,《文艺争鸣》2020年第9期。,也间接影响了这些留美学生的白话文言说习惯,使得当时的一批留美学生使用白话时也夹杂着英语的痕迹。在陈衡哲应胡适之邀于夏季年会上所发表的一篇白话演讲稿《平和与争战》中,每句话的语序结构都没有摆脱古文的“之乎者也”,“衡哲曰平和问题者”“世界大同之先兆”“而二十世纪之表征也”⑤陈衡哲:《平和与争战》,《留美学生季刊》1917年第1期。之类的说法比比皆是。相较于这次演讲,陈衡哲的《一日》所使用的“白话”更为“平易近人”“明白晓畅”,“之乎者也”等用语已被她悉数抛弃,相反借鉴了古代通俗文学中的“古白话”,且增添了不少英语的语法结构。
胡适在留学初期的日记中曾记录他聆听英文演讲的事情。1911年7月19日的一则日记,胡适意识到“吾辈在今日,宜学中国演说,其用较英文演说尤大”⑥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他提出建立中国演说会,训练中国式演说的想法,并得到一些人的认同,遂成立了“演说会”。直至1915 年4 月25 日日记里胡适还说:“吾久决意不演说,此次不得已复为冯妇,今后决不再演说矣(此但指学生时代)。”⑦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册》,第90页。他在留学期间进行了多次演讲,大多采用古文或英文。尤其是在演讲初期,他尚未形成白话演讲的自觉,而只是关注演讲的“现场感”,如在演讲中“每句话完时常作鼻音‘nn’声”,认为此习惯“当改之”⑧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事实上,用古文或英文演讲,在1915—1916 年初的留美学生中流行甚广,胡适的古文与英文并行的演讲风格也绝非孤例,演讲会中其他留学生同仁的中文演说也均是古文。1916 年7 月,在胡适说他决意不演说之后的两个月,又于16 日的日记中写道:“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语言。”⑨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册》,第354—355页。此则日记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视作《文学改良刍议》的雏形。关于白话和文言的适用范围,他也有了较为清晰的新认识。在演讲一隅,他肯定白话演讲“可读又便于传播”的重要性,而如何使用白话,则可“阅读通俗文学”⑩胡适、席云舒:《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当然,胡适演讲语言的从“古文”“英文”到“白话”也影响了他的一些好友们,任鸿隽、陈衡哲便是他的支持者。在1916 年9 月3 日的科学社年会上,任鸿隽进行了白话演讲《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而陈衡哲也在1916 年的夏季年会上完成了她的第一篇白话演讲《平和与争战》。与陈衡哲的演讲不同的是,任鸿隽的演讲白话气息更浓,语法结构基本摆脱了“曰”“之”“也”“焉”,已较为娴熟地使用“是”“的”等现代汉语中的“系动词”和“助词”,“是……的”的表达结构也较为多见。与陈衡哲的《一日》类似,当这批留学生开始进行白话文的文学实践时,他们的语言表达始终未能完全脱离已有的语言习惯,或沿袭已深,写文章时经常匍匐“古文传统”,试图以通俗文学中明白晓畅的“古白话”替代讲究规则形式、端起架子死气沉沉的“文言”;或受到正在学习和使用的英语的影响。
其实,不仅是演讲语言受到欧美书面语与口语的影响,留学生的一些诗歌也具有中英文混杂的迹象。留学生接触到欧美等国较为新鲜且中文中未曾有的词语时,往往会直译为汉语、直接书写英文,或者在白话与英文之间找到相近的语法予以形式互换。如赵元任的白话诗写道:“才完就要做,忙似阎罗王。”并且在“忙似阎罗王”之后还补缀一句英文解释:“元任自注:work like h——”“work”意旨“工作”,延伸为忙碌,“like”即是“似”,英文与中文相互对照,基本结构无异。而当下一句说到“picnic”①胡适之:《回忆明复》,《科学》第13卷第6期,1928年。时,由于没有中文的对应翻译,赵元任则直接音译,以“辟克匿”代之。胡适的一些白话诗也常见这样的“音译”,白话俗语夹杂着英文或拉丁文的语音、语法习惯,并且,这变成他们书信往来,写诗唱和时的语言“共识”。不过这样的语言混杂在胡适归国之后有所改变,在1917年6月9日至7月10日的归国记中,胡适还保留着英文与中文夹杂的习惯,甚至还保留着古文的气韵;可在1919年的杂记中,胡适的语言风貌不仅由古文演进为白话,且英文单词也愈来愈少。对于此时的胡适来说,由留学时期广泛的“语言的接触”②戴庆夏:《社会语言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6页。形成的古今中西语言混杂现象渐次消失了,脱离了欧美留学时的语言环境,他的语言逐渐与国语运动所构造的现代汉语体系趋同。
20 世纪初,地缘环境和语言接触引发着中国语言体系的调整。以胡适为例,他在美国与赵元任等人从共商白话到归国后参与文学革命,期间存在着两个白话言说系统——留美群体的“白话”和归国后与国语运动合流的“白话”。留美时期胡适和陈衡哲等人所说所写的“白话”和来自国内不同方言区的欧美留学群体使用的语言一样,有其地域性和归属性。如粤语区的“白话”主要是指广州话,即整个粤语方言区的“标准语言”,而吴语区的“白话”又不同于“粤语区”的白话,多指“很随意状态下所进行的‘谈话’、‘聊天’、‘闲谈’”③黄华:《语言革命的社会指向: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传播学考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119页。。在马西尼看来,“白话原来也是指一个方言群中被认为是有代表性的一种语言(这个方言群常常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经济渊源)”④[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3页。。诸如“粤语区”的“白话”和“吴语区”的“白话”。那时各地的留学生聚集于欧美的高校,为了言说的方便,又受到地方性的影响,“白话”在胡适、赵元任、任鸿隽等人的倡导和实践中应运而生,倒可视为“欧美留学区”的“白话”。
其实早在胡适、赵元任、任鸿隽等人在美国进行白话实验之前,晚清中国已经有了“白话”的实践。有学者统计,“‘从现有资料来看,我们知道早在1897年,就出现了两份白话报。到1900年以后,数量开始急遽增加。根据统计,从1900 年至1911 年间,共出版了111 种白话报’事实上,这份统计资料还不完全,我就在一些报纸的记载中另外辑出二十份在这个时期内出版的白话报”⑤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18页。。这些白话报刊也影响了胡适、李劼人等人的创作。胡适在谈到《竞业旬报》时说:“1906年,我在中国公学同学中,有几位办了一个定期刊物,名〈竞业旬报〉——达尔文学说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系以白话刊行。”⑥胡适:《我的信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13页。这份以白话刊行的报纸给了他“发表思想”和“整修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⑦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第85页。。在成都,李劼人也给当地的《晨钟报》《娱闲录》等报刊投稿白话小说《游园会》和《儿时影》。对胡适影响颇深的《竞业旬报》“注重于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语言接近民间俚语。它以中国公学为核心,与胡适一起尝试白话的任鸿隽曾是其中的一员。正是在中国公学和《竞业旬报》的驱动下,任鸿隽和胡适在美国的白话实践也多围绕“教育”展开,演讲内容也多以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为己任。而身处四川的李劼人,其《儿时影》使用了很多四川方言俚语如“捱”“恁早”“欢喜过”“莫说那些虚话”“我道希奇”等。这说明,阅读习惯和方言中孕育着生成白话的可能性,作为一种语言现象,白话有其内在的发生逻辑和建构基础。
可以说,由于方言的差异,清末民初各地均存有各自的“白话”体系。有学者认为,当语言杂多时,则标志着“向心力与离心力、中心话语和非中心话语同时共存,多元互生,而不是新的向心力和中心话语的独白”①刘康:《全球化/民族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不过,既然存在着“中心话语”和“非中心话语”之分,当众声喧哗、多元互生的格局被打破,“中心话语”的向心力作用就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换言之,一旦形成了“中心话语”,虽不至于只呈现“中心话语的独白”,但其他声音也会被“中心话语”推至边缘。就此而言,陈衡哲的《一日》虽然属于曾有过的白话文学先声,可却未能符合文学革命时期的“白话”标准,就自然不能将其视作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同理,李劼人、刘韵琴的小说亦是如此。这些小说的语言多是来自创作者的地方生活语境,当以北京为中心的文学革命拉开序幕时,这些“地方的声音”便被淹没在以文学革命为轴心的“中心话语”之中了。
三、情感的不“现代”
必须承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白话”并没有成为文学语言的主流,这也是胡适所说的尚未有文学的自觉。相较于以文言为中心的中国语言版图,“白话”还位于边缘,仅被士大夫文人视为“可存”的语言载体。晚清追求“言文一致”,并非以“白话”取代“文言”。胡适归国与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等人推行白话文运动时使用的白话,也并非胡适在美国时留学群体通用的“白话”。胡适留美时讲求的“白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字”到“文学”,二是与教育形式相关的“留学生活”。可当他回国之后,他与陈独秀等新青年试图掀起一场文学革命时,则认为亟需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工具,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②[法]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审美之维》,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14—115页。。在这场决裂中,他们不仅要与“古文”较量,也要整合四散各处的文化资源。
在蔡元培的推动下,“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合流。胡适说:“这时候,蔡元培先生介绍北京国语研究会的一班学者和我们北大的几个文学革命论者会谈。他们都是抱着‘统一国语’的弘愿的,所以他们主张要先建立一种‘标准国语’。我对他们说:标准国语不是靠国音字母或国音字典定出来的。凡标准国语必须是‘文学的国语’,就是那有文学价值的国语。国语的标准是伟大的文学家定出来的,决不是教育部的公务员得出来的。”③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导言》,王蒙、王元化总主编,郏宗培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第30集史料·索引卷2》,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6—37页。国语研究会设想的“国语”更重国音,可重“国音”的“国语”在陈独秀、胡适看来却不能代表“国语的标准”。他们提倡的是“国语的文学”,“白话”“国语”不仅涉及字音、“语法”,更应该富于文学的意旨。换言之,“白话”是“文学”的白话,“白话”小说不在于是否使用了白话,而在于用“白话”写了什么。
陈衡哲的《一日》写的是留学生生活,李劼人的《游园会》写的是少城公园的见闻,而刘韵琴的《大公子》则将焦点聚焦在袁世凯的大公子身上,以他的“本事”作为小说的内容,揭露政治的腐朽与黑暗:“我于今想写的事,既不能脱小说家的范围,又安能使读者不存着看变把戏儿似的心思来看呢?岂不辜负了我一片稗官纪实的苦心吗……我这小说,不是捏造出来的,不是有营业性质的,是要使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知道,于今政界的种种的黑暗事实,都是由这万恶政府酝酿出来的;我绝对认为于人心世道上有绝大关系,绝非浪费笔墨,供人玩笑。本意已明,便叙实事。”①刘韵琴:《韵琴杂著·小说》,上海:泰东图书局,1916年,第3页。刘韵琴所写的故事内容触及众人皆知的政治风云人物,隶属于传统的“王侯将相系列”,她关于小说缘何的目的是借小说争取政治话语权,有以小说谏政的意味。而这一领域却与广大普通民众所处的生活世界关联不大,与他们的日常情绪也没有太大关系,仅仅只能满足他们对政治世家、豪门贵族的猎奇心理。同理,李劼人的《游园会》虽有广阔的社会空间,但他发泄的依然是政治情绪。而且两人都有新闻采编的经历,他们的小说也多脱胎于社会时闻,关注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情时事。
实际上,在谈到中西小说的不同时,陈独秀认为:“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亦意在善述故事;这时候小说、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但西洋近代小说受了实证科学的方法之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遂完全划归历史范围,这也是学术界底分工作用。我们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②陈独秀:《〈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林文光选编:《陈独秀文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小说的内容本质上与历史并未分家,习惯于记录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将其演变为故事,或者掌故;也写人情,可写的多是历史中的“王侯将相”,关注的也是君臣父子关系。蔡元培则说得更明白,他曾将文学(小说)当作“民史”以补“正史”看待③蔡元培著,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在他们看来,近代小说虽并非帝王实录,可却迫近民史,其文学意趣则主要在于以个人的视角来记录社会事件。而《大公子》和《游园会》实际上与历史也并未完全区隔,袁世凯的大公子是政治事件中绕不过的历史人物,《游园会》中所说的故事也是实际发生的事件,或多或少有些借小说评点时事的“民史”意味。与这两者不同的是,陈衡哲的《一日》描写的并非“大事”而是“小事”。其主人公是普通的学生群体,内容是生活中的“碎语”和琐碎的上课、下课等生活日常,可这份日常却又有些过于“无意识”。
周作人曾在1919 年的《平民文学》中盛赞过“新青年”所推举的“白话圣经”《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写出了“中国家庭中的喜剧悲剧,到了现在,情形依旧不改,所以耐人研究”④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1年1月19日。。“新青年”从《红楼梦》中看出中国家庭的固有桎梏以及生存的种种遭际。他们推举《红楼梦》的不仅是其通俗的文学语言,而是《红楼梦》潜藏的“平民意识”。《红楼梦》深挖出的琐碎日常及其情感谱系,与人休戚相关,具有普世价值。新文学提倡“平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很多作家突破了古典文学的边界,将从前未曾关注到的,或者不能关涉的人和现象纳入文学场域,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形象和意象。鲁迅说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⑤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这种极不容易被察觉、注视到的大多数,他们的生命消耗在平淡往复的生活中,个人的“悲剧”鲜少被提及和关注,而新文学家们将其拾起,并引发他们对人生、人性的反思和追问。然而,这些“普通人”的离合悲欢却在陈衡哲的《一日》中不曾产生多少情感上的涟漪。针对青年学生,陈衡哲不过呈现了她们上课、考试的烦恼,可“新青年”却将青年学生视为“社会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
针对1918 年的“李超之死”事件,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表了重要的演讲,一举将“李超”的个人悲剧推至公众视野的前台,“李超之死”演变为“公共事件”。蔡元培、胡适等人均从李超的“个人”身份出发,表达个人在不合理社会制度下的生存隐忧。安德森指出“民族国家没有清晰可辨的诞生日”,基本上是通过“记述烈士之死来为民族国家立传”⑥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3/2003,p.205.谭桂林等:《从南京走向世界“鲁迅与20 世纪中国”青年学术论坛》,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74页。。所以晚清的秋瑾等虽是女烈士,可“一旦升上民族主义的祭坛后,道德约束似乎益发严格,女烈士之‘女’全无任何身体特征或颠覆性的潜能,而仅仅意味着烈士添加了一点色彩和多样化”①胡缨:《性别与现代殉身史:作为烈女、烈士或女烈士的秋瑾》,游鉴明等主编:《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甚至当秋瑾等人被“神圣化”“英雄化”之后,他们为“女性代言”的一面基本上被完全淡化,“女杰的豪情”被当做“英雄气概来解读”,“新的女性时间也只有在与男性时间交汇时才能感觉得到”②[美]季家珍著,杨可译:《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5页。。可是在“李超之死”事件的叙述中,颠覆了秋瑾等女英雄的叙事模式,她的身份特征十分明显,李超是“个体”,是“女性”,是“弱幼”。在追悼仪式中,胡适、蔡元培等人有意识地将追悼会“神圣化”,可并未将李超叙述为“英雄”。他们始终强调李超作为青年个体的悲惨,将其看作普通人生存际遇的缩影。不过,对于“普通人”的强调并非逻辑的终点,胡适将其看作“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研究的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而研究李超的一生,“可以联想到许多问题,比如家长族长的专制,女子教育问题,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力,有女不为后的问题等等”③胡适:《李超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591页。。陈独秀也将李超之死归结为社会制度问题,社会上存在专制压迫,才使诸如李超等女性丧失了生命。胡适、蔡元培、陈独秀不仅将“李超之死”当作个人悲剧来看,也将其上升为社会问题、青年问题、全体女性的生存问题。
可以说,胡适、陈独秀等书写的不仅是“普通人”,也要表现“大情怀”。他们为普通人立传,是要通过普通人的行迹与遭遇建构人的普遍价值。这既是“新青年”构建启蒙思想的方式与旨归,也是他们从人的普遍价值出发,构建民族国家的愿景。比较之下,虽然陈衡哲明确表示其小说描写了“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④陈衡哲:《自序》,《小雨点》,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第17页。,可与“新青年”文学所欲追求的情感内涵显然不在同一维度。难怪陈衡哲会发出这样的自嘲:“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他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⑤陈衡哲:《自序》,《小雨点》,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第17页。“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或许也正体现她的小说不够现代,不够五四。
结语
在白话尚未自觉的时代,胡适、陈衡哲的白话文学实践其实位居边缘。这“边缘”不仅是话语权力的“边缘”,更是地理位置的“边缘”。但胡适的归国让他从虽然多元但是边缘的欧美留学文化圈进入正在建构和确立的中心文化圈,属于欧美留学文化圈的《一日》、四川地方文化圈的《游园会》等小说则成为中心之外的声音。在以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中,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大多围绕“启蒙精神”“现代民族国家”等方面展开,陈衡哲的《一日》、刘韵琴的《大公子》、李劼人的《游园会》由于形式不“现代”、语言不“现代”与情感不“现代”,很难融入研究的视野。与其说陈衡哲、李劼人、刘韵琴等人的白话小说与已经发生变化的语言风貌及“新青年”提倡的普通人的“大意义”格格不入,毋宁说是它们无法适应社会文学圈的中心—边缘之变。换言之,文学话语中心的形成,使之退回到边缘。随着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中心的出现,这些曾有过的白话尝试极容易被中心话语折叠封存。因此,研究孰为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并非纠结于真正的答案是什么,而在于引出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以往认为的新文化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文学圈层之外,可能还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圈层,亟待我们打捞更多元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