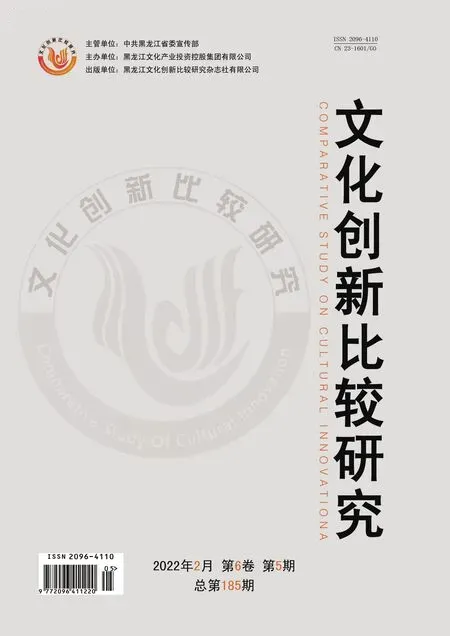简评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2022-12-06张子阳
张子阳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自1939年第一版出版以来,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已经重印无数,广为流传。这部脱胎于北大和联大国史课堂,著成于抗战艰难时期的中国通史讲义,时至今日已成为国史研究界的一个标杆,收获了海内外学者的诸多赞誉,就连全国高考都曾引用其中的素材作为题目[1]。然而,对于《国史大纲》也不乏争议甚至于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从政治立场、史学观念、史实引用等不同的角度展开,指出了《国史大纲》存在的诸多不足之处[2]。但作为一部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战烽火之中诞生的史学著作,《国史大纲》的意义与价值,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学与考证学层面,其所探讨的也并非只是单一的逻辑实证,而是更加宏大的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存续之问题,是对于中国五千年文明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深情忧思——在抗战进入白热化,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冲击与危难的时刻,这大概是每个有识之士共同的忧虑。
《国史大纲》便是在这样的忧思之下写就的,而这本巨著的思想纲领,则被浓缩在了写于正文之前,长达万余言的《国史大纲·引论》(下文简称《引论》)之中。可以说,《引论》是整本《国史大纲》的总目和灵魂,钱穆先生在后文中的诸多历史叙述背后的逻辑,甚至于他在其他著作中所展现出来的观点,都建立在这篇引论的基础之上,钱穆本人也非常重视这篇引论的意义与影响,他在《国史大纲·书成自记》中说:“然此书虽草略,其所以为此书之意,则颇有为国人告者,因别为引论一篇。”足见《引论》在全书中地位的特殊性、核心性与其号召之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理解了这篇引论,才有可能更加清晰地把握钱穆的史学思想与家国、文化发展的意识,把握那个时代的迷茫、忧思以及支撑人们前进的希望。
1 《引论》内容概述:史学与文化之未来
《引论》通篇共十五章,这十五章的内容与思想,大致可以按照论述的主题划为3 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全篇的一至四章,主要论述了目前中国史学发展的现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但却是最缺乏“历史智识”的国家。正因如此,近世之史学锐意革新,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建议,于是产生了传统派(亦称记诵派)、革新派(亦称宣传派)以及科学派(亦称考订派)。传统派类似古人考订工夫,流于琐碎,缺少现代因素;科学派只主张所谓“科学实证”,有割裂史实,过于空洞之嫌,以至于“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而革新派介于二者之间,其治史带有很强的现实性,且着眼于历史整体发展脉络,因此对于提高国人历史智识的影响最大。
然而,同上述两派相比,革新派最大的缺陷在于对史实把握不足,加之革新现实之愿望过于强烈,因此往往将中国当今社会之种种问题,一概加诸古人,认为过去五千年之历史不过是一部“专制黑暗、文化停滞、封建经济”之历史。而在钱穆先生看来,若这种“国史黑暗论”的观念依旧存在,则“我国史仍将束之高阁……国人仍为无国史智识之民族也”。因此,新的通史便应该从以上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以记诵、 考订派为工夫,而达到宣传革新派之目的”,从而达到“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者必要之智识;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的目的——这想必也是写作《国史大纲》的初衷之一。
因此在第二部分,亦即《引论》的五至十一章,钱穆先生就治国史的方法以及国史中的核心问题展开了论述,提出当前治史最大的问题在于“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发现中国史的个性所在,而非盲目地套用西方的史学理论。在这一理论前提下,钱穆先生提出,与跌宕起伏、常发生大冲突大争斗的西方史相比,中国史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和平演进”,是一种“情的融合”而非“力的斗争”,如同群山聚拢般绵延不绝。政治、学术及社会史的发展,都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诠释,从而发现中国史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当抛弃了单一的西方视角时,同样能够发现国史中潜藏着的民主议事、平民思潮等诸多精神,此种精神的演进,即为一民族文化发展之力证,从而也能驳斥所谓的“专制黑暗”之说法。
但无论如何对激进的史学思想进行反驳,当时的中国受到诸多问题与痼疾的困扰,毕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亦即《引论》的第十二至十五章,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对未来的期望。首先,钱穆先生认为,文化发展有高峰亦有低谷,而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病态”,恰表明中华民族处于发展的低谷期。以本国文化发展的“低谷”,与同时段其他国家文化发展的“高峰”进行比较,自然无法得出客观的结论。其次,“病态”的起因不全是古人之罪过,更多是近世以来文化传统的丧失和大一统的“情的融合”格局的断裂。再次,走出这段“低谷期”的关键,绝非一概诉诸西方的理论与发展之路,从外部解决问题,而是要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再建构,依靠自身的努力,从内部焕发民族之生机,重振文化的辉煌。《引论》的最后,钱穆先生重申了自己撰写此书的目的与个中苦楚,希望此书能够成为“新国史之马前一卒”,为国史乃至中华文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总的来说,整篇《引论》的基调是积极的,展现出了鲜明的忧患意识、 对中华文化强烈的自信心及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全盘西化理论的否定。作者相信中华文化带有现代性的因素,同时也具备无可比拟的独特价值,不应用所谓“专制黑暗”一概抹杀;而当下种种危机的解决,也需要借鉴国史中的积极因素,从内部找出问题,寻得出路,以获得新的生机和希望。
2 《引论》中的思想透析:民族意识、文化价值与儒者情怀
通过纵览《引论》的十五章内容,我们得以发现钱穆在抗战的特殊时期里,所展现的不同于当时其他思潮的鲜明的历史观念。
其一,强烈的民族观念和文化意识。钱穆的史学思想在20 世纪30年代的转向,通常被学者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史学观”或“民族文化生命史学思想”[3],这是钱穆先生最为核心与关键的思想,贯穿于他此后的几乎全部的代表性史学著作当中。例如,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便这样说道:“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专看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4]《引论》自然也不例外。首先,《引论》展现出了对文化发展的极度重视,认为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核心在于文化,若无文化之存在,则民族火种也将断绝;其次,以此为基点展开横向与纵向的论述,阐明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钱穆先生反复强调中西方历史演进的不同之处,通过“网球家与音乐家”“流水与群山”等诸多比喻,说明东西方文化之不同,治国史须把握本民族之个性,不应削足适履,事事仰仗西方,学习西方,而应着眼于自身进行改造,正所谓“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为成者依然为我”;从纵向比较的角度看,强调在各个时代的特性中既要发现变化,更要发现变化背后的动态同一性,以及由此推知的文化精神之所在,认为这是国之根本。正因为这“根本”源于古代,因此将民族发展的问题归罪于古人,甚至于提倡“以今代古”,既无益于解决实际问题,更会使得国家的发展失去文化根基与灵魂,“譬如治病救人,须以人为基础治病,不能因其有病而要求其换一个身体,否则无异于自掘坟墓”。
以上观念与当时流行的西化、 疑古等诸多思潮相比,无疑是大相径庭的,体现了钱穆深厚的儒者情怀,以及在复兴中华文化方面所展现出的苦心孤诣的努力。钱穆先生敏锐地觉察到了当时国人在民族文化理解上的诸多问题,对诸如“斜角现象”之类的误区做出了批评,同时强调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亦即其继承性,这些观念对于中华文化的存续和弘扬,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二,对考据派治史方法的批判和对经世史观的提倡。事实上,钱穆先生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就经历了从“考订派”到“革新派”的转变。钱穆早年以深厚的考据功底为其治史的主要特点,且具有较强的疑古意识,《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其早期代表作,他也因此在史学界广受赞誉,并与当时新考据派的巨擘顾颉刚、傅斯年、胡适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钱穆亲身经历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与刺激,治史思想也因此发生了转变,认为单纯的历史考据难以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立足,也无法培养国人的忧患意识,因而更加强调经世致用的治史方法,以期达到“史学救国”的目标。在思想理论上,这种转变体现在其由乾嘉学派到宋学的“转向”以及对于宋学的推崇[5];而在其著述方面,《国史大纲》 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在《引论》中,钱穆虽然对当前的所谓“革新派”有所批评,但是他对革新派的整体评价显然高于其他两派,认为其“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今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以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且“今国人对于国史之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显然,对于有着“岂能背时代而为学”思想的钱穆来说,其在抗战时期的治史路数,是与革新派相契合的,而他额外所做的不同于以往考据派的努力,则是改变革新派“怠于问材料”的弱点,其核心仍为经世致用,促成国人对中华文化的再认识。
其三,以平稳渐变的观点理解国史,在此基础上加以“温情与敬意”。该观点也是钱穆先生儒者身份的一大表征,特别带有孔子乃至上古儒者的遗风。钱穆虽生于一个日渐破落的书香世家,但仍接受了较为良好的传统教育,7 岁入私塾读书,饱读儒家经典,且受到了父辈言传身教的影响,故其后来的思想体系也带有强烈的儒家色彩[6]。一方面,崇尚和平渐进是儒家的一大特征。孔子在《论语》中就有过“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的表述;此外,在史观表述上,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与钱穆强调文化继承性的观点十分相似,从中可以窥见钱穆的史学思想受其影响之深。另一方面,儒家倡导“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的礼乐文化,其所具有的人文关怀色彩,及所展现出的对祖先的敬意与尊重,即是钱穆在《国史大纲》开篇所提出的“对国史怀抱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这种温情与敬意,即是维系整个民族的合力与精神纽带,所展现出的功效和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3 《引论》的不足与无奈:特殊年代下的文化困境
在对钱穆《引论》 中的史学思想做出积极评价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其中仍然有一些不甚完美,值得我们注意的方面。
首先,《引论》中的许多观点是极具争议性的,需要进行讨论与商榷。最典型的例子是对中国专制说的驳斥。如前所述,钱穆的这种辩护是以一个儒者的眼光,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进行诠释的,但也正因如此,他的驳论与对中国文化的再理解便不免有失真之处出现[7]。在论述学术思想的演进时,钱穆认为东汉以后,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其表述就显得较为夸张失实;认为汉立五经博士之后,学术便“于政治势力下独立”,学术地位“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展现出了其观念过度理想化的缺陷;而在驳斥“中国专制说”时,钱穆先生并未正面给予反驳,而是反面立论,说明“民权宪法”在实践中屡遭挫折,同时认为科举体制和相对稳定的准则使得“上情下达,本非无路”。这种论述虽然能够使读者思考专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但在论据的充分性和说服力上,却依旧显得较为苍白。
其次,钱穆史学观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使得他在面对民族问题时难以做到客观公允。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其对元、 清两个入主中原的外族王朝的评价。这两朝在中原的统治固然展现出了民族歧视、文化禁锢等种种消极因素,但其中的民族交融、制度发展(如行省制)、社会经济变革等客观进程与积极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国史大纲·引论》及其他著述中,可以明显看到钱穆对前者的论述远远多于后者,且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对于元朝,称其入主中原为“暴风雨之来临”;对于清朝,斥之“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此乃斫丧我民族永久之元气,而以换造彼目前之荣华者也”。在展现其民族观念的同时,便在全面和客观性上显得不足。
但若对钱穆先生所处的时代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便能知晓他的种种观点甚至于“偏见”,乃是一种时代的合力下所生发的必然结果,是在近代化的浪潮与民族文化的火种之间徘徊的文化困境,而非其一个人的错误。或许在那个战火连天、个人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情境下,民族情绪、欧风美雨、自由平等伴随着炮响与铁蹄交织而来,思想文化的漩涡混乱狂暴,又能有几人可以独善其身,超脱凡尘,成纯然客观之学术?
而从另一个角度讲,钱穆先生大概已经做出了与时代和他本人的学者身份均相契合的选择。他心系国家之命运,文化之兴衰,但是并未直接从象牙塔中走出,而是从象牙塔中探出身来,将天下景况收入眼中,然后奋笔著成《引论》,力图为构建民族的精神大厦做出自己的努力,用“史学救国”“文化救国”的理想警醒国人,让更多的国人真正去了解古代文化,唤醒国人沉睡的忧思与情怀。这恐怕是《引论》除史学价值以外,更令人称道的价值,也庶几能弥补一些内容与观点上的缺陷。
4 结语
1990年,钱穆先生于台北驾鹤仙逝,余英时先生为其恩师题写挽联一副,以表缅怀追思之情。联曰:“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这40 个字道尽了钱穆先生一生的学术所系,也道出了贯穿钱穆一生的文化精神。钱穆先生曾说:“人类苟负有某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而《引论》,便是其文化使命的外化,是其文化精神的结晶与硕果,也是民族危亡之中振聋发聩的强音。透过钱穆先生充满温度的文字与叙述,读者们从《引论》中所感受到的不只是史家的手笔,更是身为儒者、文人以及中华民族的一员所传达的文化忧思,以及对绵延五千年的中国文脉的深切敬意与复兴之担当。在全球化的今天重提《国史大纲》,重提《引论》中的文化忧思,也因此而具有了历史的指向和现实的意义,引导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承担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