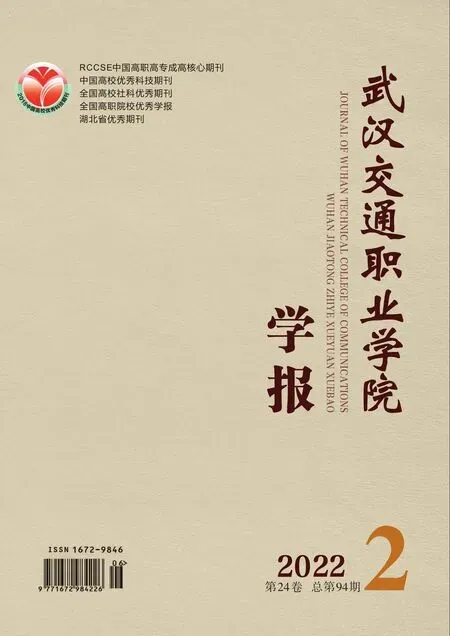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述论
2022-12-06任谢元
任谢元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城市道路交通系统是城市的骨架和动脉,在城市布局结构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其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基于此,近代济南市政当局极为重视,且不遗余力地推进城市道路交通建设。从学术史着眼,学界关于20世纪上半叶济南城市道路交通的研究,多是在市政建设、城市规划等研究成果中稍涉道路建设情况[2-6],鲜有系统性的梳理与研究,更未能很好地说明道路交通建设中的材料与经费来源。本文希望立足上述方面,梳理其发展历程①,考析其材料与经费的来源、种类及影响,并揭示道路交通建设背后官民博弈的深层动因。
一、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的历程
20世纪上半叶,在近代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下,济南城市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道路交通建设的表现最为抢眼,这无疑成为各时期市政当局关注的重点。据此,依据不同的治理时期,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分为四个阶段。
(一)晚清时期: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的正式起步(1904—1911)
1904年,济南自开商埠,在旧城之外划定商埠区,并首就街道和马路展开工作。因其是为接纳外商而规划设立,故街道设计比较整齐,但街道仍是沿袭过去的棋盘方格形状,以东西向街道为主路,南北向街道为辅路。东西向主路街道与胶济铁路平行,南北向辅路街道与铁路垂直。除此之外,道路走向的安排也考虑到了与老城区相交的问题[7]。由于旧城和四关是在19世纪60年代修筑的外廓圩墙以内,而与商埠相邻的西面,只有永镇、永绥两座城门,交通很不方便,形成了“洎商埠开,民物殷阗,道途拥塞”[8]的现象。为改善旧城厢与商埠间的交通,1908年,在永镇和永绥两门之间加开普利门,加宽柴家巷,并改名普利街,向西与经二路相连,形成了与东关马路的对称格局。1909年,以经一路为开端,从馆驿街西口修建到纬五路,通到经二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商埠区内的道路数量急剧增长。此时期因自开商埠的推动,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开始突破旧城区的封闭空间,并形成旧城区与商埠区道路交通建设交融发展的格局。商埠区道路的规划与建设,拉开了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近代转型的序幕。
(二)市政公所与市政厅时期: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的缓慢发展(1912—1928)
1912年后的几年中,政局动荡,军阀混乱,当局无心于系统的市政建设。城市道路处于缓慢发展期。至1916年,又向西展至纬十路,向南展至经七路,并开麟祥门,以通经四路。然而,后期的这些展路只修了路基,很少修建路面[9]64。1919年,在西圩添设新建门,形成了“群门集西,直达普利”的局面。1921年,随着商埠区工商业的发展,又将院前街、府东大街至普利街、运署街、筐市街等修筑碎石路。为与东关马路相对称,城西面也修了一条连接普利门和济南火车站的碎石马路,以便利与车站的交通。1927年,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将济南城内交通冲要街道进行改造,因估衣市街联结济南旧城与商埠区,交通流量大,商业繁荣,遂将东起泺源街、西至筐市街南口的估衣市街,按照天津、青岛等地经验,改修成沥青路面,这是济南第一条沥青马路。该道路在1928年“五三惨案”期间毁坏严重。
此时期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缓慢发展。道路材质虽无实质变化(除估衣市街外),主要以青石板路、碎石路为主,但旧城区与商埠区因道路交通建设的持续推进,联系更为密切,出行更加便利。因“五三惨案”的发生,济南城内街道损失严重。前曾述及,济南街道的扩展,前期多源自商埠建设需要,是政府主导下的被动扩展;后期因一战期间民族工商业发展,出现了许多因新建工厂而形成的街道,及源于工商业聚集形成的商业街区。另有因军阀混战、自然灾害,促使流民、灾民涌向省城,自发聚居建房形成的里弄、棚户区。此外,由于军阀军事调动而出现了在城郊扩建交通大路的情况,其道路宽大,路基多为土路。
(三)市政府时期: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的全面展开(1929—1937)
济南在历经市政公所、市政厅时代后,道路虽略具规模,而基础多未坚固,十分之九的路面都是“年久失修,坎坷不平”[10]。鉴于此,1929年济南市政府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市内街道的翻修与展宽。首先,市政府下设道路修筑和维护的机构工务局,将道路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并设常年经费20万元,派员分头调查各马路情况;其次,按照调查情况,计划施工事项;再者,遵据市政计划大纲,大规模整修街道。1929年底,基本上完成计划施工的各街道。1933年至1934年,道路整修成绩更是非凡,先后完成23条道路的改修,将沥青路面扩展到魏家庄街、舜井街至朝山街、经二路,并修筑东门至南门城头马路及市郊龙洞、长清道路[11]。至此,济南市道路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道路质量大幅提升。
嗣后,工务局继续不遗余力展开道路的修建工作,先后完成东门大街、大小梁隅首等16条道路的改修[12]。1935年9月,完成布政司大街、按察司街至大东门月城、宽厚所街的改修沥青路面,南北经一路、丹凤街、官扎营的改修黑砂路面,新东门至青龙街口、经二路西端至津浦机厂门前的改修花岗石板路面。但尚有部分道路,如五三路、金牛山路、济洛路,或因工程量浩大,亦或开工较晚,未能及时竣工。此后,继续大举整理市内马路,其坎坷不平者,均一律加以翻修,其交通要衢者,则一律改为柏油路[13]。这些翻修或改修的道路不仅数量大幅增加,而且路网系统逐步贯通,通行保障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有利于城市商业活动的开展。
除整修、新建道路外,展宽街道亦是此时期重要工作。城内各街异常狭窄,交通极感不便。建设伊始,市政府就强调要加以展拓。1929年11月28日,工务局规定“凡起造及改造筑屋,或翻修门面,均应依本局之展宽路线图规定之尺寸,实行退让”[14]。据此,工务局规定城厢各街宽度为干路二丈五尺、支路二丈、小巷甲一丈六尺、小巷乙一丈二尺[15]。但城内大小街道为数颇多,路线长短不同,尺度宽窄有异,工务局遂将街道路线尺度详列计划,以凭分别缓急、次第兴修。1931年后,因人口增多与城关道路过窄,而引发的“交通时生阻碍”矛盾更为突出。于是,又规定“凡新建和翻修临街房屋,拆动墙壁的,须按《全市街道展宽表》退让出街道的宽度”[9]112。此后,随着商埠的日臻繁盛,继续规定“新辟街道尤须按照规定尺度预先划出,以免市民修房侵占”[16],为后续道路的修筑与维护提供了便利。
事实上,关于路面的宽度,按实际需要,应行展宽者甚多。南北中大槐树一带,向未划定路线,市民既无所依据,遂任意建筑,致街巷错乱,宛如迷城,不但交通困难,即公安之稽查,火灾之消防,亦感不便。为安全起见,工务局重新划定路线,继续规定街道宽度。至此,济南市道路宽度,均依其“所接通地域之广狭、所通区域内商户之众寡、是否与各项拟定设施有关”[17]等形势而定。道路宽度虽经分别规定,但欲严饬商民即时拆除退让,颇觉困难。为渐进改革计,1937年,工务局再对济南市道路宽度按照等级、质料、路面情形,分别拟定展宽度,并特别指出“凡新建筑房屋时,必须按照规定道路宽度,施以建筑;如系旧有之房屋,于改建或翻修时,亦须按照规定之道路宽度退让”[18],以利于改善城市交通条件和市容环境。
此时期济南市道路交通建设全面展开,且呈现出与城市空间拓展齐头并进、相互协同的格局。一方面,商埠区的道路不断地改造升级与建设,显现出依附铁路走向的鲜明特征;另一方面,旧城区道路的改造与整修,也从加强交通安全管理、改善城区交通环境、密切与商埠区的联系及与商埠区道路网多点相交着眼。据统计,此时期道路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绩,共修道路79条,其中沥青路37条,石板路21条,碎石路18条,土路基3条[9]116。与前一时期相比,路面材料有了较大发展,沥青等高技术材料普遍应用,并开始上升为主导,这表明沥青路的优点开始显现,并为国人所认同。然而,人行道建设却不容乐观,在市政府统治的九年时间里仅修筑1条;沥青路中部分是由碎石路、石板路等改修而来,其拓宽工作成效不大,仅有西门月城、东门月城、南门瓮城、魏家庄街4条道路进行了拓宽,尚有31条道路宽度保持不变,更有经二路宽度由原来的11米缩减至7米。因抗战爆发,部分道路建设被迫停止。
(四)市公署时期: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的曲折发展(1938—1945)
济南沦陷后,路政停顿将及一年。鉴于路政攸关经济掠夺的重要性,日伪济南市公署成立后,即令饬建设局积极修治。然民生凋敝,收入短绌,未能有大规模之修筑,至1940年仅修石碴、石板、沥青等路面积471046平方公尺[19]。1941年,日伪济南市公署制定《济南市公署管理道路暂行规则》,对占用道路、因公刨路作出规定。此后,又以乡区道路关乎“警备治安与交通便利”,颁布《济南市公署修补乡区道路暂行规则》,规定“各乡区道路应由各区长督饬各坊长随时派人分赴各道路查看,遇有损坏处,即时派附近村民修补平坦”[20]。据此,日伪济南市公署开始对市内主次干路及郊外警备路次第施工,路政渐入轨道。与此相伴,为便于经济掠夺及军事运输,修建了许多通往城外的大路,铺装了纬十二路通飞机场的混凝土路。另外也修缮了一些日军所需的警备路[9]147。
在翻修旧路的同时,还开辟新的道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侵略的需要,成立了伪济南工程局,隶属于伪建设总署,凡新辟道路和扩建旧有道路宽25米以上的,都归该局办理。新辟道路的范围环绕于市的四周,而集中于南郊新市区。当然,新辟道路并非易事,其时“官扎营街拆房建路”一案就曾名噪一时,由此引发了官扎营街一带居民赵恭琴等17人联名条陈,其要求“对于马路两旁隙地之房屋,请求暂缓拆除”,“对于拆除房屋之价额请求监现时物价工资之高昂,酌予增加”[21]。区联会暗查后呈称“情形确系属实”,并函请伪建设总署济南工程局鉴核指示,因缺乏相应材料证实,处理结果不得而知。
此时期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曲折发展。道路数量虽有所增加,路面宽度较以往也有所增大,但路面材料较差,多为土路、碎石路面。这些新建的道路因服务于掠夺需要,大多环绕于城市的外围,无形间成为联结乡村与城市的要道,促进了城乡间的交流与联系。据统计,此时期修筑沥青路仅2条,黑砂石、青石板、水泥板路29条,碎石路23条,土路7条,水泥砖人行道3条,总计61条,总长59823米,面积592032平方米[9]147。很显然,此时期筑路质量较市政府时期大幅下降,这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资源满足战争需要有密切关系。
二、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中材料的来源
从上述历程来看,济南城市道路建设取得较大发展,道路的重要物质基础,逐步由青石、石碴、黑砂石向混凝土、沥青等转变。据统计,在道路的修建费用中,材料费约占30%~50%,某些重要工程甚至可达70%~80%[22],所以降低工程造价,材料的选用具有很大意义。除沥青、混凝土等新科技原料全部购买外,其他道路修建的材料大多采掘于周边,其中以砂石需求最大。因黑砂石质地坚硬,是修筑马路的必备材料之一,故而官民争相采掘。据民生林场看山夫马岱霖报称:“1934年8月2日,植树工人在东白马山工作之际,忽而作响,碎石散落如雨,连续数次。经往查问,知系居民刘振声、杨明亮、王金城三家打石,用火药炸石坑,撞伤树苗,危及工人。”[23]为杜绝私人随处开采之行为,1939年5月26日,日伪公署呈奉山东省公署建矿字第511号指令,拟具《采石取砂暂行规则》,提交第36次省政会议修正通过,划定许可采取砂石地区,先将产石之丁家山、刘长山,产砂之黄岗堤口开放,嗣后凡无执照者,一律禁止采取[24],并布告称:“本署对于应修各街现已斟酌缓急及应需材料,除用沥青、青石及石碴修建者不计外,如天桥街、小纬一路、县西巷、剪子巷等均因年久失修,坎坷不平,又均系车辆行人来往频繁之地,自应用黑砂石重新修筑,以期坚固而便行人,以上各街共需黑砂石料二千立方公尺,须由黄岗山、标山、金牛山、凤凰山等处采取,此系修筑公路需用,完全为全体市民谋通行之便利,与商民自用者不同,所有各该处附近村民届时均应保护开采”[25]。由此可见官民对砂石材料的争夺程度。
令人更为惋惜的是,名胜古迹之山也同样未能幸免。日伪公署以凤凰山所出石料,极合修路之需,特圈定该山不碍风景之处,作为修路专用采石场,四周树立木牌,撒以灰线[26]。此举引发了凤凰山庄庄长杨永信等的诉呈,“凤凰山夙称济南重要名胜,山上并建有佛殿,庙貌焕然,风景尤为可观,每届齐蘸之期,则信徒络绎于途,泃属佛家胜地,曾于去年四月间经钧署布告划为采石山场。自经此次采挖之后,不仅山石凌乱不堪,即该山原有之树株亦被采石工人等毁坏四十余棵,近闻又有在该山采石之说,窃以该处山石本属无多,若任期一再采取,势将成为童山秃岭,似有违政府保护名胜古迹及倡导造林之旨。民等世居山下,实难缄默,惟有仰恳钧署恩施格外,俟后准予免在该山采石,以维名胜,而保古迹”[27]。村民之所以公开表达反对劈山采石,定有保护世居家园、维护名胜古迹之环境的成分。毕竟,“乡土意识与情结”素为人们所看重。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村民的诉求与盼望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当局经派员查明,东面采石处距上山盘路甚近,应即停止采石,其西面北面两处,目下尚无妨碍,暂从缓议,除批示外,此后不准再在东面采石”[27],此结果初步实现了村民维护世居家园环境的预期愿望。
同样,四里山、马鞍山也素为济南市名胜之区,有市民在该山采石作为建筑材料,长此以往对于该山风景,大受影响,亟应严厉禁止,并函请山东省会警察署饬属查禁[28]。随稽查力度的不断强化,相关行业工人的生活受到冲击。济南市山石运输业职业工会会长徐希圣称:“本职会会员散处本市各山采石,历有年载,赖为专业。近因四里山、马鞍山一带各山,为本市风景区域,严禁采石,是以一般采石工人顿失其业,其全家老小生命无所寄托,盖因靠山吃山,近水吃水,原为人民之世俗生活,今山石禁采,该等不得另谋其他生活,值此严寒冬令,其苦情实堪悯恤,数日以来,已形成局部社会之一大问题矣!”[29]群体性的呼吁,产生了实际作用,“当局谕令职会另觅他山,急速办理山石采取许可手续”。随后,山石运输业职业工会确定南郊新市区南,有山名七里山,地距市区较近,且山石尚可采用,拟在该山采石,才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
由此可见,就近开山采石尽管节约了成本,减轻了当局的经济压力,但砂石的开采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随着城市道路建设的不断延展,所需建筑材料只会越来越多,在当时有限的技术条件下,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采砂取石之法,还会继续吞噬绿水青山。
三、济南城市道路交通建设中经费的筹措
城市道路作为商业活动与市民出行的主要载体,它的建设不仅依靠政府筹措经费,还需要得到社会的赞助支持。前曾提及,济南市政府成立之初就设立常年经费,次第展开了道路的整修工作。综观20世纪上半叶,济南市道路建设的经费来源以常年经费、商民摊款为主,兼有临时费、省预备费等形式。
开埠之初,济南市政当局开征马路车捐,以作养路之用,此举似是济南收取养路费的开端。此后,各项车捐规章陆续颁布,据笔者所见,连同车捐在内的各项收入均由市政府统筹核拨,用于全市的公用事业项目的支出,筑养路经费自然囊括其中。
官方修筑道路,除极少数自营外,一般都是以招商投标方式进行。招商是登报或贴布告说明要举办的工程,由领标人各自根据实际情况,将工料数量、需款数目、竣工日期填入标单,定期投标和开标。开标时由省市府派员到场监视,启开标箱,拆开封缄,将所投标价从最低到最高列表比较,然后顺序审查每标各项数字是否合理。如无特殊情况,一般以第一标(最低标价)作为中标[9]113-114。按照此种程序,工务局招商承办了诸多道路的建设,如“修筑经七路路面工程,招商承做,注册各建筑业可携标单图样费二元,来局领取标单及做法说明,自行计算填入标单内,随缴押标金二百元,并于八日下午三时以前投入省政府大礼堂本局所设之标柜内,听候当众开标,择定中标人”[30]。这种程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节俭建设经费,但最低价中标的方式弊端也非常明显,某些承包方往往不计成本,片面追求低价中标,致使建设过程偷工减料,工程搁置现象时有发生。如馆驿街改修石板路,已修筑及半,包者因赔累不堪,又因限已届,惟官方罚半,竟私自潜逃,致街面工程无形停顿[31]。鉴于此,市长闻承烈对于市内各项工程,决定亲自验收。1934年10月22日,其率同市府技术专员常国华,工务局局长张鸿文等,前往小布政司街、芙蓉街翻修石板路验收工程,因该街路面不平,沟帮垒砌不固,当面饬包工人重行修理。后又至经七路查验石碴路工程,在进德会东端一段,石碴厚度不足二公分,即令该包工人将路面沙子扫去,加添石子重作。嗣后市政工程均由闻氏亲自验收,如查有包工人偷工减料,及监工人不尽职情事,定予严惩[32]。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大,道路建设经费也逐年增加,1934年达424004.87元(不含常年经费),较1933年增加166330.01元[33]。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济南道路建设上投入更大,仅省预备费就达365794.87元,工务局临时费18174.27元[34]。可以说,正是由于市政府时期筑路经费的不断投入,才改善了城区内外的交通环境,形成了城市交通网络,市容面貌为之一新。
与此相对,商民摊款构成了道路修筑经费又一来源,如1934年济南市政府规定“新修马路须由商家铺设人行道,一律用灰色洋灰砖铺砌”[34]。自此,筑路摊费有了制度保证,无疑缓解了市政当局的财政压力。除强制摊修外,部分同业公会还主动提出改修道路。粮业同业公会主席苗杏村呈称:“官扎营前街东自津浦铁路天桥洞西至华庆面粉厂门首土路一条,南运津浦货厂为本市商民运货要道,素无修理极行坎坷,每逢阴雨泥泞常有陷车之虞,人力车夫每行至此,泥水没膝进退维谷,尤令人目睹恻然。鉴于此,属会会员各号于本月十七日开全体会议,众愿集资由属会领袖倡修花岗石路。”[35]同时,为使商民明了商款用途,市政府还及时公布商款修路账目,“查此次翻修院前街、西门大街、普利大街各马路所需款项概由商家担负,自与动用公款不同,以后翻修马路尚须商民摊款者,当复不少。着令工务局迅将此次翻修各路商家纳款数目及用途,声叙明白,分期送登各报”[36]。1936年商民摊款50240.1元[34],修筑了南北经一路黑砂石板路、南北天桥街黑砂石板路、东北天桥街黑砂石板路、丹凤街北端至引河桥黑石板路。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因筑路财政经费没有正常保障,商民请求补助修路及自愿出资修路者,在日伪济南市公署时期亦有多起。如面粉、造纸、颜料贩卖业等民族工商业者为运输原料和成品的需要,自筹资金翻修了制锦市、铜元局、杆面巷一带的八条街道的黑砂石板路;布庄、银号等工商业者修筑了靖安巷、福康街一带的五条街巷;纱厂、面粉业等工商业者修筑了成丰街、官扎营、丹凤街、成通前、天桥一带和宝华街等处[9]147。为求原则遵循,获取较多的民间募资,1941年4月,日伪济南市公署《管理市民请求合资修路暂行规则》及《济南市公署管理商民自费修路暂行规则》草案,经第41次市政会议修正通过,对商民摊款规定更为规范。6月,日伪济南市公署颁布《管理市民请求合资修路暂行规则八条》[37],其第二条规定“凡市民请求合资修路者,应依据规定(路宽五公尺以上不足七公尺者,摊款工费总额五分之三;路宽七公尺以上不足十三公尺者,摊款工费总额二分之一;路宽十三公尺以上不足十六公尺者,摊款工费总额三分之一;路宽十六公尺以上不足二十公尺者,摊款工费总额四分之一;路宽二十公尺以上者,摊款工费总额五分之一)缴纳摊款”;第三条规定“凡宽度在五尺以下之里巷,均由两旁地主自行集资修筑”;第四条规定“凡应摊之款数,于接到通知半个月内一次缴清,但应摊之款超过三千元者,得分二次缴清,超过六千元者,得分三次缴清,超过万元者,得分四次缴清,每次缴款均不得逾半个月期限”。12月,日伪济南市公署又以“关于修筑街道征收商民应摊款数向无规定,商民自愿出费修路者颇多,对于管理办法亦尚缺”为由[38],参考各都市成规,制定《济南市公署修路征费暂行规则》和《济南市公署管理商民自费修路暂行规则》,这两个规则其实是对《管理市民请求合资修路暂行规则》的进一步细化和规范,给沦陷区的人民套上了新的枷锁,人民受剥夺程度再度加深。
1942年6月,日伪济南市公署建设局对商埠纬四路、经一路与经二路间一段,改修洋灰砖步道,所需工款每平方公尺9.6元。按照修筑步道暂行简章第十三条之规定,“由临街各房主、租户并本署各担三分之一,计每平方公尺为3.2元。其原铺洋灰砖新旧程度在80%以上者,由本署采用原砖修筑,房主与租户共得减缴担负金一半。如原有步道系房主所修,房主得免缴担负金。租户所修,租户得免缴担负金,双方共修,双方各缴担负金六分之一,计每平方公尺1.6元”[39],这种繁杂的协款方式仅注重费用的分担,而忽视了统一的规划与组织,致使资金利用效率不高。不仅如此,日伪济南市公署还职请省政府拨款补助,进行灾后道路修复工作。《济南市政公报》载:“水灾之后,沟濠淤塞,道路污泥遍地,坎坷异常。为修复冲毁工程,经估计共需款25万余元。惟目下职市既筹办赈济灾民,又增修防卫工事,市库民财,罗掘俱空,情出无奈,恳请拨款补助。”[40]据笔者统计,日伪公署时期修筑的29条石板路中,商民集资修筑的就有17条,占58.6%。其中,面粉业、造纸业、颜料业集资兴修了朝阳街、制锦市前街、铜元局前街、铜元局后街、镇武街、锦缠街、锦屏街、西杆面巷等8条街巷;布庄、钱庄业集资兴修了福康街、靖安巷、竹杆巷、上元街、太湖石巷等5条街巷;银行、粮食、面粉业集资兴修了乐康街、宝华街、官扎营前街、成丰街等4条街道。可见,由于日伪当局醉心于掠夺与盘剥,致使商民无奈集资修路而维实业,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沦陷区民众生活的状态。
四、余论
概而言之,自开商埠是济南城市发展的重要契机,因城市空间的拓展带动了城市道路交通的延伸,无疑成为助推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引擎。20世纪上半叶的济南因横跨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社会变动剧烈,道路管理机关迭经更替,致使城市管理的职权关系纷繁复杂,是故城市道路建设状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三个时期。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济南城市的道路建设也变化繁多,虽各个时期中建设成绩参差不齐,但总体上是渐由疏松到密集,由分散到集中,且呈放射状流向周边区域,城市路网系统逐步贯通与形成,市内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促进了城市商贸往来与人口流动,提升了济南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水平。然而,在近代济南城市道路建设的过程中,市政当局与民众由于认知层面的分歧,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互动的博弈或争论。市政当局通过不断地制定、完善道路建设与管理的规章,来确保道路建设的顺畅推进;民众囿于眼前或局部的自身利益,表达出自身的观念和理由,这些争论基本上是在相互的妥协中得到了暂时的解决,这一过程也从另一侧面折射出近代济南城市转型的艰难步伐。
注释:
① 本文仅就20世纪上半叶济南街道的建设进行研究,至于街道的基础设施如水道、桥梁及附着于街道上的配套实施,则不在研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