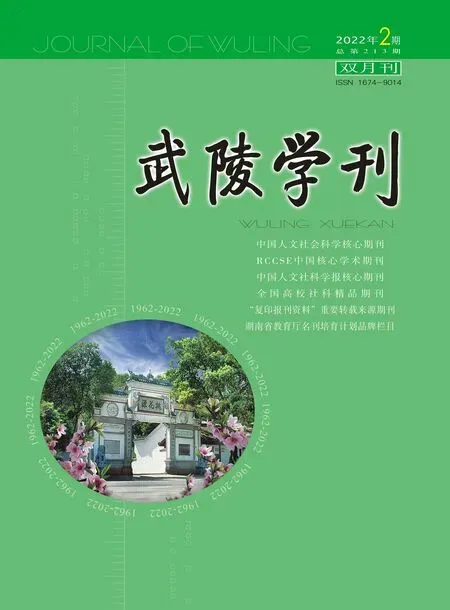个体伦理与历史书写:司马迁的“金縢”
2022-12-06李光柱
李光柱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金縢》目前主要有三个版本。关于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篇,《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相应部分的整理者认为“全篇简文与《尚书》的《金縢》大致相合,当系《金縢》篇的战国写本”[1]157。而司马迁亦“嘉旦《金縢》”[2]2864,在《鲁周公世家》中以独特方式讲述了一个《金縢》故事。由此,今传本《金縢》与简本《金縢》、《鲁周公世家》本《金縢》形成一组“对观文本”①。从目前的研究生态来看,无论是从文献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简本都以其行文之简洁、叙事之完整、信息之明确为诸多研究者所称道,尤其以简文辨文献疑难、证周初史事,得出许多有益的成果。然而,毋庸赘言,作为叙事作品,在把不同版本的《金縢》作为“史料”进行研究的时候,是无法置作者的叙事意图于不顾的,因为,伴随文本多样性而来的文本差异最终凸显的是叙事意图的差异。西方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认为,史学家编纂历史的工作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将历史材料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组织成编年纪事,然后进一步编排整理,把这些事件叙述成有头有尾、有中间过渡的故事;在故事的组织过程中,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可能被打乱——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一样,在编排故事的过程中也有“创造”的因素,根据不同的需要,某一事件或放在故事结尾,或充当过渡情节[3]。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视野的观照下,我们尝试把“对观《金縢》”的研究重点转向对不同文本叙事意图的考察,尤其是其中最为繁复的版本即《鲁周公世家》中的《金縢》故事——司马迁独特的编纂方式透露出他对《金縢》故事以及周公形象的独特理解。笔者将在文本绎读的基础上对司马迁的叙事意图做出一种解释。由此,本文不涉及对历史事实的考证,而仅仅是“为诗辩护”。
一、叙事时间:简本的“三一律”
在简本《金縢》所提供的诸多信息中,时间信息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文本层面,简本主要有三处时间标识与其他两个版本不同,引起了研究者较多的讨论:第一,开篇“武王既克殷三年”[1]158,其他两个版本作“二年”[1]162[2]1390;第二,中段“周公石(宅)东三年”[1]15(8简文“石东”,李学勤另读作“适东”,解为东征[4]119),其他两个版本作“二年”(“二年而毕定”[2]1392;“周公居东二年”[1]162);第三,末段“是岁也,秋大熟,未获”[1]158,今传本无“是岁也”,《鲁周公世家》作“周公卒后,秋未获”[2]1395。此外,简本在文末“天反风”之前又有“是夕”[1]162,其他两个版本无。
《金縢》故事大致可分为三个叙事段落:穆卜—藏书、东征—遗诗、天变—见书。(传统经学家对《金縢》文本也作三段式划分,如《尚书今古文注疏》[5],其划分重点并不在叙事层面,而在文本性质和来源上。)而这三处时间标识的差异也恰恰与三个叙事段落相对应。前两处,依照杜勇的观点,只是计算方法不同,对叙事内容并不造成实质差异[6]242,今从。第三处比较关键,它涉及所谓“信谗说”与“葬疑说”之争[7],具体到叙事时间层面,主要涉及风雷之变(第三叙事段落)发生之时周公是否还在世。根据简本,研究者多认为,“是岁也”明确标识出第三叙事段落与第二叙事段落的时间统一性,并由此明确了成王由“未逆”周公(第二段落)到“亲逆”周公、“出逆”周公(第三段落)的行动连续性,因此认为第三叙事段落显然讲的是周公生前故事[4]121。而今传本此处由于没有明确的时间标识,所以被认为存在叙事上的歧义。实际上,在简本未面世之前,已经有学者在今传本的基础上通过采用一种新的断句方法得出了与简本研究者几乎相同的结论。杨朝明认为“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存在断句错误,应为“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这里的“二年”指周成王二年,而下文的“秋大熟”之“秋”也即是周成王二年的秋天,此时周公显然在世[8]。同理,简本《金縢》“周公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可断句为“周公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这一解释策略十分富有启发性。因为如果严格从叙事学角度来看,仅仅依据简本“是岁也”就对“金縢”第二、第三叙事段落作“时间统一性”解释,似乎存在可商榷之处:“是岁也”可以是“故事时间”(故事内的时间),也可以是“叙述时间”(讲故事的时间);如果“是岁也”只是作为叙述时间,那么它只能确切地指示其所起段落的叙事时间,而无法将之前的叙事也纳入同一个叙事时间中。杨朝明虽然依据的是今传本,但其在第二叙事段落中事先确定一个明确的前置时间标识(“二年”),相较于简本的后置时间标识,显然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策略。如此一来,可以说,简本《金縢》所提供的“是岁也”的时间标识,只是为一种内在于今传本《金縢》的合理化解释增添了一项佐证。
研究者似乎也意识到仅仅用时间标识佐证段落连续性的不充分性,因此在论述简本的时间统一性的同时,又佐之以对“行动连续性”的论证,也即简本与今传本另一处重要的差异:“王亦未逆公。”今传本作“王亦未敢诮公”,《鲁周公世家》作“王亦未敢训周公”。简本的“逆公”在字面上显然比另外两个版本能更好地跟下文的“亲逆”“出逆”形成呼应关系。由此,成王对周公由“未逆”到“亲逆”再到“出逆”,这一态度和行动上的连续转变就为第二叙事段落与第三叙事段落的时间统一性论证提供了重要支撑。
对于简本而言,时间统一性论证与行动连续性论证构成了密不可分、相互强化的关系。我们不难理解这种论证策略的优势:压缩叙事时间,强化行动的连续性,这无疑极大地凸显了第二、第三叙事段落的戏剧性,由此整个《金縢》故事显得更加整一和合理——这十分类似于西方新古典主义诗学的“三一律”。但如果就此推定这种“三一律”是简本作者刻意为之,则还需要更多证据。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简本在明确第二、第三叙事段落时间标识的同时,却似有意似无意地模糊了另一个时间标识。在第一叙事段落和第二叙事段落之间,今传本和《鲁周公世家》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标识:“翼日”“/明日”。今传本作“王翼日乃瘳”,《鲁周公世家》作“明日,武王有瘳”。这一时间标识本质上指示的是一个单独的叙事段落:武王病情好转。因此,今传本和《鲁周公世家》本在同样的故事时间跨度内事实上比简本多出了一个叙事段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简本作者很可能同样是出于对叙事整一性的考量,刻意删除了这一叙事段落,客观上造成了叙事时间的压缩,加快了叙事节奏,强化了整个故事的戏剧性和整一性。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简本的另外两处差异:第一,简本没有提到今传本和《鲁周公世家》中涉及占卜的文句;第二,简本在第一叙事段落和第三叙事段落两次以直接引语重复了周公藏书时对执事人的诫命——“勿敢言”。单从叙事层面看,就第一处差异而言,简本作者很可能是意识到,对于“周公藏书—成王见书”这一贯穿全文的情节线索而言,周公的占卜行为以及武王病情是否好转这两件事是叙事上的累赘,会延缓整个故事的叙事节奏,因此他不惜将关于武王命运的内容剔除,从而最大限度地聚焦周公—成王这一对人物关系。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安排是由简本作为“志”的功能决定的,其目的在于为当时的贵族提供政治鉴戒,因而聚焦君臣关系就比聚焦鬼神之事更有价值[9]。这一解释与我们的解释有契合之处:故事对现实的鉴戒功效是建立在对原初历史语境有选择的脱离基础上的。就第二处差异而言,显而易见的是,周公嘱托执事人“勿敢言”是周公藏书的必要条件,也是整个《金縢》故事的戏剧性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但相较于今传本,简本作者两次以直接引语明确地重复这一信息,尤其是“乃命执事人曰:‘勿敢言’”,造成第一叙事段落与第三叙事段落直接而强烈的呼应关系——这一点即便是在《鲁周公世家》中也表现得没有这样直白(《鲁周公世家》在相应位置用的是间接引语“诫守者勿敢言”[2]1390)——这尤其显露出简本作者对叙事整一性的优先考量。明确了这一点之后,简本的更多细部就可以得到类似的解释。比如简本在第一叙事段落中提到“周公乃纳其所为功自以代王之说”,第三叙事段落再次提到“周公之所自以为功以代武王之说”;前面提到“秋大熟未获”,后面则提到“秋则大获”,似乎简本作者尤其看重这种字面上的、直白的前后呼应,这也侧面反映了其对叙事整一性的刻意追求。
亦有研究者将上述部分差异解释为版本传流所致[6]251。而从叙事学角度来看,版本传流的差异其实也是叙事意图的差异,它显示出不同传抄者对故事的不同理解。对于简本作者而言,他唯一看重的是周公之书由隐藏到被发现所带来的戏剧性突转。他全部的叙事意图就在于明确和强化这一突转的戏剧性——在文本层面表现为明确的时间标识、前后呼应的文句处理以及“冗余信息”的最大限度剔除。而今传本在文本层面虽然与简本同中有异,但研究者多认同二者源于一个初始祖本,且二者在宏观叙事结构上同大于异,因此学界主流研究也多倾向于以简本证今传本。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今传本与简本在叙事意图上没有重大差异呢?比如,相较简本,今传本第三叙事段落无“是岁也”的时间标识,这会给整个故事的阐释带来怎样的可能?再如,今传本第一叙事段落中有周公占卜及其对占卜结果的解释,这部分内容是否蕴含足以改变整个故事阐释方向的叙事意图?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要想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解答,仅仅有两个相似文本是不够的,需要一个关键的且具有足够差异性的“第三文本”。这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对《鲁周公世家》本《金縢》(以下简称《鲁》本《金縢》)的解读。
二、叙事意图:《鲁》本的春秋笔法
《鲁》本《金縢》在诸多方面都显现出令人惊讶的特质。它被认为是司马迁采用西汉今文经学(如《尚书大传》)之框架并杂采其他史料编撰而成[10]。如果说简本尤其追求一种叙事形式的整一性,那么司马迁的编纂方式则尤其体现出他对其所见《金縢》故事之叙事意图的关切和不同理解。我们首先悬置这样一种可能,即司马迁在《鲁周公世家》中不加修改地沿用了某个完整版本的《金縢》文本。也即是说,我们认为,《鲁周公世家》中所见的《金縢》故事是由司马迁根据其所见《金縢》及相关材料编写的、独属于司马迁的一个《金縢》文本。
相较于今传本和简本,《鲁》本在宏观叙事结构方面有两处显著的不同:第一,《鲁》本包含两次模式相同的“周公藏书—成王见书”的叙事,一次是周公代武王之书,一次是周公代成王之书;第二,《鲁》本鲜明地将第三叙事段落(风雷之变)发生的时间标识为“周公卒后”。就第一点而言,周公代成王故事不见于今传本和简本,但另见于《蒙恬列传》;就第二点而言,虽然《鲁》本认为风雷之变发生时周公已去世,但给出的解释却与“葬疑说”不同。以下分别详释之。
首先,针对第一点需要解释的是,司马迁基于什么样的意图将周公代成王故事加入到《金縢》故事之中?原文如下: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2]1393
传统解释持“调和论”,如顾颉刚认为,司马迁是有意调和周公代死的两种传说,其所用之“亦”字即为证据(“亦藏其册于府”),并指出司马迁的这种调和造成了史实的混乱[11]67。这种解释不够充分——司马迁为何一定要“调和”两种传说呢?这就需要在文本内部对“周公藏书—成王见书”这一情节的叙事功能做出解释。对观今传本和简本,我们注意到,在这两个版本中,风雷之变后的“成王见书”(周公代武王之书)情节,其叙事功能非常明确,即消除成王与周公(无论是否还在世)之间的某种嫌隙。我们惊讶地发现,单就叙事功能而言,虽然《鲁》本采用了不同的材料——周公代成王——但就“成王见书”(周公代成王之书)而言,它的叙事功能跟简本和今传本是等效的:“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既然成王与周公的嫌隙已经解除,那么相应地,《鲁》本在下文风雷之变后的“成王见书”(周公代武王之书)情节就不再承担此叙事功能,而是承担了另一全新的叙事功能(详后)。由此,我们不能不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即司马迁并非仅仅是为了调和两种周公代死的传说而采用了周公代成王故事,而是通过增加一条“二等史料”(如果周公代成王故事作为史料的可靠性较低的话)将《金縢》故事的第三叙事段落解放出来,从而服务于其《鲁》本《金縢》的叙事意图。类似的处理方式在《史记》中并不鲜见,比如对观《晋世家》与《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故事,可以发现司马迁同样在《赵世家》中采用了类似的“二等史料”(屠岸贾、公孙杵臼、程婴故事)以服务于《赵世家》的叙事意图。同理,相较于《鲁周公世家》中的杂采史料,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只是极其谨慎地使用了《金縢》中周公代武王的部分材料。而《鲁》本在杂采史料的同时又对两则史料的功能做出不同的分配:“一等史料”(周公代武王之书)服务于更高的叙事意图,“二等史料”(周公代成王)则只承担较弱的叙事功能。而这两种史料的分工离不开一个必要条件,即史料中叙事时间的模糊。周公代成王故事发生的时间存在表述上的模糊,为这条史料的“乱入”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根据叙事需要将其置于任何一个大致合理的时间范围内。风雷之变发生的时间事实上同样如此——这一事件的传奇特质使其无法像一般的“历史事件”那样介入和改变历史,因此不同的作者只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化处理即可——重要的是让人们相信这件事发生过,但不必让人们知道确切的日期。这也就能解释为何诸多研究者都无法最终真正确定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这一事件蕴含的“诗性”特质成为了它的一个叙事难题,于是在历史书写过程的某个环节,历史性让位给了文学性。
由此,司马迁虽兼采史料但有轻重之别,很可能是试图以一种全新的叙事策略传达出他对《金縢》故事的某种理解。这就需要对第二点即《鲁》本的风雷之变场景做出阐释。
原文如下:
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2]1395-1396
如何解读这一段,对理解《鲁》本《金縢》的叙事意图至关重要。本段之前,《鲁》本已经以成王葬周公于毕结束了对周公生前故事的主体叙述,且由于上文已经给出了一个成王见书(周公代成王之书)故事,事实上也就结束了传统意义上《金縢》故事的全部主题(解除嫌隙)。由此,这里的风雷之变虽然在文句上与简本、今传本《金縢》类似,但从叙事功能上看,已经不再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金縢》故事。因此,与其将之看作是司马迁对《金縢》故事的一般化改写,毋宁将其看作是司马迁以文学笔法对《金縢》主旨作出的某种解读。本段关键信息有三:第一,“自今后其无缪卜乎”今传本作“其勿穆卜”,简本无;第二,“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今传本、简本无;第三,(司马迁)对“鲁有天子礼乐”的解释:“以褒周公之德也。”
首先,第二、第三条信息无疑表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鲁》本《金縢》的编撰方式是隶属于《鲁周公世家》的整体写作语境的,因此其最终落脚于鲁国政道传统之由来。这与今传本和简本作为周王室历史叙事作品的基本定位是不同的。关于这一点,杜勇在其论著中指出,“细绎《金縢》可以发现,周天子始终处于权力核心的地位,位尊权重的周公也只能附从这个最高权力执政”,并由此推测“或许《金縢》就是出于这种维护和强化王权的政治需要,由王室史官根据自己掌握的有关材料在春秋前期写成的一篇文字”[6]249。而夏含夷在其相关研究中也曾提出这样的观点:随着周初政治的逐渐稳定,朝堂权力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周公为代表,主张任人唯贤之思想,一派则以召公为代表,宣扬王权至上之政策;随着周公隐退,其思想也逐渐式微,直到孔子时代重新兴起贵贤思想,周公才作为贤相代表得到重视[12]。我们可以由此反观《鲁》本,作一假定和推理,即司马迁在编撰《鲁》本《金縢》的时候,首先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周公重新置于叙事的核心位置,从而让整个叙事的主旨潜在地指向“贤相”而不是“王权”。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再看《鲁》本风雷之变,就有些春秋笔法的味道了:“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集解》此处引《礼记》曰:“鲁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引郑玄曰:“鲁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庙也。”[2]1396——周公凭借其德行为鲁国赢得了使用天子礼乐的权利。这无疑是对作为臣子的周公至高无上的尊崇,颇有“无冕之王”的意味,但在表述上仍然是合乎礼的。而更重要的信息则隐藏于第一条之中:“自今后其无缪卜乎!”周成王赐鲁天子礼乐还在其次,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司马迁认为周公在某种意义上竟然终结了“缪卜”(穆卜)这种仪式。今传本作“其勿穆卜”则无此决绝意味。为什么这是令人惊讶的?这就涉及对《金縢》故事中至关重要的穆卜仪式的阐释。
三、表层叙事与深层叙事:喜剧或悲剧
从表层叙事来看,《金縢》故事是一个关于隐匿和发现的故事。基尔克果曾以如何对待隐匿和袒露这一问题对美学与伦理学做出如下区分:“美学呼唤隐匿并给予丰厚回报,而伦理则要求袒露并对隐匿施以惩罚。”[13]伦理学重普遍性,美学重个体性(特殊性)。基尔克果所谓“回报”的意思是,当美学的隐匿凭借巧合得以袒露并得到回报的时候,美学也就臣服于(普遍性的)伦理学了。美学的隐匿如何不依赖伦理化的袒露而获得正当性?由此,基尔克果试图为美学找到一条超越伦理学之途。他在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中看到了这种可能,即亚伯拉罕凭借其信仰与“绝对”建立了一种私密联系——这种私密性为美学的隐匿提供了一种超越普遍性伦理的正当性。我们将借助基尔克果的这一洞见来重新审视《金縢》故事中周公的行动。
我们的问题是:《金縢》到底是一个关于“袒露”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隐匿”的故事?目前的研究,无论是对简本还是对今传本,基本都支持前者:一个隐藏之物被重新发现,周公的德行得到彰显。只要研究者聚焦表层叙事,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个“隐藏之物”背后的意义是否同样得到彰显,抑或仍然维持在隐匿和缄默的状态?换言之,这个“隐藏之物”究竟是什么?
对观简本与今传本、《鲁》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被简本删除了:穆卜。如前所述,诸多证据表明,简本作者为了维持叙事的整一性尤其看重文句的前后呼应。由此,上文的特定信息是否在下文得到呼应,可以被当作判断简本作者编辑意图的一种标准。今传本和《鲁》本在开篇都提到“穆卜”/“缪卜”,并且都在结尾呼应了这一信息(“其勿穆卜”/“自今后其无缪卜乎”)。而简本虽然在开篇提到“穆卜”,但在结尾却没有呼应这一信息。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显示出简本与今传本、《鲁》本对开篇场景的不同理解,即简本认为,开篇周公所举行的仪式并非穆卜仪式。今传本注疏中亦有类似观点,如林之奇《尚书全解》认为,开篇二公建议举行穆卜,而周公的“未可以戚我先王”乃是对二公这一建议的否定:“周公既以未可戚我先王之辞而却二公之言卜,故自以请命之功为己任而设为坛墠之礼也。”[14]529但林氏下文对周公占卜行动的解释似乎又认为周公最终还是举行了穆卜:“盖古者卜龟既毕,必纳其册书于匮,从而缄之,异日将有大卜则复启焉。不然则否此故事也。”[14]531可见林之奇注意到了今传本存在首尾呼应的两次占卜,但并不确定周公之占卜是否为穆卜。《鲁》本开篇对是否举行穆卜的处理方式则十分微妙: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2]1390
对观今传本: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1]162
今传本给人直观的感觉是周公与二公处于一种对话关系中,对话的主题为是否“为王穆卜”,因而很容易让人得出林之奇的结论,即周公否定了二公穆卜的建议。而《鲁》本则不存在这一对话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出林氏的结论。再对观《周本纪》的处理方式: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2]117
这里的行文更加明确地表明:首先,司马迁认为在《金縢》故事中“穆卜”是一个发生过的事实;其次,此次“穆卜”被周公植入了自己的特殊意图。所以《鲁》本说:
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2]1390
结合以上材料可见,司马迁认为,周公并未否定穆卜,而只是在穆卜之前增加了另外一个仪式——一个秘密的仪式——用以解决他所担心的“戚我先王”的问题;由连词“于是乃……于是乃”可知,周公在解决了这一问题之后,他所举行的占卜仪式就是穆卜。司马迁的理解和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正因如此,今传本和《鲁》本都在风雷之变场景中明确呼应了这一信息,再次提到了穆卜。
事实上,单从叙事逻辑上也可判断,周公不可能否定二公提出的穆卜建议。观上下文,对于“武王有疾”这件事而言,穆卜应是一个常规操作。如果周公否定了穆卜,他就必须明确说明自己的理由,而这将导致后面周公的行动以及周公代武王之书无法保密,从而整个《金縢》故事不能成立。简本作者对周公的秘密——《金縢》表层故事的核心要素——所营造的悬念太过关注,以至于他忽视了这一简单的逻辑合理性。他无暇考虑周公的秘密与穆卜的关系,于是将穆卜这件事从主题叙事中剔除了——而一旦剔除了穆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周公的“未可以戚吾先王”这句话也就无从谈起了。简本作者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周公的秘密行动上。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对这个秘密唯一感兴趣的只是它的“秘密性”,而对“它为什么必须是秘密的”这一问题不感兴趣。正是这种对表层戏剧性的单一追求,使得简本作者毫不犹豫地将穆卜信息舍弃了。而穆卜仪式后的周公言辞恰恰是整个第一叙事段落中唯一没有被记录在“金縢之书”中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的推断成立,即简本作者在处理史料的时候仅仅为了追求一种表层戏剧性而舍弃了这一最关键的信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追求表层戏剧性的结果是,简本《金縢》成为一个喜剧故事,而且是一个大团圆的喜剧。也许,正是这一喜剧内核才使得简本叙事显得更加紧凑,行文显得更加流畅,信息显得更加明确,因为这是实现喜剧效果的基本保证。而我们在《鲁》本《金縢》中看到,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一个悲剧。
《金縢》故事第一叙事段落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仪式:周公的祝祷仪式(或为代祷,如钱穆:“如周公金縢,即代祷也,然未尝先告武王,又命祝史使不敢言。”[15)]和穆卜仪式。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鲁》本的表述方式(于是乃……于是乃……)表明司马迁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两个仪式之间的关系。前者是秘密的,后者是公开的。所以相比今传本,《鲁》本对如下场景做了改动:
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1]162
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2]1390
从以上对比可见,相较今传本,《鲁》本给出的第一叙事段落场景更加清晰、完整:始于为武王穆卜,终于把穆卜结果告知武王,武王是这个场景中明确的参与者。《鲁》本没有像简本那样轻易舍弃任何情节,这种扎实的场景铺垫是建立在作者对场景意义的深刻领会之上的,其最终的意图是为了揭示被隐匿之物的意义。
先来看第一个仪式——周公的祝祷仪式。它的主题被认为是“替死”。但如果这个仪式的主题仅仅是“替死”,那么它有什么理由需要保密呢?并且,从后来的事实来看,作为有记录的一次行动,彻底的保密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这里需要探讨的关于保密的“理由”应该是“充分性理由”。在文本层面可见,《鲁》本(以及今传本)认为,周公的祝祷仪式是有效的——“武王有瘳”。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真有某种神秘力量使武王痊愈了——武王的痊愈可以解释为病情本就时好时坏,或者如杜勇的解释“回光返照”——而是仅仅表明作者对周公仪式有效性的认可。但有效性是否等同于合法性?如果合法性问题才是保密的充分性理由,那我们就必须重新考察这个仪式的主题,即周公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了仪式的“有效性”。《鲁》本祷词原文如下:
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2]1390
简本、今传本、《鲁本》在祷词开篇部分的一处显著不同引起学者较多讨论:
惟尔元孙发也,遘害虐疾,尔毋乃有备子之责在上。[1]158
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1]162
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2]1390
何为“备子之责”?李学勤先生认为,简本的“毋乃”一词证明“备子”是一个有贬义的词,因此其从郑玄说,将本句解作“三王也要负不慈爱子孙的罪责”[4]117。但从大的语境来看,这个解释似乎与周公的建议相矛盾:如果武王病死意味着三王不慈爱子孙,为天所责,那么同为三王的子孙,又有什么理由让周公代替武王死去呢?因此这一解释事实上也就否定了周公替死的合法性。相比之下,廖名春先生解为“服子之责”即“用子之求”更优,意即“三王在天上有使用儿子的要求”[16]。《鲁》本《集解》引孔安国曰:“大子之责,谓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则当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请代,圣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索引》曰:“尚书‘负’为‘丕’,今此为‘负’者,谓三王负于上天之责,故我当代之。”[2]1390-1391曾运乾《尚书正读》解“丕子”为“布兹”,“为弟子助祭以事鬼神者之一役”[17],也认为三王于“天”有某种义务,是这个义务造成了武王的病重。这个义务也即下文所说的“事鬼神”。只有在这一语境下,周公所谓的“以旦代王发之身”的提议才能在字面意义上成立。这里存在一个三项关系:周公/武王—三王之灵—“天”。三王之灵是氏族神,而“天”是至上神,其权威高于三王之灵[18]。周公作为在世者是无法直接与至上神对话的,他必须以氏族神为中介,这也就是下文“即三王而卜”的原因。《大诰》中亦有周公“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19],即借助三王之灵来探究天命。《论语》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周公与三王之灵的谈话方式犹如面对在世者,这对于理解整个祝祷仪式的基调是重要的:正因为事死如事生,所以面对三王之灵,周公不是唯唯诺诺,而是敢于据理力争。周公的意思是:如果说你们(三王)有侍奉“天”的义务,并且拣选了一位在世的“王”去帮助你们,那么,就让我代替武王死去帮助你们吧。继而他将自己与武王比较,强调自己多才多艺更能胜任侍奉鬼神之事,而武王则更适合秉承天命治理周王朝的天下(“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周公的秘密正隐藏在这种比较之中:周公为了与武王作比较,同时也为了说服三王,他事实上赋予了自己“王”的身份——因为出于某种神秘的理由,被拣选的应是一位“王”。这种替代对在世者(武王)而言,无疑是一种僭越。因此这一仪式必须秘密进行,这一“协议”必须私下达成。换言之,周公祝祷仪式的有效性依赖于它的“非法性”,而它的非法性则依赖其“秘密性”——这正是周公告诫执事人要保密的原因。
由此,我们反观上文周公的“未可以戚我先王”。“戚”,传统注疏或解为“近”,或解为“忧”。林之奇辨析之后认为解“忧”较长,并佐之以孔子“父母唯其疾之忧”[14]528-529,意即不应该让先王为武王的疾病而忧戚。然而这种解释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先王一定会忧戚,因为武王的疾病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所以,周公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其实是:的确不应该让先王忧戚——但至于先王为什么会忧戚,则另有原因。周公的建议只有针对这一原因“对症下药”,才能解除先王的忧戚。理顺了其中的逻辑关系之后便不难看清先王忧戚的原因:他们一方面需要一个“王”去帮助他们侍奉鬼神,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王”来安定周王朝的社稷。所以,周公才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让自己代替武王。这个建议的惊人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僭越,更在于它的冷峻和理性。换言之,周公不是“动之以情”,而是“晓之以理”。或许在周公看来,所谓“先王的忧戚”是非常虚伪的,它需要被“净化”——“以旦代王发之身”这一建议就其残酷性来说其目的便在于“净化”。净化的结果便是回归理性。周公在祷词中事实上提出了两种“王”:一种“王”服务于上帝(天)之城,一种“王”服务于地上之城。而更深层次的含义则在于,周公更改了“王何以为王”的合法性标准:不是“受命于天”,而是以地上之城为优先考量。这是继“受命于天”之后“王”的真正诞生。周公的占卜以及对占卜结果的解释是点睛之笔:
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2]1390
“新受命”正是周公所要达到的目的。它赋予“替死”仪式以真实的意义。“予一人”,或说解为武王,或说解为周公,耐人寻味。仪式的本质就在于身份的转换。《逸周书·度邑解》中有武王训导周公并传位周公的说法:“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20]周公卜三龟的仪式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武王的回应——它直指权力的来源和合法性的根源。
由此,《金縢》第三叙事段落的那个信息将得到解释——“其勿穆卜”(今传本)。风雷之变发生后,需要举行穆卜以探知天意。然而成王见书之后却中止了穆卜,原因并非是成王被周公替死的心意感动了,而是他领会了周公祷词中“地上之王”的思想。对于地上之王而言,“穆卜”丧失了意义。然而成王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僭越。因此,虽然成王的“执书以泣”作为姿态的确容易让人动容,但成王的言辞却无比克制:
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1]162
“天动威”成了成王的“丐词”。对观《鲁》本风雷之变中成王言辞的“不克制”(“自今后其无缪卜乎!”),就辨析叙事时间而言,今传本中成王的这种“克制”(“其勿穆卜”)似乎比简本“是岁也”更能说明此时周公未去世,司马迁应是领会了以上信息的。也正因如此,在司马迁那里,风雷之变必须发生在“周公卒后”。周公仪式的秘密性是一种保障,当这个秘密一旦被揭示,必然会给周公带来威胁:无法指望君臣双方对这个秘密心照不宣同时又获得一个大团圆结局。现实中已经没有了周公的位置。正如基尔克果笔下的亚伯拉罕,当他在一个秘密场景中与“绝对”(上帝)建立了私密联系之后,他就无法再以俗世的普遍性伦理为自己的行为(以子献祭)和信仰辩护了。周公的“信仰”与亚伯拉罕不同,但周公的处境却与亚伯拉罕相似。司马迁深知,只有一个死去的周公才能在秘密被发现之后获得合法的荣耀。为此,他不惜采用了“二等史料”(在周公代成王故事中披露周公的秘密行动和言辞,不涉及严肃的争论,它只是功能性地服务于解除成王对周公偶然的一次误会[“人或谮周公”])来最大限度地延宕真正的秘密被发现的时间,让周公的行动不至于因秘密的提前揭露而丧失合法性。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司马迁笔下,周公的整个行动都有双重含义:周公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摄政之王”(七年后归政成王)而存在;在武王死后直到去世,他实际上都作为“王”而存在。司马迁在对周公行动的叙述中不惜笔墨罗列了《诗》《多士》《毋逸》《周官》《立政》等篇,鲜明地将周初故事笼罩在《金縢》之下,表里呼应。最终,司马迁在风雷之变后借成王之口隐秘地将最高的荣耀归于周公: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这是司马迁所理解的《金縢》故事:一个关于(潜在的)“王”的故事。由此反观第二叙事单元的周公“居东—遗诗”,不当以“臣事”视之,当以“王事”视之,或可为避居说不成立的一个佐证。
由此反观简本,对周公穆卜仪式的正确解读将打破简本努力营造的表层戏剧性。这种表层戏剧性乃是依赖形式上的整一性来维持的,本质上是美学/诗学对伦理学的臣服:机缘巧合,周公被一种普遍性伦理所拯救,回归为一个忠实的臣子——宋代理学尤其钟情于这种解释。顾颉刚曾因为周公拿璧与圭与三王讨价还价而将《金縢》解读为喜剧[11]72——真正的喜剧而不是大团圆意义上的喜剧——这是看到了真理的影子:周公的仪式与其被理解为感人的戏码,倒不如被理解为喜剧,因为喜剧以反讽的方式接近真理。只有司马迁笔下的周公实现了美学对伦理学的超越:他与三王建立了私密关系,并借助三王之灵与至上神“天”达成了一个以普遍性伦理无法明言的秘密协定。虽然,他期待金縢之书被发现,他期待二公和成王都窥探到他的秘密,但他深知真正的秘密只能以缄默的方式传承下去,成为一种隐秘的传统。周公必须死去,现实中没有他的位置——这对所有信奉这一隐秘传统的人而言,都将是一个悲剧,甚至一个伴随着“恐惧与战栗”的悲剧。
四、跃迁:周公、孔子、司马迁的个体伦理
刘小枫在点评陈桐生著作时说:“司马迁的孔子传说明了他承孔子继‘先哲王’的素王精神,《史记》笔法只能从孔子‘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来理解。这种行为是政治的,是继孔子立法后的又一次立法行为。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政治哲学家,同样,《史记》首先是政治哲学。”[21]在春秋公羊学的视野内,要理解司马迁的政治哲学,首先必须理解其历史写作。
关于《史记》(《太史公书》)写作的缘起,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祖述先人之志曰: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2]2855
然后记述了与上大夫壶遂的一段对话,论及两个问题:第一,“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第二,“夫子所论,欲以何明”?而正是这第二个问题险些摧毁了司马迁论述的合法性: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2]2857
壶遂认为《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的论断是对第一问中司马迁思想的总结,可谓一语中的。然而他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却让司马迁措手不及。司马迁只能搪塞道:“唯唯,否否,不然”,并且强调自己只是“述而不作”,不可与《春秋》相提并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2]2858但很快,命运就让司马迁“摆脱”了这一窘境: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2]2858
李陵之祸的牵连让司马迁“身毁不用”,这彻底摧毁了司马迁的伦理生活,将他置于完全不同的处境。多年之后,他在《报任安书》中剖白心曲,详细描述了作为一个被普遍性伦理抛弃的“刑余之人”的内心痛苦: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锺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22]2061
……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22]2063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22]2065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22]2066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祇取辱耳。……[22]2069
司马迁被普遍性伦理所抛弃,只能将心中苦闷诉诸一个将死的囚犯。这是一个私密处境,虽然是被动进入的。在这样一个私密处境中,司马迁得以重新思考圣贤写作的意旨,由此,他自己的写作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2]2858在这一私密处境中,司马迁与某种传统获得了秘密的联系。他的切身体验告诉他在普遍性伦理背后贯穿着一种个体伦理。如果说他之前只是被动地承续先人之志,那么,真正让他主动参与到一个伟大传统中的关键事件则是他对个体伦理的领会。相较于“文化复仇”心理[23],这一领会更可看作是一种由传承到信仰的跃迁。
有理由相信,孔子与那个伟大传统亦存在私密联系。孔子遇大事常言天,危难时刻亦以信仰者自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然而孔子死前梦见了自己: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24]
孔子死前梦见自己坐在主位与宾位之间,这看似对大限将至、落叶归根的感叹,实际上是在感慨现实中没有自己的位置。这与周公的处境何其相似!孔子也是一个被现实弃绝的人,无论是梦见周公还是梦见自己,孔子之梦都是他与伟大传统的私密联结。
而《金縢》中的祝祷仪式即是周公与伟大传统的一个起点。到了司马迁这里,被司马迁以一种春秋笔法和隐微书写再次揭示出来。一个无法被普遍性拯救的周公成为一种传统的象征:它依赖个体的激情,凡是信仰此传统的个体凭借其激情传承这个传统,孔子如此,司马迁也如此。如果说孔子梦见周公是独属于孔子与周公的一种私密联结,那么,《鲁》本《金縢》的书写则是司马迁精心建构的、独属于他与周公的一种私密联结。
结语:藏书
《孔子世家》中有孔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2]1738-1739《太史公自序》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2]2875《报任安书》亦有:“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22]2068-2069《春秋》之于孔子、《史记》之于司马迁,它们的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在自己死后成为自己理念的承载者。“金縢之书”也不例外。对于追求“垂空文以自见”的司马迁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金縢》故事中的“藏书”意象会给他带来内心的震动,甚至为他带来创作的灵感:作为一种隐秘传统的载体,“金縢之书”不能在周公死前被发现;“金縢之书”的真正意义也只能以春秋笔法再现。为此,司马迁精心设计了一个“死后的周公故事”。这是司马迁刻意营造的一个“意外”——相较于简本作者,司马迁懂得如何最大化地利用“风雷之变”为自己的叙事意图服务:周公死后,风雷之变使周公的老朋友们(成王、二公)意外地需要再次“面对”周公。这是司马迁所追求的戏剧性。若考虑到成王与周公的嫌隙、周公与二公的理念分歧,如何面对死后的周公就成了一场博弈。简本和今传本在“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的名义下,把周公降格为“勤劳王家”的好管家。而司马迁解除了这种克制,首先以穆卜仪式的终结回应了周公的穆卜仪式中的僭越成分;继而在丰收场景后以成王赐鲁天子礼乐作结。于是在司马迁的笔下,周公完成了对其政治传统的认领。司马迁所指认的这一传统,以及这一传统所反映的政治理念,包括孔子的和司马迁自己的政治理念,是这个故事真正的主题。这也许就是司马迁为何要舍弃一个简单流畅的版本而采取一种在叙事上冒更大风险的结构的原因。由此,司马迁的《金縢》写作应属于“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范畴。
注 释:
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在《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篇后附有今传本《金縢》(繁体字版)以为对照,其文字与今传本权威版本一致。为便于展开论述及方便读者查阅,本文亦采纳此对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