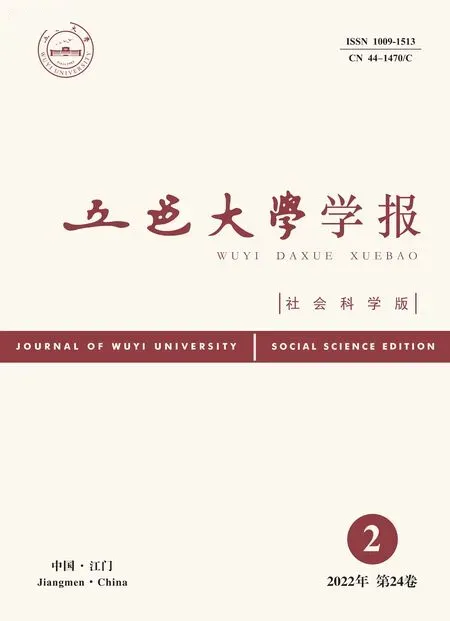梁启超中西兼通的教育思想
2022-12-06花宏艳
花宏艳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宣传家和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同时也是近代社会科学及教育领域的奠基人,在引领近代中国教育思潮和倡导教育改革等方面具有卓越的贡献。梁启超有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早年曾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后承办上海中国公学,并任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身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晚清社会,“中西兼通”的思想是梁启超教育理论的核心,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对时代思潮的回应。
一、从“乡人”到“世界人”
梁启超“中西兼通”的思想与他从“乡人”到“世界人”的文化身份的转变密切相关。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远走他乡的梁启超,在1899 年完成的《夏威夷游记》中谈到“世界人”身份的形成:“去年九月以国事东渡,居于亚洲创行立宪政体之第一先进国,是为生平游他国之始。今年十一月乃航太平洋,将适全地球创行共和政体之第一先进国,是为生平游他洲之始。于是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1]588从狭隘的“乡人”到具有国际视野的“世界人”,梁启超文化身份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梁启超出身于耕读世家,幼年熟读四书五经,12 岁应试学士院,日钻研于帖括之学,17 岁中举人。彼时的梁启超和芸芸众生一样,并不知道八股文之外,还有一个西学的世界:“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1]587此时的梁启超,还是一个没有世界概念的纯粹的“乡人”,但转折的契机很快来临。
1889 年梁启超途经上海,偶然接触到西学书籍,从此打开了探索世界的窗口。1891 年,18 岁的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并受业于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春秋公羊传》 《宋元学案》 《明儒学案》、“二十四史”及诸子书、佛经、清儒经注和西学译本等。在康有为的启发下,新的知识体系开始构建,为梁启超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同时也奠定了他“中西兼通”教育思想的根基:“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2]134可以说,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梁启超接受并借鉴了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开始从世界的视角来思考中国问题。
1898 年戊戌政变失败,梁启超赴日本避难,在日本居停一年后“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2]136这是梁启超学术思想上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梁启超在日本受到的思想影响,不仅来自一些日本著名学者的著作,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为数众多的学校教科书、讲义和杂志文章,以及日本社会中已视为常识的普遍观念。梁启超有些很有影响的文章,甚至就是直接把日本教科书、文章的内容译成中文,而又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他的理解有所损益,并增加一些自己的议论。[3]
以日籍西书为媒介,在全面接触西方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潮的过程中,梁启超“中西兼通”的思想不断深化:“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589
1899 年12 月,梁启超在从日本横滨开往美国夏威夷的“香港丸”船上,写下了著名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其时人静月黑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海底蛟龙睡初起,欲嘘未嘘欲舞未舞深潜藏。其时彼士兀然坐,澄心摄虑游窅茫。正住华严法界第三观,帝网深处无数镜影涵其旁。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在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节选)[4]
身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接之际,面对东西两半球之界的太平洋,梁启超并没有感伤和颓废的世纪末情怀,而是油然而生发出一种承先启后的壮志豪情。这首诗歌所体现的是一个成熟的“世界人”的眼光。可以说,从“乡人”到“世界人”,梁启超文化身份的转变,于此完成了从理论层面到现代性体验的过程。
二、中西兼通与政艺并举
教育启蒙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一个主要领域,他将教育的重要性提升到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层面,所谓“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5]155。梁启超认识到,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教育是开启民智和培养人才的关键,放眼世界,莫不如此:“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藉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 强也。……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 教。”[5]150
向西方学习,发展自身独立的教育政策,首先必须正确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梁启超提出“中西兼通、政艺并举”的原则,这一教育主张较之顽固派和守旧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念有了质的飞跃。
梁启超首先强调本国之学是他国之学的根柢,向外寻求先进的西学知识必须先有扎实的中学知识的积累:“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西人之教也,先学本国文法,乃进求万国文法,先受本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乃进求万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此各国学校之所同也。”[6]197既要建立民族性的教育体系,又要以世界性的眼光学习先进的西学知识,即“中西兼举,政艺并进。然后本末体用之间,不至有所偏丧”。[7]
梁启超“中西兼通”的教育思想虽然同样涉及“本末体用”的问题,但他的观点与晚清洋务派“中体西用”的观点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中西兼通”的教育思想是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上积极向外寻求理性之光,而梁启超本人也曾多次批判过“中体西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观念。
“中体西用”是晚清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当时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大都持此种观点。这一思想的产生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所遭遇的民族危机密切相关。
1840 年后,从鸦片战争开始,晚清中国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遭受的创巨痛深的苦难使得知识分子痛彻觉醒,向西方学习成为首要任务。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即提出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1861 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进一步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8]冯桂芬的“中体西辅”说认为西方的优势仅限于科学技术,西学知识必须以中学为根柢,这一观点正是“中体西用”思想的 雏形。
此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更是对“中体西用”的思想进行了集中阐释:“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9]
1920 年,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严厉批判自鸦片战争以来晚清中国社会所流行的“中体西用”的观念:“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10]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希望建立的是与洋务派“中体西用”观念不同的教育思想。
在当时占主流地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新学”教育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其表现即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所说:“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于是震动于其屡败之烈。怵然以西人之法为可惧,谓彼之所以驾我者,兵也。吾但能师此长技,他不足敌也。故其所译,专以兵为主,其间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诸门者,则皆将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此为宗旨刺谬之第一事。”[11]204“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诸书。……惟西政客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12]
“中体西用”的局限性使得晚清洋务派将“西学”仅仅等同于器物层面的格致之学和制造之业,而对于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的先进知识视而不见。狭隘的“中体西用”观念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竟然是“英法之文亦未上口,声光化电之学,亦未寓目。……而揣摩风气,摭拾影响,盛气压人,苟求衣食”之流。他们虽然号称是西学之士,但实际上,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都仅仅识得皮毛,对民族国家毫无益处:“今日中国为洋学者,其能识华字,连缀书成俗语者,十而四五焉;其能通华文文法者,百而四五焉;其能言中国舆地、史志、宗教、性理者,殆几绝也。”[6]194
梁启超所强调的西学不仅仅是西方的器物文明,而更是能够获得自由之基、富强之路的政治制度:“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会靡闻焉。”[13]在片面保守的文化观念下,不论是制造局还是教会学校,人们读到的西学书籍大多是兵器工艺以及医学之类,而近代中国社会启蒙所需要的政治、教育等制度层面的西学知识却无从获得。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启蒙知识分子,梁启超主张翻译西学书籍从而达到参照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救治中国的目的:“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参西法以救中国,又必非徒通西文,肆西籍可以从事也。必其人固尝邃于经术,熟于史,明于律,习于天下郡国利病,于吾中国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挈枢振领而深知其意,于西书亦然。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互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之异。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夫是之谓真知。”[11]201
1896 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西学书目表》,该目录分西学、西政和杂类三大类介绍近代西学书籍,其中西学又分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等13 类;西政类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10 类;杂类包括游记、报章、格致、西人议论之书等5 类。可以说,涵盖300 种书籍的《西学书目表》充分体现了梁启超“中西兼通”教育思想。
三、广求智识于寰宇
梁启超论教育有明确的宗旨,他提出今日之中国应以世界各国为参照,确立自己的教育宗旨:“第一当知宗旨。使欲造成文学优美、品格高尚之国民也,则宜法雅典;使欲造成服从纪律、强悍耐苦之国民也,则宜法斯巴达;使欲造成至诚博爱、迷信奉法之国民也,则宜法耶稣教会;使欲造成自由独立、活泼进取之国民也,则宜法英吉利;使欲造成团结强立、自负不凡之国民也,则宜法德意志;使欲造成君国一体、同仇敌忾之国民也,则宜法日本。苟不能者,则虽学法国之拿破仑可也,学奥国之梅特涅可也,学俄国之皮里加辣陀(现任宗教大匠)可也。”[14]59
身处列强环伺、民族命运岌岌可危的过渡时代,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宗旨归根结底仍在于启蒙与救亡。他建议所有有志于教育之业的人,必须先认清楚中国教育的宗旨,要明白教育的目的是开启民智,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教育事业,“不可不具经世之炯眼,抱如伤之热肠,洞察五洲各国之趋势,熟考我国民族之特性,然后以全力鼓铸之。”[14]53近代中国教育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民智与启蒙,更是在二十世纪中西竞存的环境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群体,实现民族独立:“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14]55
梁启超“中西兼通”的教育思想要求全面而深入地学习西学知识,因此,广泛地阅读各类西学书籍便成了当务之急。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巨大成就而深受震撼。因此,梁启超多次主张积极地学习日文,通过日语转译的西学书籍学习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等各类现代学科知识:“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以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15]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不仅提出了阅读西学书籍的主张,还指出了具体的读书门径和方法。一方面必须广泛阅读西学书籍,但他所主张的“读万国之书”,不仅仅是声光化电等格致之书。另一方面,梁启超认为中国学者需要以数年之精力透彻阅读中国的经史等书籍,然后再转而攻读各类西学书籍。此外,将经学、子学和史学书籍与西学书籍隔日阅读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今之服方领习矩步者,畴不曰读书。然而通古今达中外能为世益者,盖鲜焉,于是儒家遂以无用闻于天下。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然西人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纪载,岁出以千万种计,日新月异,应接不暇。惟其然也,则吾愈不能不于数十寒暑之中,划出期限,必能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谓之学……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16]
为别求新声于异邦,梁启超除了推荐西学书籍之外,还按照日本现代学科的划分,为有志于新学的读书人介绍普通学、伦理学、历史等不同学科的西学书目、阅读方法和读书门径。
在所有学科中,梁启超以“普通学”为读西书的门径,“凡求学者必须先治普通学,入学校受教育者固当如是,即独学自修者亦何莫不然?”[17]501具体而言,普通学所涵盖的内容有:伦理、国语及汉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经济等,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自学,“以上诸学,皆凡学者所必由之路”。[17]502
梁启超以现代学科的划分为阅读西学书籍的门径,正体现了他一直以来所提倡的“中西兼通”的教育思想。以“普通学”中的伦理学为例,梁启超批驳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观点,“中国自诩为礼义之邦,宜若伦理之学无所求于外,其实不然”,在进行了中西之间的比较之后,强调“其广狭偏全,相去奚翅霄壤耶?故外国伦理学之书,其不可不读明矣!”[17]502同时,梁启超还提供当时可获得的西方哲学经典学派和研究书目,如《杜威伦理学纲要》 《斯蒂芬伦理学》 《阿里士多德伦理学》 《倍因氏伦理学》 《斯氏伦理原论》(斯宾塞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