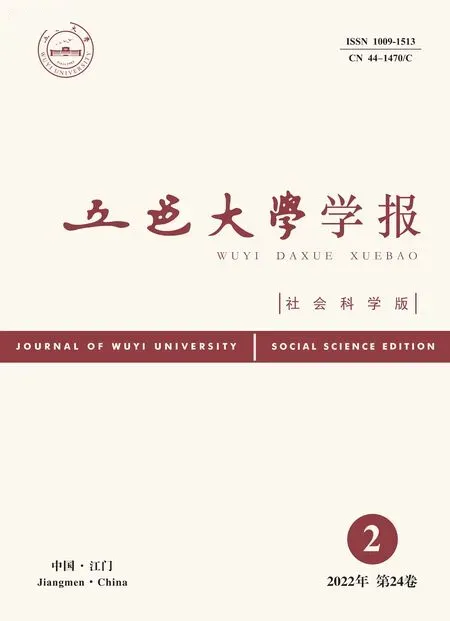隐蔽的战场,无声的功勋
——评衣向东新作《身份》
2022-12-06宋雯
宋 雯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炮火隆隆,硝烟弥漫,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三大战役等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被写进教科书,被改编成小说和电视剧,家喻户晓,成了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记忆。这些战役,都发生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面战场。而在正面战场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隐蔽的战场,这个战场不像正面战场那样厮杀震天,却杀机四伏,波澜深藏,活动在这个战场上的革命者就像在悬崖上走钢索的人,稍有不慎,就会跌落万丈深渊。正面战场和隐蔽战场互相补充,共同抗敌,最终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隐蔽战场,都涌现出了一批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和革命英雄,可是,被大众熟知的多是正面战场上的英雄,如黄继光堵机枪眼、董存瑞炸碉堡的英雄事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隐蔽战场由于其特殊性,革命者们往往隐姓埋名,常常牺牲了也无人知晓,就像盛开在人迹罕至的山谷里的花朵。
21 世纪以来,涌现了很多以隐蔽战场为题材的小说和电视剧,如《惊蛰》 《潜伏》 《暗算》 《悬崖》等,都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也许正如作家麦家所言:“这是个消解崇高和英雄的年代,但同时我们又无比需要他们。”[1]这些作品的大火,反映的正是当下大众对崇高人格和雄浑人生的渴望与尊崇。2021 年4 月,当代著名军旅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衣向东推出新作《身份》,也为我们还原了一段隐蔽战场鲜为人知的历史。与一些纯虚构的谍战作品不同,《身份》是根据革命烈士龚昌荣的真实经历改编的,具有较强的纪实性和传记色彩。龚昌荣是广东江门水南乡一侨商的养子,早年常参加水南乡农民自卫团组织的革命活动,广州起义时担任工人赤卫队敢死连连长,起义失败后,他随队撤至海陆丰一带,担任工农红军第四师连长,坚持革命斗争。后因组织需要,从正面战场转到隐蔽战场,担任中共中央特科红队队长,负责锄奸、保护共产党领导人等地下工作。在此期间,龚昌荣率队员掩护中共中央领导人转移,铲除了众多叛徒特务,特别是先后处决了国民党三大“反共高手”(史济美、黄永华、雷大甫),为保护上海党组织以及党中央立下赫赫战功。在大量真实史料基础上,衣向东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地下工作者形象,再现了一段比纯虚构谍战作品更加真实的隐蔽战场历史。
一、有血有肉的凡人英雄
20 世纪上半叶以来,涌现了不少以隐蔽战场为题材的作品,如《永不消逝的电波》 《英雄虎胆》 《羊城暗哨》等,里面的地下工作者都有着极为相似的特质:智勇双全、意志坚定,无论是性格还是人品,都显得十分完美,而敌人、对手则都是丑恶、凶残或愚蠢的,故事的结尾,代表正义的共产党一方必定战胜邪恶的反动派。此类“高大全”的完人英雄和“神魔对立”的叙事模式在中国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里很常见,这与革命英雄主义传统有关,也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有关。对革命者的拔高和神化,极大凸显了革命者英雄的一面,而他们作为常人的一面,则被遮蔽了。我们看不到他们内心那个丰富的情感世界,也无法窥见他们在革命之外的日常生活,他们仿佛只有革命者这一个身份。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除了革命者,还可能是父亲、儿子、丈夫,他们同样拥有作为常人的喜怒哀乐。
比起这些没有七情六欲,从不为儿女情长所累的圣人、完人式英雄,《身份》里的革命英雄明显接地气多了,比如主人公龚翰文被组织派到上海执行“打狗”任务之前,是工农红军某连连长。比起隐蔽战场的谨小慎微,他更喜欢正面战场的酣畅淋漓,因此当得知自己将要从正面战场转移到隐蔽战场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乐意的,纠结的,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才接受了组织的安排。龚翰文到了上海之后,租住在一户民居里,房东女儿冉墨萱秀气的眉眼让他想起了妻子张秀芳。接下来,作者用大量篇幅写到了他和妻子张秀芳相识、相知、相爱的点点滴滴,写到了他对妻儿的思念、担忧和歉疚。这样的描写很少出现在过往的革命历史类作品中,可正是这些看似闲笔的段落,生动展现出革命工作者的情感世界,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身份》里革命工作者的性格、人品也不像传统革命小说里的那样完美无瑕,他们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如“打狗队”队员刘小光虽聪明机灵,可是性格急躁;董全胜外表憨厚,擅长社交,却缺乏耐性;陈一石本来冷静沉稳,可最后还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为了保护女友不惜供出了“打狗队”成员的住址,害得打狗队几乎全军覆没。此外,《身份》还重点写到一类叛变的革命者,他们也曾有过忠于共产党、报效祖国的理想,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之下,他们最终选择背叛,甚至成为迫害共产党员的得力助手。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华老板,他很早就参加革命,机敏过人、有勇有谋,很快成为党的骨干,担任上海中共特科总负责人。可是,随着官职的不断攀升,他开始飘飘然起来,迷恋起赌博和女人,沉醉于声色犬马中,后终于在一个娱乐场所被国民党抓住。被逮捕后,为了自保和高官厚禄,他主动供出了大量中共联络站和领导人的重要信息,给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身份》之前,很少有革命历史小说对共产党员中的此类叛徒进行如此大篇幅的描写。
在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英雄们不仅智勇双全,能力超群,还总能在危急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化险为夷。比起这些超人一般的革命英雄,《身份》里的革命者显得平凡多了,在执行任务时,他们要认真部署,详细规划,确保每一步都较稳妥后才会开始行动,可就算这样,他们也常常因对方的谨慎和伪装而失败,比如叛徒何家才,住所飘忽不定,也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即便是出门,也必定把自己伪装起来,要么化装成老人,要么戴墨镜礼帽,很难辨认他的相貌。龚翰文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一条他要去一家茶楼看戏的线索。去茶楼刺杀的时候,龚翰文本已摸准何家才所在的包厢,可是没想到他扮成了一个走路颤颤巍巍的白胡子老头,等龚翰文回过神来,何家才早已逃之夭夭。“打狗队”接到暗杀熊国桦的命令之后,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并亲眼见到熊国桦被击毙,却没想到对方是倒地假死。更糟糕的是,身边的战友一旦叛变,就会危及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诸多地下工作者和领导人的生命,在《身份》里,无数地下工作者就是因身边叛徒的出卖而牺牲,包括主人公龚翰文和其领导的“打狗队”。龚翰文和“打狗队”队员本来都十分谨慎,平时将自己伪装成商人、小贩,名字也是假的,互相不知道住处,由一个指定联络人负责联络,联络时用暗语,联络点也设了花盆等日常物件作为提醒物,可由于指定联络人的出卖,“打狗队”成员的住址被一一供出,整个“打狗队”被国民党一网打尽。小说的最后,以龚翰文走向刑场而结束。一些读者可能对这个结局感到不满,因为在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不管过程多么曲折,取得最终胜利的,往往还是代表着正义的共产党一方,比起来,《身份》的结局显得过于残酷。可这样的残酷,在真实的中共地下斗争史上比比皆是。龚翰文和他的“打狗队”队员,都是在战争年代牺牲的无数地下工作者中的一员,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个性和情感,也想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日子;他们没有超能力,遇到问题也会生气、急躁、痛苦、感情用事,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心中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们宁愿牺牲个人的幸福和生命,来换取中国更光明的未来。比起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那些“高大全”的完人式英雄,他们不够完美,可更加真实,小说也因此具备了一种平民化的美学气质。
二、日常化的谍战叙事
如果说正面战场是惊涛骇浪,那么隐蔽战场就是波澜深藏的水面,看似平静,却有无数暗流和漩涡在下面涌动。正面战场拼的是武力、装备、战术,隐蔽战场则更加考验人的智慧、谋略和谨慎。隐蔽战场隐藏于日常、市井之中,看起来岁月静好,实则凶险异常,因此《潜伏》中余则成对翠平说:“我们的敌人是空气,每一个窗户后面都有一双眼睛,每一片树叶后面都有一只耳朵。”所以地下工作者必须学会伪装,在外人眼中,他们是商人,是小贩,是工人,唯独不是革命者。《身份》里,龚翰文初到上海时,化名祁广辉,身穿青蓝长褂,手戴串珠,伪装成一家陈皮店的老板;后来该联络点被叛徒暴露,龚翰文又化名邝惠安,摇身一变为家具店的老板。“打狗队”其他成员也有着各自的营生,董全胜在鱼档卖鱼,张明德和张善峰当杂工,刘小光在陈皮店里当小伙计。平时里,他们行事低调,尽可能把自己隐藏在人群中,但任务来临时,他们就会迅速行动起来,像黑暗里的一柄利剑,直插敌人心脏,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很多以地下工作为题材的作品喜欢着重凸显地下工作凶险的一面,确实,隐蔽战场看似平静,危险却无处不在,无论我方还是敌方,都在竭尽所能伪装自己,联络、策反、杀戮也都在暗中进行,今天的战友,明天可能就变成了敌方的帮凶,稍不小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在隐蔽战场上奋战,犹如在悬崖上走钢索,步步惊心,神经时刻都要绷紧,任何细小的错误都可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诡谋和暴力刑罚,对地下工作者来说毫不陌生,诡谋属智慧的交锋,暴力刑罚刺激人的感官,考验人意志的极限,这因此也成了谍战作品的叙事重点,如麦家小说《风声》,讲述的就是国民党特务科为了找出内奸,把几个有嫌疑的人带到一个别墅软禁,引诱他们互相告密、互相揭发的故事。真假难辨的信息,花样百出的刑罚,诱供和反诱供,对谁是“老鬼”的猜测,都吊足了读者胃口。与这些作品相比,《身份》显得平实许多,虽然主人公龚翰文带领“打狗队”队员执行的大多都是暗杀之类的危险任务,可作者并没有渲染其中的诡谋和暴力,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地下工作者日常的一面。确实,地下工作者并不是时刻都陷于诡谋、暗杀或刑罚中,相反,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扮演人群中的普通人,在敌人看不到的地方静悄悄地蛰伏,积蓄力量;任务来临时,才会带上武器,像黑暗中的利剑一样向敌人刺过去;任务完成后,又戴上“面具”,退回到日常生活。在《身份》中,有大量关于地下工作者日常生活的描写,如龚翰文化名祁广辉开陈皮店的时候,经常有顾客光顾,伪装成老板的龚翰文,常常要接待顾客,回答顾客们关于陈皮的各种问题,如5 年陈皮、10 年陈皮、20 年陈皮的区别,陈皮的药用价值,陈皮入菜的方法等等。陈皮店开张之后,生意很好,可是很久都没接到组织交待的任务,伪装成陈皮店店员的刘小光按捺不住,抱怨道:“俩大活人,天天围着这堆坛坛罐罐转,再这样下去,我看咱俩真成了卖陈皮的了!”龚翰文平静地说:“你以为我喜欢天天坐在这里喝茶看报?我像你一样,恨不能将那些可恶的叛徒一个个除掉,可你别忘了,靠我们一两个人,打不垮国民政府。”[2]51《身份》中的这些场景、对话,不仅给小说赋予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外壳,还还原了地下工作平淡、日常的一面,这一面因为不够惊心动魄,常常被那些以编织惊险情节见长的谍战作品所忽略,却是真实地下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蛰伏在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中,等待组织的命令和任务的到来。
地下工作者是隐蔽战场上的战士,也是生活中的儿子、父亲和丈夫。对于地下工作者的感情生活,一些作品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很多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地下党,似乎只有革命者这一个身份,这一方面与“英雄无性”的传统观念有关,一方面与当时“主题先行”、塑造“高大全”人物形象的写作理念有关。在一些作家眼中,英雄都是大公无私、舍小家为大家的,描写其感情生活会显得其不够理性,不够神圣。上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大众文化的流行,很多作家在以地下工作为题材的作品中加入了言情小说的元素,男主人公不但智勇双全、能力超群,在工作时所向披靡,在情场上也是魅力无边,十分招惹女性喜欢,如当下的一些谍战剧中,编剧常常将谍战人物置于情感的多角关系之中,这样的描写迎合了部分读者的审美心理,可并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实际,因为在隐蔽战场中,面对周围潜在的危险和暗处的敌人,必须理智冷静,伪装好自己,时刻保持警惕,尽可能低调,尤其忌讳感情用事,因为一旦感情用事,就可能给我方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身份》的结尾,“打狗队”全军覆没,正是由联络员陈一石私自和女学生谈恋爱引起的。因此一个训练有素的,合格的地下工作者,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感情。龚翰文和妻子张秀芳青梅竹马,感情甚笃,可因为革命的关系,两人长期处于分离状态,龚翰文来上海时,敌人为了诱捕龚翰文,还把张秀芳关进了广州监狱,本来幸福美满的一家人,被迫天各一方。难忍思念之苦的龚翰文多次想过要把妻儿解救出来,接到自己身边,可鉴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念头一次次冒出来,又一次次被打消。在上海的时候,龚翰文认识了房东女儿,一个追求进步的漂亮女青年,在观察、接触的过程中,房东女儿对他的感情由敬佩慢慢上升到爱慕,这样的情节如果放在有的谍战作品中,很可能被处理成“一男二女”的三角恋模式,可是《身份》没有陷入这样的俗套,无论是龚翰文、张秀芳,还是房东女儿冉墨萱,对待情感的态度都显得理性且克制,虽然冉墨萱在和龚翰文扮演假夫妻期间忍不住向龚翰文表达了爱慕之情,可对待爱情十分忠贞的龚翰文不为所动,而冉墨萱也不是胡搅蛮缠的那种女性,当她得知龚翰文有妻室后就默默退出了。比起一些谍战作品中周旋于几个女人间的情场浪子式人物,龚翰文显得不够风流,可这恰是一名地下工作者必备的素质:冷静,克制,把炽热的情感都深藏心底。
三、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
隐蔽战场看似平静,实际上却危机四伏,处处藏着凶险,地下工作者们都是一群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人。很多谍战作品为了凸显地下工作的凶险,把情节编织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悬念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这样的故事很吸引人眼球,可过快的叙事节奏容易让读者神经紧绷,至始至终都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比起来,《身份》的叙事节奏显得从容舒缓、张弛有度,地下工作者执行任务时的惊心动魄和蛰伏期的日常场景交替出现,既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又缓解了读者的紧张情绪。
《身份》的开头,是几个共产党员被处决的场景,很快,主人公龚翰文就出场了,他的任务是刺杀出卖战友的共产党叛徒、国民党侦缉处处长谢成安,为牺牲在香港的这些地下党员复仇。龚翰文思维缜密,冷静内敛,勇敢过人,先假扮成接头人来到被特务盯梢的裁衣店,在裁衣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伪装成裁衣店老板的叛徒干掉,再设计将老谋深算的谢成安诱骗到一家餐馆,自己则提前潜入酒店,伪装成酒店服务生,趁谢成安独自一人留在房间里时将其击毙,后迅速离开现场。完成这两个任务之后,龚翰文就隐藏起来,沉寂一段时间,等风声过一些了,再开始新的行动。在沉寂期里,龚翰文和“打狗队”队员们认真扮演陈皮店老板、鱼档工人等角色,空闲时候会去海上练枪,学美术的陈一石还会在船上作画;龚翰文和冉墨萱扮演假夫妻时,随时面临被特务盯梢和国民党反动派突击检查的危险,每天都如履薄冰。此外,龚翰文还常常要冒着风险外出执行任务。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之下,人会不自觉绷紧神经,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不过龚翰文和冉墨萱的日子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灰暗压抑,在家呆着的时候,龚翰文会跟冉墨萱学做菜,冉墨萱还给龚翰文织起了围巾,“初冬的早晨,龚翰文像往常一样出门的时候,突然被冉墨萱喊住,她拿起一条深灰色毛线围脖,追到了门口”[2]123。这些温馨安宁的场景穿插在惊心动魄的暗杀行动之间,调节了原本紧张的叙事节奏,也给小说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身份》中的龚翰文和他所率领的“打狗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革命者,他们生逢乱世,对党忠诚,信仰坚定,匍匐在黑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只要组织一声号令,便如出鞘利剑一般展开行动,令敌人闻风丧胆。长夜难明,总有人舍命燃灯,他们就是这漫漫长夜中的“点灯人”。小说中一些情节,如策反、伪装、酷刑、暗杀、“细胞”战术也是隐蔽战场上司空见惯的残酷。这段真实的历史不应该被忘却,龚翰文们的故事值得代代流传,他们肉身虽已消亡,精神却化作天上的星星,永远指引着后人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