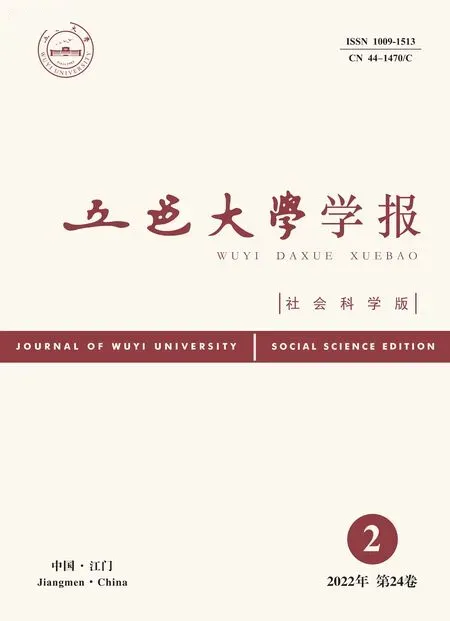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管辖权基础及启示
2022-12-06马铭骏
马铭骏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在传统国际法理念中,出口管制法作为公法,其效力具有严格的属地性。[1]但随着国际经贸交往的深入,公法禁忌被逐渐打破。[2]美国是最早、最频繁地域外适用其出口管制法的国家。在理论界,许多学者都对美国出口管制法的域外适用进行过批判,相关做法也在实践中遭到了许多国家的反对。但随着科技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国立法者逐渐认识到,要想真正发挥单边出口管制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效用,就需要对某些境外行为实施必要的管辖。考察国际法上的管辖权理论与美国的相关实践,是探寻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约束性条件与思考中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制度完善问题的重要进路。
一、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管辖权基础
管辖权是指国家对人、物和事件的管理和支配权。[3]根据“荷花号案”的经典论述,国际法并不必然排斥国内法管辖发生在其境外的行为。①在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实践中,其中一些立法管辖权(或称规范管辖权)[4]基础被国际社会所公认,而另一些则被认为违反国际法。
(一)属人管辖原则
属人管辖原则是指,无论行为发生地是否在一国境内,该国都可以对具有本国国籍的主体的相关行为实施管辖。该原则为出口管制法的域外管辖提供了理论基础。
除了对自然人适用外,各国也会对法人主张以国籍为基础的管辖权。国际法院(ICJ)在“巴塞罗那牵引案”中确认,公司可被视为一国的国民。②从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公司的国籍主要由其注册地、主要营业地或管理中心地等标准来决定。[5][6]
然而,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还基于所谓的“控制理论”将属人管辖约束的对象扩张到了某些由美国公司控制的外国子公司。例如,美国1979 年《出口管理法》(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将 “美国人”的定义扩大到了被美国国内公司所实际控制的外国子公司与分支机构。③但在上世纪80 年代“苏联输气管案”欧共体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在“巴塞罗那牵引案”中确立的认定公司国籍的标准并未将公司股东的国籍作为考量。④因此,在涉及公司或法人行为的情况下,仅仅基于本国母公司在股权上实际控制某一外国子公司就对该外国子公司实施管辖是不被接受的。
(二)属地管辖原则
随着国家主权相对性的逐渐凸显,[7]越来越多的国际实践突破了属地管辖原则的传统理解。第一个层次的突破来自于“客观属地原则”的提出。当犯罪的行为地与结果发生地不在同一国家时,主张结果发生地国家有管辖权即为客观适用,它也逐渐发展成为“客观属地原则”。[8]
此外,“效果原则”的提出为属地管辖原则带来了新的维度。基于效果原则,即使行为发生地与结果发生地都在境外,只要行为对境内产生了某些影响,国家就可以主张管辖权。一些学者认为它已经独立构成了一项管辖权基础。[9]目前,至少在反垄断领域,效果原则逐渐成为了一项被普遍接受的管辖权原则。[10]
但在出口管制领域,效果原则仍然是存在争议的。美国1996 年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就在其条文中直接宣称自身域外效力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即为效果原则。⑤但有学者指出,该法宣称对抗的行动是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政府对一些美国公司和个人财产的征收行为,而该等行为与该法的出台之间有36 年间隔,援引效果原则不具有合理性。[11]由于效果原则存在争议,美国自身也通过《第四次对外关系法重述》中的礼让原则、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等限制基于效果原则主张美国法的域外适用。[12]因此,效果原则可以为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提供管辖权基础,但应当有所限制。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反垄断领域的经验,以是否对出口国有“实质性”或“直接、重大、合理可预见”的影响为标准。
(三)保护管辖原则和普遍管辖原则
根据保护管辖原则,一国可以在其至关重要的利益(安全、独立等)遭到侵害时,合法地对相关外国人的行为行使管辖权。而普遍管辖原则是指,对于那些违反国际法且危害国际社会普遍利益的犯罪行为,无论发生在哪里,所有国家都有权对其进行管辖,但需要遵守“或引渡或起诉”的原则。
保护管辖原则与普遍管辖原则都是在国际法上被广泛接受的管辖权基础,它们同样是出口管制法在域外适用中可资援引的合理管辖权基础。但结合目前的国际实践,主张这两项原则时应当提供一定的证据证明满足相应的条件。例如,援引保护管辖原则时,就应当至少证明相关犯罪行为的存在以及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了何种侵害。模糊地声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并不能合理地主张保护管辖原则。[13]
(四)基于“产品国籍”的管辖权基础
除了航空器、船舶和外空发射物外,在国际法中并没有关于确定物的国籍的规则。[14]由于缺乏国际法上的约束,美国在立法中常以货物或技术来源于美国为由实施管辖。基于物项的来源国主张管辖权实际上是将国籍原则这一管辖权基础扩张适用于货物与技术,在事实上赋予了货物与技术一个无法变更的“产品国籍”。[15]
毫无疑问,基于“产品国籍”的管辖权基础招致许多批判。欧共体在“苏联输气管案”中发表的声明对此作出评论:“产品和技术不具有任何国籍,而且根据国际法,也没有使用了国外的货物或技术就可以对控制它们的人确立管辖权的规则。”⑥有学者指出,即使是在美国法中,国家对于产品的管辖权也并非及于交易流转中的所有阶段,当货物中断了与美国的原有联系,主要变成“外国货物”时,美国应当停止对其管辖。[16]
作为对批评意见的一种回应,美国在《出口管理条例》中引入了“微量允许规则”,从而对含有不超过一定比例“美国成分”的物项实施豁免。但这并没有改变“产品国籍”作为一项管辖权基础的不合理性。一方面,认定外国产品中含有多大比例的“美国成分”有时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技术出口的情况下,如果进口商对来源于美国的技术进行了改进,那么新技术中包含了多大比例来源于美国的技术是难以计算的。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产品中往往包含许多国家的技术与部件,如果这些国家都主张相关产品具有本国“国籍”,进而在产品出口时都以出口管制的理由要求出口商申请许可证,这显然不利于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因此笔者认为,“产品国籍”并非合理的管辖权基础。
二、中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制度存在的问题
2020 年10 月17 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以下简称《出口管制法》)规定了一系列具有域外效力的条款,并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域外适用制度。整体来看,这一制度已经基本具备了国际立法例中常见的规则要素,其中的管制理念、管制方式都是比较现代化的。但是,相关规则仍然存在概念模糊、制度缺失等有待完善之处。
首先,《出口管制法》对受管辖主体的界定不够明确,这主要体现在对“境内主体”或“境外主体”的定义不明。虽然《出口管制法》明确其管辖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但考虑到该条文在适用条件上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与“妨碍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的限制,《出口管制法》适用于境内主体与境外主体的条件也是有差异的。例如,虽然中国公司法中规定了“外国公司”的概念,⑦但某一管理中心地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是否属于《出口管制法》中的“境外组织”却缺乏判断标准。
其次,《出口管制法》对管制物项范围的规定也尚不清晰。从种类上看,《出口管制法》中“管制物项”定义的覆盖范围已经较为全面,但该法并没有明确当管制物项被进口商加以加工、合并、改造、改进或生产等行为后,是否依然受其管辖。从表面上看,如果排除此类物项的管辖,《出口管制法》将很容易被规避,从而无法实现立法目的。那么,是否需要仿照美国设置“微量允许规则”,从而将含有一定比例“中国成分”的外国产品纳入《出口管制法》的管辖呢?相关规则的取舍和具体设计必然是未来立法中的难点。
再次,《出口管制法》缺少对再出口行为的定 义,从而导致受管辖行为的范围不明确。对于再出口的含义,至少可能存在两点争议:第一,再出口是否包括外国主体的“视同再出口”行为?第二,再出口所管辖的物项是否适用“微量允许规则”?此外,《出口管制法》也并未明确是否管辖所有对于管制物项的再出口行为,以及对于再出口行为的管辖是否需要具备某些条件。
最后,《出口管制法》并没有规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排除自身管辖权的豁免条款。欧盟在其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中规定,对以转移“公共领域”或“基础科学研究”的信息为形式的技术协助不予管辖;同时,如果相关技术协助只为满足安装、操作、维护已被批准许可出口的管制物项的最低需要,也不受条例管辖。⑧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同样设置了十余项许可例外规则。⑨从国际经验上看,对《出口管制法》的域外适用设置某些豁免条款是十分必要的,相关规则的缺失可能加剧《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带来的管辖权冲突。
三、管辖权理论对完善《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制度的启示
《出口管制法》的域外适用制度只有建立在坚实的管辖权基础之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用,并减少国际冲突的发生。笔者认为,国际法的管辖权理论为《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关于受管辖主体的判定
“境外主体”范围的判定关乎《出口管制法》基于属人管辖原则可实施的范围。这一判断的难点在于法人方面,亦即《出口管制法》第44 条“境外组织”的范围问题。中国公司法实际上已经确立了中国公司国籍的判断标准为注册地主义,因此“境内组织”也至少应当包括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公司。然而,在国际法上广泛接受的公司国籍判断标准除了注册地之外,还包括管理中心地与主要营业地。笔者认为,《出口管制法》中“境内主体”的范围可以扩大到管理中心地或主要营业地在中国境内的公司。这样的解释在最大限度发挥《出口管制法》效力的同时,也并不违背国际法的相关理论与规则。但是,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国际实践也证明,“控制理论”是非常有争议的。因此,《出口管制法》的“境内主体”不应包括中国公司所控制或实际控制的外国公司。
(二)关于管制物项范围的确定
笔者认为,在《出口管制法》的实施中不宜引入“微量允许规则”,否则难免会将一些与中国并没有实质联系的交易纳入管辖。在相关的管辖权理论中,只有所谓的“产品国籍”理论可以解释此类管辖的逻辑。但是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基于这一理论主张管辖权是不具有合理性且违反国际 法的。
那么,如果不将含有一定比例“中国成分”的物项列入管制物项的范畴,是否会纵容交易主体规避《出口管制法》呢?笔者认为,对于此类情况,并非只有引入“微量允许规则”才能解决。目前《出口管制法》中关于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制度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此类问题。管制物项的最终用户被要求承诺不得改变最终用途,因此最终用户对于管制物项进行的加工、改造等行为就很可能违反承诺,从而受到《出口管制法》相应的处罚,并不会出现“切断联系”的情况。
(三)关于再出口行为的管辖
笔者认为,对于外国主体再出口管制物项行为的管辖,应当限制在效果原则、保护管辖原则与普遍管辖原则所允许的范围内,理由如下:
首先,再出口是发生在境外的行为,它会受到行为发生地国家的属地管辖。如果对于所有的再出口行为都进行管辖,这将极大增加中国与他国发生管辖权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再出口行为的管辖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仅在满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实施管辖。
其次,由于“产品国籍”并非合理的管辖权基础,那么对于再出口行为的管辖就只能在其他几类管辖权基础中寻找依据。对于管辖再出口行为而言,效果原则、保护管辖原则与普遍管辖原则是较为合理的管辖权基础。因此,管辖再出口行为的条件也应当与主张这几类管辖权基础的条件相一致。
最后,由于《出口管制法》的域外执法难度更大、耗费的资源也更多,排除掉那些虽然涉及管制物项,但对中国并无实质影响的再出口行为的管辖,也有利于节约执法成本,从而将更多的执法资源集中到更有必要管辖的行为上。
(四)关于豁免条款的设置
从管辖权基础的视角看,豁免条款是法律对于自身域外适用范围的自我限制。基于合理性考量,立法者将一部分域外管辖的情况予以排除,也体现了审慎的态度。
以再出口的规则为例,设置豁免条款可以排除掉《出口管制法》某些明显缺乏合理性的管辖。比如,进口商在获得来自中国的管制技术后,向其公司的外籍员工公开管制技术的行为,在构成要件上就有可能成为《出口管制法》所管辖的再出口行为(或称“视同再出口”)。然而如果对于这类行为一律要求向中国申请许可,或是对其进行处罚,必然会遭到进口国的反对,因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进口国公司正常业务的开展。关于这一问题,国外的立法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参考的。比如,根据美国《出口管理条例》,如果外籍员工是“长期“且“正式”的雇员,且满足一定的身份和国籍条件,那么上述行为就不会受到管制。⑩此类规定涉及到管辖再出口行为的具体操作细节,相关的规定还需要执法部门在实践中逐步细化。但对于那些可能造成管辖权冲突的规则,应当尽快予以明确,从而为执法部门提供明确的指引,并减少国际摩擦发生的机会。
四、结 语
在实践中,国际社会一般会根据是否具备合理、公认的管辖权基础来正当化或批判国内法域外适用的现象。中国《出口管制法》的出台正值美国借助其出口管制法强力打压中国企业之际,因此该法的域外适用制度不但是中国法律域外适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对外政策的角度说,它更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保护中国企业和个人合法权益的制度工具。《出口管制法》的域外适用制度不仅需要进一步细化以满足实践的需要,同时也应当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地检视,从而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尊重他国主权、缓解管辖权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17]从更为长远的视角看,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美好愿景,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注释:
① See Lotus Case, PCIJ Series A, No. 10, pp. 18-19.
②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Belg. v. Spain) , 1970, ICJ, 70.
③ See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 Sec. 16(2).
④ European Community, Note and Comments on the Amendments of 22 June 1982 to 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Presen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n 12 August 1982, pp. 5-6.
⑤ See 22 US Code, 6081 (9).
⑥ European Community, Note and Comments on the Amendments of 22 June 1982 to 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Presen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n 12 August 1982, pp. 6-7.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1 条:“本法所称外国公司是指依照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设立的公司”。
⑧ See Regulation (EU) 2021/82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May 2021, Art. 8.3(b)(f)
⑨ See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15 CFR 740.
⑩ See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15 CFR 73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