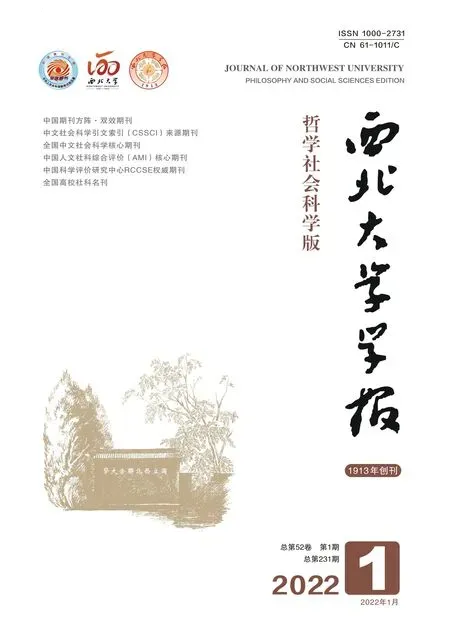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2022-12-06黄朴民郭相宜
黄朴民,郭相宜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2)
一、“夷夏东西说”与中国上古历史的解读
自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以来[1]1-46,从东西部族互动考究中华文明起源,诸如政治格局的变化、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文化价值观念的交合与互补等问题,成为学术界认知和解读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换言之,一部中国上古史,正是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东西两大区域及其相关势力之间长期对峙冲突并不断同化融合的文明进程[2]。
今人将秦朝建立以前先后更递的历史称作夏、商、周“三代”,但是在先秦两汉人们的心目中,夏朝之前的虞舜时期,也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特殊朝代,即有虞、夏、商、周“四代”:“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3]67-68又如《新唐书·啖助传》载啖助之言:“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弊!’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4]5706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很显然,四代如傅斯年所言,虞和殷商为一组,代表东方夷族势力,而夏与周又为一组,代表西部夏族势力。
夏朝时期,东部势力受压制。但东部势力的屈服与顺从只是暂时的,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仍然要与西部势力角逐,以控制中原核心地带。这一历史进程由商族完成。商的先祖以鸟为图腾,《诗经·商颂·玄鸟》有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5]1342,这显然与东夷有一定的关系。众所周知,鸟为夷(华)部落的图腾,少昊氏的后裔郯子曾向孔子讲述过该部落联盟图腾由来与官制的详细情况:“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5]4524商族以“玄鸟”为图腾,当亦属同一性质。关于商族的发祥地,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是辽东说、华北说,还是山东起源说、江苏北部说,都处于中原大地偏东的位置,说明商族主要活动于东方。相传其第三世先公相土作“东都”,故《诗经·商颂·长发》言“相土烈烈,海外有截”[5]1350。商汤时“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5]5897,最终战胜桀,灭亡夏朝,建立商朝,这表明东方势力再次在东西部战略角逐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时易世变,到西部的“小邦周”在甲子朝奏捷牧野,一举“殪戎殷”、推翻“大邑商”之后,华夏大地上东西部的政治格局又被重新改写了。西部力量又成为中原地区的主宰,东部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西部胜利者成了“国人”,以“君子”身份治理天下,而东部的民众与族群作为失败者、被征服者,成为所谓的“野人”,不得不臣服于西部势力。这恰如傅斯年所说:“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人民是殷人。”其实,此说法可适用于东土的全部。孔子尝言:“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5]5426其中隐隐约约地透露了这种东西部关系更替、势力消长的信息。
在这场东西部势力大角逐、大博弈的过程中,代表西部势力的周族在战略运筹方面可圈可点,其中的策略之一便是设法在殷商的侧后开辟战线,让殷商王朝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暗中煽动东夷某些部族发动叛乱,让商室在平叛过程中消耗实力,大伤元气,“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5]4419等。由于史料缺乏,这一点我们只能做合乎逻辑的推测。在周人来看,灭商大局更为重要的是较早开始对东南一带的经营,换言之,周族对东南吴地的经营,可以视为其灭商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步骤之一。史称泰伯、虞仲兄弟在周室权力继承问题上主动谦让,“以让季历”[6]149,遂栉风沐雨,远奔吴地。虽然听起来是兄弟相互成全的温馨历史场景,但这或许是后世儒学伦理道德化重构古史系统的产物。泰伯兄弟奔吴背后真实的动因,当是周族将势力锲入商人的后方,以实现周邦翦灭殷商的迂回包抄战略[7]219。故徐中舒论断:“余疑太伯、仲雍之适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端。”又曰:“周人自大王居岐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之国策。”[8]
二、周公东征背后的东西对峙因素
既然东西部势力的对峙冲突及其同化融合是了解和把握先秦政治格局演进的关键,那么它无疑也是我们探讨周初政治形势发展与周初统治者诸多战略部署动机的重要切入点。东西政治势力冲突的客观存在,能够帮助今人理解为何在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又爆发武庚叛乱和大规模东夷反周起事。
武王伐纣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军事上的一次征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被征服地区的政治结构与社会文化基因。毕竟“小邦周”无法在短暂时间内平定“大邑商”的东方地区。所以,除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推行初步的分封制、进行武装殖民之外,周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实,遵循传统的做法,将纣王之子武庚立于商王畿邶地为监,“俾守商祀”[9]544,世守商王的宗庙社稷和治理当地的殷民。伐纣成功后,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依然偏居西方,对黄河中下游、古济水流域和淮河中上游乃至江汉地区,都无法直接加以控制,这些地区实际上仍是在东部势力的继续掌控之下。当然,周武王对此非常警惕,他深知东西部势力之间的对峙与冲突属于结构性矛盾,故不敢放任武庚。为防备武庚,周武王派出管叔、蔡叔和霍叔,屯驻于故殷之地,监视控制武庚的动向,史称“三监”。
灭商后仅两年,武王便因积劳成疾而撒手人寰。继位的成王尚未成年,身在宗周的周公旦摄政,代行王权。因此周王室内部波诡云谲。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早已不在人世,武王为次子,管叔是三子,周公是四子,在武王去世后,管叔自认为地位甚高,应在中枢执政或至少也该与周公共同摄政。可是,因他和蔡叔等远在殷地为监,在周室内部的权力重新分配中完全被边缘化。因此管叔联合众人以替成王争王权为名,诋毁周公,“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10]33。战败的东部势力乘虚而入,“管、蔡启商,惎间王室”[10]611。那些不甘心被征服的殷商残余和其同盟者东夷诸方国,认为这是让东部势力重新崛起,再次成为天下主宰的绝佳机会,于是积极行动,以求一逞。
长期追随殷商王朝的奄和薄姑积极向武庚献计献策:“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11]236-237武庚正处心积虑地想夺回失去的王朝,重振东部势力,对奄君等人的说辞当然深表认同,遂游说管、蔡,争取他们一起兴兵犯阙。而管、蔡等人亦利令智昏,居然不顾周室的根本利益,决定与武庚等合作,共同举事。双方互相利用,决定发动反周叛乱。
叛乱一起,东方势力纷纷起兵策应、配合武庚和三监的行动,“徐、奄及熊、盈以略(畔)”[9]548“三监及淮夷叛”[10]597“淮夷、徐戎并兴”[10]511,大抵可见当时的局面。东夷诸方国之所以对三监与武庚之乱闻风而动,景从响应,从本质上看是因为他们和武庚都属于东部势力集团,仇恨以周人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东进和控制。所以,这场动乱对管叔、蔡叔而言是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对武庚和诸多东夷方国来说,则是东西部势力的对抗与较量,是牧野之战的延续。尽管性质不同,目的有异,但是在针对周公为主导的周王室这一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交集,所以双方暂时结成统一战线,一致以周公为敌。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叛乱,在宗周朝廷主政的周公没有退缩与妥协,而是以强硬的手段坚决应对。他先是作《君奭》,劝说召公支持平叛,又作《大诰》申明武力平叛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进行战前动员。在统一认识,实现内部团结,激发起从上到下同仇敌忾之气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作战准备。一切就绪后,周公遂率大军东进平叛,史称“周公东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第二次灭商战争。
周公东征进展顺利。周军率先进攻武庚封地邶,武庚的军队很快被击溃,“殷大震溃”,迫使“王子禄父北奔”[9]552。部分周军在召公的指挥下乘胜追击,不久将武庚残部彻底歼灭。与此同时,周公统率周军主力直捣管叔驻地鄘,一举而下,诛杀管叔。周军转而又将兵锋指向蔡叔驻地,将其生擒,囚禁废锢。与叛乱活动牵涉不多的霍叔,也未能逃脱惩罚。至此,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周公非常清楚,这场大叛乱除了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外,更是东西部两大集团之间的政治主导权和势力范围之博弈。所以,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当借此平叛的良机彻底解决东部藉以抗衡西部的要害问题,摧毁东部的抵抗力量,毕其功于一役。于是,周军全面展开了对参与三监、武庚之乱的东夷大小方国的征伐,血腥镇压。自此,东征之役进入了更为残酷、更为激烈的第二个阶段。
周族大军浩浩荡荡向东挺进,率先指向鲁北的薄姑国,通过残酷的厮杀,薄姑国被周军攻陷,金文记载:“唯周公于征东夷,丰伯、薄姑咸。”[12]1409咸,意为全部,,是斩杀的意思。这表明此役激烈血腥,薄姑国的统治者与广大民众被屠戮殆尽,所谓不嗜杀人的仁义之师,只是后世儒家的理想化想象与虚构而已;“血流漂杵”才是上古战争的常态与真相。《汉书·艺文志》所称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13]1762,其实只是后世儒者的凭空想象而已。
屠灭薄姑之后,周公挥师南下,长驱直入,势不可当。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周公采纳辛公甲所建议的作战方略,“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14]180。周师先攻地处鲁南和泗水以北的众多东夷小国“九夷”,以孤立最强之敌商奄。周师的进展还是相当迅速的,很快就平定了“九夷”:“凡所征熊、盈(嬴)十有七国,俘维九邑。”[9]552
至此,周军也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敌手奄国了,亦是整个东征之役中最艰巨的战役。奄,其都城所在地,正是商王南庚、阳甲的旧都,故史称“商奄”。该地民众与商人有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国势又是东夷诸国中最为强盛的。所以面对周军的大举进攻,奄国上下进行了殊死抵抗,“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15]128。这里的“商人”其实就是商奄人。这场鏖战,让周军与奄国人都伤亡惨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诗经·豳风·破斧》一诗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周公东征之役的激烈程度。最后,周军经过极其惨烈的苦战击败了奄人,赢得了胜利,实现了所谓“践奄”的战略目标。
“践奄”的残酷程度,较之于征服薄姑与“九夷”,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践”字充分体现了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5]850也就是说,不仅奄国当地的青壮男子被残杀,其老弱妇孺也沦为奴隶,宫室彻底毁坏,再在原址上挖一个大池塘,从地面上完全铲除象征东夷方国存在的标志物。
周军在整个东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残忍与暴虐,其实也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反抗予以无情的镇压。换言之,正是因为夷夏东西的客观存在与长期对峙,才酿成这场几乎颠覆周族统治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同样的道理,为了彻底解决东部势力的死灰复燃与卷土重来,周公不得不全力以赴加以镇压,不但要摧毁东部势力赖以抗衡的物质基础,而且更需要在精神意志的层面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完全摧毁其反抗的心理,彻底屈服,最终顺从于周族统治。
普鲁士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其《战争论》中指出:“在战斗的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因此,使敌人精神力量遭受损失也是摧毁敌人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16]245法国军事理论家安德烈·博福尔(Andre Beaufre)也说:“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首先创造,继后利用一种情况使敌人的精神大大崩溃,足以使它接受我们想要强加于它的条件。”[17]8可见,当年周公“咸”薄姑、残酷“践奄”的动机和做法,或许也是出于类似考量。而他之所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残酷镇压,这也许是因为他代表西部势力,视殷民与其附庸东夷方国为“异类”。这样的政治作为,能够证实傅斯年所主张的“夷夏东西说”。
三、周初的分封布局与洛邑经营所显示的东西对峙态势
周公制礼作乐成为中国古典文明全面兴盛的标志性事件,后人习惯于将这种文化气象与文明的核心内涵及相关表现形式,概括地称之为“礼乐文明”。
从制度建设层面来看,西周礼乐文明体现为经济上生产经营模式的井田制、社会管理模式上区别并规范征服族与被征服族各自权利与义务的“国野制”、处理和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关系与权力分配的宗法制以及整个国家机器从事治理天下基本模式的“分封制”。这四个基本制度支撑起西周礼乐文明体系。
所谓分封,就是周天子根据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对自己的子弟、亲戚、功臣和古代王族后裔,授予一定范围的土地和子民,以拱卫周王室,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种统治据点,就是“封国”,众多的封国就是“诸侯”。诸侯受封时,要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由周天子委派专门机构的官员,代表周天子向受封侯颁布“册命”,其主要内容就是“授民授疆土”,同时授予受封者官属、奴隶、车旗、命服、仪仗等象征诸侯等级的标志物。受封的诸侯,则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交纳贡赋、朝聘述职、参与祭祀等义务。
西周的大分封,先后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5]4601。第二次大分封,是在周公东征平定武庚、管蔡之乱以后,这次也许更为重要。康王之后,周王室仍陆续有所分封,但规模和数量皆不能与周初相比。
周初大分封的对象,主要有四类。一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此类封国数量最多,又集中于文王、武王及周公的后裔,“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鄷、郇,文之昭也。于、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5]3944。二是异姓的功臣谋士,如封姜尚于营丘,国号齐。三是殷商之后,先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后又封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四是前代帝王之后,如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四类中,第一类与第二类是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天然的第一类“兄弟之国”,便是通过缔结婚姻的方式,形成所谓的第二类“甥舅之国”,以起到“股肱周室”[5]3954的作用。
分封的目的是“夹辅王室”“以藩屏周”,但相关分封内容中蕴涵武王、周公等人的心机深沉、他们通过分封要实现的战略考量与战略目标,则需予以关注。稍加留意即会发现,武王、周公的谋略似一盘大棋,而整个棋盘上他们的每个投子、每个谋势,都以西制东,防止东部势力再度崛起为原则。理解这一点,则需关注周初政权中核心人物的封国地点。众所周知,西周开国以及随后在周初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以及康叔等人。为了应对东部势力的抵制与反抗,他们受封的地点,无一不在东方区域、即原先殷商王朝与其同盟者的根据地,以便就近监督与控制东部势力,从而紧紧扣住了东部势力的命脉,使殷商及其同盟者无法破坏天下稳定之大局。
鲁国,为周公的封国,建于东夷大国奄的故地之上,可见它立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镇抚东方的战略部署中发挥核心作用。由于周公本人在朝廷摄政,遂由“伯禽代就封于鲁”[6]1836。伯禽就封后,所有的做法,包括治国理念的确立、治国方略的推行,皆遵循了周公的教导,可谓中规中矩。其中,防范和打击东夷残余势力,也是伯禽及其继承者致力于践行的职责之所在。为此,伯禽等人积极主动反击徐戎与淮夷的侵扰,并将敌人赶到淮河下游地区,从而实现了“大启尔宇,为周室辅”[5]1328的战略目标。这正是周室分封鲁国的一个重要初衷。显而易见,周公受封鲁国和占有商奄故地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都带有一定的东西大对峙色彩。
召公,是武王宾天后周室新政治理格局中仅次于周公的政治人物。即使周公也无法独断专行,制定战略与规划必须首先获得召公的首肯与支持,东征之举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他和周公旦、太公望同为武王灭商的功臣,成王时又是协助周公平定“三监之乱”的副手。依常理,他的分封之地应该是位于交通发达、土地肥沃、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中原核心地带或王畿周围。可事实上召公却被赐封在遥远而苦寒的燕地。金文载:“召公建匽。”[12]2556东征结束后,召公返回宗周佐助成王,“以元子就封”[6]1875。此说在克盉等铭文中得到证实,它们明确记载,燕国的受封人为召公奭,而就封者是其子克,“令克侯于匽(燕)”。功高德劭的召公之所以被册封在东北一隅,显然同样是出于对压制东部势力的考量,它南有北国原(原殷商与国,今河北易县),东有孤竹(今河北迁安、卢龙一带),北有蓟,越燕山而东可与肃慎发生瓜葛,军事和政治地位十分重要,孤竹等方国与殷商关系较近,也属东部势力集团。如果放松警惕,一旦它们与东夷及殷商残余势力联合,势必对周室的统治造成重大威胁,所以有必要将重臣分封在这里,控制局势,维系安宁。
太公望姜尚,是最重要的异姓功臣,在武王伐纣灭商和周公东征时,功勋卓著,“后世言兵及周之阴权者,皆宗太公为本谋”[6]1791。后世多认同司马迁的看法,如《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言:“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18]19-20缘此,太公在武王时被赐封于齐,并被授予“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5]1351的征伐大权和辅弼王朝的使命,其征伐范围“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5]3891。周室的战略意图很明显,有太公坐镇齐地,镇抚薄姑、莱人,南可得鲁国之策应,北可恃强燕之奥援,即可无惧东方集团的势力寻衅滋事。即使变生腋下,事起仓促,也无需惊慌失措,因为有齐、鲁、燕携手应对。所以,太公望受封于齐,亦是从东西势力之间对峙的大局出发运筹帷幄的产物,要真正起到“夹辅周室”[5]3891的作用。
除了上述周公、召公、太公之外,周室的其他重要人物,大多也被分封到东方一带,共同致力于防范和镇压东部势力的反扑。如武王少弟康叔,在平“三监之乱”中立有大功,故受封于殷墟,封建卫国,都于朝歌(今河南淇县),镇守殷王畿故地,治理殷遗民七族。康叔兢兢业业,统领封在豫北和冀南的邢、凡、胙、祭、原、雍等姬姓诸侯和其他异姓诸侯,确保了周室东土的安全,实现了周公的战略目标。又如,蔡国本为武王之弟蔡叔度的封地,都于蔡。因参与叛乱而被囚禁,其国一度被废,但其子胡与乃父行事完全不同,能“率德训善”,故不久就被复封于蔡。蔡国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它立国于淮河支流汝河之东,是淮河中上游诸姬中的大国,对于防范东部势力,控制该地局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由此可见,周初大分封过程中的具体布局,都是依据东西势力双方角逐较量这个根本问题而展开的,这是认识周初政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同样,周公经营成周的战略动机与相关做法,也应该置放在东西势力竞逐无已、纷争不休的历史演进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周公东征,历尽千辛万苦,虽然凯旋奏捷,但是叛乱让周公等人从因伐纣灭商的胜利耽溺中清醒了过来,对“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道理有了切身的感受,知晓了“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19]282的昭示。其知悉以“小邦周”完成对“大邑商”的治理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更何况殷商作为东部势力的代表者,还有广大东夷集团的支持。这中间缘由很多,但从战略地理来考究,因为宗周的位置过于偏西,对军事防御体系的完善有很严重的弊端,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5]4096,一旦东部势力卷土重来,宗周应对就会比较迟钝,容易错失战机,不便及时制止动乱,控制形势。当务之急,就是要做好东西势力长期胶着于博弈状态的准备,果断地调整周室的军事部署,将战略前沿基地东移,将军事防御建立在东西部势力博弈的第一线。
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几点是必须考虑并事先做出安排的:一是权力结构要有所调整,职责划分要合理区隔和明确。周公固然强悍能干,但事务过重,一人难以完全承载。于是与召公分别承担起治理王朝东、西部两地的重任。东部问题多、难度高,由周公来处置,则“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而东,周公主之”[6]1875。二是掌控东方局势的战略中心点需要有地理上的形胜之利,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地位。洛邑自然成为这个军事战略前进基地的首选。洛邑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东西交通的要冲,地势易守难攻,东有成皋之固,西有崤函之险,“背水向雒,其固亦足恃”[13]2032。且有经济方面的优势和便利,“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6]170。由此观之,洛邑适宜周人的战略考量与日常所需。
由于清晰地意识到镇抚东方的迫切需求,又看到了成周的特殊地理优势,周公辅政后,便以其为政治与军事重心来治理东方。东征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和召公通力合作,全面规划与营建成周,仅短短一年,成周便初具规模,最终成为一座牢固的城池。至此,西周朝廷终于分别建立起以丰镐和成周为中心的战略防御体系,两大中心东西相望,互为表里。归根结底,这种战略布局也是东西势力角逐竞雄的现实形势与战略条件下的自然结果。因为从相关史料记载来看,成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一是周室军事力量的大部分部署在成周,宗周为六师兵力,称“西六师”,而成周拥有八师兵力,号称“成周八师”,也称“殷八师”。甚至有学者认为,殷八师与成周八师是两支部队,那么成周拥有十六师兵力,更是占据绝对优势[20]。二是周室的重大军事行动往往从成周出征,周王渐渐习惯于在此处理朝政,接见诸侯,颁布政令。三是洛邑同时成为手工制作与生产基地,大面积铸铜遗址的发现,或标有“新邑”“成周”铭文铜器的出土,显示出成周在当时已是手工业发达,经济逐渐繁荣的大都会,是西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向东拓展与交流的中心,功能上已渐渐超越宗周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东西势力博弈下的产物,是周人为了全方位压倒东部势力的策略。笔者推想,其首先是依托成周为了战略上就近掌控、力量上完全压制;其次是为了展示新生王朝对殷商王朝的全方位超越,在精神上击溃对手。
四、余 论
周初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与发展,其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势力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这种情况早在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时便已存在,上古数千年未发生本质改变。但是在指出这种对峙状况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另一方面,即在对峙过程中夷与夏、东与西的畛域在不断淡化,这样才有夷(华)夏的融为一体。此现象在卫康叔的做法上就有鲜明体现,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5]4636,既尊重殷人的文化与风俗习惯,又以周室的法规制度实施管理,从而较快地得到殷民的理解与顺从。卫康叔在殷墟“能和集其民,民大说”[6]1924。亡国之民至于“大说”,此说法大略可认为系卫康叔夸大之词,不可偏信。但是,殷商故土一带矛盾相对缓和,周之征服者与殷商之遗民彼此之间大体相安无事,也许比较接近事实。
司马迁曾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6]836“夷夏东西说”或许与此论断密不可分。先秦的王朝兴衰存亡,往往与东西平衡的战略举措上左支右绌、顾此失彼相关联。商纣过度经营东方,导致殷商西部防御的空虚,给周族趁机东进提供了机遇,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5]4473。西周的兴衰成败,同样与此有关。周公等人锐意致力于防范和镇抚东方,如在分封问题上,过分强调殷商王畿及其周围殷商与国的战略地位,把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大国都安排在东方和东北方,驻兵守土。这固然防止了殷商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然而却严重疏忽了对王畿西部等地区的防范。具体来说,王畿西部几乎都是异姓公侯处于守边的第一线,而二线的姬姓侯伯实力单薄。周初几代国君凭借文、武的余威,尚可勉强保住西土的安宁。共、懿之后,戎族急剧崛起,势力膨胀,对周室构成严重的威胁。可此时周室仍然局囿于东西势力竞逐的视野,以抗衡东部势力为战略导向,因此在西线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弥补措施,造成戎族多次突破周室的西部防线抵达渭河中游地区,甚至逼近镐京附近。这种困境,周室无法打破,到了西周晚期更是彻底失控,王室两大集团军“西六师”与“成周八师”东西两线作战,疲于奔命,其结果即是犬戎长驱直入、宗周失陷,王室不得不仓皇东迁洛邑。
两汉之后,随着北方地区游牧民族的蓬勃兴起并南下侵扰,引发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两大文明圈的冲突与对撞。为了维系各自的生存空间与生产生活方式,两大文明圈之间无止无休地进行较量。与此相关联,中国古代军事斗争的战略轴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东西的角逐演变为南与北的竞雄。但即便是南北之争,东与西的对峙与冲突的影子也始终相伴随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王朝的兴起与强盛,取决于统治者能否在东与西的战略部署与应对上保持适当平衡、维系相对均势。而王朝的中衰或崩溃,则通常是因为这种脆弱的均势被打破,导致统治者顾此失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后者是常态而前者往往属于特殊。如隋炀帝,应该说经营西域还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在应对东部问题上明显力不从心,数次征伐高丽都惨遭失败,最终导致隋王朝土崩瓦解。明朝的覆灭,也是陷入东西两个方向同时面临危机的结果,既要对付东北女真族的军事威胁,又要防范发韧于陕西的农民军进攻,首尾无法兼顾。再如晚清,也是东西防线都岌岌可危,因资源有限不能从容应对,故有李鸿章“海防”与左宗棠“塞防”之间的重大争议。因此,瑞士军事学家约米尼(Antoine-Henri,baron Jomini)才强调:“必须尽量避免两线作战的战争,而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战争,则最好先对邻国中的一个敌国采取克制忍辱态度,到适当时机再报仇雪耻。”[21]56因而,从长时段考察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嬗递,能够发现东与西的对峙与历史的进程如影相随,这也能够为解释诸多相关历史现象提供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