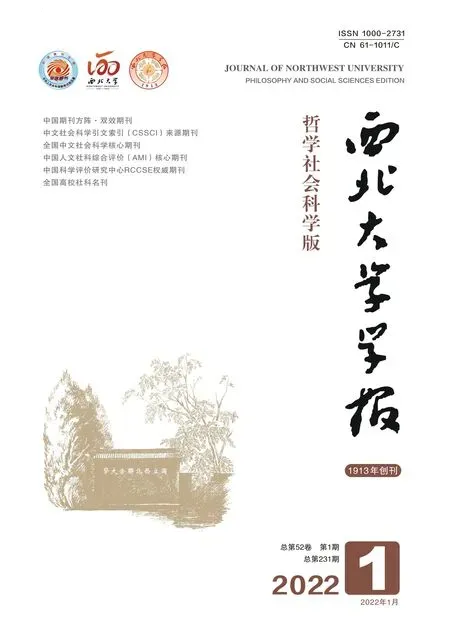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论
2022-12-06李芳民
李芳民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杜甫是一位具有远大政治理想的诗人,其理想概括言之,一是他《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云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再则是后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所谓之“窃比稷与契”。两者实则是统一的,“致君尧舜”是其努力的目标,“自比稷契”则是对自我之期许。相较而言,前者的影响更大,学界亦多所讨论(1)其中较为重要者如吴淑玲的《致君尧舜:杜甫终身不渝的政治理想》(《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陈昌渠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儒家政治理念解读》(《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邓芳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试论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的文儒思想及其文学影响》(《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胡永杰的《开元盛世与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3期)、杜晓勤的《杜甫的政治悲剧及其文化史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等。。本文拟在前此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杜甫这一政治理想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揭示其文化语境,并分析杜甫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作为以及与他仕宦遭际之间的关联,阐释其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一、杜甫“致君尧舜”理想生成的语境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记忆中,上古的有虞氏被认为是社会治理的理想时代,次则是夏、商、周三代。就帝王而言,则以有虞氏的唐尧、虞舜为圣君之典范,夏禹、商汤与周之文、武二王次之。这一认知,经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的形塑,至战国时期已基本定型。孔子在政治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对他上古四代的评价则有差别。他称道尧、舜的时代为“大同”,禹、汤、文、武、成王之时代为“小康”(2)参见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中册,第582至583页。。在他看来,失去淳朴之风的夏、商、周三代,比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唐尧虞舜时代已差了一个层次。由此,孔子所推尊之上古君王,也就常以尧、舜为圣君之最(因舜传禹,故有时禹亦顺带而及)。《论语》中孔子言及尧、舜,常常赞美有加,如赞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感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1]83。孔子的赞美,不仅使唐尧虞舜时代成为后世的盛世记忆,也使尧、舜作为贤君明主而成为历代君王学习的楷模。
唐王朝建立后,特别是太宗时代,施行何种治国理念,达致怎样的社会治理目标,曾是当时君臣间热烈讨论的话题。面对前代之经验教训,是效法上古之崇尚德治教化,还是取则秦汉之尚霸道任法,贞观君臣间曾有过讨论与分歧。《贞观政要》曾载:
贞观七年,太宗与祕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懿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淳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懿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2]17-18
太宗最后接受了魏征的意见,“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他因此自豪地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2]18
崇尚德治,奉行以教化为本,则尧、舜就自然成为君王仿效的楷则。整个贞观之世,尧、舜及其德治教化思想,几成为当时君臣的中心话语。李世民曾屡次称道尧、舜,表达仰慕之情。其《求直言手诏》称:“朕闻尧舜之君,自愚而益智,桀纣之主,独智以添愚,故异顺逆于忠言,则殊荣辱于帝道。”[3]37在对诸王子谈话时,则还以梦事表现了其对尧舜的寤寐之思:“比尝梦中见一人云虞舜,我不觉竦然敬异,岂不为仰其德也!向若梦见桀、纣,必应斫之。”[2]128君以尧、舜自期,臣也就常以之作为诫勉之标杆。贞观后期,李世民渐生骄逸之心,魏征之谏诤即多以尧舜之道下针砭。其《十渐疏》言李世民之渐尚奢纵,失其初心,即责之以有违尧、舜之道,谓“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而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淳朴之理,渐不克终”;又言其“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返朴还淳。顷年已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3]624。太宗得奏,虚心纳之,并赐以黄金及厩马,且予以高度赞扬。
贞观君臣在对前代政治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往古历史的追溯中,形成了以尧、舜为君王楷模的认知。而由于贞观政治的巨大影响,太宗之后,唐之历代君王也就形成了几相近似的“尧舜意识”,追慕远古,效法尧舜,并因此达致风俗淳朴、天下清平,就成了唐代君王共同的治理理想(3)如高宗《禁留狱诏》:“……如闻率土州县,留狱尚繁,困于囚系,致于病死,一岁之中,数盈二百。盖繇上愆亭育之化,下乖尧舜之心,深责在躬,兴言多愧。”(《全唐文》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以下注凡同出此书者,出版社省略。)玄宗《报裴漼等请封禅手诏》谓:“朕承奉丕业,十有余年,德未加于百姓,化未覃于四海,将何以拟洪烈于先帝,报成功于上元。至若尧舜禹汤之茂躅,轩后周文之懿范,非朕之能逮也。”(《全唐文》卷二九,第1册,第140页)又《答裴光庭诏》:“……既内平而外成,且刑清而讼息,端拱多暇,留意典坟,以为道者玄妙之宗,德为教化之本,讲讽微旨,稽详秘文,庶无为而政成,不宰而物应,岂敢比德尧舜,论功禹汤者哉!”(《全唐文》卷三○,第1册,第143页)肃宗《禁藉田雕饰农器诏》称:“……如闻有司所造农器,妄加雕饰,殊匪典章,况绀辕缥轭,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谅为国所疵,静言思之,良用叹息,岂朕法尧舜重茅茨之意邪?”(《全唐文》卷四二,第1册,第202页),穆宗《长庆宣明历序》:“……是以钦昊天、协时月,必首于尧舜之典,叙九章、用五纪,亦冠于周宗之书,则知履端受命,斯为本也。”(《全唐文》卷六七,第1册,第309页),敬宗《南郊赦文》:“……《书》称望秩,《礼》著不封,仰尧舜之聪明,慕文武于方册,遐想忠贞之迹,缅怀义烈之风,能御大灾,咸申祀典。”(《全唐文》卷六八,第1册,第315页)等。。
君王要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则需要臣子的有力辅弼,二者相辅相成。“致君尧舜”,由此也成为唐代士人政治上的努力方向。但是,考察“致君尧舜”之成为唐代士人的政治理想与理念,其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追溯“致君尧舜”一词,其初出现当在南北朝时。就当时对此语之使用来看,主要是作为褒奖有殊功勋劳大臣而使用的语词(4)蒋金坤以为,“唐代之前,士人将时君与尧舜对比,或用于进谏,或为虚誉浮词,尚未内化出‘致君尧舜’的政治理念,也没有意识到自身作为‘致君尧舜’的行动主体。至魏晋南北朝时对尧舜话题的持续关注,使‘致君尧舜’作为固定用法开始流行,其最多者出现在北朝墓志中”。并引《魏故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冀州刺史王元(乂)公墓志铭》之“翼亮王猷,辑熙治道,济斯民于贵寿,弼吾君于尧舜”及《齐故齐仓二州刺史高(建)功墓铭》之“翼厥主于桓文,致其君于尧舜”以为证。见蒋金坤《“致君尧舜”:唐代皇帝的神圣化与士人转型》一文,《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至唐代,其意仍被袭用(5)唐代帝王褒奖重臣,常用此语意,如太宗以之称赏魏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诸葛)亮无以抗”(《新唐书·魏征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册,第3876页);玄宗《赏定策功臣制》褒奖郭元振“伟材生代,宏量镇时,经纶文章,今之王佐,出入将相,古之人杰,夙侍帷扆,畴咨庙堂,思志尧舜,以期管乐”(《全唐文》卷二0,第1册,第98页);宪宗《授李吉甫同中书侍郎平章事制》“自擢于纶阁,列在禁闱,鼓三变之文,润色王度,总五才之用,参赞庙谟,化俗思迈于成康,致君愿及于尧舜”(《全唐文》卷五六,第1册,第264页),等等,皆是。。但是,自初唐后期始,其用法与指向则有所变化,这就是在君王以尧舜为慕效对象的语境下,其逐渐成为君王对臣下之政治期许。从现存唐代文献看,最早采用此意者乃唐睿宗,其《拣择刺史诏》云:
朕闻彰善瘅恶,有国之常典;纠宽济猛,为政之通规。朕以薄德,滥膺明命,瞻言赏罚,未适时宜,至使忠良未进,小人未退,贪吏未惩,流亡未安,贤良者未归,怀冤者未理,在予之责,有愧良深。不能致君于尧舜者,亦群公群士之所耻也。卿等将何规补,使致咸亨,各以状闻,朕当亲览。其才望兼优,公清特著,可以宣风道俗者,具以名闻。但百司承宽,共为苟且,事多愆咎,无复纪纲,令各本司长官,审善恶才识,限十日进状。[3]91
此后,玄宗在《大赦制》中也用此意,谓其当初发兵剿灭韦氏及诛除太平公主等行为是“事殷家国,义感神祇,吟啸风云,龚行雷电,致君亲于尧舜,济黔首于休和”[3]98。
君王之倡导,自然对官僚文人以较大的影响,由此,“致君尧舜”便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上而下流行开来,而其运用时的意涵有所变化。开元时,张说《让右丞相表》文即云:“臣学惭稽古,早侍春宫,阶缘旧恩,忝窃枢近,虽思致君尧舜,而才谢伊皋。”[3]991与睿宗、玄宗制诏对读,不难看出二者在运用“致君尧舜”时语义的差异,也即一为居上之号召,一为在下之响应。由此可见,“致君尧舜”在初盛唐之际,经由帝王的倡导,已逐渐演化为盛唐时期官僚文人一种自觉的政治意识。而一种语词之化出新意,特别是经上层统治者的倡导,必定会在士大夫文人中流播。由此也可以推知,“致君尧舜”作为一种士人新意识的形成,也当始于初唐末至盛唐初期。
杜甫生于睿宗先天元年,其青年时期正是在玄宗开元时期度过的。玄宗的励精图治与当时社会欣欣向荣的气象,对于当时士人之政治理想的形成,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杜甫当然也不例外。不过,从现存文献看,开元时期高唱“致君尧舜”者,实多为已居于政治高层之官僚文人,而杜甫在诗中表达其“致君尧舜”理想时,尚处于困守长安生计最为艰难之际。了解此一点,则可知杜甫政治理想之不凡,也即与一般普通士子汲汲于利禄的巨大差异。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曾将他人与自己做比云:“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4]668这虽是牢骚语,但也的确可看出他志向的高远。只是“致君尧舜”理想虽然远大,其实现则需要有相应的仕宦为基础,因此,当杜甫在天宝十一载申述这一理想时,也只能是一种愿望的表达而已,其具体之实践,则有待于后来的仕宦际遇。
二、“致君尧舜”与杜甫的谏诤精神
杜甫在困守长安十年后,于天宝十四载终获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从“致君尧舜”的角度看,这一微职,是难以给他提供实现远大抱负的条件的。但是,紧接着发生的安史之乱却使他的仕宦发生了变化。他因乱中奔赴凤翔行在,被肃宗授左拾遗。 “拾遗”一职虽然品阶并不高, 但因其“掌供奉讽谏, 扈从乘舆。 凡发令举事, 有不便于时, 不合于道, 大则廷议, 小则上封”[5]1845, 故可使杜甫得以常参官身份接近天颜,预闻大政, 因此也就给予了他实现“致君尧舜”理想以实在的机会。 杜甫“致君尧舜”理想的实践, 正自兹而始。 而就其一生看, 他之切实在行动上将实现理想付之于实践, 也主要在此一阶段。 至乾元元年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 因离开政治中枢,不再能够预闻并参与朝廷大政, 其欲“致君尧舜”, 已无法有所作为, 故以下考察杜甫有关实践其理想之具体政治活动, 主要围绕其任拾遗之职期间而展开。
前文已述,“致君尧舜”至开元时已逐渐成为官僚文人自觉的政治意识,但在实践层面如何“致君尧舜”,则因个人境遇有异,禀赋有别,具体之表现亦各不相同。就杜甫而言,其践行“致君尧舜”主要体现为自比稷、契,要做辅弼之臣,而辅弼之道,则表现为对谏诤之道的追求与持守。至德二载五月任拾遗不久,他即因谏诤肃宗罢免房琯事而引起风波,同时也成为其一生仕宦经历中影响最大之事件。关于此事之始末,两《唐书》本传皆有载,虽微有差别而大端不殊。其中《新唐书》所载稍详,谓:“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按,应为“左”)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庭兰,罢宰相。甫上疏称:‘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6]5737杜甫上谏罢房琯之举,惹怒肃宗,差点引来杀身之大祸,后虽因张镐仗义执言而幸得缓颊,却从此则失去了肃宗的信任,即所谓“然帝自是不甚省录”[6]5737也。那么,杜甫履职未久,何以会有他后来自嘲的“愚戆”之举呢?在这场风波之后,他对此行为又有着怎样的认识呢?对此,其《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正可作为分析的最佳文本。状文虽稍长,但为全面了解杜甫当时的心理,因不避繁琐,引述如下:
右臣甫,智识浅昧,向所论事,涉近激讦,违忤圣旨,既下有司,具已举劾,甘从自弃,就戮为幸。今日巳时,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镐,奉宣口敕,宜放推问,知臣愚戆,舍臣万死,曲成恩造,再赐骸骨。臣甫诚顽诚蔽,死罪死罪。
臣以陷身贼庭,愤惋成疾,实从间道,获谒龙颜。猾逆未除,愁痛难过,猥厕衮职,愿少裨补。
窃见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康济元元。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琯之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况画一保大,素所蓄积者已。而琯性失于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工,游琯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一至于玷污。
臣不自度量,叹其功名未垂,而志气挫衄,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何思虑始竟,阙于再三。
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复解网罗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劝勉来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岂小臣独蒙全躯就列,待罪而已。无任先惧后喜之至,谨诣閤门,进状奉谢以闻,谨进。
至德二载六月一日,宣义郎、行左拾遗臣杜甫状奏。[4]6385-6386
就状文看,大致包含了以下内容:一是三司推问与被放情由始末;二是其上谏之原因;三是对房琯其人的看法;四是对本人谏诤之检讨;五是对肃宗处理的认识。五点之中,除第一点介绍事之始末外,其余四点则关涉杜甫对此一事件之体认,而中心之意乃对其谏诤行为的辩解。其第二点,意在说明自己蒙肃宗恩顾,忝为朝廷官员,期于裨补朝政之阙,故动机纯正;第三点从房琯之学养、才性论其为人,坚持其房琯大醇而小疵的看法;第四点虽略有反省,但认为只是“思虑未竟,阙于再三”,乃思虑未能周全之失。第五点则是说肃宗宽贷,目的仍是容直臣、劝勉后继者。由此来看,杜甫在缓颊免死后,并没有认为自己在谏诤房琯罢相一事上有根本之大错。而末一点,在表面颂圣中,仍表达的是希望肃宗能效法古人,包容直臣,以激励直谏者的意思。
经历这样一场几乎丧命的风波,杜甫于谢状中做出这样的“检讨”,颇有点未思悔改的意味。他不仅不认为自己有大错,且在事后的实际行动上,也仍然不改初衷。因谏诤房琯,他为肃宗所疏远,长安收复后,他依然坚持谏诤之道一如往昔。“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4]1022“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4]1025“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4]1028的诗句,以及他从裨补朝政出发,向肃宗力荐岑参为补阙(6)杜甫在《为遗补荐岑参状》中曾云:“窃见岑参,识度清远,议论雅正,佳名早立,时辈所仰。今谏诤之路大开,献替之官未备,恭惟近侍,实藉茂才。臣等谨诣阁门,奉状陈荐以闻,伏听进止。”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二二,第1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93页。,皆为此之佐证。
那么,杜甫何以如此不懈地坚持其谏诤之道呢?这当然既有他所受思想影响的因素,也与历史上直臣典范的影响有关。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其“致君尧舜”理想,当然脱离不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其中儒家的君臣观念,可谓是杜甫思想的根基。而在儒家思想中,君臣关系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孔子重视伦理道德,其视君臣之道同于父子,故齐景公问政,他即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对之。而君、臣之准则,则应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当然,孔子教学生以出仕为目的,臣子事君之道,也为学生特别关心。孔子教学生事君,突出者则有两点,一为直道,二为忠勤。当子路问其如何事君时,其简言之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并对直道事君极口称道,如谓卫国之史鱼云:“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赞“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是“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同时他还主张“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要“先之劳之”,“无倦”(《论语·子路》)也即臣子应忠于职守,勤于政事。
相较于孔子,荀子则对此有更全面深入的论述。《荀子》之《君道篇》《臣道篇》,专论为君与为臣之道。其中《臣道篇》云: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彊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7]249-250
荀子谓“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国之宝也”,实际上也就是对臣子谏诤精神的肯定与推崇。由于儒家思想自汉已降已成为士人思想之主导,故历代贤臣,莫不以直言谏君为臣道之宗极。当杜甫立朝为臣时,儒家对臣道谏诤精神的推崇也必然会影响到他的仕宦心理与为臣之节操,而左拾遗之职,本就以拾遗补阙为务,因此,他也就自然视谏诤为最基本的职责与使命所在。
杜甫的固守谏诤之道,除儒家思想的影响外,历史上贤臣直谏精神及当代贞观遗风的影响,同样也不容低估。就历史上的直臣而言,汉之朱云可谓典型。《汉书·朱云传》载其事甚详,其中所记朱云谏不畏死,攀折殿槛,不仅震动当时,且流传久远,后世之直谏者,莫不奉为楷范。杜甫不仅熟知其人其事,且对其谏诤精神亦极为推赏,他大历初漂泊西南,曾以朱云之谏诤故实为题,写有《折槛行》一诗,即可见对其影响。
但是,杜甫最为深刻的政治记忆,还是距其不远的贞观与开元时代,而这也可能直接影响到他对为臣之道的认知。在诗文中,他不止一次表达了对太宗、玄宗两代君明臣直政治风气的向往与追慕。其称颂太宗贞观时代是“天属尊尧典,神功协禹谟。风云随绝足,日月继高衢。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4]185;称道玄宗时代是“先朝纳谏诤,直气横乾坤”[4]5379。而从为臣的角度,令其心仪的则是魏征等贤臣的直道与谏诤精神。广德元年房琯卒于阆州,因追悼故人,唤起了他对先世君臣遇合与谏诤之道的历史记忆,《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即叹息:“呜呼!纯朴既散,圣人又殁。苟非大贤,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群公间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画一。娄宋继之,不坠故实。百余年间,见有辅弼。”[4]6452文所称之魏、杜与娄、宋,分别指太宗时期的贤臣魏征、杜如晦与初盛唐之际的名臣娄师德与宋璟。其中魏征、宋璟以直谏与忠谠著称,杜如晦、娄师德分别以善断与谨厚闻名。祭文回顾历史,推仰前代,其核心则在于对臣秉谏诤之道与君容直臣的先朝政风的追慕。这从《折槛行》诗即可明白其意旨所在:
呜呼房魏不复见,秦王学士时难羡。青衿胄子困泥涂,白马将军若雷电。千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嶙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4]4356
诗与祭文所提及的当代贤臣,完全一致。而诗中所称道者,上自汉之朱云,下及本朝之四贤臣,核心所在,一则叹“千载少似朱云人”,再则为今日缺少直臣与君王之不能容纳谏臣致慨。宋人洪迈即谓“此篇乃专为谏争而设”[4]4359,明人吴见思亦称:“唐太宗开瀛洲,以房魏等为学士,岂不盛哉!而今时不可及矣。盖以士子困辱,诸将横行,非修文偃武之时耳。况千载以下,无朱云者,虽折槛空存,而直言岂可得进乎?然先皇能容直臣,朝廷如有阙失,苟娄公不语,则宋公语矣,岂若今之钳结哉!”[4]4359-4360其《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则称道魏征直道事君并慨叹魏佑之沦落:“磊落贞观事,致君朴直词。家声盖六合,行色何其微。”[4]5908《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密论贞观体, 发挥岐阳征。”[4]3982如此再三致意直臣, 追忆先朝, 不难看出历史上直道谏诤对杜甫谏诤精神品格形成的影响。 而从这一点看, 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的实践, 其根本所在, 也就是通过直谏辅助君王, 弥补为政之阙失, 以形成君明臣直之社会政治环境, 如此则尧舜可期, 德化可成。 但是, 杜甫希冀践行的这种为臣之道, 恰成为其仕宦悲剧之根源。 究其原因, 乃在于他理想化的臣道认知与其所处现实环境之错位与抵牾。 此一点容后再论。
三、杜甫对“致君尧舜”理想的坚守
乾元元年六月, 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离开了京城长安, 也因此而失去了预闻朝廷大政与直言谏诤的机会与可能。 这对于其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 无疑是一个挫败。 至乾元二年七月之后, 他又辞官西行, 自尔脱离宦籍。 那么, 脱离仕宦之后,杜甫改变了其原来的理想初心, 不再坚持“致君尧舜”了吗?(7)学界于此似有不同的意见。袁行霈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谓:“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他有巨大的抱负,自谓能立登要路,致君尧舜。但这幻想在天宝五载(746)到长安之后,便彻底破灭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以为杜甫在天宝五载,其“致君尧舜”理想即已破灭。也有人认为,杜甫天宝五载到长安后,“‘立登要路’的愿望确已破灭。但是,‘致君尧舜’仍是杜甫终身不渝的追求”。(见吴淑玲《致君尧舜:杜甫终身不渝的政治理想》,《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从根本上说,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须藉助君臣两方面的协合相应。一方面,臣要有尽力辅弼、直道事君的精神,另一方面君王也需要有容纳直臣的雅量气度。而与此两者紧密相关且特别重要的,则是君臣的遇合。杜甫离开长安后,君臣暌违,因此,就其实现政治理想而言,已经失却了客观条件,但是,如其在主观上不放弃,坚持谏诤精神不变,则亦不可谓改变初心。
杜甫离开长安后对于“致君尧舜”理想的坚守,观其华州司功参军期间所拟之《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可以见之,其试策之第四首云:
问:昔唐尧之为君也,则天之大,敬授人时,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帝舜之为臣也,举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为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聪明,加之以劳身焦思,既睦九族,叶和万邦,黜去四凶,举十六相,故五帝之后,传载唐虞之美,无得而称焉。《易》曰:“君子终日乾乾。”《诗》曰:“文王小心翼翼。”窃观古人之圣哲,未有不以君唱于上,臣和于下,致乎人和年丰,成乎无为而理者也。主上躬纯孝之圣,树非常之功,内则拳拳然,事亲如有阙,外则悸悸然,求贤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恭己而已。寇孽未平,咎征之至数也;仓廪未实, 物理之固然也。 今大军虎步, 列国鹤立, 山东之诸将云合, 淇上之捷书日至。 二三子议论引正, 词气高雅, 则遗祲荡涤之后, 圣朝砥砺之辰。 虽遭明主, 必致之于尧舜; 降及元辅, 必要之于稷卨。 驱苍生于仁寿之域, 反淳朴于羲皇之上。 自古哲王立极, 大臣为体,眇然坦途, 则何往不顺, 子有说否? 庶复见子之志, 岂徒琐琐射策, 趋競一第哉……[4]6418
将“致君尧舜”作为考核选拔人才之策问题目,表明其于“致君尧舜”的理想,并未因仕宦挫折而有所改变。追慕君臣协和的唐尧虞舜时代,坚持致君于尧舜,仍然是贬官后他坚持的政治理想。
但是,自乾元二年七月后,杜甫的境遇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由一位著籍于朝的官员,变成了远离朝廷的沧江野老。身份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他的心理。大历元年至夔州所作的《壮游》曾有诗句谓:“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4]4085一方面回顾早年任拾遗之廷争直谏经历,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弃官远游,不复能在朝廷直谏议论而倍感痛伤。陆游于此曾致慨说:“……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谬,坎壈且死,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4]4103-4104朱彝尊也说此诗:“追叙一生,由少而壮,壮而老,始而文章,继而交游,继而忧国,终有望于英雄之救时,此希稷、契心事也。”[4]4104由此可见,当杜甫暮年漂泊流落殊方之时,仍不忘其稷契之志,乃心于致君尧舜,但因迤逦远方,议论断绝,无能参与朝政,因而不胜其悲。
杜甫暮年远离朝廷,于论议廷诤、“致君尧舜”之事,念兹在兹,但也深知再归朝堂的机会十分渺茫,因而也就对通过本人亲力谏诤以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不再存有奢望。他所希冀的则是期望朝臣们能够恪守直道事君之理,尽力辅弼,这样通过他人的努力,间接也就实现了其“致君尧舜”的理想。故在暮年漂泊流离之际,每与友人赠别或交流,都不忘以讽谏君王期许对方。大历二年,王崟北归长安,他写有《奉送王信州崟北归》一诗送别,在慨叹时事艰虞、苍生困顿的同时,希望王崟体恤天子之思得直臣,勉其绸缪庙略,有所献纳,其诗之末尾即云:“九重思谏诤,八极念怀柔。徙倚瞻王室,从容仰庙谋。故人持雅论,绝塞豁穷愁。复见陶唐理,甘为汗漫游。”[4]4585至大历四年流落潭州所作《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韵》,亦念念不忘以谏诤之道期许卢侍御,诗后半部分云:
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刺规多谏诤,端拱自光辉。俭约前王体,风流后代希。对扬期特达,衰朽再芳菲。空里愁书字,山中疾采薇。拨杯要忽罢,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盖,儿扶立钓矶。清霜洞庭叶,故就别时飞。[4]5902
凡此都不难看出,晚年流离巴蜀与漂泊湘楚之际,杜甫对于以谏诤而致君尧舜的基本态度,以及因个人暮年遭际而对于实现其致君尧舜方式所发生的变化。
如前所说,“致君尧舜”不仅在于臣子以直道谏诤辅弼君王,而且也需要君王容纳直谏的气度雅量。杜甫一生经历玄、肃、代三代君王,其中玄宗是开、天盛世的创立者,杜甫对其早期励精图治、任人以贤而达致社会繁荣有着深刻的记忆,但他未曾宦于玄宗朝。相较而言,肃、代二君尤其是肃宗与杜甫的关系更为密切。
杜甫对肃宗的心理较为复杂。肃宗擢他为左拾遗,予他以切实的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故一开始他也就把肃宗当成了实现“致君尧舜”理想的对象。肃宗在位,正是唐王朝平叛最紧张的时期。天下不宁,政事纷纭,朝端多故,而杜甫则每以忠耿之心与谏诤之道,尽其辅弼之责。至德二载谏房琯罢相风波后,肃宗放其还家省亲,但他于离别之际仍念念不忘谏诤之责:“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4]944。这一时期,因对肃宗寄予厚望,故评价也多所褒扬,“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4]944。而当长安收复,他亦为肃宗之能中兴大唐而欢欣:“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4]1254但是肃宗回銮,杜甫返京后却不为猜忌心甚重的肃宗所优容。郁闷之际,他流连曲江,诗酒放旷,借伤春而表达不满。至出为华州司功参军,肃宗对他的疏远已为明显的事实,他对肃宗的认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4]1466至流离陇右,他对于肃宗不能容纳谏诤之不满,已溢于言表。而在某种意义上,杜甫的辞官远行,脱离仕宦,也与他对肃宗的失望不无关系。他在仕宦上自我放逐,从根本上说也是他希望通过肃宗实现其“致君尧舜”理想幻灭的结果。
代宗即位后,安史之乱终得平定,但国之元气大丧。内有殷忧,外则吐蕃东掠,遂致有车驾幸陕之狼狈。永泰元年春正月,代宗下诏罪己云:
……朕嗣膺下武,获主万方,顾以薄德,乘兹艰运,戎麾问罪,今已十年。饮至策勋,惟凶渠之授首;劳师黩武,岂人主之用心。军役屡兴,干戈未戢,茫茫士庶,毙于锋镝。皇穹以朕为子,苍生以朕为父,至德不能被物,精诚不能动天。俾我生灵,沦于沟壑,非朕之咎,孰之过欤?朕所以御朽悬旌,坐而待曙,劳怀罪己之念,延想安人之策。亦惟群公卿士,百辟庶僚,咸听朕命,协宣乃力,履清白之道,还淳素之风。率是黎元,归于仁寿,君臣一德,何以尚兹。迺者刑政不修,惠化未洽,既尽财力,良多抵犯,静惟哀矜,实轸于怀……[5]277-278
远在巴蜀的杜甫,可能听闻罪己之诏而心有感慨,因作《往在》一诗,于回顾往事的同时,希冀代宗能继体太宗,容纳谏诤,完成中兴之大业,其中末尾云:
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千春荐陵寝,永永垂无穷。京都不再火,泾渭开愁容。归号故松柏,老去苦飘蓬。[4]4130
由此亦可见杜甫对代宗冀望之所在,只是由于他此时年老衰惫,无力返朝,故末尾乃发出了“归号故松柏,老去苦飘蓬”的无奈慨叹。
四、余论:杜甫政治理想及其悲剧性遭际的典型意义
杜甫自壮年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经中年仕宦之力行实践,而最终却于晚年不得不以沧江野老之身,流离漂泊,赍志以殁,这无疑是他人生的悲剧。追溯杜甫这一悲剧之成因,既与杜甫主观认知与现实环境的错位有关,同时也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
杜甫坚持以谏诤作为臣道之基本精神,从远因上,自然与儒家直道事君的思想传统有关,而就近因而言,则与杜甫的近世记忆密不可分。这后一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对于太宗容纳直臣的贞观政风的无尽眷恋与追忆。在杜甫的想象记忆中,太宗就是当世的尧舜之君,因此,他每以太宗作为标准来衡量后来的帝王。“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4]296,“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4]185,“俭约前王体,风流后代稀”[4]5902,认为只要能学习效法太宗,后代的君王也不难成为尧舜之君,但他却忽视了作为个体的帝王的复杂性。实际上,即如太宗那样具纳谏雅量的明君,亦何尝能够与魏征始终信任不移(8)两《唐书》皆载魏征死后太宗对魏征的猜疑。《旧唐书·魏征传》载:征“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征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诸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见刘昫《旧唐书》卷七一,第8册,第2562页。《新唐书·魏征传》谓“仆其所为碑”,余大略同。。而在魏征死后,贞观时代君明臣直之政风,实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
就帝王的统治思想而言,秦汉以后已不再是儒家独占了,儒、法结合,交相为用,大致已成为帝王统治之主要手段。法家最看重的是君王的权威,“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8]514因而认为“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8]510这种主张,和儒家倡导的直言谏诤精神与君王虚心纳谏之德,显有不同。由于士人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故进入仕途的士人,莫不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其思想行为之准则。而从君臣关系来看,在政治上臣处卑势,因此,当君臣发生冲突时,谏臣悲剧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故直谏者的悲剧遭际,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来看,也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由此而言,杜甫坚持儒家直谏的臣道原则,并希望藉此以实现“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实早已具悲剧之因,而杜甫的政治理想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生悲剧性遭际,也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杜甫的悲剧,实际上也即是古代持守直道事君与谏诤精神的醇儒之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