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区分“怨天”与“尤人”
2022-12-04桑田
桑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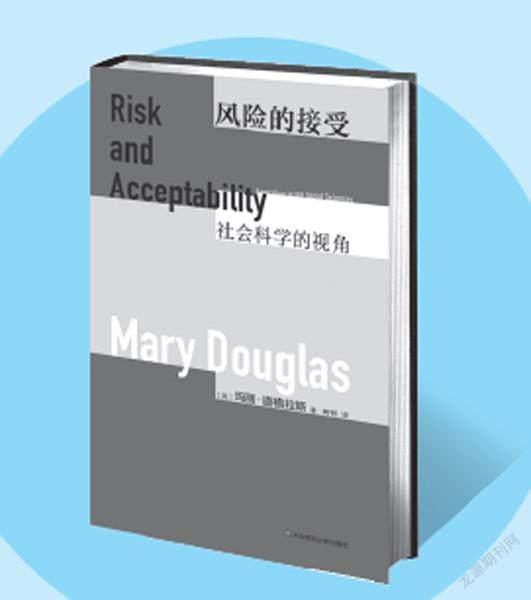
《风险的接受》 [英]玛丽·道格拉斯著 熊畅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现代社会是一个注定要与风险打交道的社会。所谓风险,通常是指在特定时段、特定环境下发生损害的可能性。但在这样一种界定中,“损害”的具体内涵是十分模糊的。因此,自从一九八六年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有关风险问题的理论就愈发丰富起来。从安东尼·吉登斯到尼克拉斯·卢曼,众多社会学名家皆对现代社会的风险及其规制问题展开过探讨。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21-2007)所著的《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一书,也是这一领域新近研究的代表。
在导论部分,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她想撰写的,是一部有关风险感知问题的文献综述。她认为,先前的风险社会研究大多围绕在“外围领域”,对风险感知的社会影响则关注较少,而她则聚焦于风险的“可接受性”问题。从“风险”到“风险感知”,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飞跃。
一
如果我们按照一般理解,将风险视为客观的损害,那么风险感知就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它缺乏一个“纯客观”的度量——风险是一回事,对风险的感知及责任划分是另一回事。前者是科学性的,后者是社会性的。然而两者都可以造成较大范围的后果。作者在书中援引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即阿马蒂亚·森(Amartya K. Sen)对非洲饥荒的研究:气象条件和粮食歉收显然属于自然事件,但它们并不一定会带来大规模灾害。如果从国家到民众层面都感知并判断“这是天灾”,那反而可能带来真正的灾害。正如书中所言:“一直以来,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粮食供应问题上,忽略了经济和法律结构的崩溃,而这正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即使是在粮食丰收、储备充足的年景里。”可见,有时社会力量所导致的损失,未必就比自然力量小,并且无法厘清二者反而更容易导致残酷的后果。
因此,同样是损害,我们还是会下意识地区分“自然”与“人为”,尤其后者还涉及后果承担与责任分配的问题。中文里的“归咎”一词十分生动地表达了这样一个社会过程。如果是纯自然灾害,那么无论国家还是社会就都仅有赈灾意义上的责任;而如果是个人原因导致的不利后果,则有时会被判定为“咎由自取”。当然,剩下那块最重要也最需要仔细研究的,是那些既不能怨老天也不能怨自己,而是要“怨他人”的情形,这就属于典型的社会学问题了。本书作者所侧重的,正是從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出发,探讨大众对于风险的感知与接受问题。
纵览全书,作者综述了两个主要的解释方向和三种新兴的解释方法。我认为,两个解释方向可以概括为理性选择理论与文化道德理论:前者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亲和,诉诸计算、利益衡量与博弈论来理解全社会对于风险的感受与转嫁问题;后者则将多元社会的价值观纳入考量,强调历史传统和社会伦理对于政治,特别是风险处理问题的影响。与此同时,既然风险的感知与接受涉及人类的主观世界,那么诉诸心理学的解释也是很自然的。作者专门考察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即“风险感知学”,它由具体的三个小分支构成:工程学方法、生态学方法与认知科学方法。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21-2007)
三种方法其实是对人类形象的三种素描,对此我们可以稍作展开。
第一种工程学方法假定公众是由孤立的个体组成的,人人都渴望知晓事实如何,并且当事实清晰地呈现在面前时,他们立马就会相信基于科学依据所提示的安全性或风险性。然而这显然是非常理想化的。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天生就像工程师那样,沉着冷静地“坐等科学报告出炉”再决定自己的情绪与行动,一切遵照公开信息而“知命不忧”(译者选用的译辞十分精妙)。第二种生态学方法则始于洪水研究,它试图弥合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差异。但是这反倒混淆了种群之外的观察(类似动物)与种群内部的实践,尤其是在告别了部落时代的现代风险社会中,以动物世界的还原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实际上是非常牵强的。最后一种是“最具主导风险感知研究之趋势”的认知科学方法,它的假设前提和心理测量方法已经蔓延到了整个风险感知领域。
对于第三种认知科学方法,作者用了第三、第四章来介绍和回应,可见其影响之盛。比如“侥幸心理”和“豁免心理”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代表。侥幸心理是自然演化筛选的结果:通过忽视概率较低的风险,人类将“节约”下来的精力与心力集中于更为重要的生存任务上。但是,进入现代风险社会以后,人们暴露于风险的概率成倍地放大了。比如,原始社会根本不会出现的高空作业,如今却成了摩天大楼窗外的现代人为了工作与生存而不得不挑战的风险。这说明我们数万年来演化出的本能,特别是自然演化所筛选出来的心理与适应能力,未必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特别是难以抵御更加细密复杂的风险。“豁免心理”也与侥幸本能相关,这是一种“不会摊到我头上”的心理状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交通事故,比如嫌戴头盔麻烦而选择不戴,对一个具体的个人而言,发生事故或许只是小概率事件,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车祸则是一个大规模发生的风险事件。种种认知心理的研究都彰显出人类本能与现代社会不相匹配之处,因为风险本身的量度,未必可以决定风险可接受的程度,而且认知偏差所导致的人对风险的感受和其危害往往是不成比例的。
二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三种方法仍然是不够完备的。它们几乎完全立足于自然科学与心理学层面来处理风险感知问题,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社会科学与社会理论的运用。果然,在使用了漫长的篇幅介绍这些前沿学科的研究之后,作者随即为这些学科打上了一个“幼稚”的标签。得益于作者多年从事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的经历,她深谙分析者模式与行动者模式的差异,知道“置身其外的分析者”无法替代“置身其中的行动者”。“感知”当然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但“风险感知”却不只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更像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诉诸纯心理认知的研究,甚至将动物认知心理的规律也纳入进来,是一种明显的歧途。
作者玛丽·道格拉斯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和社会化理论也十分熟悉,她关注多主体间的关系互动,更关注宏观社会运转对微观个体的规范性约束。由此,在“风险”与“风险感知”之上,我们可以继续区分出一个“风险沟通与风险责任分配”的维度,相比于前两者,它具备更鲜明的社会性特征。简而言之,风险感知的敏感度(sensitivity)和风险分配的可接受度(acceptability)是两个层面,风险本身的危急程度与风险分配的公平程度也是两码事。通俗地讲:当天上的锅已经掉下来时,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唯一背锅的那个人,若有可能,怎么把这口锅甩出去——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学问题。学理地讲,则是风险的归责、转移与救济问题。理解这一点,对于理清本书后面的多个章节都有启示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即从全人类到人类个体都不总是像工程师那样镇定客观的,相反,他们时常处于恐慌与自负的两极:有时相信捕风捉影的危险,有时却又忽略近在咫尺的威胁。如若叠加上公众认知偏差,恐慌的放大也随之而来。然而从社会学视野来看,这种夸大的效果何嘗不是一种“客观事实”呢?只不过相比于科学事实,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事实。如前所述,它所发挥的影响一点也不比自然事件更小,因此此时的重点就应该是“风险沟通与责任划定”。
对此,社会学家常举的例子就是核电站带来的恐慌,本书的作者也说:“强烈道德义愤足以让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超出认知范围的危险上。”相比日常生活里的“中等风险”,核污染的发生本来是极其罕见的,但是它集中凸显了现代风险的两大特质:一旦发生就难以逃脱,以及承担的非自愿性。虽然自然灾害同样是非自愿且难逃脱的,但社会性风险最重要的特质在于“人为”,这就带来了归咎的可能——从“只能怨天”变成了“可以尤人”,无法以自然力量的不可抗拒而稀释人为的责任。事实上,卢曼就曾以“风险/危险”的区分来界定这种实质上的不同:同样是损害,风险的损害源于人为的参与;而危险是由外部环境因素引起的,它不是一个社会事物。简言之,风险归咎于决策,危险归咎于环境。当然,不决策往往也是一种决策,它等价于不作为和失职。也因此,在现代社会,复杂的归责与免责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作者在介绍了所谓“自然风险”(第五章标题)之后,开始用整本书的后半篇幅来阐释制度与归责问题,这是从社会内部对损害的一种分配及消化。
三
客观地讲,本书的后半部分是相对细琐的,作者切分了多个主题来对数十年来基于社会科学的风险感知与风险应对研究做了综述,比如可信度(第六章标题)和制度约束(第八章标题),涵盖了当代风险认知理论的几乎所有前沿成果。如果想要跟进这部分知识密度非常大的梳理,可能需要花费较大的气力。
在我看来,在这一部分中较有启发性的,是对浸润于不同文明中的社会所做的比较分析。比如同样是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移民,同样面对着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大陆,“亡命之徒”的风险感知及其风险偏好程度与“洁净的清教徒”所秉持的忠笃与平静是差异极大的。再如借助麻风病诅咒所做的社会规训和基于自然灾害而对统治者所做的天罚警示,已经很有将人类学、文明比较研究与观念史研究融合起来的架势了。不过作者显然没打算深入探讨,而是选择了浅尝辄止,承认自己对不同文明观念所导致的风险处理的制度与价值比较问题力有未逮。作者本人的视野限制了她在这些领域做延伸性探讨的可能,比如她未意识到,对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中华文明而言,灾害在传统社会中是有独特意义的,并且关注一些传统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模式,恰恰可以“碰撞”出新的风险处理路径。即使到了现代社会阶段,作者的探讨本来也可以继续延伸。比如对免责保护所带来的更高风险决策偏好问题,但本书仅做了文献综述和一些蜻蜓点水式的点评,这大有“不解渴”的感觉。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烂摊子由谁收拾、后果由谁承担”,以及围绕这一问题的风险规制,是一个大可以深挖的好问题。
应当说,这本薄薄的小书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风险,它更不是一本风险规避手册,甚至它面向的读者受众就不是“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人”,而更像是一本写给社科生和同行们看的文献综述。如果寄希望于它通俗易懂,那读者很可能是要失望的。可它仍是一本有独到见解并带来启发的优质作品。在我们对风险问题关注还不充分,甚至还未清晰区分“怨天”和“尤人”时,书中纳入综述的内容已经细化讨论了风险的感知与可接受性问题,给出了风险容忍度理论,并在风险责任划分领域给出了许多优质的学术梳理与制度概述。
归根结底,现代社会是一个高连接度的复杂社会,因果链条的细密使得任何一环的崩溃都可能造成全社会或其他领域的不可控的后果。在任何一个社会,人并不总是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做选择,反倒总是在一种情绪与另一种情绪之间做选择。在此意义上,越早正视风险问题,越早关注风险的感知、接受、分配问题,就越有可能预先在制度设计上给出更优的方案。风险是残酷而无可避免的,但人类社会面向光明,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