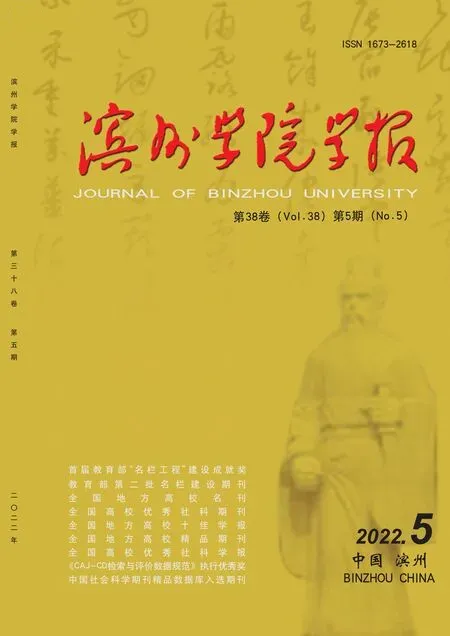论刘璋小说中的占卜与梦境
2022-12-04孙伟航
孙伟航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清初山西阳曲(今属山西太原)小说家刘璋一生除讽刺小说《斩鬼传》外,还有《飞花艳想》《幻中真》《巧联珠》《凤凰池》四部才子佳人小说流传至今。综观其五部作品,占卜与梦境情节为其小说中的共性,除《凤凰池》外,在刘璋的其他四部小说中均有出现。我国的梦文化与占卜文化源远流长,《周礼》中即有将梦境与日月星辰相结合来考察梦之吉凶的记载。另外,《礼记》《仪礼》等文献当中亦有关于龟卜等占卜情节的记载。中国古人十分看重占卜与梦境所传递出的信息,认为它是天人感应的一种媒介,于是梦境与占卜情节很自然地就成了小说的一部分。考察刘璋小说中占卜与梦境情节,不仅体现了作者独到的叙事特色,也蕴含了作者本人的思想价值观念。
一、占卜与梦境情节的多样性
不同于其他作家的世情小说,刘璋笔下的世情小说对于占卜与梦境情节的描写更加多样,因此使得故事情节变得更加复杂,小说中的时代与文化的类型特点也随之丰富起来。
(一)多样的梦境情节
刘璋小说中为我们展示了其占卜与梦境情节内容的多样性。首先是梦境的多样性展现,《周礼·春官·占梦》有“占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1]的相关记载。除去自然而然的“正梦”一般没有真正含义体现,并不会出现在小说中之外,在刘璋小说中,亦有“思梦”“噩梦”“喜梦”“惧梦”等多种梦境类型。《飞花艳想》中第六回柳友梅梦见与五花仙子、六花仙子在合欢亭邂逅,流连于“欢乐之际”,显然,此为“喜梦”。《幻中真》中的另一梦境情节同样出现在第四回,易任同妻子睡在房中,竟梦见一黑面红须大汉“把他妻子扯去”“强奸起来”[2]。此梦使易任又惊又惧,当归为“噩梦”一类。《巧联珠》中闻相如在科举之途寻的僧房梦见科举试后,文昌帝君将第五十七名举人胡同革去功名,又将“持《太上感应篇》甚敬”的自己补上,“又喜又怕”[3],此亦即“喜梦”。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柳友梅、吉梦龙还是闻相如,这些“喜梦”的背后都暗含着人物本人内心的心理愿望,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故亦可归为“思梦”一类。
刘璋笔下的梦境不仅停留在《周礼》中那样简单的分类层面,而是包含着更深层的特色。如《幻中真》第四回中,吉梦龙被关监中受尽酷刑,梦见神官赐予美酒,并告知其脱离法网之期。而后又见尊神将其推下半山,大叫惊醒。此梦前半段可理解为主人公吉梦龙梦中畅饮,归家有期,可视为“喜梦”一类;梦的后半段使吉梦龙饱含惊惧,可归为“惧梦”。这种同一梦中却饱含不同梦境心理种类的手法不仅增加了小说梦境情节的多样性,也蕴含着更深刻的艺术价值。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强调了其“同中有异”“特犯不犯”的叙事特色,如考察武松打虎和李逵杀四虎情节,金氏“深入到人与虎较量的两回书的所谓‘重复中的差异’,从而揭示了《水浒传》似真传神的审美追求”[4]。刘璋小说中的梦境情节亦正是这种“同中有异”“特犯不犯”艺术特色的具体表现,使读者真切体验到小说不同旨趣的妙笔。
(二)不同的占卜情节
刘璋小说中的占卜情节也具有其多样性,体现了明清时期社会上的一些信仰民俗。以占卜类型来分,刘璋小说中展现了求签、相面、枚卜等占卜方式,展示了时代与地域文化特色。
其一,求签类的占卜情节体现了明清时期山西民间神灵信仰的民俗。《飞花艳想》中有柳友梅的两次占卜均在庙庵中为婚姻而求签问卜,第一次是在栖云庵向伽蓝菩萨求签,第二次是在杭州的一处古寺在大汉关帝像前求签。明清时期,除观音大士等菩萨信仰在社会上比较流行外,关羽也受到人们较多的崇敬与礼拜。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明清上层统治阶级的推崇不无关系。据《宛署杂记》记载,仅北京宛平区内的关王庙主就有50余座。而在清代,随着山西商业的发展,晋商更是因关帝的信义而将其视为财神。关羽又是山西解州人,山西百姓对关羽这位前辈更是依赖与推崇,在晋商活跃的经商活动中,“不断地新建祭祀关公的坛庙”[5]。刘璋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商业相关的情节即为佐证,如巨富汪百万、商人之子王楚兰都是作者赞扬的对象。刘璋中出现的相关求签占卜情节,正是这种时代与地域文化的深层体现。
其二,与相面相关的占卜情节。“相面术”亦是历史悠久的一种民间风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大多世情小说中,“相面师”除与其他占卜类型相似的串联故事情节的作用外,更多的是借相士之口叙相面者之不凡,也对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做出预示。《斩鬼传》中即通过袁天罡的后代袁有传之口说出钟馗之相貌不凡,“只见钟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俺这半日,都是些庸庸碌碌,并无超群之才。这人来得十分古怪!’”“足下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更有两额朝拱兰台,自有大富大贵之相。”从钟馗之相貌上点出其不凡。“只是印堂间现了墨气,寻日内必有大祸。”[6]此则对钟馗接下来的遭遇进行了预示。另外,从钟馗对于占卜结果的反映进一步深化了人物的形象:“君子问凶不问吉,大丈夫在世,只要行的端正,至于生死祸福,听天而已,何足畏哉?”[6]
其三,枚卜起课相关的占卜情节。枚卜是通过静态的观察,“表现出对未来生活的关注”[5]。《飞花艳想》中第十五回“掷金钱喜卜归期”即是如此。梅如玉与雪瑞云通过李半仙枚卜起课的方式来问柳友梅与雪太守的归期,这形成了一种预叙结构,为下面故事情节的展开做了铺垫。
其四,观天象类的占卜方式。观天象的占卜方式是通过天上的云气与异象来判断吉凶的方法。在古代,观天象类的占卜方式多与统治阶级有关,如《国语》中即记载楚人“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的“视祲”行为。在刘璋小说《幻中真》中亦出现了占天象的占卜方式,“天上彗星出现,大如鸡卵,有数十道毫光,照耀如同白日,半月不散。京师里边又地震数次。”于是皇帝颁诏“大赦无辜”,主人公吉梦龙也因此被释出监。此小说情节的背后也暗含着时代内涵,明清时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活动“较之历代更为频繁”[7],这些修省罪己与大赦天下等行为往往发生在天灾或异象之后,是安抚百姓的重要举措。
山西大地上自古即盛行占卜谶纬之术,有着深远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左传》涉及晋国的篇章当中,多次记载了晋国战争前所发生的占卜、梦境、天象等充满神秘色彩的相关史实,如“秦晋韩之战”“城濮之战”“子犯为晋侯释梦”等相关篇章中的故事情节均有所展现。即使是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山西民间占卜习俗也多有表现。如在山西晋城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与“三仙姑”这类沉迷占卜、鬼神的普通百姓形象就是作家批判的对象。活跃在清初的山西阳曲作家刘璋小说中的占卜与梦境情节实际上正是封建社会下民风民俗的自然流露,亦是百姓、士人再到统治阶级普遍的迷信心理的展现。
二、占卜与梦境的叙事特色
刘璋小说中的占卜与梦境情节中,展现出其特有的叙事技巧,主要体现在其空间塑造艺术以及结构特色两方面。
(一)独特的空间叙事
刘璋小说中的占卜与梦境的空间设置并非随意生发,而是与主人公现实所处的环境与占卜、梦境的内容有着直接联系。从梦境或占卜情节发生的场所来看,刘璋往往将这些情节设置在家宅、庙宇、花园等场所中发生,而这些梦境与占卜空间场所的构造上明显有其独到之处。首先体现在现实空间与梦境或占卜空间的关联结构。苏轼在评价陶渊明《饮酒(其五)》“悠然见南山”一句之妙处时认为其“境与意会,故可喜也”[8]。而这种“境与意会”的描写,在刘璋小说中占卜与梦境的相关情节刻画中也有体现,《飞花艳想》第五和第六回中柳友梅宿于栖云庵,此庵位于杭州城外的一座旷野,“树影阴翳,竹影交加”“幽雅可爱”。“那小庵门前抱着一带疏篱,曲曲折折,鲜花细草,点缀路径;到得庵门,门栽着数株杉树,排列着三四块文石。”[9]景色宜人,俨然一副静谧的风景画。在这个幽然的小庵中,主人公柳友梅由老僧带领前往伽蓝菩萨像前占卜婚姻,得到五花为梅、六花为雪、婚姻两重的占卜结果,而这恰好符合柳友梅想要迎娶二位佳人的心愿。称心如意的卜卦结果与现实空间中小庵的优美景色显现出高度一致。另外,柳友梅在庵中借宿时的空间设置也体现了梦境与现实的一致性。梦境中,主人公柳友梅与五花仙子、六花仙子共度巫山,梦中的空间环境则是另一幅优美的风景画,“忽走到一座花园,四周花木,一带槿篱环抱着曲池,流水潆绕着石经……周围绕着那座亭子,亭子上梅花如雪,香气连云”[9]。这一场景的塑造一方面有利于烘托二位仙女姿态容貌不凡的形象,为几人的云雨提供了合适的场景;另一方面则与柳友梅所处的现实环境栖云庵之景相吻合。
刘璋在刻画小说梦境与占卜相关情节时,往往设置一种中转空间,来改变主人公的行迹,从而加快故事进程。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幻中真》中吉梦龙误入深山的情节。吉梦龙来到宜兴的龙池寺借宿并题诗,实际上这借宿以及题诗情节意在引出静玄大和尚对于吉梦龙的占卜情节,并借大和尚之口催促梦龙早行。从某种程度上说,龙池寺本身没有特定的含义,它是主人公游历旅途中的短暂一站,但借此引出的深山遇神猿情节则是关键。自龙池寺出来后,吉梦龙流连于深山,由神猿指引进入石壁,习得天书。而从山中走出之地并非是来时南直隶的宜兴县,竟是相隔三千余里的山西。这一深山具有明显的空间转换作用,不仅使主人公发生了时空上的转变,使他离妻子家人更近,而且使他得到了天赐兵书,为日后习得兵法平定山东叛乱做了铺垫。
刘璋作品中的类似描写并不止于此,再如《斩鬼传》中钟馗受唐王所封成为驱魔大神后,并没有直接在阳间斩妖邪,而是先前往阴间,受阎君协助,得了坐骑白泽、三百阴兵以及咸渊、富曲二位英雄,而后才返回阳间斩妖除鬼。实际上,阴间在《斩鬼传》中亦完全可看作是中转站之作用,钟馗的行迹可简要梳理如下:
(1)在阳间:卢杞进谗言,钟馗因此自刎而死,受封成驱魔大神;
(2)往阴间:得到阎君帮助,获得斩鬼“任务”,得到斩鬼助手与坐骑;
(3)重返阳间:斩鬼除妖;
(4)完成斩鬼“任务”后再次回到阴间:得知奸臣卢杞等人罪有应得的下场;
(5)入天门:受到玉帝封赏。
由此可见,钟馗两次前往阴间与斩鬼情节并无必要的联系,阴间的相关故事情节也并非不可代替,实际上阴间也可看作是连接两次阳间活动以及阳间与天府间的转换场所。
(二)多样的结构作用
美国批评家卡勒认为:“行为功能是故事事件在整个故事中起的作用,每种行为功能都是由接下去的一连串行为功能限定的,只有确知了后面已发生的事,才能确定前面事件的功能。”[10]占卜与梦境作为小说人物的功能性行为,自然服从于小说中主人公的行为与目的,起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刘璋小说中的占卜与梦境情节亦是如此,这主要体现在其才子佳人小说中。在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作者一般通过设置拨乱小人来作为功能性人物串联故事情节,达成才子佳人终成好逑的结局。而在刘璋小说中占卜与梦境叙事情节明显较其他才子佳人小说更多,于是作者往往在文中设置相士、庙宇、和尚道士等占卜相关的功能性人物或梦境来串联故事情节,从而分担一些拨乱小人串联情节的功能。
占卜与梦境叙事的情节推动作用首先表现于其在小说中的隐线作用。金圣叹将“运用某种事物贯穿全文中以增强情节有机性的艺术构思方法,形象地总结为‘草蛇灰线法’。比喻在文学创作中多次交代某一特定事物,可以形成一条若有若无的线索,贯穿于情节之中。这条线索,犹如蛇行草中时隐时现,灰漏地上点点相续,故喻之为草蛇灰线”[11]。实际上,《飞花艳想》中的占卜与梦境情节亦有此作用,从故事开始柳友梅遇见并钟情于二美再直到故事结束婚姻两重,终成眷属,其间由三次占卜情节(第六回、第十一回、第十五回)与一次梦境情节(第六回)贯穿整部作品,且内容均与婚姻相关。由此观之,占卜与梦境情节在《飞花艳想》中的确起到了“伏线千里”的隐线作用,从而使小说内容整体化。
其次,占卜与梦境情节之作用体现在“占卜/梦境—实现”的预序结构上。小说中往往将与功名和婚姻相关的占卜梦境情节安排在故事发展的开始阶段,为故事发展定下基调。《飞花艳想》中主人公柳友梅借宿庙庵时,涉及两处有关梦境的描写。第一处为庵中老僧之梦,梦见此庵中伽蓝菩萨吩咐他道:“明日有柳月仙到此,他有姻缘事问你,你须牢待他”[9]。另一处为主人公柳友梅在庵中之梦,在合欢亭与二位仙女——五花仙子、六花仙子巫山云雨,共度良辰。于是再由老僧这一功能性人物点出主人公的姻缘“不在梅边定雪边”的预言,从而使柳友梅的行程轨迹及心理历程发生转变,给予读者一种“婚姻两重”的心理暗示的同时,也使故事结构更加合理。但故事发展到最后,果然是柳友梅与梅雪二位佳人终成眷属,从而构成“占卜/梦境—实现”的结构。“占卜/梦境—实现”结构对于小说情节最直接的影响即为设置悬念作用。古代的世情小说往往利用占卜与梦境的神秘性来设置悬念,从而达到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好奇心的目的,刘璋小说也不例外。以《斩鬼传》为例,相面先生袁有传为钟馗相面时,道其有大富大贵之相,然其“印堂间现了墨气,寻日内必有大祸”[6]。而后来随着故事发生,钟馗果然在金銮殿自刎而死。这既为后文钟馗的祸患做了铺垫与揭示,又能使故事结构更加完整,迎合了人们的好奇心理。
最后,刘璋笔下的占卜与梦境叙事并非相互隔绝,相互独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小说的完整结构。如上文所提到的《飞花艳想》,柳友梅两次在神像前求签:第一次在栖云庵的伽蓝神像前,第二次则面对宜兴的关帝像,但两次占卜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结果上都完全相同,“依旧是栖云庵的签诀”。林莹认为,人物叙述自觉“文本参与”的表现有两种,其中一种即是重提旧事的“温笔”,“指人物在非必要的情况下重温前文,使绵长的文字序列共享某些值得反刍的重要内容。”[12]如果将签诀内容看作是一种变相的“文本参与”,那么显然,第二次的占卜情节有回顾前文的“温笔”作用。
这种占卜与梦境的互通结合作用在《幻中真》中展现得更加明显。第四回吉梦龙于梦中梦见神仙预言其牢狱的“十月之期”,而他出狱的原因并非是人为之力,实际上与占卜密切相关。在其入狱第十个月,“天上彗星出现,大如鸡卵,有数十道毫光,照耀如同白日,半月不散。京师里边又地震数次。”[2]皇帝颁布诏书,使吉梦龙大难不死,出离牢笼。这构成了上文“预言—应验”的完整结构:前文梦境情节是后文占卜情节的预言,后文占卜情节是前文梦境情节的应验。除此之外,上文提到的和尚静玄所作偈言的第一句“遇猿开石壁”与吉梦龙入深山受神猿所赐天书情节相对应。如果将深山幻境看作是梦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那么静玄的预言与深山幻境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占卜与梦境”双向互动,从而使小说结构更加完整紧凑。
三、占卜与梦境情节背后蕴含的价值观
文学作品的背后往往蕴含着作者深层的思想内涵,正如韦恩·布斯所说,“当人的行动被赋予形式,创造出一部艺术作品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形式就永远脱离不了人的意义,其中包括每当人行动时就暗含于其中的道德判断”[13]409。刘璋在小说中对于梦境与占卜情节的塑造往往寄寓了刘璋本人的善恶因果观以及其对于科举不第的精神寄托。
首先是梦境与占卜情节中体现的因果报应观念。先看梦境相关情节,《巧联珠》中,主人公闻友关于科举功名的梦境与善恶报应直接相关。闻友在进京赶考路上梦见文昌帝君宣读本科中举名录,而第五十三名胡同“好贱淫人家妇女,前到山东,又冒认人家婚姻”,“因他三代积德,三心忠厚,所以该有大贵之子;因他父亲立心不正,放债图利,十分刻薄,折去他进士,与他一个乡科,今他自又犯淫戒”,于是革去他名字。“秀才闻友少年才美,能不涉淫戒,持《太上感应篇》甚敬”[3],将其补上,另外还有革去的,均查有行的补上。揭晓之日,闻友果然中了五十三名。作者借梦境中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关于果报观念:“万恶淫为首。上天所最恶的,有人犯了淫戒。有功名的减功名,无功名的折福寿,还要将自己的妻女去赏人。”[3]弗洛伊德认为,梦“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梦中所呈现的情景“是一种愿望的满足”[14]。当然,国外的梦境分析理论并不能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梦境构建一概而论,但仅就刘璋小说而言,其梦境情节设置不仅可见刘璋本人对于名教及果报之看重,亦符合人物的潜意识投射。
再查其占卜情节,仍以《飞花艳想》为例。主人公柳友梅两次路过庙宇,占卜的结果近乎相同,“五十功名心已灰,哪知富贵逼人来。绣帷双结鸳鸯带,叶落霜飞寒色开”[9]。即功名富贵,婚姻两重。而上文提及的伽蓝菩萨助柳友梅之姻缘占卜并非偶然,实际上亦可归为善恶果报。老僧与柳友梅之父柳继毅曾有过交往,在京时,曾蒙柳继毅护法,柳继毅“是极信善”的,从报应观念来看,柳友梅受神相助亦是其父行善的果报。
刘璋的因果善恶报应观念多由占卜梦境表现出来,其实这种因果报应观念在才子佳人小说中较为常见,但通常是由才子佳人大团圆,拨乱小人受到应有惩罚来体现,只是在刘璋小说中展现得更加明显。除上述通过占卜、梦境表现外,还通过小说叙述者直接表达。《幻中真》十二回本醒言中直叙:“为善者降祥,为恶者降祸”[2]。而这也直接在故事当中展现出来,吉梦龙之父为人忠厚,其母素性温良,“积代好善,斋僧布施,补路修桥;遇人患难,无不拯救;逢人贫困,莫不周施”[2]。于是一直苦于子息艰难的夫妇二人终于求子成功,而所生之子日后的不凡亦是通过梦境来预示的,“将分娩之际,梦一黄龙入室,遂生一子”[2]。甚至为了实现因果报应的结构加入违背才子佳人现实主题的神异元素,如逼迫素娥母女俩让出房产的易任家中妖异百出,见神见鬼,女儿为娼,儿子充军,自己也被收监半月而死。助纣为虐的地方官白有灵为事革职,充军边外,最终被做主人公吉梦龙(汪万钟)所斩。
其次是作者刘璋屡试不第的遭遇之下,在作品中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士人所有的精神寄托。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刘璋本人于现实生活中科举蹭蹬,屡试不第。他康熙三十五年(1696)中举人,其后一直未能考中进士,直至雍正元年(1723)才被授任深泽知县。在这27年间,春闱屡试不第一直是其心中的隐痛,难免将个人的主观愿望诉诸作品之中。在小说中,那些有才无德之士人或尸位素餐的污吏,便成了作者谴责的对象,如《幻中真》中学子阶级的易任兄弟与胡同,又如《斩鬼传》中的奸相卢杞。而这些人的下场多通过梦境或神异事件展现出来,易任家中妖异百出、胡同则被革去功名,卢杞因果轮回在地狱中被下入油锅,而后众阴兵分而食之。相反,对于伸张正义的正面人物,正直的官员与士人则同样有着应有的圆满下场,除展现出刘璋的果报思想之外,还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寄托于小说的情节之中。
不仅如此,除占卜与梦境情节之外,文中其他情节亦能作为管窥其渴望功名的情感寄托之佐证。如刘璋小说中出现的另外一种现象,即才子在考中举人之后,并未参加会试或殿试而直接获取功名,如《凤凰池》中的云剑、《巧连珠》中的闻友。小说《凤凰池》中云剑因病错过会试,只因皇帝赏识人才,“钦赐云剑进士,与琼林宴”。《巧连珠》中闻友亦是如此,其虽年少才美,诗才横溢,然从小说中其应试表现来看,其科举方面的才华并不如刘璋其他几部小说中的才子,从其乡试仅中五十三名即能表现出来,而他能够考中举人第五十三名也只因胡同被革除后由其补缺,如果闻友参加会试,其未必能够一举功成。这一情节之中亦是有着梦境的预兆。为使故事情节更加合理,作者又一次在闻友的诗才上大做文章。皇帝亲自考校其诗才,出题做《文华殿赋》(何晏体)、《平番凯歌》(李白《清平调》体),闻友俯伏金阶拾笔而就,于是皇帝大喜,封其为翰林学士,赐进士出身。明清科举考试制度严格,要想获取进士功名必须迈过八股取士的门槛。小说中闻友之进士功名完全凭借其诗才而得则显得并不合理。然而从这一情节之中,却饱含作者渴望功名的情感寄托。
上文提及,刘璋一生科举蹭蹬,中举人后一直未能考中进士,直至雍正元年才被授任深泽知县,春闱屡试不第一直是其心中的隐痛。《巧连珠》可与堂写刻本西湖云水道人《序》中署时“癸卯”,应指代雍正元年,即该版本刊刻在避讳制度较宽松的雍正元年之后。而该书在刘璋手中成书时间应更早,即刘璋出任深泽知县(1723)之前。日本亨保十三年(雍正六年,1728)《舶载书目》著录有《凤凰池》一书,可知《凤凰池》成书于雍正六年之前。[15]相同的是,《巧连珠》与《凤凰池》作者均署名烟霞散人,《巧连珠》可与堂写刻本题“续三才子书”,《凤凰池》耕书屋刊本题“续四才子书”。由此可以认为,《凤凰池》与《巧连珠》二书所作时间相距不远,且有可能均作于作者中举后至出任县令前的27年间。于是,可以更容易地把握《巧连珠》中闻友与《凤凰池》中云剑两位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即两位人物形象均带有刘璋本人的影子。其屡试不第、怀才不遇、为名场所困,于是将自己的希冀与期望寄托在小说当中,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来实现自己不用参加令自己伤心的春闱考试即可进士及第的愿望。
通过对刘璋小说中占卜与梦境情节塑造的分析,可明显体会其特有的叙事艺术特色以及其作品中所蕴含的道德观念。而这些情节的塑造与刻画与其所处时代、地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探究其占卜与梦境情节,不仅能领略作者所处的时代与地域文化,更能挖掘出作者善恶因果与精神寄托的深刻思想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