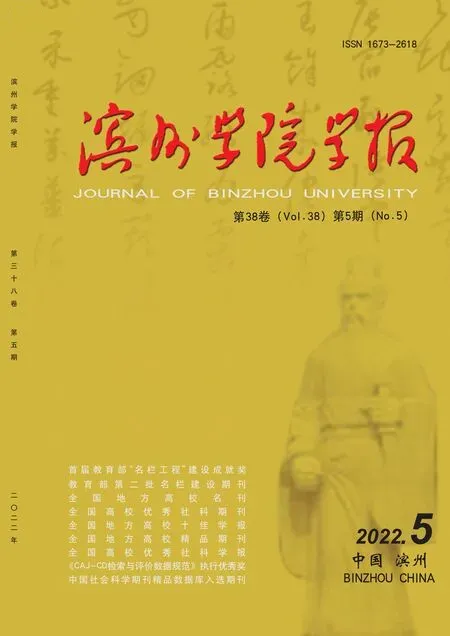跨文化视域下“那羊”与“驿马”的生态隐喻研究
2022-12-04李彦红
李彦红
(滨州学院 人文学院,山东 滨州 256603)
在中韩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和金东里都是善于运用“民间故事”进行创作的大家,二人文学创作所呈现出的共同的主题、乡土意识、流浪意识等使二者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作为二人的代表作,《媚金、豹子与那羊》和《驿马》这两部作品在爱情和命运书写等多方面均存在相似之处[1],题目中不约而同出现的“动物”——“那羊”和“驿马”更是惹人注目,因为其在自然、社会、精神等层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的隐喻。因此,从生态学的隐喻意义出发,考察那羊和驿马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心灵生态上的异同,考察二者共同的文学所指与独特的美学特征和文化特性,可以引发对文学生态学,乃至跨文化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一、自然生态隐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那羊”的外表是极美的。根据文中的描写,“那羊”这只被豹子发现的“出生不到十天的小羔”,它“一身白得像大理的积雪”,叫声是“柔弱”的。而这些特点恰与文中的女主人公是相配的,因为它的“纯白”可与“新妇的洁白贞操相比”,它的“温柔”则与“新妇一样”。而且,媚金本也是“白脸族极美的女人”,文中关于她“丰腴滑腻”的皮肤、“甜香气味”“比黑夜还黑的头发”等描写都足以证明这一点。[2]196-205即,只有极美的羊才能配上极美的新妇,这应当也是男主人公豹子为何一定要寻到“那羊”的原因之一。
“那羊”还是美的自然的代言人。首先,羊是动物,这本身便是大自然的造化。其次,从“那羊”被发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也可窥见美的自然。如文中所写,“借到星光拨开了野草,见到了一个地口”,这里涉及三个意象,即星光、野草、地口,都是自然的意象。最后一个“地口”指的是一个坑,而正是因为“近来天气晴朗”,导致“坑中无水”,豹子才得以顺利地拿到“那羊”。在这里,坑是否是天然而成不得而知,然地是自然的产物,坑的无水显然是大自然的推力。如此一来,星光、野草、干坑、那羊已浑然成了一体。据此可以说,“那羊”从出现便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再次,再看更广阔些的环境背景。“那羊”被发现的地点是豹子所在村庄通往另一个村庄的道路上,文中关于村庄没有着墨描写,但是关于村庄周围环境却有着详细的阐述。如“到秋来满山一片黄”的唱歌山、“包围在紫雾中”的野猪山、“铺满了白色细沙,有用石头做成的床同板凳”和“有天上凿空的窟窿”的宝石洞等等。这些景致无不在诉说着美的自然。
综上可知,美的羊衬托着美的人、美的自然,美的自然又孕育了美的人和美的羊,三者彼此联系,互为关系,共同谱写了一曲美美与共的颂歌。而这种对美的赞颂恰能很好地反映出“美在生命”的沈从文的“独特的生命美学观”[3]。而三者的互为关系也从侧面烘托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
不同于《媚金、豹子与那羊》中“那羊”的实在,《驿马》中的“驿马”可以说是虚拟的。“驿马”并非以实际动物的形式登场,而是借原意为国家传递公文等的驿马来表达有“驿马煞”的人。然马虽虚,却着实是贯穿全文的核心所在。
一方面,驿马诉说着凄美的人。《驿马》中的人物并不像豹子和媚金那般拥有极美的外表,但是“椭圆形的脸上一双眼睛黑白分明,花朵般鲜艳”“有发达的四肢、胖乎乎的双手和小巧的厚嘴唇”“红扑扑的、健美的小腿”[5]57-75等有关身体的直接描写在通过感官的刺激诉说“肉欲的爱情”[1]的同时,也明显传递出健康与青春的自然之美。然而“驿马煞”的存在使得主人公在享受过恋爱的欢愉之后便“沉浸在哀伤中”,甚至“带着怒气”,最终相爱但不得不分开的两人共同诉说着凄与美的合力。
另一方面,驿马衬托着凄美的自然。这点是通过“驿马”展示出的地点表现出来的。“驿马”所代表的流浪必然要伴随着地点的转换。作品中的地点也如《媚金、豹子与那羊》那般展示着不同凡响的自然之美。“载着青山与黑色苦栋木的倒影,湖水般静静盘桓流动”的小溪首先开了美之先河,接着还有“流淌着的溪水与岩石、山峡的壮丽风光”和“郁郁葱葱”的智异山小路等等。显然,这些美不胜收的风光都在展示着自然的美好。然而不同于《媚金、豹子与那羊》中自然的单纯的美好,《驿马》中的美好中还平添了“一份凄凉”,如“山谷的稚鸡的叫声听起来好像旷野里秋虫的悲鸣”“布谷鸟的叫声使人感觉可怕起来”等。不同于《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唯美,《驿马》中的自然却在美中平添了凄凉的调子,加上了命运的隐喻[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有驿马煞的人,还是随着驿马辗转而出的自然,其体现出的凄与美是并存的,这恰恰证明了“凄能与美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6]。从这一点上来看,金东里也在一定程度上诉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然而相比起沈从文笔下的美美与共,金东里笔下大自然的美丽与杂糅着淡淡哀伤的牧歌情调相配,这也正是金东里赋予《驿马》的诗意倾向的审美体现[7]。而凄美所暗含的伴随着泪水的生命美感,更多的则是韩国“恨文化”的外显[8]。
二、社会生态隐喻:人与人之间爱的桥梁
在豹子与媚金的爱情故事中,“那羊”是主人公伟大爱情的见证者。首先,羊是爱情的信物。恋爱中,男女间互送信物古来有之。文中豹子要送媚金的羊与媚金要给豹子的荷包等均可以理解为这种定情的信物。而所谓“睹物思人”,定情信物在一定程度上实则代表着相赠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羊已经与豹子有了紧密的联系。即要赠予媚金的定情信物羊实则代表着豹子本人,代表着爱情。其次,羊是爱情的承诺。羊是豹子答应送给媚金的。答应便是一种承诺,在后文,豹子在找羊的过程中几次提及找羊是他“第一次与女人取信的事”,也就是“第一次答应了女人做的事,就做不到,此后尚能取信于女人么”。据此,可以断言,豹子之所以花费那么大力气寻羊正是为了“守信”,这是他做人的原则,更是对爱情的尊重。基于此,羊在文中便有了男子信守爱情、对爱情忠诚的隐喻。再次,羊是女子的隐喻。相比起豹子的勇猛,羊有纯洁、温顺、细腻、柔弱,甚至甘心臣服、任人宰割的传统意义存在[9]。而文中的“那羊”恰是这样的羊。这种与女性在诸多方面都契合的气质使得“那羊”隐喻了媚金[10]所代表的女子。
可见,“那羊”隐喻完美的爱情。虽然豹子预期的完美恰因寻羊的过程出现了偏差。但是纵然是死亡,豹子和媚金的爱情依然是热烈的。最终,豹子向媚金献上了羊,也从某种意义上“换取”了媚金的血。从这个意义上讲,羊的价值实现了也发挥了其在爱情中的作用。而这点特别体现在豹子和媚金的结合上。媚金临死前曾与豹子带来的羊亲嘴,再联系之前说的豹子在发现羊一身雪白后,也“忙把羊抱起来亲嘴”这个举动,可以得知,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羊,二人已然实现了“结合”。当然这种结合比起豹子和媚金曾经期待的肉体上的结合,更偏精神性。此外,豹子和媚金虽因“那羊”而成悲剧,然后世却没有因此而将“那羊”视为爱情的禁忌,相反,后来“每一个情人送给他情妇的全是一只小小白山羊”,且“男人总说这一只羊是当年豹子送媚金姑娘那一只羊的血族”,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忠诚,与这恋爱的坚固”,这充分说明“那羊”的爱情作用已被世人认可,已然成了一种符号。而且,在寻羊时又多次拒绝羊的豹子证明,他的承诺其实不是羊,而是“那羊”。他追求的不只是“守信”,更是完美。因此,“那羊”不只关乎对爱情的忠诚,更关乎爱情的完美。这份完美的爱情,是由完美的外表、男子的忠诚守信和女子的贞洁等因素共同构成。显然,“那羊”具备了这完美的所有因素,自然便入了豹子的眼,让它充当起完美爱情的代言。而这种追求完美爱情的爱情至上主义恰是沈从文对爱情理想追求的体现。[9]而这种完美同样也从侧面印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种人际间的和谐再次衬托出中国人对和谐文化的追求[11]。
同“那羊”一样,《驿马》中的“驿马”也在爱中担负了桥梁的作用。与豹子和媚金山歌定情后,“那羊”只是为完美爱情增添筹码不同,性骐与契妍的爱情可以说绝对有赖于“驿马”。据契妍父亲所述,在他带女儿契妍来到花开集之前,他至少经过了“丽水—求礼—木浦—光州—珍岛—求礼”的辗转,而根据“带着这么大的孩子怎么赶路”的询问,可以推测出在这些辗转中,至少有过契妍的身影。正是她像驿马般随父亲辗转,才有了花开集暂居玉花家酒馆的经历,而这一经历显然为她与玉花的儿子性骐相遇并相爱提供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驿马”甚至可以说是成全性骐与契妍爱情的手段。而这点,不仅体现在性骐与契妍的爱情上,性骐奶奶与只在那里演出了一天的男艺人的结合,母亲和云游四方的和尚缔结姻缘,均是拜驿马所赐。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爱的桥梁是不稳定的,因为古代用于传递公文的驿马,其意就是多方奔波,用小说中的词讲就是“流浪”。文中的男主人公性骐“八字里注定流浪”,女主人公契妍的父亲也是“本想到死也不出门流浪了,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于是带着女儿依旧流浪。“驿马”指注定流浪,只要活着,便不会终止在某一个地方。男艺人走了,留下了怀了玉花的性骐奶奶;和尚走了,剩下有了性骐的玉花;契妍走了,留下了性骐。甚至不同于上述的爱情,在母子之爱中也存在性骐走了,只留下了玉花。驿马的离开似乎让爱的桥梁塌陷,落下了孤独。
面对离别的驿马,文中的人物几乎清一色地选择了远望的态度。性骐“呆呆地望着渐渐远去”的契妍,玉花“透过垂柳遥望”性骐的背影。当所爱之人要离去时,留下的人选择的是哪怕独自承担孤独,也要默默地相送,这里面显然蕴含了“对无法实现的梦想的憧憬、遗憾和无奈”的韩民族的“恨文化”[8]。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曾经做过男艺人的老头儿也好,还是没有选择爱情的性骐也罢,他们在提起爱情时都是记忆犹新,而非忘却的。因此,如“那羊”一样,“驿马”虽然也让爱情无果,让母子不能守在一处过活,却绝称不上是爱的终结者。因为,不在一起不代表爱的不在。爱发生过,长久后仍会让人“悄悄搜寻记忆的痕迹”,这显然不是无爱的表现。在每一匹“驿马”的孤独外表下,其心灵深处都交织着甜美与忧伤并存的关于爱的回忆。在面对分离的远望中,显然有爱与恨的交织。
综上所述,“那羊”和“驿马”都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那羊”甚至成了后世爱情的代言。然而“驿马”因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在流浪中既成就了爱,又为爱留下了孤独与悲凉,是“恨爱”的缔造者。显然,前者更关乎至上的爱情,后者则多了些韩民族独有的“恨”的气质。
三、心灵生态隐喻:人与神的契合
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作者沈从文不止一次地提到“神”,如“所作的纵是罪恶,似乎神也许可了”“拿去献给那给我血的神”等等均是如此。且先不论此处的神与人们日常所说的神究竟是否一致,单就这个说法来讲,沈从文是认可了。
在作品中,羊是近神的。古今中外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用羊祭神的记载,而这种祭祀就是人们在通过羊表达对神的虔诚和敬意。文中,豹子去地保家寻羊时曾明确表示过,他寻羊是为了“拿去献给那给我血的神”。即,羊在豹子的概念中也同样是为了献神,只不过,豹子口中的“神”,更代表的是他心目中的女神,显然与一般意义上用羊祭祀的对象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当豹子言说自己“比起新妇来,简直不配为她做垫脚蒲团”时,跪在神脚下蒲团上的那微不足道的人的形象便一览无余了。尤其是豹子献羊,是为了祈求神对其“所做的纵是罪恶”的“许可”。那么在这里,用羊献祭,换取神对人罪恶赦免的意义就更加明确了。显然,这里的神已不再单指女神,而是要凌驾于人之上的神了。
此外,羊的近神还体现在文中那羊是“天赐的”这点上,因为“那羊”是豹子在村中到处想求都没寻到,去别村的路上无意间在路旁草里发现的。这份“天赐”使“那羊”从出现便有了几分神意。
羊的近神为人与神的交流提供了机会。将羊献祭给神时,献祭的人也是近神的。豹子通过对“那羊”的追寻,表达自己对神的谦卑和膜拜,不停地追寻“那羊”也意味着不停地追寻着神。从这个意义上讲,豹子寻找羊的这个出发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与神的和谐,至少是和谐的指向。而“那羊”恰恰就是人与神和谐关系的一个反映。作品中,如果豹子能将那羊顺利地献给他的女神,而女神也接纳了,那该和谐关系将达到最大值。
然而,这份和谐却恰似被“那羊”打破了。在求羊的过程中,豹子曾对作为预言家、相面家的地保说过:“我来此是为伯伯匀一只小羊,拿去献给那给我血的神。”通过地保“一惊”的反应和对“凶信”的预测,以及最终二人自杀的结局,可以得知,“血的神”的出现显然就已经决定了这场爱情势必是悲剧的命运。在这里,神与命运挂上了钩。因此,这里的神不只是豹子至上的爱情,更拥有了能够左右人命运的权威。当然,沈从文通过会相面的地保还赋予了它些许巫俗的神秘,但无论如何,都是在诉说着“在喜事上说到血”与死亡预兆之间的联系。而这些命运与巫俗的神秘均因“那羊”得到了实现。作品中也直言“都因为那一只羊,一件喜事变成了一件悲剧,无怪乎白脸族苗人如今有不吃羊肉的理由”。
关于“那羊”与悲剧命运的关联在文中有多次呈现。作品中“那羊”是“天赐”的不假,然而被发现的时间是错位的,“那羊”是在豹子找遍了全村,又要到另一村去寻的路上发现的,但是那时应当已过了豹子和媚金约定好的“见了星子就来”的时间。“那羊”是“白得像大理的积雪”不假,但却是“一只脚跌断了”的,刚出生的羊因掉入深坑而瘸脚,不由让人联想到出生就被抛弃的双脚肿胀的俄狄浦斯王,这跌断了脚的“那羊”似乎也在昭示着无法逃遁的宿命。而豹子、媚金死后“那羊”也是“业已半死”的状态,这符合悲剧的结局。如此一来,羊便成了神意的载体,而豹子和媚金最终也成了神意的实践者。
然而,我们在注意这种宿命式的神意时,也不能忽略这背后隐含的,正是人对神的追求。
一方面,这个神意的命运是由豹子自己说出口后而有的。在豹子的心目中,媚金对他便是神一般的存在。而宝石洞之约的目的恰是要取得媚金的贞洁。因此“献给那给我血的神”便应运而生。但是豹子只关注了自己的追寻,却未曾想血还有血光之灾的另一层含义。“喜事上说到血”已让老地保有了“预兆”,即豹子和媚金的美好初衷极有可能最终会演变成“血”的祸事。而这种颇具巫俗神秘色彩的“预言”也成了豹子和媚金结局的导向。
另一方面,这场命运悲剧提前预留了“随便”的缺口。这个缺口是通过通神意的地保表现出来的。在文中,会相面的地保一直反复在催促豹子“随便”选一只羊。那么,据此是否可以做这样一个推断,即“血的神”的出现决定了这场命运悲剧,假若豹子能够随便选一只羊就去赴约的话,那这场悲剧是能够避免的。不难看出,这个“随便”豹子显然是可以做到的,即豹子是可以突破命运缺口的。而“随便”即自然而然之意,假若豹子能够顺应自然,那么羊便不会被特指为“那羊”,反而会很顺理成章地成全豹子与媚金现世的爱情。即,羊虽然肩负了神意,但这份神意并不是绝对的,也有留给世俗人发挥个人意志的空间。然而,羊若不是“那羊”,对豹子来说,那爱情显然也不会是完美的,豹子对完美爱情的追求使得他反对“随便”的选择,他执意寻找“那羊”,执意找地保为受伤的“那羊”敷药,并且执意抱着它去宝石洞赴约。这种执着最终堵住了神留有的这个缺口。豹子的执意寻羊和献羊,可以理解为世俗人在刻意、过度地追求一种仪式感,仿佛只有献了最好的才会最完美。然而这种人为的刻意显然与神性的自然是不和谐的,执着与自然而然达不成统一,因此悲剧也是必然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豹子的这份执着正是为了他的神,只有“那羊”才配得上他的神,因此,豹子不顾一切地寻羊、治羊,以求与神达到完美的契合。即,豹子的初衷和他的所有行为全都指向神。虽然豹子的行为使得命运悲剧有了实现的可能,且最终实现了。但是也正是他的执着,成就了后世成为爱情信物典范的“那羊”,成就了豹子的“守信”,成就了爱情。
综上可以发现,沈从文笔下的神虽然也兼有宿命的意味,却更接近人心中的追求,而这个追求,不外乎正是沈从文对生命爱与美的追求[3]。而且,为了这个追求,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与神契合。这恰恰体现了沈从文创作中的“神性意识”,正是这样的“神”才使“人的生命有了意义,有了活力”[12]。同时,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也暗含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传统“和合文化”[13]634-640。
在命运的启示方面,相比起《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神的“配角”作用,《驿马》中的神更占有主导地位。在作品中,“驿马”本身就相当于神的旨意。在《驿马》中,性骐三岁时,通过被算命便有了自己人生的定论,即“八字里注定流浪”,这便是“驿马煞”。这里的“算命”本身便带有了几分预言的性质。关于算命的人,作品中提到了“住在河东穿丝绸裙子的矮个老太太”“双溪寺的老和尚”“在智异山修行的高个老人”三位,可以看出,这些算命的高人涉及多个领域,无论是民间的,还是佛家的,抑或是道家的,都不约而同地将性骐的人生定论在同一个点上,要说巧合确实也太巧了。因此,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具有某些超验性质的“命运”一词,即“驿马”就是性骐的命运,而这些算命的高人则更像神的代言人,将神的旨意传达给人。
不同于豹子为追求神而进行的对所谓命运的无意识抗争,《驿马》中专门设有对抗命运的情节。如性骐的奶奶和母亲竭尽全力想要为其“磨没”这“驿马煞”,性骐十岁起便送其去庙里当和尚。不仅如此,“只要是听他说要去哪儿,母亲就会两眼冒火,大发脾气”,甚至母亲还主动让契妍去服侍性骐,企图通过爱情和婚姻紧紧拴住性骐,让他没有机会去当他的“驿马”。然而,无论人如何抗争,最终的结果却是仍陷入命运的罗网之中。性骐母亲给儿子创造的恋爱机会,却恰恰将他推入到血亲禁忌的万劫不复当中。而当性骐说出“娘,给我置个卖麦芽糖的案板”时,“驿马”的预言在性骐身上终得实现。换句话说,“驿马”是不可对抗的命运。这种绝对性显然是有别于有缺口的豹子的命运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命运悲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信奉基督教的金东里对神的膜拜程度要远高于沈从文。西方的两希文化似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融合。
而且,在《驿马》中,“驿马煞”是延续的。当性骐奶奶说出“看来命里注定随他爹啊”的时候,当老头儿说出“这次本想到死也不出门流浪”的时候,就可以确定,这“驿马煞”是多人的。爷爷、父亲、儿子,祖孙三代都实践着“驿马”的命运,甚至随父亲辗转多处的契妍,也可以算作其中的一员。“驿马”的命运几代延续着,但无论谁,都摆脱不了这“驿马煞”,甚至可以说大家似乎都在接受着这种命运,尤其在主人公性骐处体现得尤为明显。
文中,性骐本人是有机会向命运挑战的。第一次是当契妍“用已通红的双眼最后一次寻找着性骐的视线”与他三次道别时,他从“直愣愣”到“费力地抓住垂柳枝”,再到“呆呆地望着渐渐远去的罗纱小褂儿”,却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做出任何契妍等待的“给予奇迹般的救援”的行动,此时的他尚不知晓契妍便是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姨,他完全可以挽留契妍,但他却任由对方痛苦地离开了。第二次是文末他在契妍离开的次年,选择离开村庄,在三岔口上,他选择了背向契妍所去的求礼方向,“朝河东方向缓缓移动了脚步”。已经独立并离开母亲的性骐可以选择去寻找契妍,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而且,没有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步,又一步,随着脚步的移动,他的心情也轻松起来”,最后“他竟然边走边哼起了小调儿”。“轻松”与“哼起了小调儿”足以证明他对自己选择的满意程度。即在神谕面前,他也如豹子一般,做出了自我选择,但是不同于豹子为了追求神而对命运的背离,他选择了与神走相同的路,既归属了命运,又遵从了内心。如此一来,他的心灵与神意便达成了完美的一致,这与作者金东里小说中“内涵神的人”的“与神性”也是相符的[14]。而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似也印证了金东里的东方文化观[15],证明了金东里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坚守了东方文化。
本文立足中国作家沈从文的《媚金、豹子与那羊》和韩国作家金东里的《驿马》,从两者题目中共有的“动物”着眼,结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心灵生态三个方面,解读了“那羊”与“驿马”两个意象的生态隐喻。在自然生态方面,“那羊”的极美与人和自然的极美相称,隐喻了人与自然的美美与共,而“驿马”在描写美的同时,无论人还是自然身上,都被赋予了些许凄凉。然而凄与美并存的人与自然依然昭示着和谐的指向。在社会生态方面,“那羊”与“驿马”都在爱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相对于在悲剧中依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自己完美爱情作用的“那羊”,“驿马”虽为爱搭建了桥梁,却因它本身的不稳定性让爱中充斥了韩民族“恨”的精神文化,成了“恨爱”的缔造者。在心灵生态方面,相对于“那羊”的近神,显然“驿马”的神谕是更具有权威性的。二者都隐喻了人和神的契合。其中,“那羊”更彰显了人对神的不懈追求,而“驿马”的选择则体现了人的心灵与神的契合与统一,是一种“与神性”的表现。在这些生态隐喻背后,内涵着中韩文化的异同,即在共同的东方文化背景之下,中国更突显的是和谐文化、和合文化,而韩国更多表现出来的是韩民族的“恨文化”,以及对东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