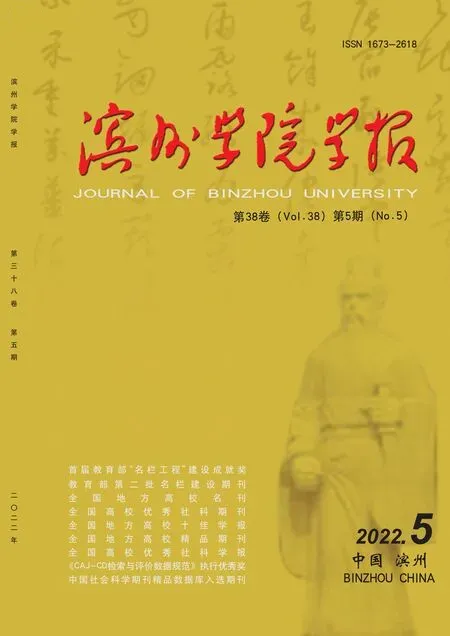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基层治理管窥
——基于地方志书写的考察
2022-12-04张斌
张 斌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民间地方力量是中国古代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用的发挥事关基层社会的稳定。有关民间地方力量的研究,学界多从绅士、乡绅和地方精英等概念入手,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构建研究理论框架,但在不同地域下地方精英力量的构成侧重不同,在参与基层治理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侧重点,因此有必要进行区域研究。黄河三角洲地区不同类型的地方力量在基层治理、稳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沾化县志》中甚至记载:“士安于庠,农狎于野,相助相望,至老死不识官府”[1]169。本文拟以黄河三角洲(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过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主要包括今山东省滨州市、东营市全部及潍坊寒亭区、寿光市、昌邑市,德州乐陵市、庆云县,淄博高青县和烟台莱州市,共19个县(市、区)。为符合明清朝代行政区划归属统一完整,本文所论黄河三角洲地域以清雍正十年武定府区域为中心,共领州一县九,包括滨州、惠民、青城、海丰、阳信、乐陵、商河、利津、沾化、蒲台。参见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2051-2052.为研究区域,立足于地方志中传统基层社会的书写,注重不同事务的基层治理运作形式,自下而上地对该区域地方精英的基层治理活动加以梳理,进而探讨黄河三角洲区域中国家与地方的互动。
一、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地方志中的地方精英
孔飞力等美国学者将对地方富有影响力的人物称为地方精英(名流)[2-3],不同地域的地方精英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征。从黄河三角洲的地方志历史书写中可以发现,民间对“对地方富有影响力的人物”概念有着自己的认同与理解。笔者爬梳文献发现,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中的地方精英至少分为乡绅、乡耆和乡贤三大群体。地方志中“人物志”所记的典型人物是地方精英群体概念的具体呈现和补充,各地地方志专门列“人物志”记载对当地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及事迹,又分列如任恤、义行、文苑、武功等众多细目,虽然不同县域的人物志细目分类有所不同,但此种差别正体现了不同地方精英发挥基层治理作用的不同路径。
对于地方精英,国家往往给予的一定优待或特定权力。如皇帝出巡泰山时,乡绅作为单独的群体列出以示区别,“地方官率乡绅、士民迎于十里之外”[4]6036。咸丰《武定府志》中明确记载,乡绅在赋税过程中享有优待,如对于乡绅、举贡生员之类的人丁税推行“合优免”。[5]152乡耆作为地方长者,多为德高望重年长之辈,明代发布的《教民榜文》中明确赋予其决断民间事务的权力:“民间婚姻、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本里老人、里甲决断”[6]352。清代更是在民间设立耆老,但此时耆老“不过宣谕王化,无地方之责”[4]5044。地方乡耆和乡绅在公共事务中经常共同出现,但耆老掌握一定的祭祀及乡里讲约的话事权。“每岁仲春亥日,府州县等率所属之员,耆老农夫恭祭先农,行九推礼。”[7]421当有诏书颁布到地方,乡绅与耆老位于文武官员之下以示地位,“绅士班于文官之末,耆老军民集于武官之末”[8]256。
乡贤入祀的激励也推动了乡贤成为基层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乡贤是一种自明代开始授予对于民间本地有卓越贡献者的头衔。自明洪武四年(1371)开始,诏令在各地建立乡贤名宦祠,并对本朝及前朝的乡贤进行推选,由地方选出后经官府层层予以确认。乡贤的选拔和祭祀,对于教化地方风气有重要意义。民国《青城县志》中记载“举乡贤以光国典,以励风化”[9]552,《建乡贤名宦祠碑记》则用“以祠彰善阐幽,劝来者也”[10]56阐释乡贤入祠的作用。乡贤的推选也有民间的认知标准,“德修于家则为乡贤”[7]895“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传于世者谓之乡贤”[11]500-501。由此可见,民间对于乡贤的推崇主要还是基于道德和学问。明代以后重修的地方志中也多特列乡贤加以记载,而对地方志乡贤人员的修订也十分谨慎,如无法确认,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保持空缺。如咸丰《滨州志》在记载元代张德新时本应参照前志补入乡贤传,但“出身无凭查考,不敢增入,仍缺之”[12]20。乡贤祠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分布十分广泛,利津、乐陵、青城、沾化、邹平、博兴、无棣等地都曾记载建造乡贤祠。
综合来看,地方精英群体虽然或多或少受国家影响发生作用,士人的形象特征极为明显,但在国家影响较弱的基层社会,儒家的伦理内核依旧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文化符号和行为规范认同了这些精英,赋予他们社会凝聚力并宣扬他们的优越性”[13]。地方精英因此形成的民间权威甚至可以荫蔽后世,深受民间尊重。明代乡贤李聪,“成化间,以子芳贵,敕赠监察御史,人以为让德所报云”[14]251。《海滨潘公传》中曾记载沾化缙绅之子中举后的民间反应:“仲子士彦举于乡都之人,士走而相告曰:此天所以彰有德”[1]619。
二、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基层治理生态
黄河三角洲的地方精英广泛参与到基层治理的各个过程,参与方式有共治和自治两种。
(一)共治视角下的工程修葺
长期的战乱以及匪患导致黄河三角洲地区不少建筑年久失修,加之元朝对城墙大肆破坏,许多城墙残破不堪。刘效祖记载:“正德间,流贼突起,山以东七十二城遭残破者多矣。”[10]63上至文庙、考院,下至城墙、县学,对于涉及地方公共领域内建筑物的修缮,黄河三角洲地方精英几乎参与工程修葺全过程。
在公共设施的修缮过程中,地方精英充当了地方智库的角色,其建议和意见是地方官员动工的重要参考。正式动工前,地方官员往往将地方精英聚集起来征询意见,确保万无一失。在引沁河济运河时,虑及盐河是否能够容纳,地方官员“细询绅士民人,令各抒所见,讲求万全之策”[10]451。咸丰《武定府志》中记载,重建利津县学时“爰与学博蒋君柱东集诸缙绅议,诸缙绅咸义阙举,而尤虑议焉而无成者屡矣”[10]94。滨州城自万历年间重修后五十年未予以修葺,受到风雨虫蚁侵蚀严重,官府意图重修时,官员也“聚诸士绅暨父老而谋之”[12]543,倾诉重修所需物资及人力的困难。地方官员事前听取地方精英的建议并给予一定的尊重,主要还是希望后期得到地方精英的支持,以便保证政务顺利进行。地方精英的意见也推动了地方古建筑的保护和遗留。清光绪二年(1876),邹平城上的魁星楼也因邹平绅耆认为“爰度以为有其举之,莫敢废也”[15]489,得以重修。青城县邑绅士则以“及未颓坏而葺完之则费省而事易”[9]511为由呈请县令重修文庙。地方精英不仅给地方事务提供意见,有时还参与实际规划。例如,海丰县重修考院时,地方官员协同邑绅现场考察,“乃召邑绅李维垿等同履勘估”[10]483。
捐资捐物、以身示范是地方精英参与公共事务常见的方式。黄河三角洲地方精英利用自身优势对民间资源的整合与再利用,在地方形成了良好的引领导向作用。例如,利津乡绅高容阁“凡邑中庙宇、桥坝诸工作先捐资为众倡”[5]530;阳信乡耆姚大志首倡义举捐资重修东岳庙,在其感染下重修工作吸引了大量乡民“捐资兴役,竞趋劝工”[16]368;众多地方精英本身作为文化知识的代表,对于地方公共的教育设施极为关注。民国《沾化县志》记载,重修儒学大成殿,“邑中绅士自百金以至一二金,莫不量力乐输,共襄其成”[17]1069。《正德间重修儒学记》记载,重修利津儒学建材耗尽时也得到了地方精英力量的帮助,“义官、乡耆等三十余员名,皆乐助才木价银百十余两”[14]353。如遇地方事务中物资缺口较大的情况,地方精英还会积极动员本地士民参与建设。康熙《新城县志》有关于重修明伦堂的记载:“诸公又捐义资于缙绅群彦,董作则委之贤慕度材更选。”[18]611地方精英作为引领地方的单独层级,委以监督责任对防止地方官员腐化,减少对于地方官员的抵触心理也有一定的作用。在《重修商河庙学记》中记载:“且立耆以劝众,设吏以监耆,委属官以防吏。”[11]497张映蛟记载重修武定府考院过程中,“官倡而民应之,以绅士领其事,不假胥吏之手”[10]116。
建筑物的修缮通常具有周期性,但对于构筑物的修葺,例如河湖堤坝、桥梁道路等经常是迫于形势紧急的需要。游百川在《察看黄河酌议办法疏》中介绍济河上下,北则济阳惠民滨州利津,南则青城章丘历城至邹长、高博等地,多处水位高涨滥溢,于是拟进行紧急处理,“急筹物料,商调熟习河工之将吏,并谆饬地方官率同绅董料集民夫,极力抢办”[19]5309。黄河三角洲地势平坦、水系丰富,一旦突遇暴雨,易发河堤溃决,从而造成严重损失,特别是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河道变换频繁,水灾频发。光绪十五、十六年(1889—1890)黄河泛滥,阳信乡耆蒋离明“联络各县绅董沿河筑长堤以资保障”[16]208。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黄河在惠民决堤,“迁出历城、章丘、济阳、齐东、青城、滨州、蒲台、利津八县灾民三万三千二百余户”[20]3761。对于筹集的修葺堤埝的善款以及物资有时也由地方精英保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善款和物资的妥善利用。民国《阳信县志》中就记载,黄河泛滥,乡民捐助修堤款项,后将所有捐助款项“移交绅董妥为安置”[16]377。
除了官府出面进行大堤的修建和保护外,清代组织民间力量修筑民埝作为常态化治水的一种形式,黄河三角洲是修建民埝的重地。光绪十三年(1887)张曜奏折中提到黄河三角洲地区部分民埝修筑情况:“齐河县民埝修筑长九千零八十七丈,惠民县民埝修筑长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一丈,滨州民埝修筑长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八丈,利津县民埝修筑长四千一百一十一丈九尺。”[21]515-516对堤坝进行修补,则多由地方官府出面组织,地方精英参与人员调度。光绪四年(1878)惠民白茅坟决口,又遇知县杨倬云离任,督修工作由地方精英援助,“绅董援徒骇堤工”[10]304。当遇到紧急事务时,地方官员甚至不惜将事务自主权交给地方精英以求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力物力。《惠民魏景晫家传》中记载:“公乃具酒馔,约耆老,而谓之曰:水势危急,堤如不保,则吾乡不可问矣。予请自任斯役。”[10]457民国《青城县志》记载了建立护城堤抵御洪水中地方精英的重要作用,“民食振而不知劳,事以义而成功速,严君之义、邑绅之功可不朽矣”[9]104-105。
在整合乡村公共资源方面,地方精英在基层的儒家伦理权威显然要比地方官吏更具有优势。基层社会的地缘性也在公共领域事务中不断被强化。实际上,处理公共领域事务中也一直存在着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互动模式,而这种互动模式就是地方精英作为国家治理缓存阶层的重要体现。赵长龄称:“自元迄明,暨我朝乾隆八年,蹱事修葺,为次计十有二。或官师倡率,绅耆佐之;或绅耆合谋,官师董之。”[10]119
(二)自治视角下的慈善和教化
为了稳定乡间的社会秩序,地方精英积极开展慈善救济义举。在开展慈善救济中,物质财富付出的多寡并不是衡量贡献的唯一标准,不少家中不甚富裕者也热心开展慈善活动。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灾害类型多样,水灾、虫灾、旱灾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贾三策在《山东旱蝗疏》中就写道:“但念被伤之地,倍宜加怜,就臣所见之切者,则有沾化、滨州、海丰等处。所闻之真者,则有利津、蒲台、武定、阳信、商河、乐陵等处。”[1]668一旦农业生产因自然灾害遭受损失,易出现无粮可食、无地可耕的情况,基层的社会秩序便会难以控制。大量个人慈善行为能够结合地方所需及时予以救助,其中就包括对地方遗孤的赡养、钱粮的赈济等。阳信人史学义长子经商致富后“为乡董建修义仓,岁饥施赈”[16]251。民国《青城县志》中记载,“县中绅董即禀请县长史公振镛设立义仓为储蓄之所,丰年敛之,凶年散之”[9]518,众乡董总共捐助了三千余石粮食,极大地填充了青城的义仓储备,增强了受灾地的抗灾能力。出于儒家宗族的意识,地方精英多开展家族性的恤孤,进行生活和教育上的救助,这也极大缓和了国家恤孤的压力。博兴人吴岚“敦睦宗族,赈贫恤孤,村人称好义焉”[8]464。开展慈善救济中也不乏为了公共利益舍弃自身的情况。邹平乡贤张玺对于民间大旱造成的聚谋劫掠现象多方抚恤,耗尽心力,“形神皆敝怔忡之病作矣”[15]1387。
黄河三角洲地方精英是兴办学务、教化百姓的典型代表。“古昔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22]797中国古代各级学校共同构成了官方教育,而在基层乡村社会,由地方精英兴办的私学是其主要的教育形式,其办学形式多以义学、私塾为主,教授儒家经典。山东作为孔孟之乡,教育氛围浓厚,但因明清战乱动荡,黄河三角洲许多县学场所废弃不用。孙承荣讲,武定州“自汉庶人败后,凋残极矣,而数十年来日甚一日,前后刺州者非岁计,即月计,刀笔筐策日弗暇给,夫谁而遑问庠序之事?”[10]468私学因办学成本相对较低、办学场地灵活、受朝代更迭以及战争影响较小等优势在黄河三角洲发展起来,不少地方精英以普及知识为己任。明正德年间阳信乡贤在城中设立专门藏书地点以方便治学,藏书量巨大,“毛中丞继贤公构万卷书楼于城西南隅”[16]379。
黄河三角洲地方精英多身怀功名,积极通过自身力量进行施教讲学。乡贤之子张毓泰对于乡中愿学的儿童“推广父乡、贤公义塾旧法,延师训之”[15]1385。灵活的形式让私学得到有效延续,武定乡贤李之庄建立义学“三十余年不废”[5]521。地方精英广泛兴办学务,自身充当师资,不仅弥补了基层教育力量的不足,还邀请其他有学之士担任教师,甚至聘请教学的费用也由自己承担。惠民赵公辅连同邑中绅士“建义学于文台之侧,延师膏火之资自任且以终老为期”[10]410-411。为保证教学的规范,他们对于日常活动设立严格规定加以约束教师,如有不称职者予以相应的惩罚。《复八社学碑记》中记载,延请长厚有行者充任教师并规定“不立章程,不勤提撕者,轻则夺其糈,重则易其任”[16]366。地方学务的兴办吸引有学识之士前来登门求学,对于区域教育氛围的改善起到一定作用。乡贤李掌圆闭户著述,“诱掖来者及门,皆彬彬文学之士”[16]237。刘文确在《义学记》中称:“师道立则成材多,士习端则民风淳。”[23]153除了兴办学务对民众加以教育外,地方精英也作为评判事理者出面调解乡间邻里矛盾,民众多信服。陈用光在《昆源贾君家传》中记载:“里闾有争竞事,得兄一言立解。”[10]144
从活动效果上看,无论是兴办学务、教化一方民众,还是施赈救灾、接济民众于水火之中,地方精英都对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的地方精英还通过设立乡规民约对基层秩序进行规范。清人王士禛记载海丰张公事迹,“县有大姓马氏同室相倾轧,公为立族长、设约束,谕以水木之谊。久之,遂为义门,其治先教化如此”[22]901-902。当然,地方精英的教化作用不仅针对整个基层社会,而且其自身的行为还对后世子孙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祖父辈民间权威形象、言行要求后代举止契合民间价值标准,侧面推动了后世子孙在基层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
三、结语
作为承载记录地方历史责任的地方志,是研究地方基层社会活动所参考的重要文本。实际上,众多地方志的编撰和修订也是在地方精英的推动下进行的。在受政治影响较弱的基层社会,刚性的法令并不适合千差万别的基层社会情况,这为地方精英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条件。咸丰《武定府志》记载:“故一乡有善士,每足以佐牧令,条教法令所不及。”[10]145具体来看,从家族伦理到公共事务,黄河三角洲地方精英参与的基层治理几乎涉及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而通过黄河三角洲地方精英共治和自治的两种路径中可以看出,地缘性的文化传承以及儒家伦理认同是地方精英力量发挥作用且得到有效延续的基础,自身素质品格以及道德追求是地方精英能够承担乡村事务的保证,国家的平台和激励是地方精英发挥作用的动力。黄河三角洲地方精英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在明清时期国家治理能力不够成熟的前提下,也确实起到了减少基层治理下沉的时间和行政成本的作用。反观在日益需要实现乡村振兴、呼唤新乡贤回归的今天,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的基层治理形式或可为发挥地方精英力量提供一定借鉴。积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进而能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国家与地方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