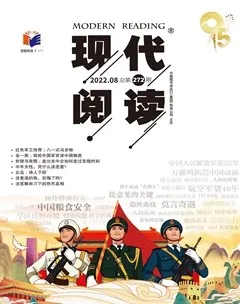儒与侠,禅与道
2022-12-02薛仁明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第五》第26章
如果我能“穿越”回两千五百年前,而且当上了《论语》的总编,我愿意把《论语·公冶长第五》第26章选为全书的开篇。
原因之一,是重要的人物全部都登场了:孔子、颜回、子路、子贡,这个顺序历朝历代基本没太多异议。开篇第一章,就先让前三号人物登场,我觉得比较符合位阶。原因之二,这一章非常具有代表性,能让我们看到孔子的魅力所在,也能读到孔门的气象所在。
一开始,“颜渊、季路侍”,颜回跟子路侍奉在孔子身旁。“侍”是以前师徒制的特点,学生陪侍在侧,跟着老师过过生活,看看老师的所有应对,也包括看老师怎么开开玩笑、说说反话,甚至还包括如何面对南子那样有争议的女人。这时,老师就不只是“经师”,而更是“人师”。
孔子闲来无事,忽然起了兴头,言道,“盍各言尔志?”你们怎么不说说自己的志向呢?
事实上,孔子之后,我们就不太容易看到有哪个儒者会老跟学生提这个问题。这是孔子很特殊的一点,他不时就要问问他的学生。大家尤其对照一下孟子,个中的氛围与口吻,完全不一样。
孔子言未落定,子路就说话了,“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他最大的志向,就是他的宝马与貂皮大衣,能与朋友共享。譬如将现代的一辆顶级好车借出,最后变成被拖车拖着回来,4个轮子还少了一个,钣金也凹了一块,可他心里面没有一点点的不爽,这叫“敝之而无憾”。
对我们来说,做到这样是有点困难的。一般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嘴巴说:“没事!没事!”可心里总是会嘀咕一下:“早知道,就不借给你了!”而有这种嘀咕,就是心里“有憾”了。
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能彻底“敝之而无憾”的,并不多见。子路所说的这种生命状态,在中国传统的典型里,并不在儒家,而是在“侠”那里。
《史记》里面的游侠,就有这种气质,也就是“侠气”。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里,体现的就是这种“侠”的精神。
如果在诸子百家里面找,可能是墨家的“兼爱”更接近一些。看墨子在当时的所作所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救人之危、急人所急,真会感受到一种侠义的精神。墨家虽然在秦汉之后看似没落了,可墨家的精神传统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尤其是在民间。
“侠”的民间传统有正、反两面,若说负面,就变成了所谓的“黑道”。可即便是黑道中人,真上了档次,也讲究个黑亦有“道”。也要有可让人佩服的人格特质,不然,又怎么能服众?单单靠手段、靠耍狠,只能混到某个级别,不太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哥”;换言之,他肯定得有某种人格魅力,有某种“德”,必须符合某种“道”才行。
如果能够理解这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司马迁要把“游侠”写到《史记》里。后代读书人多半不屑于这些黑道中人,可在司马迁眼里,他们的是非善恶固然有争议,却也有其动人之处与光芒所在。
就这个层次而言,司马迁的生命状态非常相近于孔子。孔子也会看到某些被世俗非议之人仍有其过人之处。
这个能力,按说是儒家最该有的核心处,也就是孔子所强调的“恕道”。“恕”是“如心”,将心比心,穿透表象,看到人的最骨子里去。这也是最重要的“格物”。
从子路的生命形态,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孔门里,儒家与侠客可以有某种程度的接轨,换句话说,本来儒跟侠是可以交通,并非对立的。可惜,后来的儒者鲜少有子路这样的生命状态;加上儒者越来越强调纯粹性,“纯儒”越来越掌握话语权,从此,侠义的精神淡薄了,儒门的气象也变小了。
子路之后,接着,颜回讲话了。颜回说,“愿无伐善,无施劳”。“善”,是善意,是好事,是被认可的作为。所谓“伐善”,就是被“善”所“伐”,就是因为“善”而伤人或伤己。
“善”是桩好事,为什么又会伤人伤己呢?中国人说阴阳,“善”与“不善”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阴阳的相生相克与流动互转。“伐善”就是因“善”而生出了“不善”。“好心办坏事”,这很常见;如果办了坏事,还拿自己的“好心”来开脱,说得振振有词,甚至还自觉委屈、自哀自怜,显然,这就被“善”所“伐”了。事实上,只要把自己的“善”太当一回事,大概就要出问题了。所谓“伐善”,就是对于自己所存的善念、所安的好意,不仅放在心头,还久久不能忘怀。“伐善”的前头再加个“无”字——“无伐善”,则是将对于别人种种的好、种种的善意,都能像浮云一般,过了,也就过了,完全不挂在心上。
这种生命状态就更难了。今天我们只要回头想想最日常的家庭生活,大概就明白了。譬如说,倘使我们为另一半认真做了些什么事,或者付出了些什么辛劳,对方却丝毫不领情,这时,我们不仅心里不是滋味儿,可能还会心生不平,甚至多有恼怒。而就根本说来,早先如果没做这些事、心里没有存这个“善”,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愤怒;恰恰因为有了这个“善”,我们又在意,才会好事变成了坏事。大家知道,当我们的生命还不够通透之时,常常会让一件件的好事“莫名其妙”地变成一件件的坏事,于是把自己弄得很难受、很沮丧。这“莫名其妙”的关键,正在于我们对人的“好意”不知不觉中已成了心里的一种执念,自己老在意曾经做了什么、付出了什么,这就是“伐善”。
颜回与子路二人的志向,初一看,像是风马牛不相及;可细细一想,就某个层面而言,却完全是同一回事。他们最大的心愿,无非是把生命的“实然”与“应然”彻底结合起来。当“实然”与“应然”能完全统一,人就是个真实的人,人就是个不撕裂的人;人能真实而不撕裂,才会有最根柢的身心安顿。
“愿无伐善”后面的这3个字——“无施劳”,历代争议很多,我倾向于跟“无伐善”并列成一组对偶的词句。“善”是被认可的作为,“劳”是付出的努力与辛苦。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无施劳”,刚好跟“无伐善”形成对比。“伐善”是说做了好事,如果没人感激、没人称赞,你心里会不爽;“施劳”是很努力地付出,觉得即使没功劳,至少也该有些苦劳,可一旦这功劳与苦劳统统被忽视,甚至被一笔抹杀,心里就会有委屈,会有抱怨,会心有不甘。
这样的“伐善”与“施劳”,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心理状态,我们可能常常都处于这样的状态中。这些善啊、劳啊,本来都是好事,可一旦太在意,太当回事,就会在心里不断翻搅,澎湃汹涌,平白增添许许多多的纠结,于是就产生这样的念头:我何必对人这么好?凭什么我要做得这么辛苦?这样的状态愈演愈烈之后,甚至会制造出某些冲突。这也是为何我们人生有种种的具体目标,一旦达成,却往往发现烦恼可能才真正开始,而不能获致内心真正的喜悦与踏实感。
孔门师生似乎很早就看清楚了更接近本质的这一层。所以,他们言“志”,都没谈得那么具体,而是着眼于更根柢的生命状态。“无伐善,无施劳”,明亮通透,心中无事,这是颜回的生命气象。他的这种生命状态,直接跟道家相通,也与佛教相通,尤其是禅宗。
孔门两个大弟子,一个与侠相通,一个与禅、道毫无隔阂,这就可看出当时孔门的宏大气象。
今天大家关注有没有一个好工作、一间好房子,这当然重要,但孔门(乃至整个儒释道三家)都去问更后头的那个问题——假设你有个好工作、有了好房子,然后呢?
(摘自中华书局《乐以忘忧:薛仁明读〈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