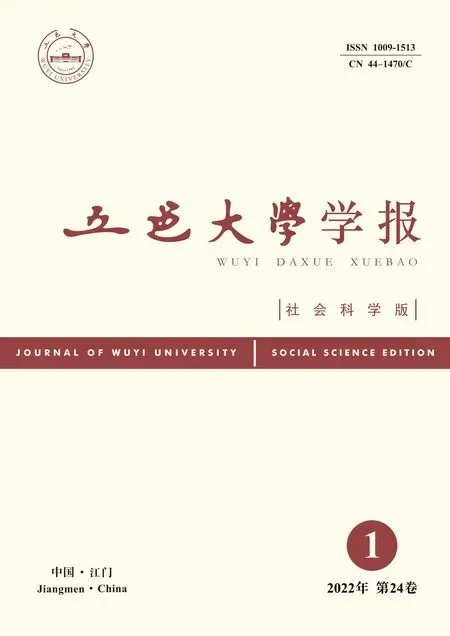简论新版《 辞 源 》
——兼谈何九盈先生对新版《辞源》的贡献
2022-11-29庞光华
庞光华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一
《辞源》是研究古汉语和古代文化的重要工具书,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长期没有修订,在诸多方面都未能与时俱进。商务印书馆于2011年聘请何九盈先生为第一主编,主持修订《辞源》,另两位主编是北师大的王宁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董琨研究员。何先生参与《辞源》的工作实际上在2010年已经开始,商务印书馆要求一定要在2015年出书,工作量和难度非常大。何先生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学术研究,以年近80的耄耋高龄,每日为修订《辞源》工作8小时,经常是审稿盈尺,全面审查文字的形音义以及词语的释义、书证和例证的年代,提出各种修订意见。在先生的督导下,修订《辞源》这件浩大工程如期克竣。新版《辞源》成就恢弘,好评如潮,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何先生为新版《辞源》撰写前言《〈辞源〉: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1],此文可以见出先生编撰大型辞书的思想。先生指出:“从《辞源》自身而言,有诸多问题、缺失,亟待改进,如字头要适当增加,语词条目要限量增加,百科条目要大幅度增补,插图也要重点增补。须新增的内容还有音项、义项、书证等。修旧也很艰巨,如释义是否准确,如何保持价值中立;音项、义项的或分或合;书证的全部核实;异文、标点的斟酌;书名、篇名、卷次、作者的查对;人物生卒年涉及新旧纪年的换算;古地名与今地名的对应;书名线、地名线、人名线的落实;参见条目的照应、沟通;凡此种种,都有可修可补之处。辞书无小事,标点之微,一线之细,都关乎信息、知识的准确性问题。修旧的最大难点还不在此,而是所谓‘《辞源》无源’的问题。此说虽言过其实,但‘源’的问题的确非常复杂,故此次修订的重点在正本清源。”这些意见深中肯綮,针针见血。何先生随后阐述了新版《辞源》必须注意的“行源问题、音源问题、义源问题、典源问题、证源问题”。先生论述到:形源问题,有造字之源、用字之源,《辞源》讲究用字之源,原则上不涉及造字之源①。音源问题,作为《辞源》,不注上古韵部,乃系统上的缺失。至于今音与反切的对应关系,总体而言是正确的,可往往一个今音与多个反切相对应,今音与反切的匹配很不严格,散漫无纪,殊乏裁断。另外,对反切上字声类的标注,内部也不统一。此次修订伊始,即规定了《辞源》第三版审音注意事项二十条。总的原则是:音义契合,古今贯通。同时,设立审音组,专司其职。义源问题,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意义系统,本义就是“源”。不能离开书证说义源,也不必涉及造字理据和事物得名之由之类的问题。典源问题,力求搜寻记载该典发生时的原著,尽量不用后起的类书代替第一手资料。证源问题,书证力求用“始见”例,可以借助计算机来搜寻。这中间有两点要注意:一是“始见”必须要可信,宜排除伪书的干扰;一般不应舍经典名句而用时代虽早却很冷僻的作品中的例子来作证。二是书证提前,宜以大的历史时期为断限。从南宋提前到北宋意义就不大,而从隋唐提前到秦汉意义就不一样了,这是由中古提前到上古,字头的音韵地位也变了。先生的这些论述是其编撰大型辞书的重要思想,对修订《辞源》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当然天下事难以尽如人愿。何先生曾对笔者说,新版《辞源》也有问题没有解决,未能至善。我冒昧略抒鄙陋。
1.《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都充分利用了清朝小学家和20世纪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反映出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新版《辞源》由于强调辞书的稳定性,不免过于谨慎,对于学术界在20世纪和本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基本不予以吸收,不能择善而从,这就未能与时俱进,学术的尖端性有所缺失。对字词的解释,未能超越20多年前的《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很多时候有时反而失诸简略。《故训汇纂》已经汇编了相当完备的训诂资料,可供我们判断歧义时作有益的参考,编者似乎未能充分利用《故训汇纂》以改进《辞源》的释义。
2.对日本学术界的重要古汉语辞书未能充分参考。例如,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广汉和辞典》《大字源》《学研汉和大字典》都未能尽量利用,很多解释和引证不如《大汉和辞典》《广汉和辞典》详细。
3.引据经典有时只引经文,不引古注,不便于学者精确理解书证。
4.割爱了所有的古文字材料、出土文献材料及其研究成果,在溯源上难免美中不足,也未能充分反映学术界的新进展。一概漠视层出不穷的出土文献,终究可惜。
5.参考百科专业工具书和研究成果不够充分,没有足够吸取各专业的研究业绩。
6.从佛典和道藏中取材不够,吸取佛学和道教研究的成果明显不足。
现略举数例,只是吹毛求疵。
1.新版《辞源》1963页“朝元”条有二义:(1)古代诸侯和臣属于岁首元日朝贺帝王。(2)道教徒礼拜神仙,举白居易《寻郭道士不遇》诗为例。考日本学者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卷五1059页“朝元”条,释义为:“朝拜玄元庙,玄元指老子。”举例有王建《宫词》:“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大汉和辞典》的这个释义是准确的,可以精确解释王建《宫词》的“朝元”。因为是天子朝元,所以不可能是臣属在元日朝拜天子,而是天子朝拜老子(太上老君)。唐朝以道教为国教,李唐王朝以老子李耳为远祖。公元666年,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考《旧唐书·高宗本纪》:“麟德三年二月己未,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元年丁丑,两京玄元庙改为太上玄元皇帝宫,天下准此。”同篇:“(天宝)二年春正月丙辰,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 三月壬子,亲祀玄元庙以册尊号。”唐玄宗亲自祭祀“玄元庙”,给老子加尊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因此,“玄元庙”是老子庙。“朝元”是朝拜老子,这是精确的训诂。白居易《寻郭道士不遇》诗“洞里朝元去不逢”的“朝元”也是朝拜道教始祖的老子,不是礼拜一般的神仙。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非常多。
2.1963页“朝日”条只引《周礼》和《礼玉藻》的经文,不引郑玄注,一般学者难以准确理解经文。《玉藻》郑玄注:“朝日,春分拜日于东门之外。”郑注清楚揭示了“朝日”的时间和地方,这是重要文化信息,惜墨如金也不能把郑注省了(《大汉和辞典》就引了郑注,还引有《汉书·郊祀志》和《汉书·贾谊传》)。另外,最好引文作《礼记·玉藻》,而不是《礼玉藻》,因为单独一个《礼》,容易误会为《礼经》,即《仪礼》,但是《仪礼》没有《玉藻》篇。虽然清人常常引作《礼玉藻》,但是新版《辞源》在引述文献上可以更加完美一些。另外,《国语》的时代性很早,绝大部分是春秋时代的文献,肯定早于《礼记》,只有《吴语》《越语》可能成书于战国初期。因此,在文献溯源上应该充分利用《国语》。例如《国语·周语上》:“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韦昭注:“礼,天子搢大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拜日于东门之外,然则夕月在西门之外也。”韦昭注比郑玄注更加详尽精审。如果引书证采用《国语》和韦昭注,则更加完善,可惜《辞源》一字不提郑玄注和韦昭注,导致重要学术信息缺失。
3.2317页“泰山”条有三义:(1)山名。(2)郡名。(3)岳父。这就忽视了至少自东汉以来就有的泰山是地府的文化,泰山是人死后亡魂所归的阴间地狱。这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辞源》非收不可,不应该遗漏。《汉语大词典》“泰山”条列举七个义位,也没有泰山是地府这一义项,这属于关于泰山文化的重大遗漏[2-3]。
4.3437页有佛教术语“般若”:“梵语,犹言智慧,或曰脱离妄想,归于清净。为六波罗蜜之一。”书证引《大智度论》。这个解释过于简单,缺乏专业性,还不如《汉语大词典》“般若”条:“梵语的译音,或译为‘波若’,意译为‘智慧’。佛教用以指如实理解一切事物的智慧,为表示有别于一般所指的智慧,故用音译。大乘佛教称之为‘诸佛之母’。”②举《世说新语》等为证。《汉语大词典》在书证上不举早期大乘佛经《般若经》,如东汉末年支娄迦谶翻译的《般若道行品经》或《大智度论》而引《世说新语》,固然不妥。二者都应该更多列举“般若”不同的音译名。《辞源》称“或曰脱离妄想,归于清净”,这实在是片面的发挥,没有圆满阐释“般若”的含义③。如果重视参考佛学专业工具书和研究成果(有条件还要参考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应该会解释得更好。另外,“般若”还是唐朝的一位佛经翻译家、密宗高僧的法名,很有成就,《辞源》应该介绍。
5.2381页“涅槃”条:“亦作‘泥洹’,意译为灭度。”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涅槃”条列举异译“又作泥曰,泥洹,泥畔,涅槃那等。旧译诸师,译为灭,灭度,寂灭,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另参看《佛光大辞典》“涅槃”条。《辞源》提供的各种音译和意译的学术信息显然不够。更重要的是在佛经翻译史上,“泥曰、泥洹”在汉译佛经中的出现要早于“涅槃”,在东汉三国西晋甚至东晋的汉译佛经中没有使用“涅槃”的。例如东汉桓帝灵帝之间支谶所译有《胡般泥洹经》一卷[4]27;魏文帝时,支谦在东吴孙权处翻译了《大般泥洹经》[4]28,31;西晋竺法护翻译了《方等泥洹经》;东晋法显译《大般泥洹经》六卷和《方等泥洹经》二卷。可知东晋法显还用“泥洹”一词。但是天竺沙门昙摩谶(或作昙无谶)到了西凉州,于河西王沮渠蒙逊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公元421年)翻译完了《大般涅槃经》[4]52,用的是“涅槃”一词。这部重要经典流行后,“涅槃”逐渐取代了“泥洹”“泥曰”等。宋文帝时还翻译了《泥洹经》一卷④,还是用“泥洹”,没有用“涅槃”,是因为《大般涅槃经》的传播和流行有一个过程。更考慧皎《高僧传》卷第七《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条:“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后《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5]足见六卷本的《泥洹经》(当是法显翻译)先流行,用了“泥洹”一词。到了刘宋时代,在北凉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南传至南京。“涅槃”一词在南朝流行,实在是从刘宋时代《大般涅槃经》南传才开始的[6]。梁代法朗奉梁武帝之命,制《大般涅槃经集注》72卷,甚为梁武帝所重,从此“涅槃”在江南地区几乎完全取代“泥洹”“泥曰”,因此“涅槃”在南朝广泛流行是在梁武帝时代。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只有“泥洹”,没有“涅槃”。《水经注》的产生年代在公元520—527年,是郦道元晚年[7],可知《大般涅槃经》翻译出来后在北朝反而不如在南朝流行。直到北朝的昙延(516—588)撰著《涅槃经疏》之后,才广泛流行[8]。这个词汇史的源流是很重要的,而且关系到文化史的变迁。
6.在历史地名上,例如574页“南京”条,列举历史上四个叫“南京”的地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9]中册2059页“南京”条列举了历史上的“南京”地名有八个,多出《辞源》一倍:渤海国以南海府为南京;契丹升东平郡为南京;辽国升幽州为幽都府,升为南京;金国以平州为南京,后废。另参看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10]“南京”条(列举九个“南京”)。而且,据慧皎《高僧传》卷第七《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条,刘宋时代有都城“南京”(上文已引),各书都不提,尚应补苴罅漏。《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的解说也很细致,例如二者都称在安史之乱后,朝廷将成都府建号南京,但是《大辞典》还称:“上元元年(760年)撤销京号。”这个重要信息在新版《辞源》没有,实为不应该。类似的情况很普遍,表明在百科上面的专业性不够。
7.在历史人物上,2726页“王应麟”只有区区数十字的简介:“公元1223—1296年宋庆元郡县人,字伯厚。淳祐元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给事中。博学多识,著有《深宁集》、《通鉴地理通释》、《困学纪闻》、《玉海》等二十三种。《宋史》有传。”评价仅有“博学多闻”四个字,然后著录其主要著作,不免过于简略。而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11]554“王应麟”条可称:核而能要,精而不泛,学术价值高下立判,而且注明《深宁集》100卷,今不传。又称其《困学纪闻》20卷和《玉海》200卷“征引宏富、贯串古今,考订精深,尤详于宋代史实”。《辞源》全无如此的说明。其对“王应麟”的介绍和评述颇嫌粗陋,无足参考。1933页“曹丕”条仅仅略述履历和著作,其历史意义只有一句话“所作《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11]118“曹丕”条,事义核要,措辞精密,语无废墨,句句可观,《辞源》的评述实在简陋,这次修订未能改进,难称完璧。另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曹丕”条都是高水平的撰述,学术水准超过了日本学者编撰的《亚洲历史事典》(日文本)和《世界大百科事典》(日文本)的“文帝(魏)”条、《日本大百科全书》(日文本)“曹丕”条、《大美百科全书》[12]第27卷148页的“曹丕”条,《不列颠百科全书》[13]第18卷173—174页“曹丕”条。《辞源》对类似的重要历史人物的撰述,大多简而寡要,省而不精,文化信息未能精粹,难尽人意。
8.在书证的时代性上,1125页“宰相”条,举书证为《韩非子·显学》:“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但更早的文献是《吕氏春秋·制乐》:“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按照《辞源》的原则,应该举《吕氏春秋》的书证,因为时代更早。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宰相”一词很可能起源于西北地区的秦文化(或三晋文化),不可能是来自北方的燕文化和南方的楚文化。现在学术界对汉以前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时代性,而且重视地域性。另外“宰相”还是辽代的职官,辽朝北面官有北南宰相府,各置左右宰相为长官。参看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第764—765页“宰相”条[14]。新版《辞源》漏收,这是应该增补的。
9.在制度的时代性上,2915—2916页,“相”(七):“官名,后专指示宰相。”书证举《荀子·王霸》《吕氏春秋·举难》《史记·陈涉世家》,时代嫌晚。《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这是春秋时代齐国有“相”之始。我国历史上有“相”是在公元前548年。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第627页“相”条称:“春秋齐景公初年置。”[14]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信息。
10.在引述文献上尚待完善。4314页“陈奂”条称其著有《毛诗传疏》,这就不精确,应该是《诗毛氏传疏》。
11.在标注古人著作上没有著录最新整理本。4317页“陈献章”条称其有《白沙集》《白沙诗教解》,笔者以为应该提及其最新的编校本《陈献章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2012年第四次印刷)⑤。“钱大昕”条应该著录《嘉定钱大昕全集》,“戴震”条应该著录《戴震全书》,“顾炎武”条应该著录《顾炎武全集》,“俞正燮”条应该著录《俞正燮全集》,“程瑶田”条应该著录《程瑶田全集》,“王夫之”条应该著录《船山全书》,“王鸣盛”条应该著录《嘉定王鸣盛全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的专集都应该这样处理,著录最新的整理本和校注本,否则不能反映学术的进展。
12.《大汉和辞典》《汉语大词典》收录的很多典故,例如“紧箍咒”“期牛”,《辞源》没有收录,但在3228页收有佛教名词“紧那罗”。中国人虽然都知道“紧箍咒”,但是不明白其含义和来源,却不收录。《汉语大词典》和新版《辞源》都不收“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不可思议。《汉语大词典》虽然收录“紧箍咒”,却不知道注明“紧箍咒”就是“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可参看《佛光大辞典》《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的“六字大明咒”条以及相关条目。
从很多方面来看,新版《辞源》不能取代《汉语大词典》,更不能取代《汉语大字典》。我们也不能忽视还有台湾的《中文大字典》。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对有关历代官制阐释较详,理应充分参考,新版《辞源》对职官的解释远远不如《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文化信息量大。又如,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和《佛教大辞典》⑥,还有震华法师遗稿《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三册)、七大卷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各专业工具书都未能充分参考利用。
三
在编撰体例上,《辞源》应该吸收国际学术界更多的方法。国际学术界著名的《钱伯斯语源学辞典》,分析了超过25 000英语单词的词源和演变源流,对每一个单词都能标注其出现在某个年代,其语源是什么?在某种文献中作什么形式,是什么意义?词汇源流一目了然。此书初版于1988年,在《汉语大词典》之前。这样编撰辞典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国内学者刘洁修《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的编撰方法对于梳理汉语成语的源流有极大的裨益,对汉语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是辞典学的一大进步。如果新版《辞源》能够借鉴《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的思路和方法,则成就必然更上一层楼。朱祖延编著《引用语大辞典》(增订本)在梳理典故源流上很下功夫,值得借鉴。我们期待学术界将来能够将《辞源》修订成《汉语历史大词典》,这项工程任重道远,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奋斗。
新版《辞源》应该参考借鉴多种百科全书,例如《大英百科全书》、《大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日本大百科全书》(日文本)、《世界大百科事典》(日文本),也应参考借鉴日本的《国史大辞典》(日文本)、《日本历史大辞典》(日文本),还有日本学术界编的各种《事典》(笔者以为日本的各种《事典》就是各专业的百科全书,很有价值),例如日文本《哲学事典》《日本传奇传说大事典》《日本美术史事典》都很有水平。我国七卷本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非常类似日本的《大事典》,不是一般的辞典体例。台湾学者韦政通编撰《中国哲学辞典》也很像是日本学术界的《事典》。日本的《国史大辞典》(15卷17册)在学术水平上超过了我国的《中国历史大辞典》(14卷本),希望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兴趣,以后在修订辞书时理当关注和借鉴日本学术工具书的编撰方法。
日本学术界都极其重视各种工具书的索引,《日本大百科全书》《世界大百科事典》《国史大辞典》《日本历史大辞典》《亚洲历史事典》《大汉和辞典》《广汉和辞典》都有专门的《索引卷》。卷帙浩繁的《大正新修大藏经》(100巨册),日本学术界也编撰了《大藏经索引》(16巨册),在电子检索本出现前,为学术界利用《大正藏》发挥了巨大功能。我国的《昭明文选》,现在还只有日本学者编的《文选索引》(是逐字索引)。日本的《国歌大观》每一卷原文都配有一大本的索引。《不列颠百科全书》共20卷,第19、20两卷都是索引卷。《大美百科全书》共30卷,最后一卷是索引卷。有鉴于此,笔者强烈建议商务印书馆仿效国际学术界惯例,编撰一本详尽的《辞源索引》,以提高学术界对新版《辞源》的利用功效,这并不是无所谓的事。
《辞源》这样的综合大型辞书,本来就应该尽量利用学术界的各类专业成果,带有总结学术成绩的性质,没有必要什么都是编撰者自己的研究,编者博览学术界的业绩,可以择善而从。只是近200位学者的时间太紧,还有各自单位的本职工作,资料收集和研究的功夫不一定很充分,区区5年时间,就有如此的成绩,看看高小方《〈辞源〉修订匡改释例》修订《辞源》多达1718条(何先生撰序),就知道专家们下的功夫真是非同小可。
注释:
① 笔者案,李学勤先生主编有《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三册,专门分析汉字演变的源流。日本学者前田富祺监修《日本语源大辞典》(日本小学馆,2005年版)对日语词汇的语源研究很重要,汇编各种观点,有相当大的学术性和资料性,方便学者使用。何先生提出新版《辞源》不搞形源,只搞用源,这固然是一种学术取向,也许是因为李学勤先生已经主编了《字源》,为了避免重复,这并非说形源不重要。从前的《汉语大字典》已经尽可能地排比了从甲骨文到隶书的字形,只是没有分析。在古文字学中,各种文字编非常多,对于研究形源已经夯实了坚固的基础。综合性的有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高明等编撰《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黄德宽主编、徐在国副主编的“古汉字字形表系列”,包括《商代文字字形表》《西周文字字形表》《春秋文字字形表》《战国文字字形表》。还有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和《金文诂林补编》;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刘志基等主编《古文字考释提要总览》(四册);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1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四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作为新版《辞源》完全不顾形源,从而放弃了百年来古文字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可能会有争议。
② 如果不是泛称大乘佛教,而是具体说是《大智度论》卷一百称:“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则更加精确。
③ 关于“般若”的解释可参看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星云大师监修、慈怡法师主编《佛光大辞典》;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和《宗教大辞典》;中村元《佛教辞典》(日文本第三版,日本诚信书房,平成18年即2007年);日本创价学会教学部编、池田大作监修《佛教哲学大辞典》(昭和四十八年版)第五卷101-102页“般若”条。学术性最强的是《望月佛教大辞典》(日文本)“般若”条。
④ 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二,6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2013年版。另参看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二66-67页的《般泥洹经》条所辑录的都是《泥洹经》,只有昙摩谶所翻译的是《大般涅槃经》。
⑤ 如果现在修订,就应该加上最新的《陈献章全集》《陈献章诗编年笺校》,才能提供足够的学术信息。
⑥ 另外如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星云大师监修、慈怡法师主编《佛光大辞典》;日本学者中村元主编《广说佛教语大辞典》(林光明翻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