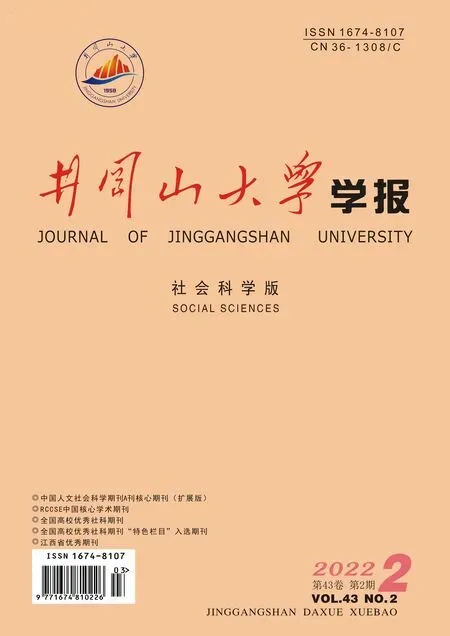试论史学碎片化的困境及出路
2022-11-29王志华
王志华
(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国外关于史学碎片化问题的讨论, 当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其主要标志是1978 年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的出版。 而国内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二十一世纪之后的事了, 最突出的要数2012年,是年,《近代史研究》杂志连续两期(第4 期和第5 期)开设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专栏,共刊登了13 篇文章,对这一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讨论。随后,陆陆续续有学者发表相关论文,进一步推进了对它的研讨。史学碎片化其实是社会存在的深层回响, 后者的变化必然赋予其新意。而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内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秩序面临重建。“碎片化”问题势必会进一步凸显出来。所以,结合后现代语境,廓清史学碎片化的内涵,论述其所面临的困境,并尽力寻找化解之道,当是学界不可回避的使命。
一、“史学碎片化”释义
国内外史学界对“碎片化”的研究并不是新鲜事,不过稍有遗憾的是,大多数文献均从否定的意义上对它进行界定, 从而无法对它的内涵给出一个透彻的分析。比如弗朗索瓦·多斯——学界一般会把史学碎片化的肇始追溯到他这里——认为“碎片化”是“时间性由单数变成复数”、“自由幻想之破灭”的后果。①多斯关于“碎片化”的经典性说法主要有两处,一是“时间性从单数变成了复数后,历史也被分解成一摊碎屑。”另一处则是,“对事实的解构与当今的幻想破灭密切相关。……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他们都致力于解读为自由而战的基础。……当事实无助于实现人们的希望时,它便失去了合理性。历史也不再有任何意义,并瓦解成了一堆碎片。”([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M].马胜利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第234,117 页。 )“复数”便是对“单数”的否定,尤其是“破灭”一词,否定性意义非常明显。再如美国史学家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则把“碎片化”定义为“一体化(integration)”的反面,后者的不可行导致了前者,①梅吉尔在其关于“碎片化”的专论中指出,“诺维克睿智而博学的著作给我最深刻的启发,似乎就是,一体化(integration)——不论是实质意义上的还是方法论意义上的——除非通过强制或遗忘, 否则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体化是不可行的。 ”(Allan Megill.“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Historiography”[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1,(3).)否定性意味也非常强。 国内学者李长莉认为, 史学碎片化“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 ”[2]注意关键词“缺乏”,典型地是否定性的。
从否定的角度去探讨史学碎片化, 尚不足以弄清其内涵,因为:第一,这种论证方式属于“旁敲侧击”,充其量只点明了“碎片化不是什么”,而未说明“它是什么”,即并未揭示“碎片化”内在的肯定性意义。第二,这些论述中“否定性”自身的确切内涵并不明朗, 因为它依赖于对一些 “元概念”——即多斯的“复数时间”和“自由”、梅吉尔的“一体化”、李长莉的“普遍性意义”等——做进一步的阐述。 按照这样的分析, 要廓清史学碎片化之内涵,尚需从两个方面下手:第一,否定性方面,需进一步论述那些元概念。第二,从正面揭示其内在的肯定性意义。
首先,以上所说的那些“元概念”,均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所说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 根据他的说法,“宏大叙事”主要有两个派别,“一派倾向于政治性,另一派倾向于哲学性;两者在现代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在知识史以及伴随知识而来的典章制度上。 ”[4](P108)根据现代史学的情况,本文把它扩展为三种类型,前面两种与利奥塔的基本一致:第一种类型是历史理论, 或者叫思辨历史哲学——即利奥塔所说的倾向于哲学性的一派——其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 他通过哲学思辨的方式确立起“英雄史观”,这是肇始于启蒙运动的“自由和解放的宏大叙事”。 第二种类型是现代史学的典范即政治史观——即利奥塔所说的倾向于政治性的一派——以黑格尔的学生兰克为代表,他秉承黑格尔的“英雄史观”,而政治天然就是英雄人物的主要活动,所以,认识历史就是要去研究每一个时代的政治, 从而历史研究就成了政治史研究。第三种类型是全面历史观,以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 一书为代表, 其理论特征有两个方面, 一是长时段, 二是研究内容囊括所有社会现象,即把历史看作是包括政治、经济、生态地理、日常习俗文化等所有因素在内的一个综合体, 而史学家的使命便是揭示其中历经长时段依然不变的地理结构、 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乃至思想文化结构。在否定的意义上,碎片化是对这三种史学宏大叙事的放弃。
其次, 需从正面揭示碎片化内在的肯定性内涵。 第一,“碎片化”指的是史学研究的一种状况,从具体的研究过程看, 任一研究都有一个包括起点和终点在内的过程,“碎片化” 体现于这一过程之始终。在研究的初始,史家的选题就刻意碎小琐屑,即“史家眼光朝下,研究原来不为人注意的、无关历史进化的日常小事或边缘人物和事件”;研究过程所采用的方法也具有碎片化特征,即“繁琐论证,就一些已经为人所熟知的题材,深入发掘,探奥求赜,希望发人所未发之新见。”[5]而在研究的终点,则体现为碎片化的史学作品,意思是指史学作品只能见微知微以小见小, 史学作品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从而“历史像一颗摔碎的油珠,再也无法聚拢起来。 ”[6]从而在史学研究的总体领域呈现出碎片化状态。第二,为何众多史家会刻意去追求碎片化呢?这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碎片化本身具有内在的积极意义,即“以‘碎片’为究竟,执意颠覆和反对任何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目标。 ”[3]
综上所述,史学碎片化的内涵,从否定性的角度看,它是对历史理论、政治史和全面史等史学宏大叙事的抛弃;从肯定性的角度看,碎片化成了史学研究的一种价值追求, 史学研究的整个过程都呈现碎片化状态。 这与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解构中心,倡导边缘与差异等等主张非常契合,可以说,它正是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中的回响。
二、史学碎片化的困境
那么,抛弃了宏大叙事,一味地追求碎片化的史学,在逻辑上能够自洽吗?不少学者对此也有所论述, 如李长莉就指出了史学碎片化由“微观实证”研究方法而导致的“意义匮乏困境”,“沿用这一方法作为研究社会与文化史主要的、 终极的研究方法, 就会导致研究论题意义微弱甚至缺乏意义。 ”[2]这确实是史学碎片化的症结所在,进一步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意义匮乏困境” 又是怎么导致的?对这一问题的追溯,就可以具体展现史学碎片化的种种困境。
(一)从理论层面看,主要是以下三大困境
1.“方向困境”
这指的是, 史学研究者无法把握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明白研究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会这样?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肇始于文学艺术领域,注重表现个体的内心自由,它是反对理性的,内心自由的实质就成了非理性的游荡,漫无目的,无所依归,必然迷失了自我。与此相对应,史学界所存在的一股以猎奇、娱乐、标新立异等非理性追求为时尚的研究风潮,其典型表现是,“一些诸如气味、想象、死亡、空间、梦、垃圾、屎、疼痛、疾病、姿态、眼泪、同性恋、手淫、食物、盐、煤、火、镜子、乳房、头发、内衣、厕所、戒指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 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与研究内容。 ”①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者的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第1 页.表面上看,史家的研究出于自己的兴趣,但为了追求猎奇、娱乐、标新立异之效果,他们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研究兴趣, 致使史家无法形成稳定的研究领域。并且,因为猎奇、娱乐、标新立异本质是非理性的,所以史家无法籍此来理解、评价自己的研究意义, 这必然令尤其是刚入道的史学研究者陷入方向迷失的困局之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眼光朝下”的研究风潮会模糊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文学等等之间的学科界限,其优势是“跨学科研究”,但由于研究过程中实难把握其“度”,必然会消解史学自身的存在合理性,即令“史学”本身陷入“方向困境”。
2.“深描困境”
当史学家乐于“眼光朝下”并开展“繁琐论证”之时, 就极易进入所谓的 “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②语出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详见《地方知识》,杨德睿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之轨道。 而其逻辑走向必然是不断地往纵深推进——即眼光不断朝下, 论证不断繁琐——而它自身根本无法评判“深描” 之合理的“度”在哪里,并且为了标新立异,反而会在史学家之间形成一种变态的评价标准——比谁的眼光更朝下, 比谁的论证更繁琐——从而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不断地往纵深推进。毫无疑问,历史书写的深度逻辑可以无限延申, 但史学家自身的书写能力毕竟有限,换言之,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它必然要在某个深度逻辑点上止步。显然,这个“止点”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随意的,完全取决于标新立异、猎奇之需要而定。如是,必会陷入“深度描写”的怪圈而无法自拔,形成“深描困境”。
3.“语言表现困境”
众所周知,史学研究的终端产品是语言制品,史家表现历史的媒介就是语言,因而,与“史学碎片化”相对应的,便是“语言表现的碎片化”。而“深描窘境”一定会导致“语言表现窘境”,这是因为“深度描写”会导致史学的“崇高”现象——而“崇高”恰恰是无法被语言表现的,换言之,“崇高”与其语言表现之间始终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与此相对应, 语言表现层面必然形成 “建构——解构——建构——解构……”的无限循环链,也就是说,每一个史学家都要不断地编织着自我的语言,每一部史作都是一套别出心裁的语言表现, 而且历史学家还要不断地进行自我语言革命, 不断地创造新的语言表现形式, 甚至于形成一种只有他们自己才理解的“私人语言”。 本来,语言是理解、表现历史的媒介, 如今历史反而成了各种语言表现的试验场了,史学研究的重心不在“历史”而在“语言”了。 所以,语言表现窘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阻断史学家之间的交流,从而消解了史学共识;二是会出现没有历史的历史作品。
这三大困境成功地阻断了意义生成机制,从而在总体上形成“意义匮乏困境”。 尽管历史作品汗牛充栋,但历史意义却非常稀缺。阅读再多的历史作品,也无法形成健全的历史感。
(二)理论层面的“意义匮乏”困境一定会表现在实践层面, 当碎片化研究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潮之时,必然会在史学研究者个体、史学界以及社会三个层面均会产生一系列的困境
1.在史学研究者个人方面,会导致“见识困境”
尽管某个史学研究者可能主持过不少有分量的研究项目,发表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由于这些科研项目或科研成果之间缺乏意义关联,从而整体上呈现出碎片化状态,更有甚者,研究者本人也无法通过他自己的研究而形成一个健全的历史观,无法提升自己的历史见识——但显然,他们并不缺乏历史知识, 只是缺乏历史见识——出现有知识而无见识的困境。
2.在史学界层面,会导致“失语困境”
历史与现实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史学研究者普遍地缺乏历史见识之时, 史学界便难以对社会问题提出有见地的观点, 有学界前辈曾心痛地说道,“正是因为缺乏理论, 史学才会在当今世界一些重大问题上沦为看客。 ”[6](P3)
3.社会层面的“共识困境”
斯蒂芬·斯密斯(Steven.G.Smith)曾睿智地指出,“生活不能离开历史, 因为没有过去的事件作为参照, 我们就无法辨认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境况, 从而也就几乎无法采取任何可以被理解的社会行动。”[10](P4)确实,一个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转,依靠的是诸如关于国家、民族、信仰、历史等等的“共识”;而“共识”往往是在历史中慢慢积淀而成的。很显然,碎片化必然会把已有的诸多共识撕裂,继而给人们的认知带来相当的混乱, 必然会令社会心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之中。 一个社会缺乏共识,便无法开展集体行动,从而形成“集体行动困境”。 若碎片化不断加剧,最终一定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身份认同危机, 因为身份认同也是在历史中慢慢积淀而成的, 也是通过历史研究确立起来的。
三、辩证看待史学碎片化
尽管史学碎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诸多困境,但并不意味着它的存在毫无合理性。 首先,碎片化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确有其逻辑依据。从学科特性上看, 作为一门实证性学科,“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 则史学即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 ”[7]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增长人们的知识,因为它“有利于从细节上再现历史情境,”[9]即可以增进人们对历史细节的认识。除此之外,碎片化还有其特定的“本体论承诺”,即它确实反映了世界的某些真实情况, 而并非纯粹的辞藻堆砌——“后现代寻求新的表现方式,并非要从中觅取享受, 而是传达我们对‘不可言说的认识’。 ”[8](P209)——世界确实有“不可言说”的一面,比如“宏大叙事”典型地就具这种性质。 面对此类实在,唯有通过表现(reprensentation)方可触摸到它们,即“我们的职责不是去提供实在,而是为‘只可意会’的事物创造出可以想象的暗示。 ”[8](P210)而在表现的层面上,必然是碎片化的。
其次, 它对传统宏大叙事的抵制也具有合理性。利奥塔曾指出:“自柏拉图以来,科学合法化的问题就与立法者的合法化有密切的关连。 从这个观点来看,确定‘什么是真的’和‘什么是公正的’这两种权力,是不可分的。 重要的是,在这种叫做科学的‘语言’和伦理、政治语言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它们产生于同一种透视,或是一种‘选择’(假如你愿意这么说的话)。 ”[8](P46-47)众所周知,“什么是真的”指向真理逻辑,“什么是公正的”代表价值或善;而真理与价值是不同的两个范畴,但自古希腊始它们就被归结为理性之“透视”。换言之,自古希腊始,真理与价值就被混为一谈。而黑格尔的“英雄史观”恰恰就沿袭了这个问题——自由解放本是一种价值追求,“理性”与“合理性”则是真理范畴——而他恰恰把自由解放与“理性”及“合理性”相等同,结果便是,自由解放是合乎理性的,是真理,它是必然会实现的,由此人类历史的发展被说成是必然的、线性的上升过程。如果说在黑格尔之前, 真理是价值的依据——即为了确立自由解放的合法性而把它奠基于理性之上——那么当它的合法性被确立起来之后, 它自身便成了真理的化身,即成了一种“元叙事”,成了知识合法化的根据, 这样的做法“其特征是把科学与真理的合法性,根植于和伦理、社会、政治常识相关的参与者的自主性对话之上。 ”[8](P25)在此,真理与价值的关系倒过来了,价值成了真理的评价标准,这是资本主义知识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简言之,就宏大叙事而言,其本质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价值的根基在意志而非理性。因而,宏大叙事的普遍性没有理性保障,从而不具有普适性。
按照这样的分析,在价值的维度上,宏大叙事与碎片化都是平等的。很自然地,在晚期资本主义爆发种种危机之时,利奥塔会趁势发出“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8](P211)之吼声。 尽管对“宏大叙事”的批判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但后现代主义对它的批判是最全面、最彻底的。当人们不再拥抱“宏大叙事”之理想时,必落入“碎片化”之怀抱。
四、“新宏大叙事”:史学碎片化的出路
一方面, 史学碎片化有其内在价值, 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诸多困境。 显然,看待它的正确方式是,既保留其价值,又克服其困境,即如章开沅所倡导的“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 ”[9]换言之, 史学研究既要做到对历史细节的精湛把握, 同时又要阐发出普遍的历史意义来。 这就是说,在学术研究的层面,碎片化与普遍的宏大叙事两种研究路径应当并立,毕竟“历史综合与碎片化这两者之间,既不是后者的累积会自动达到前者,也不是前者终归可以涵盖后者。但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把二者对立起来。”[11]它们都是学术研究之必需。
关键的问题是, 如何克服碎片化所固有的系列困境。而显然地,后现代主义或者碎片化史学均无法凭借自身的理论力而做到这一点。①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语言或话语,可以说碎片化根植于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哲学中,这是后现代主义无法凭借自身的理论克服碎片化的根本原因。 详细的探讨见笔者的另一篇拙作《史学碎片化的话语根源诊断》(《龙岩学院学报》2021,(3).)并且既然后现代主义是史学碎片化之肇因, 则超越后现代主义理当是克服碎片化之道, 但显然地不能回到传统的宏大叙事的窠臼之中, 所以基本的逻辑指向便是建构一种“新宏大叙事”。
从国外的情况看,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界便开始探讨克服碎片化之道。 较早的当属以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卡尔·戴格勒(Carl N.Degler)、 威 廉·勒 奇 坦 伯 格 (William E.Leuchtenburg)、 理查德·利奥波德 (Richard W.Leopold)、阿伦·博格(Allan G.Bogue)和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等为代表的“综合理论”。[12]进入新世纪以来,则有由约恩·吕森(J·rn Rüsen)所开创的包容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以促成跨文化交流为目的“历史思考的新途径”;[13](P3-7,123-142)有林恩·亨特(Lynn Hunt)的以平衡或矫正“民族国家史学”以及“欧洲中心论”为宗旨的“全球化史学”;[14](P1-9,119-123)有 大 卫·克 里 斯 蒂 安 ( David Christian) 和弗雷德·斯皮尔( Fred Spier)所提出的以物质的演化为线索,把宇宙、地球、生命和人文融为一体的“大历史”(Big History);[14]还有由史蒂文·斯密斯(Steven G.Smith)所阐述的以“共同行动”(Shared Action) 为归宿的“丰盈史” 理论(Full History)。[10](P1-14)
从国内的情况看,学界当有共识,即回到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观的立场、方法与后现代史观的极端“解构”思维确实存在着天然的张力和矛盾,所以,“如欲切实摒弃后现代史观的极端‘解构’思维、化解‘碎片化’问题,则必须挺立和坚持唯物史观。 ”[1]当然,立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唯物史观,毫无疑问要时代化、大众化,不断与时俱进。如果说新中国至今的历史可以分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部曲,那么,在新时代,应该主要把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与基本方法与“强起来”之时代大背景相结合, 这必然会催生新的理论,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有望成为一种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正在生成的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历史存在物,它要成为一种历史哲学,既仰赖于在实践中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也要仰赖于学术界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论述其丰富的理论内涵。 本人对此也有些思考,《“家”隐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生成》(《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1,(5).)。
这些林林总总的史学新宏大叙事, 从不同角度就如何克服碎片化给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若借用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这对范畴对其加以分析, 基本的格局当是如此:“大历史”理论可以划为“历史规律”论,它意在客观地描述人类自宇宙大爆炸以来的历史;“历史综合理论”、“历史思考的新途径” 之说、“全球化史学”以及“丰盈史”等均属于“主体选择”论,其理论的重心在于强调历史之用; 而唯物史观则典型地属于辩证论,即强调“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之间的辩证统一。
明了这个理论格局, 当有利于读者把握它们的本质。 “大历史”的物质主义取向确实可以为人类提供一个非常统一且刚性的宏大叙事, 但其最大的不足就是无法为主体的自由选择预留空间,所以它对碎片化的超越,“实际上只做了一半: 它是物质主义的超越,不涉及精神和意义。”[14]而“主体选择”论的那四种理论,因其重心在于强调古为今用, 尽管它们均不否认历史的客观性以及史学方法的严肃性, 但由于历史的客观性最终靠主体之间的共识来做担保, 所以其最终的归宿必然是堕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之中。因为很显然的,同样一个历史理论或历史叙事, 对于不同的群体或不同的个体而言,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及世界观,其所产生的“用”在质和量方面均不一样,所以,“主体选择论”在根子上就呈现碎片化之势,它与“碎片化”之间有互相“勾兑”之嫌。
这样看来, 克服碎片化的使命便落在了唯物史观的头上, 后者也确实具有完成该使命的理论潜力。 其基本思路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实践载体,整合吸纳林林总总的碎片化历史,前者好比树干,后者好比枝叶。因为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及其辩证衍生物均有其合理归属, 换言之, 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无论是国家还个体,无论是经济社会史还是日常生活史, 等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可以成功地超越碎片化, 并在碎片化的基础上阐述出一种普遍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