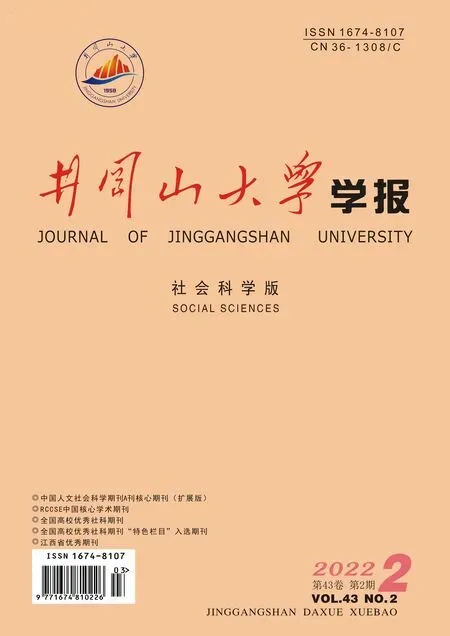发掘红色文化资源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以灵官殿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建设为例
2022-11-29罗建林刘志伟
罗建林,刘志伟
(1.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 201703;2.湖南省邵东市委,湖南 邵东 422800)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 ”为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推动红色村组织振兴建设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决定要把推动红色村组织振兴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试点工作要“紧紧围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充分依托红色资源,全面加强村党组织建设,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为建设红色美丽村庄提供坚强保证。 ”[1]本文试以湖南省邵东市灵官殿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建设为例, 就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通知》要求,发掘、利用红色资源以助推美丽乡村建设进行初步探讨。
一、深耕和修整区域内的红色文化沃土
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 不断积累起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进程中,由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 蕴含着丰富革命精神和厚重文化内涵的先进文化。 它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深厚的文明沃土,熔铸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百年来,根深叶茂的红色文化源源不断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 为中国人民奋发前行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灵官殿是一个农村小镇,地处湖南中部,面积仅150 平方公里左右,是一个形如桃核的小盆地,因清末隶属宝庆府邵阳县中乡, 人们至今仍然习惯地称之为”中乡“。 2015 年12 月31 日,由原石株桥乡和原灵官殿镇合并成新的灵官殿镇, 总人口近10 万。灵官殿四周高山环绕,山青水秀,犹如世外桃源般僻静、美丽、安详。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灵官殿境内才修了一条简易公路,在此以前与外界相连的仅仅是几条顺山间小溪而行的小道。 因为相对封闭, 这里的传统文化气息绵延而浓厚,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朴实、勤劳、友善为美德,崇尚仁爱、恪守诚信、扶正扬善、扶危济困、尊老爱幼,追求上进。 1984 年,这里曾令人惊奇地出土了一件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三千多年前西周时的王室乐器——四虎铜镈, 让人们联想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这个农村偏远小镇的渊源与联系。
在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濡染下, 灵官殿的老百姓一直以来就有很深的家国情怀, 其中有些优秀代表走出小镇, 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较大贡献,为家乡和亲人增添了光彩,为灵官殿红色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刘馥, 生于灵官殿花园村朱壤屋, 在家乡私塾接受过传统文化洗礼后进入湖南时务学堂,1903 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是同一时期留学日本的湖南有志青年。 1905 年,刘馥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同盟会首批会员,跟随孙中山从事推翻满清专制统治、 创建中华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清王朝被推翻之后,他先后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总统府、农商部、内务部任职。 孙中山去世后,他还担任过国民政府内务部总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受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之邀到沈阳东北大学任主任教授并兼任法学院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多次当面向蒋介石直陈抗日之策。 可惜的是,刘馥在南京沦陷前病逝,年仅53岁。[2](P84-87)
17 岁参加红军的曾云,1918 年出生于灵官殿镇双中村。1935 年10 月,正在外地学木工手艺的他毅然跟随贺龙部的红军走上革命道路, 成为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的一名战士。长征途中,他被分配在通讯班,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曾云大部分时间都奋战在军队电子技术战的无形战场上, 默默地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位从红军长征中一路走来,抗击过日军,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后随四野南下参加了湘赣战役和井冈山、 粤北地区剿匪战的革命军人,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人民军队的信息工程建设,他又远赴戈壁,出荒漠,呕心沥血,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机要处处长、中南军区与广东军区干部部副部长、总参谋部三部党委委员和机要通信局七局与八局副政委,1983 年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政治委员(正军级)任上光荣退休。
荣誉众多的宁重华,1926 年8 月23 日出生于灵官殿,1947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的战斗足迹从东北到海南岛,从国内到朝鲜半岛,先后参加了四平、锦州、北平、天津、长沙、衡宝、海南岛、抗美援朝等大小战斗59 次,立大功2 次,立小功9 次。1952 年因伤从抗美援朝战场退役回到老家投身家乡建设,依然保持军人的本色与情怀,先后被邵东县人民政府评为“特等模范”、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评为“甲等荣军模范”。
灵官殿深厚绵延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为这些杰出历史人物的成长打下了坚实根基、提供了丰富滋养。与此同时,在他们令人敬仰的成就影响下,灵官殿传统文化的氛围更浓郁、沃土更深厚、根系更丰满、枝叶更茂盛。 如此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氛围下形成的社会环境, 也恰恰是我党早期开展地下活动的良好社会基础。 毛泽东曾指出, 湖南是中国革命史上民主革命影响最深刻的地方,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也是“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 ”[3](P13)解放前夕,灵官殿就曾活跃着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武装——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二支队, 他们在灵官殿人民的支持和掩护下,向旧社会宣战,和反动势力斗争, 为迎接解放军南下和国统区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曾断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4](P121)正如延绵5000 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一样, 灵官殿不断沉淀、创新、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一直滋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代老百姓, 它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灵官殿人民群众投身和支持党的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也是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乡村建设中灵官殿人民群众良好精神风貌的文化根基。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我们要进一步深耕、修整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沃土, 以增强新时代乡村民众自信自强的“文化基因”,为新发展阶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支撑。
二、搜寻和整理区域内的重大革命题材
红色文化,其色调一定是红色的,而重大革命题材正是彰显红色文化特征的关键。近代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 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与广大农村有着密切的关系。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我国广袤农村不仅始终是革命战争年代无私支持党的革命事业的战略基础, 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顶力支持国家建设大业的重要依托。百年来,在中国革命极其严酷的战火洗礼下,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中,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创造、积淀了极为丰富的红色资源。 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一些农村地区的红色资源被人们逐渐遗忘, 这既对不起革命先烈,也有愧于老区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大家:“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 绝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 把红色资源运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 ”[1]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 努力搜集和整理农村地区重大革命题材不仅可能,而且十分紧迫、十分必要。
1949 年10 月, 灵官殿地区发生了一场重大战斗。这场战斗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渡过长江之后, 实施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大迂回,大包围”战略过程中发生的一场意义重大的战斗。 关于这场战斗的历史资料,主要散见于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丛书》、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解放战争全记录》、合成第一六二旅编写的《旅史》(合成第一六二旅前身为第135 师)等战史军史资料,傅静等的著作《四野:1949》、王迪康等的著作《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金立新的著作《决战——中南解放战争》等数量不多的研究成果, 以及参战双方部分人士的回忆和一些影视作品相关片段等等。关于灵官殿战斗的研究,笔者于2020 年在《军事历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衡宝战役中的关键一战——灵官殿战斗》,对这场战斗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灵官殿战斗,从战斗规模和激烈程度看,是衡宝战役中异常激烈、残酷的一场大规模战斗,也是四野进军中南以来与白崇禧部队之间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交锋。衡宝战役中,双方调动的总兵力达七十多万(其中,人民解放军54 余万,国民党军20 余万)[5](P3278),这样的阵势本可能发生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或雷霆万钧的歼灭战。然而,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处于大溃败之际, 军队快速溃退已成常态, 真正重大而激烈的对抗场景并不多见。比如,率先发起该战役的西路军程子华兵团第38、第39 军,尽管歼灭了国民党军近9000 人,解放芷江等11 座县城及湘西广大地区,控制芷江至靖县一线,从而“突破守军‘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 切断白崇禧集团西逃贵州的退路……为中路军在衡宝地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5](P448)但期间除了第39 军第116 师经历了一场西线战场最大的一次——“五小时激战,全歼该敌”[6](P383)的战斗外,全程几乎是如风卷残云般快速推进。与此同时,兵分三路由粤赣边境向广东挺进的陈赓集团的东路军战斗也比较顺利, 他们通过在粤赣边境预定地区集结、 在五岭山脉大赓岭要隘梅岭关前与北江第2 支队会师后, 相继袭占南雄、始兴,顺利到达战役集结地域,从而快速突破国民党军在粤北的第一道防线。 但灵官殿战斗则是打得异常激烈、残酷。在10 月6 日至11 日短短的一个星期内, 双方围绕灵官殿——黄土铺地区的战斗投入的兵力多达22 个军,我方参战部队为:第40、第41、第45、第46、第49、第18、第38、第39、第16、第17 军,共10 个军。 白崇禧集团参战部队为:第7、第48、第71、第14、第58、第46、第97、第125、第126、第14 军、第100、第103 军,共12 个军。[6](P440,447-453)这场发生在100 平方公里左右的南方丘陵地形战斗,几乎每一个山头、每一个可能成为掩体的障碍物附近都成了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从战斗的重要性看,这是一场让毛泽东十分牵挂并十分满意的战斗。1949 年10 月10 日深夜23 时至12 日凌晨6 时,在短短的31 个小时之内, 毛泽东向四野指战员发出的三份电文中四次提到这场战斗。 电文中称:“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 闻之甚慰。 ”“祁阳以北被歼之七军、四十八军四个师,是桂系精锐。 ”[8](P12、20)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地方? 是因为在这场战斗中,“白崇禧的4 个师除第138 师师部率1 个团逃跑外,其余2.9 万余人全部被歼,第7 军副军长、参谋长,第171 师师长、参谋长,第172 师师长,第176 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等8 名将级军官被俘。”[6](P453-454)衡宝战役中被歼的4.7 万余人中有一半以上的敌人是在这场战斗中被消灭的。 对于这场战斗的重大战果及意义, 后来毛泽东又在四野表扬第40、第41 和第49 军歼灭白崇禧主力的电报上进一步批示:“被歼者是七军两个师及四八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七军、四八军苦战四天被歼干净。 ”[9](P15)这场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还亲自安排前来参加新中国成立盛典的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一行到衡宝前线采访。 西蒙诺夫回国后, 写了一部近20 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战斗着的中国》。遗憾的是,尽管西蒙诺夫是冲着向世界报道四野的胜利追击而来的, 并且是在这场战斗刚刚结束时就赶到了战斗发生地, 但由于当时战场形势的快速发展, 他对这场战斗的现地采访非常仓促,留下的笔墨并不多。
通过对灵官殿战斗历史题材的搜集、整理,我们可以确定, 灵官殿镇发生的师团以上规模的战斗不下十次, 战斗地点几乎遍及整个乡镇的每一个村庄, 现存的烈士墓地达30 多处, 长眠着近500 名革命烈士。 那些长眠于灵官殿的先烈们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中为追击、 剿灭顽敌而牺牲的,是为打造新中国繁荣发展的根基而牺牲的,他们的英雄壮举是灵官殿红色文化中最闪亮、 最珍贵的组成部分, 从此人民解放军与此前平静而偏远的农村小镇就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了。 人民军队在灵官殿战斗中重创国民党精锐, 不仅极大地加速了中南大追击的战斗进程, 而且把灵官殿描上了中国革命的红色版图。因为这场战斗,灵官殿红色文化有了丰富而生动的感人素材; 因为这场战斗,灵官殿红色文化有了强大而恒久的传承能力。这样一场曾经轰轰烈烈的战斗, 因特殊的历史原因,除了“雷打石烈士纪念碑”等少数几处战场旧址被较好地保护起来外, 绝大多数战场遗址已经难寻当年印记,与此同时,除了那些还健在的当年曾亲历过这场战斗的老人和一些热心的志愿者外, 了解这场战斗、 记住这场战斗的人已经很少了, 不少年轻人对发生在家乡的这场战斗仅仅是“听前辈们说过”。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在当地政府、民间“志愿者”和一些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场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重大战斗正在逐步呈现出以史为镜、以史明志,催人奋进的应有影响力。
三、收集和梳理区域内的珍贵红色文史资料
红色文化就是一本无言之书, 而记录和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电报电文、音像资料、通讯报道及战地文学等历史文献是红色文化得以永久留存的重要载体。 其中,尤其是那些战地通讯、战地文学等作品,往往以其鲜活灵动的现场气息、感染心灵的艺术魅力、永续流芳的价值导向,犹如红色素材中的珍珠,十分难得、弥足珍贵。 灵官殿红色文化素材除了前文提到的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纪实文学作品——《战斗着的中国》 中有部分记述之外,竟然还被两篇著名的战地通讯——《衡宝之战》和《界岭夜雨》永久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衡宝之战》和《界岭夜雨》的作者是新华通讯社原社长、 当代著名新闻记者穆青,1949 年4 月作为新华总社特派记者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采访,生动报道了人民军队“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10](P1464)的战斗场景。《衡宝之战》和《界岭夜雨》就是穆青在这期间记录的反映衡宝战役的两篇重要通讯。 其中,《衡宝之战》 非常精彩地记录了发生在灵官殿的几个战斗场景,而《界岭夜雨》则是一篇反映灵官殿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之间至真至诚的鱼水情谊的战地通讯。
在《衡宝之战》中,穆青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发生在灵官殿的两场重大战斗。 一场战斗发生在灵官殿镇西北方向与佘田桥镇野鸡坪乡交界的山地。“6 日晨,白匪为了要拔除这支要命的钢钉,曾命令一七一师一个营尾随我军后部, 企图夺路前进, 当即在离衡宝公路不远的孙家湾一带山地与我某团三营七八连接触。 当时,白匪居高临下,以迫击炮重机枪向我猛攻。接着我军发动一个反击,敌人即慌忙丢下成堆的尸体狼狈逃走, 再也不敢组织进攻了。”“这一次成功的阻击战,我军以两个排的兵力,打垮白匪主力1 个营的4 次猛攻,使这个号称白匪‘王牌’、‘钢军’的第七军,第一次小小地尝到了一下人民解放军的厉害, 从此在白匪官兵阴暗恐惧的心壁上, 又涂上了浓重的一笔。 ”[11](P101-102)
另一场战斗发生在灵官殿的东北方向与衡阳交界的山地。1949 年10 月7 日晚上,已经陷入敌人阵地30 多个小时的我第135 师第403 团趁着茫茫的雨夜,“不顾一切疲劳、饥饿,在当地十几个群众的向导下,穿过山林小路,连夜跳出敌人的包围。这中间更出现了一桩空前壮烈的英雄故事:该团警卫排50 余人,在黑夜中迷失路径,误入敌人的巢穴,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中,遭受到敌人四边山上的猛烈射击,除10 余人突出重围外,其余40 余人全部壮烈战死,无一人缴械屈服。 ”[11](P103)
同时,《衡宝之战》还对灵官殿严峻、激烈战斗态势作了描写:“由于我军勇猛地穿插敌阵, 完全和敌人搅在一起,在周围不满百里的狭小山区,我军虽然拖住了敌人逃跑的尾巴, 但也四面八方地被敌人包围起来。七八两日,当我军后续部队正数路越过衡宝公路星夜前进时, 一三五师的全体同志们所处的环境是相当艰险的, 白匪的4 个主力师几乎同时压在他们的头上。围绕着灵官殿、石株桥一带,周围所在的村庄要道几乎布满了匪军”[11](P102)。
在《界岭夜雨》中,穆青几乎是用素描的方式,记下了灵官殿老百姓与人民军队之间至真至诚的鱼水情谊。 穆青是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下午1 点钟左右,随第45 军政治部临时组织起来的一个俘虏收容队一起赶往第135 师机关驻地时途经战火洗劫后的灵官殿,眼前已是“一片异常荒凉”的景象:从灵官殿的铜锣坪到界岭不到5 公里的山间小路上,“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到战场的景象,”[11](P115)国民党匪徒们“在沿途山坡上、稻田里、谷溪间……却到处乱丢着各种各样的物品, 其中最多的是钢盔、胶皮靯、日记本、女人照片、电线、破衣服以及一堆堆不知曾烧毁什么的灰烬。 ”[11](P115)当穆青等人在凄厉的秋雨中从灵官殿集镇一路泥泞地到达界岭时,已是夜幕降临时分,在人员极度疲惫,甚至连牲口都“统统掉了队”的情况下,全队人马决定改变直接赶到尚处在20 公里之外的第135 师机关驻地的计划,暂歇于这个小村庄。 这一住,成就了《界岭夜雨》;这一住,历史永远记住了灵官殿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至真至诚的朴实情怀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倾情奉献。 这是因为我们从《界岭夜雨》中读到的是:一些老百姓顾不上收拾已被战争毁坏的家园, 却“连忙生起火来让我烘烤”、帮助“烤火、做饭、铺稻草、放警戒”;一些老百姓在黑夜中自发冒雨到村外给前方军队筹粮;一些老百姓摸黑把前线的伤兵护送到这里安抚;也有老百姓把自己在白崇禧部队搜掠财物时冒死珍藏的食物“纷纷从床底下、屋角里挖出”送给解放军……穆青笔下这一处处近乎白描的图景, 与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地民众推着小推车踊跃支前, 以及渡江战役中成千上万的小船协同解放军披波斩浪一样, 反映的是那个年代的军民鱼水之情, 彰显的是那个年代党与人民群众心连着心的真诚关系, 以至于穆青在文章的结尾动情地感怀:“新区前线的群众在这艰苦困难的战场之夜所表现出的意志和行动, 正说明着我们的人民,在这伟大的年代,是怎样在飞速地变化和前进……”[11](P116)
如此珍贵而完整的红色文史资料, 是七十多年前战场记者留给灵官殿人民的宝贵红色文化载体, 它在将灵官殿战斗中那一个个感天动地的红色故事定格成永远的同时, 也将灵官殿战斗中那一个个英勇奋斗、 无私无畏的人物形象永远地留存在灵官殿人们的情愫之中。然而,由于时间的推移人们淡忘了这段历史,甚至有人将《界岭夜雨》的场景错误地“搬家”到与真实故事发生地相距几十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地点。近年来,灵官殿镇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已经着手对发生在境内的这场战斗进行了系统梳理, 当地一些民众也逐渐重视起对家乡红色资源的整理与保护, 他们通过广泛收集历史资料和抢救性收录当年亲历这场战斗的老人们的口述历史, 以再现并铭记人民军队英勇奋战的感人事迹和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场景。
四、汲取和融入新阶段的亮丽时代元素
红色文化,既是红色血脉传承的结果,又是红色血脉永续传承的重要载体。 红色文化丰富而灵动的资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需要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更加鲜艳和美丽的花朵, 结出更加丰硕而诱人的果实。 有着丰富革命题材资源的灵官殿红色文化, 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正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呈现出更加亮丽的光彩。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 中央宣传部 民政部 司法部关于开展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工作的通知》精神,从2019 年起, 要在全国组织开展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活动, 通过示范创建活动以推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育和树立一批乡村治理典型, 发挥其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进一步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知》规定,示范乡(镇)的创建标准是: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健全;基层管理服务便捷高效;农村公共事务监督有效;乡村社会治理成效明显。2019 年12 月24 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关于公布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的通知》(中农发〔2019〕22 号)显示,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灵官殿镇名列全国首批99 个“乡村治理示范乡镇”之一。 这样的成绩,这样的荣誉,是新时代灵官殿人民的骄傲,也是新时代灵官殿人民的财富, 更是对灵官殿党组织和政府在农村治理工作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的高度肯定和褒奖。
灵官殿镇之所以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的引领力量和全国乡村有效治理的模式和样板, 灵官殿红色文化基因对其滋养和影响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这样相对偏远的农村里, 优良的传统道德依然在邻里间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村民们性情率真而友善, 大家相处简单而和睦, 特别是敬老爱幼,邻里互助互帮的好传统、好风气依然能够得到很好的承传。 灵官殿镇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始终铭记英烈壮举,弘扬英烈精神,对在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中为追击、 剿灭顽敌而牺牲并长眠于此的革命烈士, 依然像当年的乡亲们对待子弟兵那样真诚以待,适时地到烈士们长眠的地方来凭吊他们、缅怀他们。作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最重要、最核心的领导力量, 灵官殿镇党组织和政府在脱贫攻坚、移风易俗、发展特色产业、开展环卫整治、还青山绿水、疫情防控等工作中,充分发挥全镇党员、党员先锋岗、支部先锋队的模范带头作用,并逐步探索建立起了包括镇机关干部、村干部、村民小组长与“院落长”在内的职责明晰的“3+1”管理制度,创建了镇周例会、专干月例会、材干部周例会、组长月例会、党员组织生活例会与“院落会议”相协调的“5+1”工作模式。 毫无疑问,灵官殿镇乡村治理中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必定与其红色文化的长期孕育与弘扬密不可分。
五、结束语
新时代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 为我们进一步汇聚起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的磅礴伟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像井冈山、古田、延安、西柏坡等这些享誉国内外的重大红色文化典型,因其社会影响大、开发利用时间长、积累经验丰富,是全国各地党政干部、不同年龄阶段社会人士和社会组织甚至一些世界进步人士与组织前往参观、学习的“红色圣地”,这些地方的红色文化正以其特有的优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像灵官殿这样一些小型、精致的红色文化资源,同样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军队及当地人民群众共同建立的, 是我国丰富红色文化基因库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与我国大型的成熟的红色文化典型一起共同发挥着承传红色基因的作用。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当地应该紧紧围绕“立足村庄特色,用好红色资源,做到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 把红色资源作为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作为团结凝聚广大群众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的有效载体”[1]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作用,使之成为当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教育的重要基地, 成为不断激发当地民众努力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动力源泉。近年来,灵官殿红色文化资源的影响力正在快速增长, 这里不仅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当年参加这场战斗的英雄们的后代来寻觅先辈足迹, 也引起了一些志愿者和学者的关注, 一些研究成果已相继在自媒体和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灵官殿镇也正在成为邵阳市、邵东市党政机关进行党性教育的重要基地, 成为当地党员干部、 人民群众和中小学生接受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