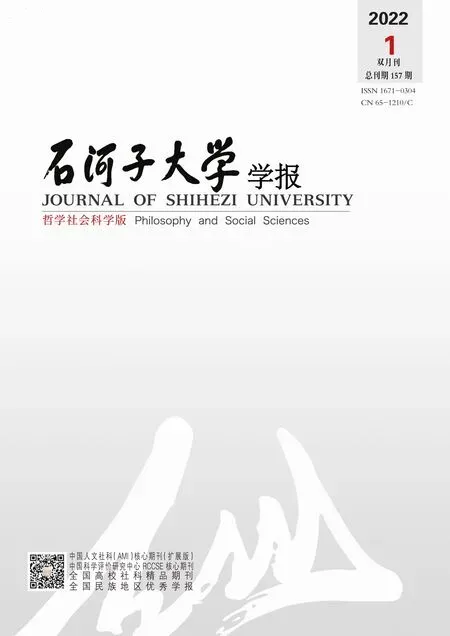目连故事流播研究四题
2022-11-26李小荣
李小荣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在中国佛教文学艺术史上,目连文化是备受关注的内容之一,研究成果颇丰。由于史籍传承的复杂性、口传文献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悬而未决的问题仍然不少。有的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然细究之下,却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兹以笔者发现的四个小问题为例,在前贤时俊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作探析。
一、《目连变》抑或《目连经》
晚唐孟棨①孟棨,据陈尚君《〈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载《新国学》第6 卷,成都:巴蜀书社,2006 年,第1-17 页),应当作孟启。《本事诗》“嘲戏第七”曰: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②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21 页。。
此则材料,因涉及敦煌俗文学《目连变文》①按:北图成字76 号(B.7707)尾题作《大目犍连变文一卷》,写经题记称所写为“《目连变》”,则知《目连变》可以是所有目连故事类变文的简称。,故深受学人重视②如曲金良据此材料推断,《目连变》早在张祜拜谒白居易的宝历元年(825)之前就广为人知,且为文人雅士举为笑谈(《敦煌佛教文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第223 页);王伟琴则联系《长恨歌》的创作史实,指出《目连变》创作于元和元年(806)十二月之前(《敦煌变文作者作时考论》,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86 页)。。然敦煌目连故事类变文写本甚多③相关情况介绍,参李小荣《敦煌变文》,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33-36 页。又,新发现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写卷及其缀合情况,参张涌泉《新见敦煌变文写卷叙录》,《文学遗产》2015 年第142-144 页。,系统不一,大致有三:一是P.2193《目连缘起》(首题,卷背题《大目连缘起》);二是北图成字96号(B.8444),首尾俱残,拟题《目连变文》;三是S.2614,首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尾题《大目犍连变文》一卷,同一系统者还有P.2319、P.3107、P.3485④按:该卷首全尾残,首题作《目连变文》。、P.4044、P.4988、S.3704 等十余种)。而张祜所指究竟属于哪一系统,目前学界尚无明确看法,如王伟琴意见是不能确指⑤参王伟琴《敦煌变文作者作时考论》,第86 页。,张涌泉则把它和P.2193《目连缘起》相联系:“本篇有‘自从一旦身亡之后,何期慈母落黄泉’和‘哀哀慈母黄泉下……地狱难行不可求’之句,和白诗‘上从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意境近似,张祜所谓《目连变》或许指《目连缘起》而言。”⑥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1017 页。又,本篇由张涌泉校注。然据尾题“界道真本记”分析,《目连缘起》很可能是五代宋初三界寺道真所作,创作和抄写时间介于公元 949—987 年之间⑦罗皓月《敦煌文献目连变文写本叙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 年第9 期,第76-77 页。,如果此种推断不误,活跃于中唐的白居易(772—846)、张祜(约 785—849?)自然不可能听到、读到后出的《目连缘起》。更为重要的是,其他文献对白、张各以对方诗句互嘲的趣事也多有记载,其间表述略有不同,如年代稍晚于孟棨的王定保在《唐摭言》卷13“矛盾”条说:
张处士《忆柘枝》诗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白乐天呼为“问头”⑧按:王定保所用“问头”,和孟棨的“款头”,含义相同,皆指官府审问罪人时的程式性提问,如S.2630《唐太宗入冥记》就说地府判官崔子玉用问头来审判唐太宗(参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322 页)。而目连之母经历十八重地狱时,情形相似与之相似,不过,她遭受惨不忍睹的折磨,且是目连亲眼所见,故加快了目连救母的进程。,祜矛楯之曰:“鄙薄‘问头’之诮,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连经》,《长恨词》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此岂不是目连访母耶?”⑨〔五代〕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第271 页。
比较孟、王二人所言,内容一样,仅文字上详略有别。所说《忆柘枝》,当指张祜传世诗作《感王将军柘枝妓殁》⑩尹占华校注《张祜诗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7 年,第363 页。,《长恨词》即白居易的《长恨歌》。而《目连经》是否和孟棨所说《目连变》同义呢⑪姜汉椿《唐摭言校注》第272 页指出:“目连经”之“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变”。但历史上更常见的版本是前者。?
两宋以后对白、张互讥事件的叙述,基本承袭孟、王之说,且王氏之语常被各种类书转引,影响似远大于《本事诗》所述相关内容⑫如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 251《诙谐七》“张祜”条(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6 册,第 1948 页)虽注明“出《摭言》”(《摭言》即《唐摭言》),然比对其引文,实出自《本事诗》。这似是编者误注,却也从侧面说明《唐摭言》的社会影响更大些。。但不同编者拟题有别,如朱胜非(1082—1144)编《绀珠集》卷 4作《目连变》,曾慥(?—1155)⑬曾慥生卒年,此据黄永峰《曾慥生平考辨》(《宗教学研究》2004 年第1 期,第138-140 页)。编《类说》卷 34 作《目莲访母》⑭目连、目莲,所指人物相同。,祝穆(?—1255)撰《事文类聚》卷236 作《张、白互讥》,许自昌(1578—1623)辑《捧腹编》卷5 作《问头诗》⑮该书把“张祜”之“祜”刻成“祐”,是形近致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祝、许二人明确标注引自《摭言》,引文皆作“《目连经》”,据此,“经”字在《唐摭言》版本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写本S.4564 即为《目连经》(尾题)①该卷首残尾全,现存31 行,始“尔时目连辞母”,止“受此苦恼”。罗皓月把它作为敦煌目连变文写卷五大系统之一(《敦煌文献目连变文写本叙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 年第9 期,第77-78 页),但证据并不充分。从今存文本用了八个汉译佛经惯用时间语“尔时”看,其形式很像译经,或至少说是经抄。笔者更倾向于它是伪经,证据详后。,它叙述目连寻母过程是“上观三十三天,遂不见其母。下观十八地狱,乃见其母在于饿鬼道中,身受极苦”②黄永武博士主编《敦煌宝藏》第36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年,第576 页。,而白居易“上穷碧落下黄泉”所用“上……下……”句式,确实和《目连经》如出一辙(仅是把佛教语汇“三十三天”“十八地狱”改成了本土道教术语“碧落”“黄泉”,此与临邛道士为唐明皇殷勤寻找杨太真的语境相契合),故张祜把《长恨歌》叙述的道教寻仙调侃成佛教的目连访母,自有一定的合理性。
S.05755《杂抄》(一名《珠玉抄》,二名《益智文》,三名《随身宝》)在“(七月)十四日十五日何谓”后注云:
为大目乾莲母青提夫人,缘背儿功德之物,避儿广买鸡肫,造之恶业,堕在十八重地狱中,即至饿鬼狱中受种种苦。目连投佛出家,后坐禅定观之,遂告诸佛,啼泣救母,令七月十四日十五日造盂兰佛盆供养,因此一切七代先亡父母并皆得食吃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九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23页。又,《杂抄》写卷还有 S.4663、P.3393、P.3769 等。。
《杂抄》类似于日常生活指南,其对盂兰盆会之缘由的介绍,同样融汇了伪经《目连经》的说法。
此外,中唐著名高僧宗密(780—841)《佛说盂兰盆经疏》卷下在疏释经文“佛言:汝母罪根深结”时云:
定光佛时,目连名罗卜,母字青提。罗卜欲行,嘱其母曰:“若有客来,娘当具膳。”去后,客至母乃不供。仍更诈为设食之筵。儿归,问曰:“昨日客来,若为备拟?”母曰:“汝岂不见设食处耶?”④《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9 册,第509 页下栏。又,校勘记指出“有经中”之“中”,甲本(指德川时代刊宗教大学藏本)无。
宗密所谓“有经”之“经”,当指成立于公元600—650 年之间的伪经《净土盂兰盆经》(又称《大盆经》《大盆净土经》,今存写卷是P.2185)⑤参岡部和雄《〈净土盂兰盆经〉の成立とその背景——伪经经典成立に关すね一试论》,载《铃木学术财团研究年报》第2 号,1966 年 3 月,第 59-71 页。。而敦煌变文目连名罗卜、其母名青提的直接依据即出于此⑥参小川贯弌《目莲救母变文の源流》(载板田要编《地狱の世界》,东京:溪水社,1990 年,第287-313 页),郑阿财、姚孟君《〈盂兰盆经〉系及其注疏与佛教中国化》(《普门学报》2004 年第1 期,第127 页)等。陈允吉先生指出,目连小名罗卜的依据是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敕扶南国沙门僧伽婆罗所译《文殊师利问经》卷上《序品》“大目犍连”名下之注文“此言罗茯根,其父好此物,因以为名”(《〈目连变〉故事基型的素材结构与生成时代之推考》,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223 页),而罗卜、罗茯,一音之转也。不过,《文殊师利问经》没有提及目连母亲名号,据北宋慧宝注《北山录》卷6“目连泣饷”“目连母,长爪梵志族青提也”(《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 册,第608 页中栏),则青提属于长爪梵志家族(长爪梵志故事,详见《撰集百缘经》卷10《长爪梵志缘》等)。P.2185《佛说净土盂兰盆经》则说“尔时目连生一婆罗门家,字罗卜,母字清提”,“清”“青”,俗文学写本中常通用。。嗣后,释元照(1048—1116)《盂兰盆经疏新记》卷下又明确指出:“世有《目连经》,与此不同,乃人造伪经耳。”⑦《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21 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6 年,第475 页下栏。“与此不同”的“此”,指题为竺法护所译《(佛说)盂兰盆经》。普观述《盂兰盆经疏会古通今记》卷下同样注明:“世有《目连经》,与此经不同,又无译者,恐是伪本。”⑧《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21 册,第503 页中栏。固然二人行文语气略有不同,却都说明伪经《目连经》两宋时期仍在流传。
有趣的是,白居易一方面与宗密交往颇深,如大和七年(833)作《赠草堂宗密上人》⑨谢思炜撰《白居易诗集校注》第5 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2367 页。,就表示了倾慕之情⑩按: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大和六、七年间于苏州作有《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诣河南尹白侍郎》(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03 年,第576 页),另一著名诗人马戴有《送宗密上人》(《全唐诗》卷5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1424 页中栏),可知宗密和当时著名文士交往甚频。;另一方面,他以佛教伪经入诗并非个案,如早在元和五年(810)作《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句下便有自注:“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头陀经》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①谢思炜撰《白居易诗集校注》第3 册,第1133 页。《心王头陀经》,即伪经《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②有关本经的详细介绍,参曹凌编著《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343-346 页。。凡此,都可以视作白居易熟悉《目连经》《净土盂兰盆经》等“目连系”伪经③按,学界对《盂兰盆经》的真伪至今尚无定论。笔者倾向于把除此之外的《目连经》《大盆经》《报恩奉盆经》(《报像功德经》)等归入这一系列。的旁证。
如果我们再联系高承《事物纪原》卷8“岁时风俗部”、吕原明《岁时杂记》谓北宋中元节祭父母时所用盂兰盆“中贮杂馔,陈目连救母画像,致之祭祀之所”④〔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437 页。“画目连尊者之像,插其上。祭毕,加纸币焚之”⑤陈元靓撰《岁时广记》卷30 引语,《丛书集成初编》本,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年,第341 页。的记载,则知当时中元节前印卖《目连经》(引文见第二节)之举,正好体现了佛教文化传播时经、像并尊的传统。而所绘目连像,当是据《目连经》等而绘制的变像,其主体内容是目连救母。当然,中元祭祀目连尊者之举,最早似与梁武帝有关。义楚《释氏六帖》卷22“武帝送盆”条引《弘明》云:“梁武每于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养,以车日送,继目连等。”⑥《大藏经补编》第13 册,第454 页。又,今本《弘明集》无此内容,当是佚文。从前后文语境判断,此“继”当是“祭”同音而误刻。《佛祖统纪》卷37 又载大同四年(538)“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⑦《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 册,第351 页上栏。之事,则知萧衍在推动盂兰盆法会向中国祭祀传统转化中起了先导之用。
综上所言,我们认为张祜嘲笑《长恨歌》是《目连经》,更符合《长恨歌》的句式结构。但仅从目连上天入地寻母这一共同情节而言,《本事诗》等比作《目连变》也说得通的。
二、“尊胜目连经”应作《尊胜经》《目连经》
两宋之际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8“中元节”条有云: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⑧〔宋〕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按:原书繁体竖排,此处引文改用简体横排),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794-795 页。另,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211-212 页)句读,与伊氏相同(邓氏未用标点符号,原书同样繁体竖排)。。
按照伊永文的标点⑨《东京梦华录笺注》,第795 页。,《尊胜目连经》仅指一种佛经。事实上,我们查遍传世佛经目录,都没有该经的任何记录⑩罗皓月怀疑孟元老所说“尊胜目连经”和S.4564《目连经》有渊源关系(《敦煌文献目连变文写本叙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 年第 9 期,第 78 页),仅猜想而已。。据宋末陈元靓《岁时广记》卷30“中元(下)”之“献先祖”条引皇朝《东京梦华录》,“尊胜目连经”五字,实作“《尊胜经》《目连经》”⑪〔宋〕陈元靓撰《岁时广记》,第341 页。又,陈氏引文比前述伊永文、邓之诚等校注本,“在上焚之”后多“以献先祖”四字,并以此为拟题依据。,即包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又称《尊胜陀罗尼经》,《尊胜经》为简称)⑫是经又称《尊胜陀罗尼经》,主要有杜行顗、地婆诃罗、佛陀波利、义净译本,最流行者为佛陀波利本。和前述伪经《目连经》。即便“尊胜目连经”五字不错,也应标点成“《尊胜》《目连经》”⑬按:陈翘已注意到这一点,参《〈东京梦华录〉“中元节”条两种版本一字之差的思考——兼议北宋目连戏之形态特征》,《戏曲艺术》2007 年第4 期,第9 页。但他认为《尊胜经》与目连救母无关,则可商榷。。
《尊胜经》属密教经典,主要有杜行顗、地婆诃罗、佛陀波利、义净等译本⑭有关该经译本系统之介绍,参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第42-46 页。,最流行的是佛陀波利本。因宣扬《尊胜咒》(即《尊胜真言》)、尊胜(经)幢具有强大的破(地)狱、救亡、祛病、延寿功能而在僧俗二众中甚为流行。自初唐以降,有关《尊胜咒》灵验和社会各阶层广建尊胜幢、尊胜坛的史料(尤其是碑刻材料)比比皆是。如意元年(692)史延福就在龙门摩崖石刻《尊胜陀罗尼经》①〔清〕叶昌炽撰,王其祎校点《语石》,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112 页。;长安二年(702),本愿寺僧知逊率合县道俗而敬造尊胜经幢,目的之一在为七代亡者祈福②〔清〕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312 页下栏。;上海图书馆藏094号敦煌文书,所抄佛陀波利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后则有题记说“开元五年岁次丁巳十一月十六日,清信佛弟子氾感儿减削净财,为其亡妻公孙敬写,愿亡者神生净土,见佛闻法,合家去离三灾九厄,福命延长。及自既身,法界众生,咸登佛果”③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368 页上栏。,抄《尊胜经》除荐亡之外,亦有其他功用;白居易开成二年(836)于洛阳所作《东都十律大德长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记》④〔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1920-1922 页。, 在赞扬其师智如(749—834)好建尊胜幢之义举的同时,更特别强调了他以尊胜幢为茶毗塔的遗愿;有的灵验记,还把“孝养父母”并持诵《尊胜咒》而超度父母亡灵生天的洛阳人张绎(活动于开元天宝年间)和“目连释子救母”相提并论⑤《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 册,第386 页下-387 页上栏。。两宋时期,把尊胜幢建于墓侧或墓道已成为流行的丧葬习俗之一⑥参夏广兴《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与宋代丧葬习俗——以尊胜墓幢的建立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5 年第1 期,第59-65 页。。明清两朝,不同佛教法会及显密佛教仪式的汇流,更是常态,钟惺(1574—1625)撰《募盂兰盆施食念经礼忏疏》即引僧人定安之语曰:“吾将以今年是日于水陆作盂兰盆会,持《尊胜咒》,施食、念经、礼忏,为五昼夜功德。”⑦〔明〕钟惺著,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502 页。清初贺裳顺治三年(1646)⑧作品系年,据朱则杰《〈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贺裳等三位丹阳贺氏家族作家为中心》,《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第 59 页。作《丙戌中元放熖口榜文》又说:“敬于中元日会演盂兰,幢宣尊胜。”⑨〔清〕贺裳:《蜕疣集》,清初鸳桨阁刻本,载四库未收书编辑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 辑第22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第 27 页下栏。由此推断,尊胜陀罗尼信仰和以盂兰盆会为载体的佛教孝道文化早已合流。
前引吕原明《岁时杂记》谓北宋中元节盂兰盆法会上,所画目连尊者像和纸币共同焚烧以祭父母;而两宋之际曾任严州太守的李裁“每夕焚《尊胜陀罗尼》以施鬼神”,庄绰大为感慨道“《尊胜》之利于幽冥,盖不可不信矣”⑩〔宋〕庄绰撰,李保民点校《鸡肋篇》卷中,《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4006-4007 页。,既言“每夕”,自然也包括中元日;日本临济宗僧无著道忠(1653—1744)《禅林象器笺》卷21“经马”条解释从宋国传入的禅林法和盂兰会焚烧纸马、《心经》的缘由时说“焚马,多见本据;焚经,难得其证。适得焚《尊胜咒》施鬼事,是可证焚《心经》也”⑪《大藏经补编》第19 册,第598 页下栏。本来,按佛教戒律,佛经不可焚毁,但特殊场合也有例外。道忠书中又引《异闻总录》所载淳熙六年(1179)李永印尊胜陀罗尼幡数十本焚施鬼道为证。;故综合判断,当时盂兰盆会所挂目连图像⑫据高承撰《事物纪原》卷8“盂兰”条“今人第以竹为圆架加其首,以荷叶中贮杂馔,陈具其救母画像,致之祭祀之”(明弘治十八年魏氏仁实堂重刻正统本,页24b),则知所焚目连像,除目连的单尊像之外,也可以是目连救母的故事类图像。,连同所抄的《尊胜咒》⑬按:当时印卖的《尊胜经》《目连经》,推想也应和目连尊者像一块焚烧而献祭于祖先。,最后都焚烧成一缕缕献祭的香烟了。
三、“目连经救母杂剧”之“目连经”含义
《东京梦华录》卷8“中元节”条又云:
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⑭〔宋〕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第795 页。。
对“便般目连救母杂剧”八字,康保成首先发现四库全书本、秘册汇函本、学津讨源本、河南省立图书馆1921 年刻本在“目连”后多出一个“经”字⑮〔清〕秦嘉谟撰《月令粹编》卷12“《目连经》”条引《东京梦华录》亦同(清嘉庆十七年秦氏琳琅仙馆刻本,页14b)。既然以“《目连经》”设立条目,自然少不了“经”字。,并标点成“便搬《目连经》(《救母》杂剧)”,尔后结合日本京都金光寺发现的《佛说目连救母经》,指出“七天演出实际上是以诵经、讲经为中心的佛教仪式活动,其中包括以‘救母’为内容的‘杂剧’”“所谓《救母》‘杂剧’,或即大体相当于变文演唱,并杂以诸般伎艺而已”①康保成:《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年,第245-247 页。。嗣后,陈翘从版本学角度详细考证“经”字不是衍文,认为孟元老所记载的北宋目连戏应是较为短小、带有滑稽、谐谑味道的,类似于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滑稽戏性质的、在中元节期间每天不断演绎诠释印卖的《目连经》的内容,反复演出的小戏,甚至可能是唐代目连变文在北宋民间复活的一种新形式,而不是一个能够连续演出七八天的大型戏剧。其历史渊源及演变过程是:《盂兰盆经》→《目连变文》→《目连经救母杂剧》②陈翘:《〈东京梦华录〉“中元节”条两种版本一字之差的思考——兼议北宋目连戏之形态特征》,《戏曲艺术》2007 年第4 期,第 3-12 页。。孔美艳从搬演主体是乐人而不是由佛教僧侣“诵”或“讲”的,“观者”主要是来观看演出而不是来参加宗教仪式活动的,进而强调:“虽然不排除有“应景”的旨归,但我不认为它是‘以诵经、讲经为中心的佛教仪式活动’,而认为它是以佛教目连经的目连救母故事为主要内容,中间穿插各种伎艺表演(这是中国戏剧的表演习惯,且越是初期这种特点应该越明显) 的供人观赏的戏剧艺术表演。”③孔美艳:《中元节演剧略论》,《中华戏曲》第44 辑,第252 页。三人其实都不同意孟元老所载东京搬演的目连戏是成熟的大型杂剧。田仲一成则别出心裁,首先通过重新考订日本金光寺藏所谓元刻本《佛说目连救母经》实际上是南宋初年的宁波刻本,然后分析其结构上的故事性、文学性、戏剧性,从而推定《东京梦华录》所说的《目连救母》杂剧也会有较为复杂的故事,甚至接近明代中期创作的郑之珍本,并得出结论说北宋末期中国戏剧已经有成熟的剧本④田仲一成:《目连戏的成立过程——以宋代佛典〈佛说目连救母经〉为起点的考察》,载黄仕忠主编《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2-31 页。。
对于康保成、陈翘的版本考证,我们还可以提供另一证据,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卷16 引明人倪绾《群谈采余》自述其考《梦华录》的结果是“但多‘《目连经》,搬其杂剧’数言”⑤《大藏经补编》第19 册,第512 页下栏。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引《群谈采余》,文字基本上和郎瑛《七修续稿》卷7《辩证类》“盂兰盆会”相同,但后者作“但多‘卖《目连经》,搬其杂剧’数言”(明刻本,页9a),即多一“卖”字。另,倪绾、郎瑛两人都是拿《东京梦华录和》和陆游《老学庵笔记》相比较,二人所用“其”字,显然指代《目连经》。,可知倪绾引用的版本也作《目连经》⑥赵义山认为“衍一‘经’字,便成病句”(《学术观念与文献释读——以王国维的“真戏曲观”与相关文献释读为例》,《江淮论坛》2016 年第 5 期,第 9 页),却未给出理由。。但我们反复研读康保成等人的结论,感觉都有不少推测的成份,原因在于孟元老所说的《目连救母》杂剧并无文本传世。而四人对《目连救母》杂剧所依据的佛典,理解不尽相同。康保成标点成“《目连经》(《救母》杂剧)”,后四字是夹注形式,意即“所谓《救母经》就是北宋的《救母》杂剧”⑦康保成:《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第247-248 页。其所说《救母经》即日本流传的《佛说目连救母经》。,但他没有找出“经”称“杂剧”可靠的历史文献;陈翘认为孟元老所说《目连经》,似是《盂兰盆经》;孔美艳赞同其师康先生之说;田仲一成则主张源自《佛说目连救母经》。考虑到后世目连戏中目连名罗卜、母名青(清)提等中国化名字,《盂兰盆经》并未涉及,因此,它自然可以被排除在外⑧按:吉川良和认为出于《尊胜目连经》(《关于在日本发现的元刊〈佛说目连救母经〉》,《戏曲研究》第37 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年,第177 页)。前文已否定了“尊胜目连经”的存在,故其说难以成立。。剩下的可能主要有四:一是前述敦煌伪经《目连经》,二是《净土盂兰盆经》,三是《佛说目连救母经》,四是高丽本《佛说大目连经》。后两种,田仲一成认为是同文异版,其说可取。《佛说大目连经》,虽题为“西天三藏法师法天译”,然从其用语及叙述内容看,显然是中土伪经。它高丽中期已传入韩国,李能和撰《朝鲜佛教通史》卷1 载睿宗文孝王(丙戌)元年(1106)秋七月:“癸卯,设盂兰盆斋于长龄殿以荐肃宗冥佑;甲辰,又召名僧讲《目连经》”⑨《大藏经补编》第31 册,第345 页上栏。,可见此次盂兰盆会始于农历七月十四日,十五日所讲《目连经》即是《佛说大目连经》。嗣后,历代皇室还五次讲过本经①卢仲邦:《韩国目连故事流传研究——以收藏在〈月印释谱〉的目连故事为中心》,南京: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23 页。。《朴通事谚解》卷下又记载了一个高丽师傅(僧人)在庆寿寺盂兰盆斋会上“说《目连尊者救母经》,僧尼道俗善男信女不知其数,人人尽盘双足,个个擎拳合掌,侧耳听声”②汪维辉编《朝鲜时代汉语均教科书丛刊》(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288 页。又,经名书名号是笔者所加。,有人怀疑所说经与睿宗元年的《目连经》是一个系统③卢仲邦:《韩国目连故事流传研究——以收藏在〈月印释谱〉的目连故事为中心》,第23 页。。若从经名推断,应和《目连救母经》是名异实同,仅是予目连以“尊者”之敬称而已。此外,从经文“讲”“说”的敷演方式看来,至少宋元明三朝仍然有故事类佛经的宣唱。换言之,目连故事的讲唱和目连戏的演出,当时并行不悖。
前述《净土盂兰盆经》《佛说目连救母经》《佛说大目连经》,其共同点在于构建了目连的中国化家庭组织,主干成员有三,即罗卜、其父傅相、其母青提,此点是《盂兰盆经》所没有的。若结合郎瑛、倪绾比较《东京梦华录》比《老学庵笔记》多“(卖)《目连经》”和“搬其杂剧”的记载,则知所搬杂剧自然是以《目连经》为依据而创作的。因此,《东京梦华录》有关目连戏演出的文字表述,正确标点是:“便搬《目连经救母杂剧》。”④如 《坚瓠集二集》卷4“讥教授”条载弘治末泉州府学某教授“一日设宴于明伦堂,搬演《西厢杂剧》”(褚人获辑校,李梦生校点《坚瓠集》,《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802 页),可知“搬×××杂剧”的说法是成立的。从其演出长达八天及“观者倍增”的演出效果推断,北宋东京的城市剧场应有以目连救母为主要故事情节的大戏(大型杂剧)⑤参赵义山《学术观念与文献释读——以王国维的“真戏曲观”与相关文献释读为例》,《江淮论坛》2016 年第5 期,第6 页。。其依据经典,应是田仲一成考订的南宋初年宁波所刻的《佛说目连救母经》。换言之,南宋初期的《目连经》与唐五代的《目连经》含义有别,它主要指《佛说目连救母经》。
四、目连救母故事与禅宗语录
较早提及目连救母故事的禅宗语录是《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是书在曹洞宗初祖洞山良价(807—869)《后寄北堂书》后附录了《娘回书》,信中母亲对良价“为报北堂休怅望,譬如死了譬如无”的决绝态度深感失望:“今既誓不还乡,即得从汝志,不敢望汝如王祥卧冰、丁兰刻木,但如目莲尊者度我,下脱沈沦,上登佛果。如其不然,幽谴有在,切宜体悉。”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 册,第516 页下栏-517 页上栏。其意是说百年之后,希望儿子至少能像目连一样举办盂兰盆会超度自己脱离恶道而成佛。嗣后,随着禅林清规的流行,盂兰盆会是佛寺七月中元(鬼)节必不可少的法事活动之一。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明清以来不少禅师的出家缘由竟然是出于目连戏的影响。如明鸡足山传衣寺释寂观在母亲病逝后“哀泣几灭,见俗演《目连》”而固请出家⑦喻谦撰《新续高僧传》卷55,载《大藏经补编》第27 册,第404 页下栏。;《天童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3载顺治皇帝问道忞(1596—1674):“闻得广东比北方人尤不信向三宝,老和尚少年因甚出家?”道忞曰:“因见《目连传》,痛念生死,遂发心修行。”⑧《嘉兴大藏经》第26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年,第297 页上栏。《即非禅师全录》卷25《广寿即非和尚行业记》谓即非如一(1616—1671)事母孝谨,十三丧父后:“一日观演《目连传奇》有感,叹曰:‘立身扬名特世间孝耳,曷若出世法遍资恩有乎?’”至十七岁终出家⑨《嘉兴大藏经》第38 册,第742 页上栏。;《正源略集》卷4 又说松江金泽颐浩子山如禅师“幼丧母,年十七,因村坊演剧,见目犍连事。即慨然曰:‘吾欲报母,何让佛祖?’遂弃聘室,至尧峰,礼西脉老宿落发”⑩《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85 册,第20 页上栏。又,杭世骏撰《武林理安寺志》卷5 作“因街坊演剧,见目连救母事,出家,得法于箬庵禅师”(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21 册,台北:明文书局,1980 年,第243 页),则更明确了所看是《目连救母》。;释印光重修《九华山志》卷4又载清末果建禅师(1848—1927)“五岁母亡,七岁父没。零丁孤苦,流离四方,遂为农家牧牛。暨弱冠,因看《目连救母》戏,乃叹曰:‘欲报父母劬劳之恩,非出家修行不可。’遂决志出家”⑪《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二辑,第22 册,第198-199 页。。五位禅师,分别是今云南晋宁、广东潮阳、福建福清、上海青浦、安徽桐城人,他们观看的必定是各自家乡上演的目连戏。由此可见,目连戏流播地域之广,教化力之强①本来,从佛教戒律说,出家人不可以观听世俗歌舞音乐戏剧,但有例外。王宇春等合编《云栖法汇》卷12“伎乐”条(参《嘉兴大藏经》第 33 册,第 38 页中—下栏)对此有详细说明。云栖袾宏(1535—1615)认为,像《香山》(指《香山记》)《目连》《昙花》(指屠隆《昙花记》)这样“以出世间正法感悟时人”的佛教戏剧是大可倡导的。。
禅师以目连救母故事上堂说法的场合,一般在七月十五日②当然也有例外,如《普庵肃禅师语录》卷上《与彭应求为母病请药语》载印肃禅师(1115—1169)为彭应求母亲说法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69 册,第393 页上栏)。。如《投子义青禅师语录》载义青(1032—1083)解夏上堂云:
诸佛欢喜之日,目连展救母之心,人天赴盂兰之会。各运精诚,庄严胜会,传大藏之灵文,灭尘沙之罪垢,共报父母六亲,各获平安之妙乐。诸仁者,“报恩”一句作么生道?良久云:“但知方寸无诸恶,便是时中报重恩。”③《大藏新纂卍续续藏经》第71 册,第738 页上栏。
义青说法,是面对教内僧众,他触景生情,要求出家修道者应从目连报母恩中悟得诸恶不作、时时处处慈悲心生,这样才算是真报恩。
《古雪哲禅师语录》卷9 载明末真哲禅师中元日为“平藩下杨守备请上堂”云:
妙净明心,本无迷悟。凡情未尽,仍假证修。所以玄沙筑破指头,父生天界。目连亲证罗汉,母脱轮回。是知情均天伦,应之则疾;法无疏戚,感之在人④《嘉兴大藏经》第28 册,第351 页中栏。。
此则针对世俗信众而说法,其特点是把目连救母故事和中土有关玄沙师备(835—908)踢破脚指头而使父生天的传说相提并论,重在强调人伦亲情及天人感应。
《石雨禅师法檀》卷 9 载明方(1593—1648)“中元示众”曰:
今日是目连救母、地官赦罪之辰,云集忏悔,亡者可以超生,存者可以获福。此是世间父母也。然出世间,亦各各有个父母,他能长你法身,养你慧命。大众,还知么⑤《嘉兴大藏经》第27 册,第110 页上栏。?
此处说法,意在从目连世间救母故事出发,引起参禅者对出世间父母的思考,出世间父母就是“非形象可求”的法。更可注意者,“地官赦罪之辰”,是郑之珍(1518—1595)《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反复出现的套语。
《频吉祥禅师语录》卷1 又谓清初吉祥盂兰会上堂曰:“目犍连馈饭青提,面然王端受供养,十世古今不离。”⑥《嘉兴大藏经》第39 册,第602 页下栏。从“面然王端受供养”一语,可见当时中元节同时举办了焰口施食法会。
在盂兰盆会及相关仪式上,宗门还有专门的佛事作品集,元如瑛所编《高峰龙泉院因师集贤语录》卷5“诸般偈赞门”之《目连》曰“欲令慈母生天界,屡启诚心问佛功。崇建兰盆燃惠炬,流传万世永无穷”⑦《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65 册,第21 页上—中栏。;卷 6“荐亡偈赞门”《荐母》其一曰“望云几度思亲面,泣笋无因表孝心。特设伊蒲伸荐果,大千佛国震雷音”,其二曰“三年泣血泪沾红,鞠育还如一梦中……愿假目连行孝力,慈亲从此往天宫”⑧《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65 册,第23 页上—中栏。。凡此,皆结合中土丧葬礼仪制度,极力赞颂目连的救母孝行。此外,像广真禅师(1582—1639)的《盂兰盆偈》(《吹万禅师语录》卷 9)、《盂兰会引》(同前,卷14)⑨《嘉兴大藏经》第29 册,第505 页上栏、第527 页中—下栏。等作品,都是实用的仪式文书,同样宣扬目连之孝。
盂兰盆会除了宣扬目连救母的中心主旨外,它还兼救度七代先亡。其实,中土还有专门救度生育而亡之女性的伪经《血盆经》⑩按:是经全称《大藏正教血盆经》。《云栖法汇》卷5 把它和《受生经》《金刚纂》等伪造经典一道列入日常课诵所允许的经典(参《嘉兴大藏经》第 32 册,第595 页上栏)。,《高峰龙泉院因师集贤语录》卷5“陈意伏愿门”之《血盆》即依经文大意而有颂曰:“母号鞠我,既全抚育之恩。子之爱亲,当报劬劳之德。爰崇上善,仰答生身……地藏能仁祈作证,目连教主望垂慈。”①《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65 册,第19 页上—中栏。明清时期,民间尤其推崇血盆斋②如王培荀(1783—1859)撰《听雨楼随笔》卷8 即谓四川荣县南禅寺诗僧云空“幼讽经,至目连救母,涕泣横流,发誓持血盆斋三载”(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页19b)。,并有和盂兰盆会合流的趋势。《为霖道霈禅师餐香录》卷上就载道霈(1615—1702)为“孝女郭淑贞忏血盆斋”说偈曰:“昔日目莲曾启教,兰盆报母得生天。特遵遗轨清斋满,愿荐双亲达九莲。”③《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72 册,第617 页下栏。本来举办的是血盆斋,讲的却是《盂兰盆经》内容。究其成因在于,两经之目连都是施救者的角色。
至于目连戏之人物和故事情节,也有禅师以之说法。《大方禅师语录》卷1 载行海禅师(1604—1670)与钱顺宇、张瑞甫、倪仁毓茶话次云:
目连至孝的证果,富相造福的升天,清提有头无尾隋在泥底,不落因果,不昧因果④《嘉兴大藏经》第36 册,第827 页下栏。。
富相,当是“傅相”之误,清提,即青提⑤在明万历十年高石山房刻本《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多用“刘青提”,仅有一处作“刘氏清提”。,行海所引人物,涵盖了《目连传奇》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即目连和其父母傅相、刘青提。
再如,《云溪俍亭挺禅师语录》卷1 载净挺(1615—1684)“中元小参”曰:
救母生天,神通第一。台山路上讨个点心,俞道婆倾翻油餈,浮杯和尚没处雪屈,木菩提树下,蓦走到忉利天宫。且道:摩耶夫人,仗谁恩力?大须弥山、小须弥山距孛跳,入八寒八热、十八鬲子地狱、阿鼻地狱,从东过西,从西过东,象宝、马宝、女宝、如意宝、将军宝,辊到饿鬼头边,向有财鬼、无财鬼、臭毛鬼等唱一声:“摩诃般若波罗蜜,观世音菩萨,将钱来买糊饼”。盂兰盆大斋,放下手却是馒头,要吃的尽吃!阿修罗与帝释天大战,着他目连看堂,从针咽里放出一星子火来,烧得金牛儿叫苦,石狮子汗流,带累他无位真人,五百生不闻浆水之名。快活,快活,阎罗大王来也!统领一班狱卒夜叉,喝散了中元地官、东皇太乙⑥《嘉兴大藏经》第33 册,第728 页上栏。。
神通第一,指目连,其母本是青提夫人,净挺却以佛母摩耶夫人喻之。更有趣的是,叙述目连救母经过(如上天入地)、所遇人物(如观世音、地官、阎罗、饿鬼、夜叉等)及食用的点心之类,都与《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相同,只不过出于戒律禁忌,把原剧中刘青提用来斋僧的肉馒头换成了一般的馒头。换言之,净挺的小参,许多叙事要素都源自郑之珍剧本。当然,净挺也串连了不少禅林话头,像“观世音菩萨将钱来买糊饼,放下手元来却是个馒头”,就出于《法演禅师语录》卷2⑦《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 册,第658 页下栏。。其他像台山婆子、俞道婆、浮杯和尚,作为目连寻母的见证人,则是净挺戏剧化说法的一种创造。
《东山梅溪度禅师语录》卷2 谓福度(1637—?)“为母归元尼三周上堂”时说:
瞿昙为母升忉利,罗卜寻娘诣狱门。独有梅溪分外别,华王座上荐慈亲⑧《嘉兴大藏经》第39 册,第383 页上栏。。
“罗卜寻娘”,恰恰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卷下《傅相救妻》中也有类似叙述:“为罗卜寻娘,不愿再嫁。”⑨按:郑氏剧本为罗卜设计了已盟娉的妻子曹赛英,但因目连(傅郎,即罗卜)寻母,才未成亲。
以上粗略分析了目连故事流播史上的四个小问题。其中,前三个悉与版本息息相关,我们通过文献比对,确认作“经”或有“经”字的版本,更契合目连文化形成的历史语境;后一个则说明,宗门语录不但重视盂兰盆会,而且经常以目连戏说法,更有甚者,不少年少丧母的禅师,其出家缘由竟然是观看目连戏深受感动所致。此外,宋元以来目连戏盛行,与其仪式化的展演,特别是和中土丧葬文化的渊源甚深。当然,佛教内部诸仪式如尊胜幢、焰口施食、水陆斋、血盆斋等的汇流,也促进了目连故事的流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