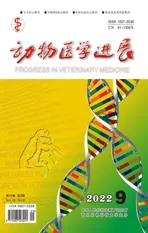防御素的结构与功能及其抗菌机制
2022-11-26杨江流宋青山乔军伟
杨江流,宋青山,乔军伟,贾 芳*
(1.河套学院医学系,内蒙古巴彦淖尔 015000;2.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西部特色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宁夏银川 750021)
防御素是一类小的(约4 ku~6 ku)阳离子抗菌肽(antimicrobial peptides,AMPs),是多细胞生物先天免疫系统的一种进化保守成分,广泛存在于真菌、植物以及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中[1]。这些富含半胱氨酸的阳离子肽对大量的微生物具有直接或间接抗菌活性,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等多重耐药细菌。另外,防御素还在免疫调节、生殖发育、伤口愈合和癌症发生调节中具有广泛的作用[2]。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抗生素耐药性的迅速和持续传播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了严重威胁[3]。同时,抗生素耐药性的迅速增长和全球扩张加速了开发新型抗菌剂的需求。防御素作为一大类抗菌肽,除了广谱抗菌活性外,与传统抗生素相比,防御素具有耐药性出现较慢、对传统抗生素耐药的细菌具有活性以及调节宿主免疫反应的能力等优势,防御素被认为是新型抗感染药物的一个有希望的先导化合物[4-5]。本文综述了不同来源防御素的结构特征及其抗菌机制,以期为解决临床耐药问题提供参考。
1 防御素的结构特征
1.1 脊椎动物防御素
脊椎动物防御素根据其分子内二硫键的排列方式分为α、β和θ 3个亚家族,α-和β-防御素均由3个保守的分子内二硫键稳定的3股反平行β-折叠片组成(即“防御素样”拓扑折叠)[6]。α-防御素在中性粒细胞和小肠潘氏细胞的颗粒中以高浓度(毫摩尔)存在。成熟的α-防御素包含由2935个氨基酸残基,形成X12CysXCysArgX23CysX3GluX3GlyXCysX3X5CysCysX14(X代表任一氨基酸)的一致序列,该序列具有9个高度保守的残基(包括6个半胱氨酸、1个精氨酸、1个谷氨酸和1个甘氨酸),半胱氨酸的二硫键连接方式位于Cys1-Cys6、Cys2-Cys4和Cys3-Cys5,高含量的阳离子残基(赖氨酸,精氨酸)主要聚集在防御素的C-端附近,保守的精氨酸和谷氨酸之间形成的盐键可抵抗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的降解。迄今为止,已鉴定出6种人α-防御素,根据其表达模式和基因结构不同,人α-防御素可进一步细分为髓样肽或人中性粒细胞多肽(human neutrophil peptide,HNP)1~4和肠肽(human (enteric) defensins,HD)5和HD6[7]。HNP-1是研究最多的人α-防御素之一,二硫键对其活性至关重要。研究发现,不含半胱氨酸的HNP-1类似物的抗菌活性比HNP-1低10倍~20倍。
成熟的人β-防御素(human β defensin,HBD)亚家族成员含有36个以上的氨基酸残基,形成X210CysX56(G/A)XCysX34CysX913CysX47CysCysXn(X代表任一氨基酸)的一致序列,二硫键连接方式为Cys1-Cys5、Cys2-Cys4、Cys3-Cys6。β-防御素中的“防御素样”拓扑折叠由N-端尾部形成的可变长度的α-螺旋段修饰[8],该额外的α-螺旋相对于β-折叠片的方向由二硫键Cys1-Cys5维持,N-末端α-螺旋序列和长度的变异性与β-防御素的抗菌特异性相关[9]。β-防御素主要在上皮组织中表达,HBD-1被认为是在上皮防御感染中更重要的AMP。HBD-1主要对革兰氏阴性杆菌有效。与HNP-1相反,HBD-1在其二硫键减少后对厌氧革兰氏共生细菌(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更具活性[10]。
在人类中,只有α和β-防御素存在,θ-防御素是在一些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白细胞和骨髓中发现的AMPs,由2个截短的α-防御素(半防御素,9 个氨基酸)连接而成,含有3个二硫键连接的环状结构(Cys1-Cys6,Cys2-Cys5和Cys3-Cys4),构成动物体中唯一已知的环蛋白。
1.2 无脊椎动物防御素
无脊椎动物防御素是AMPs中分布最广的一个家族。主要有2种类型的半胱氨酸配对,Cys1-Cys4、Cys2-Cys5和Cys3-Cys6(包括节肢动物、昆虫和软体动物防御素(牡蛎和鲍鱼))以及Cys1-Cys8、Cys2-Cys5、Cys3-Cys6和Cys4-Cys7(包含软体动物(贻贝和牡蛎)和线虫(蠕虫))[11]。一些无脊椎动物防御素的三维溶液结构的核磁共振波谱解析显示,无脊椎动物防御素的核心结构由1个α-螺旋结构域和2个反平行的β-链组成,α-螺旋通过3个或4个二硫键稳定在β-链上,形成半胱氨酸稳定的α-螺旋β-折叠片模体结构(cysteine stabilized αβ motif;CSαβ)[12],形成了一个与脊椎动物防御素完全不同的三级结构。一些抗真菌肽,如黑腹果蝇的果糖霉素含有额外的短N-端β-链,呈现出类似于植物防御素的βαββ花式结构。
1.3 植物防御素
不同植物防御素抗菌活性差异较大,但是结构基本相同。已知的所有植物防御素都具有4对二硫键的特征,并具有相同的半胱氨酸配对模式(Cys1-Cys8、Cys2-Cys5、Cys3-Cys6和Cys4-Cys7),植物防御素的基本结构由 3条反向平行的β折叠片和1个α-螺旋在4对二硫键的连接下形成的βαββ花式结构组成。其中在α-螺旋和β-折叠片上分别有1对二硫键固定,形成和真菌、无脊椎动物防御素相同的CSαβ模体结构[13],这可能使它们的抗菌作用具有高度特异性[14]。植物防御素具有一个额外的保守序列,即γ-核心模体结构(序列为GlyXCysX39Cys),这是其抗菌活性所必需的。虽然植物防御素具有共同的三级结构,但氨基酸序列和肽段长度上存在的广泛差异引起了抗菌活性的变化[15]。
2 防御素的抗细菌机制
2.1 膜透化作用破坏膜屏障
AMPs的经典抗菌作用机制是损伤细胞膜[16]。膜靶向AMPs可以由受体介导(主要是细菌产生的抗菌肽)或非受体介导(大多数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抗菌肽)的相互作用[17]。几乎所有的AMPs都是阳离子和两亲性的,已使用模型膜和各种脂质成分的单层囊泡研究证实,在革兰氏阴性菌中,带正电的高浓度阳离子防御素被静电作用吸引到带负电的细菌外膜的外小叶磷脂上后不断聚集。当防御素浓度小于阈浓度时,防御素分子平行吸附于脂质双分子双层表面;当防御素浓度达到阈浓度时,防御素分子垂直插入磷脂双分子层疏水核心,防御素的双亲结构(α-螺旋和/或β折叠)的疏水区与脂双分子层发生构想重排,在细菌膜上完成自组装,形成跨膜孔(跨膜孔模型)或以类似洗涤剂(非孔模型)两种方式破坏膜屏障[17]。例如,研究最多的人类α-防御素HNP-1采用浓度依赖性的方式产生二聚体与细菌膜的静电相互作用,其中β-折叠的二聚体跨膜形成直径为2.0 nm~2.5 nm的跨膜孔,导致细胞内容物泄漏[18]。
在所有的模型膜系统中,膜通透性取决于脂质成分(磷脂的链长和电荷)。两性磷脂或胆固醇是真核细胞膜的两种主要成分,它们可减少宿主与防御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降低防御素对宿主细胞的毒性[12]。有研究表明,在足以杀死细菌的低微摩尔浓度范围内,许多人防御素几乎不会损害体内细菌膜的完整性,而是进入细胞质干扰核酸和/或蛋白质的合成[12]。细菌表面的一些保守分子是介导各种防御素特定杀伤机制的的明确靶点。例如,在革兰氏阴性细菌中,防御素必须穿过外膜才能与细胞质膜相互作用。该过程中,防御素与带负电荷的脂多糖相互作用,导致连接相邻脂多糖分子的二价阳离子(Mg2+,Ca2+)被置换,形成不稳定的外膜区域,肽可通过该区域穿透外膜(“自我促进摄取”)[19]。这在脊椎动物防御素对抗革兰氏阴性细菌中起着重要作用。
2.2 直接靶向脂质Ⅱ抑制细胞壁生物合成
细菌细胞壁肽聚糖的合成途径是多种抗菌化合物(如β-内酰胺类、糖肽类抗生素)的作用靶点,其中一个突出的靶点是脂质Ⅱ(肽聚糖组装的基本亚单位)。与这些经典抗生素相似,各种防御素也能通过直接靶向脂质Ⅱ抑制细菌细胞壁的生物合成[20]。真菌防御素菌丝霉素对一些革兰氏阳性细菌(包括耐药性的临床分离株)具有强大的活性,研究发现,菌丝霉素在体外以1∶1的摩尔浓度比不可逆地结合到脂质Ⅱ上,使脂质Ⅱ无法与细胞壁生物合成酶相互作用,导致细菌细胞质中的细胞壁前体UDP-MurNAc五肽的积累,从而有效阻断细菌细胞壁的合成。基于NMR的菌丝霉素脂质Ⅱ复合物建模表明,菌丝霉素与脂质Ⅱ的高亲和性由脂质Ⅱ焦磷酸基团和菌丝霉素的Phe2、Gly3、Cys4和Cys27之间形成的四个氢键,以及脂质Ⅱ的谷氨酸侧链与菌丝霉素的N-端和His18之间的盐桥决定。这种结合可进一步促进细菌细胞膜上孔的形成和膜的破坏[21]。已有的报道中,HNP1和HBD3等抗菌肽也依赖于选择性结合到脂质Ⅱ上发挥抗革兰氏阳性菌的活性。HBD3作用金黄色葡糖球菌后,导致细胞壁合成前体UDP-MurNAc五肽在细胞内积累,15个细胞壁应激刺激子基因中的13个基因表达上调。当hBD3与脂质Ⅱ的摩尔浓度比为2∶1时,防御素在体外可以完全阻断金黄色葡萄球菌青霉素结合蛋白2的活性。hBD3还通过降低膜电位影响细菌的能量生成和膜转运过程。
在体外,对真菌防御素米曲霉(来自米曲霉)、欧霉素(来自阿姆斯特丹曲霉)、无脊椎动物防御素(如来自绿蝇蛆的荧光素和牡蛎防御素家族cg-def)的研究也证明,这些肽能与脂质Ⅱ直接靶向结合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合成。
2.3 中和细菌分泌的毒素
防御素的另一抗菌机制是通过破坏细菌毒素的三级结构和促进构象转变来灭活细菌。防御素是唯一公认的能中和多种细菌毒素的快速反应分子[22]。防御素能在体外和动物模型中有效地中和炭疽毒素,防御素是中和许多毒素(成孔毒素、酶毒素和其他毒素)通用的效应分子,而许多毒素的进化和结构彼此无关。这些细菌毒素大多数并不具有共同的结构,具有高度多样性和易变性,但许多细菌毒素共有的特性是其热力学不稳定。毒素对防御素失活的敏感性取决于其热不稳定性和构象可塑性[22],这与毒素形成宿主膜孔或穿过宿主膜所必需的构象可塑性密切相关。已知被防御素抑制的最大毒素家族是成孔胆固醇依赖性细胞溶解素(cholesterol-dependent cytolysin,CDC),它是许多革兰氏阳性病原体产生的主要毒力因子[23]。HNP1-3和HD5通过多拷贝与单个CDC分子结合可以防止李斯特菌溶血素O、炭疽杆菌溶素O和肺炎链球菌溶解红细胞,抑制活性需要3个二硫键稳定的HNPs,而HNP4、HD6和β-防御素hBD1-3对同一毒素没有抑制能力。研究发现,α-和θ-防御素通过增强CDC的去折叠状态抵消其毒性[24]。在人α-防御素HNP1对霍乱弧菌MARTX(multifunctional autoprocessing repeats-in-toxin,MARTXvc)毒素的灭活过程中,作者评估了HNP1对MARTXvc半胱氨酸蛋白酶结构域(CPDvc)的自动加工活性和肌动蛋白交联结构域(ACDvc)的催化活性的影响。在有HNP1存在的情况下,ACDvc催化的肌动蛋白交联的初始反应速率被抑制。另外,HNP1还抑制了MARTXvc的自加工,CPDvc的催化活性也受到了抑制,MARTX二级和三级结构呈现热不稳定以及局部去折叠状态,导致毒素疏水残基的溶剂暴露增加,从而使其易于聚集和水解[25]。
目前,只有少数防御素被证明具有灭活毒素的能力,而且大多数研究中只使用了少量或只有一种毒素。另外,毒素对防御素灭活敏感性的共同特征尚未完全确定,它们在毒素灭活机制中的作用尚待阐明。
2.4 在细菌周围形成捕获“纳米网”
人肠道潘氏细胞α-防御素HD5和HD6在防御肠道内经食物和水传播的病原体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与HD5和其他α-防御素相比,HD6缺乏直接的抗菌活性(即使浓度高达1 mg/mL)[21]。用HD6转基因小鼠进行研究,发现生理水平上表达的HD6转基因小鼠在体内可免受经口服伤寒沙门氏菌(Salmonellaentericaserovartyphimurium,STM)的攻击[26]。但和STM感染的HD5转基因小鼠中不同的是,在STM感染的HD5转基因小鼠中,从肠腔中恢复的存活的STM数量大大减少,但在HD6转基因小鼠中,肠腔STM的存活率与感染的非转基因对照小鼠相同。研究发现,在HD6转基因小鼠中,从肠腔到派尔斑(或聚集性淋巴结节)和脾脏的STM转移明显受到抑制。这种保护作用依赖于HD6在小鼠肠道内寡聚成被称为“纳米网”的延伸结构。HD6最初与细菌表面蛋白附属物(如沙门氏菌鞭毛和I型菌毛)结合形成作为触发HD6纳米网的锚定点,该锚定点触发了一个动态有序的HD6自组装过程,HD6二聚体通过二聚体-二聚体结合形成稳定的四聚体(细长的HD6结构重复单元),从而形成围绕和缠绕肠道沙门氏菌的原纤维和纳米网(“成网”活性)诱捕肠道沙门氏菌,细菌随后被免疫系统的中性粒细胞等成分杀死、清除或排出体外。这种发生在体内的自组装需要组氨酸-27的存在。X射线晶体学显示组氨酸-27通过形成HD6单体多聚所需的必要盐桥。Phe2和Phe29对于HD6的自组装和生物功能都是必不可少的[27]。小肠潘氏细胞将HD6作为非活性的前肽储存在颗粒中,在HD6释放到腔内的过程中以及在肠腔内,HD6前肽(81-HD6)被胰蛋白酶水解生成成熟的32-HD6,从而发挥先天免疫功能。HD6具有广谱的预防细菌入侵的能力,对革兰氏阴性或革兰氏阳性细菌没有明显的选择性,也不偏好特定的细菌入侵机制[27]。这种独特的机制表明,HD6在保护人类小肠免受多种肠道病原体入侵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2.5 抑制细菌产生生物膜
微生物为了适应周围环境,会包裹在其自身分泌的胞外基质中,在非生物和生物表面形成一种稳定的三维网状的生物膜结构。生物膜是细菌产生的一个关键的毒力因子,它可以促进细菌在宿主表面定植,导致临床感染和抗生素耐药性,生物膜通过调控群体感应系统、阻止宿主免疫因子和抗生素的扩散增加细菌对抗生素的耐受性。与其他AMPs一样,防御素也表现出抑制细菌产生生物膜的功能。有人研究了HBD3在小鼠胫骨种植体耐药菌生物膜感染模型中的作用机制,发现HBD3处理该模型后可显著减少钛表面完整菌落数量,抑制生物膜的形成和成熟[28],而且通过在基因转录水平上抑制多糖的合成,降低了已存在的植入物表面的生物膜。在纳摩尔浓度下,HBD2介导的生物膜抑制可能是由于HBD2嵌入细菌膜后,干扰GacS/GacA双组份系统中的GacS后诱导小分子RNA,拮抗RsmA蛋白(一种干扰psl基因表达的翻译抑制因子)表达,阻断铜绿假单胞菌胞外多糖的产生[29]。HBD2还可能与信使分子环鸟苷二磷酸(c-diGMP)结合,导致外膜蛋白种类的改变,细菌膜表面拓扑结构发生改变,干扰生物膜前体分子进入细胞外间隙的运输,该过程不影响生物膜生成的调节。另外,HBD2还可能使蛋白转移酶SecA和分拣酶的空间结构离域,导致细菌菌毛的生物合成受阻,抑制生物膜的形成。萝卜防御素RsAFP1和RsAFP2与卡泊芬净对抗白色念珠菌生物膜具有协同作用,NMR研究发现RsAFP2也采用了植物防御素中典型的半胱氨酸稳定的CSαβ模体结构[30]。这一保守结构使得RsAFP1和rRsAFP2具有与抗真菌药物协同对抗白色念珠菌生物膜的潜力。近年研究发现,HD6也具有抑制白色念珠菌生物膜的形成,治疗念珠菌病并发症的作用[27]。
3 展望
尽管目前对防御素的研究仍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如防御素结构与功能的关系,防御素的促炎和抗炎活性之间的平衡,防御素的体外活性如何转化并影响体内细菌感染以及防御素实际应用的可能性等,但防御素强大的抗菌活性和低分子质量、低免疫原性、广谱活性以及抗蛋白水解等特性,使得防御素非常适合作为一类具有广泛活性的新型抗感染药物用于治疗[31]。考虑到新的天然抗菌素的缺乏,合成AMPs将是一种非常有希望的治疗候选制剂,而各种研究模型为评估防御素在细菌感染中的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