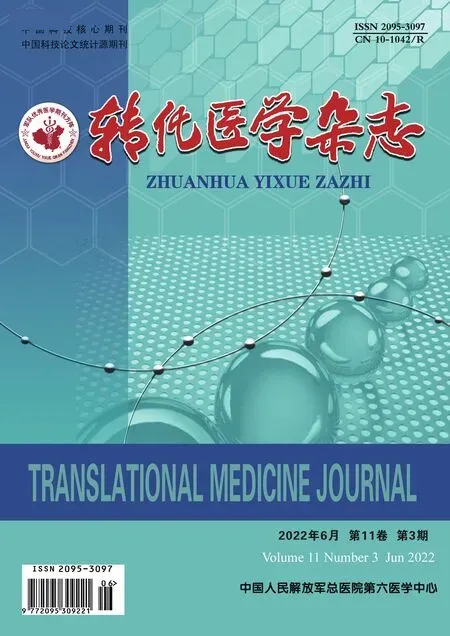黄芩苷对血液肿瘤的作用机制及逆转耐药的研究进展
2022-11-25段晓晖王健红王世雄王冰璇
段晓晖,李 宏,王健红,吕 垚,王世雄,王冰璇,梁 蓉
血液肿瘤是指发生在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以造血干细胞异常分化和增殖为特征,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疾病。在世界所有癌症总发病率中,血液肿瘤的发病率居第6 位,青少年恶性肿瘤病死率中位列1 位[1]。临床上常见的血液肿瘤有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淋巴瘤、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对于血液系统肿瘤,目前主要的治疗还是依靠传统的化疗或者联合放疗以及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有条件可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尽管如此,仍有部分患者出现疾病的难治或复发,化疗效果不理想,尤其是长期治疗后毒副作用明显,耐受性差,治疗相关死亡率增高。中药作为放疗和化疗的辅助治疗手段,显著提高了患者生存质量和生存率[2]。最新的Meta 分析显示对于恶性肿瘤骨转移患者,中药联合伊班膦酸钠可以缓解疼痛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并且安全性与单纯伊班膦酸钠治疗相当[3];中药复方能明显降低肿瘤质量,提高肿瘤抑制率,降低微血管密度,进而促进HepG2 肝癌小鼠肿瘤细胞坏死[4]。其中黄芩苷(Baicalin)就是重点研究的天然药物之一,它是从黄芩根中提取的一种有显著生物活性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抗肿瘤作用,同时可起到抑菌、抗炎、利尿、抗解痉、抗氧化剂及抗血栓等作用,研究证实其在消化道肿瘤、乳腺癌等肿瘤治疗方面显示出明显优势[5-8]。有研究通过高效液相色谱分析发现黄芩中黄芩苷占21%,进一步的研究证实黄芩苷是黄芩的主要抗癌成分,同时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阻滞抑制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系的生长,并且认为黄芩对这些造血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应列入临床试验[9]。
本文首先阐述黄芩苷在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等血液系统疾病中的相关研究及抗肿瘤机制的进展状况,同时将对黄芩苷的联合用药及逆转肿瘤耐药的作用加以总结分析,使大家对黄芩苷的抗肿瘤效应有更为清晰的全面了解,以期为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及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1 黄芩苷在白血病、骨髓瘤、淋巴瘤中的相关研究
1.1 黄芩苷对白血病细胞的作用及分子机制的研究 白血病是造血干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起病急,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发热、贫血、乏力等,根据白血病细胞的分化成熟程度和自然病程,可分为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两大类。其次,根据受累的细胞系可将急性白血病分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和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该病治疗上主要以化疗为主,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进一步清除肿瘤细胞,延长生存期,但仍有部分患者后期复发,对治疗反应差,高强度的化疗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绝大多数研究提示黄芩苷可通过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起到抗肿瘤作用。体外研究用浓度为32 μg/mL 和64 μg/mL 的黄芩苷处理NALM 细胞系(B-ALL)24 h后,与对照组相比,凋亡细胞百分比由6.4%分别增加到17.6%和21%,表明黄芩苷单独治疗(32 μg/mL和64 μg/mL)增加了ALL患者的凋亡细胞数量。同时发现黄芩苷对健康对照组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凋亡无显著影响[10]。另一研究用20 mol/L黄芩苷作用耐药的AML HL-60/ADR细胞系24 h后,出现G1 以下高峰,且随黄芩苷浓度升高比例升高。80 mol/L 黄芩苷处理细胞后,Bcl-2 mRNA 表达随时间的延长呈下降趋势。Bcl-2、PARP 蛋白表达量显著降低,PARP、Caspase-3、Bad 蛋白表达量逐渐升高,治疗组与对照组之间AKT 表达无显著差异,而p-Akt、NF-kappaB、p-NF-kappaB、mTOR和p-mTOR 的表达水平均呈时间依赖性降低,表明黄芩苷可能通过PI3K/AKT 信号通路诱导HL-60/ADR细胞凋亡[11]。此外也有研究者证实ROS通过表达Gadd153 和线粒体依赖通路介导黄芩苷诱导AML HL-60 细胞凋亡[12]。另一研究用T-ALL细胞系CCRF-CEM 为研究对象,发现黄芩苷对CCRF-CEM 具有显著的细胞毒作用,其IC(50)值为10.6 μ g/mL,黄芩苷(37.5 μ g/mL)对p53和Fas蛋白表达无影响,治疗72 h后,Bcl-2表达降低(22.0 pg/mL),导致线粒体跨膜电位丢失(52.7%),使细胞色素c含量升高(19.2 μg/mL),最终激活caspase-3(50.1 pmol/min)。故认为在人白血病细胞系中,黄芩苷诱导的细胞凋亡是由bcl-2依赖而非p53依赖途径介导的[13]。
除了凋亡途径,相关研究表明黄芩苷可通过调节Notch信号通路及细胞周期途径进一步起到抗肿瘤作用。有学者利用黄芩苷处理可调节内源性Notch 信号通路,引起K562 细胞中Notch1 受体和Notch 靶基因的mRNA 表达水平,说明该药物对Notch信号的调节可能影响K562细胞的肿瘤发生[14]。
1.2 黄芩苷在MM 细胞的作用及分子机制的研究MM 是单克隆性浆细胞异常增生产生单克隆免疫球蛋白,导致正常免疫球蛋白合成受抑,可出现贫血、骨折、肾功异常等临床表现,多见于中老年人,约占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10%,属于难以治愈的疾病。硼替佐米、来那度胺等药物的应用提高了疗效,延长了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但依然有部分患者出现复发难治,预后极差。即便自体干细胞移植后,标准风险患者仍需要来那度胺维持,而高风险MM 患者则需要硼替佐米维持[15],因此药物相关的神经毒性非常常见。而感染是MM 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正在进行的研究导致了转基因VZV 疫苗的开发,从而无需使用减毒活疫苗,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将进一步提高[16]。
在2005 年,研究发现黄连解毒汤(HLJDT)可抑制MM 细胞系的增殖和原发性MM 细胞,特别是MPC-1-未成熟MM 细胞的存活,并通过线粒体介导途径通过降低线粒体膜电位和激活caspase-9 和caspase-3 诱导MM 细胞系的凋亡。并进一步实验证实HLJDT中的黄芩对MM 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且黄芩中黄芩黄素较黄芩苷或汉黄芩素表现出较强的生长抑制和诱导凋亡作用[17]。有研究者进一步将MM 细胞株U266 细胞分为4 组,即空白组、地塞米松组、黄芩苷组、地塞米松+黄芩苷组分别培养,发现黄芩苷可抑制MM 细胞的增殖、侵袭,促进其凋亡,作用效果与地塞米松类似,与地塞米松联用,二者均可下调Wnt 通路调节分子β-catenin、GSK 3β 及下游靶基因c-myc、cyclinD1 mRNA 的表达,可下调β-catenin、GSK 3β 蛋白表达量,故可能通过调节Wnt 通路及其下游因子的表达而调控MM细胞的增殖、凋亡和侵袭[18]。
另一研究发现黄芩黄素、汉黄芩素、黄芩苷对RPMI-8226 细胞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相应的,在体外可显著降低RPMI-8226 中ABCG2 蛋白的表达水平,研究结果证实了黄芩提取物及其主要活性黄酮类化合物的一种新的作用机制,即通过调节ABCG2 蛋白的表达,靶向作用于SP 细胞,为MM 干细胞的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19]。
1.3 黄芩苷在淋巴瘤细胞的作用及分子机制的研究 淋巴瘤是一种原发于淋巴结或结外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临床上分为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 lymphoma,HL)和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NHL)。在NHL中B细胞淋巴瘤占到80%以上。近年来,淋巴瘤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呈年轻化趋势,根据最新的2019 年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数据,发病率占男性恶性肿瘤的第9位,占女性恶性肿瘤的第7 位。部分患者后期仍然出现复发难治,预后极差,生活质量严重受到威胁。
有研究显示用黄芩苷治疗CA46伯基特淋巴瘤细胞48 h 后,细胞增殖率明显下降;IC50 值为10 μM,10 μM 黄芩苷几乎完全抑制菌落形成,黄芩苷能降低AKT 表达水平,抑制AKT 及其下游信号的磷酸化水平,降低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水平,提高NF-κB 抑制剂(inhibitor of NF-κB,IκB)水平,细胞质中抗凋亡作用的NF-κB与其抑制剂IκB 形成复合体,为失活状态,活化的AKT 可诱导IκB 磷酸化并使游离的NF-κB 入核,启动抗凋亡基因的转录,故黄芩苷可通过下调抗凋亡信号通路,上调磷脂酰肌苷-3-激酶(PI3K)/丝氨酸/苏氨酸激酶(AKT)信号通路凋亡组分起到抗肿瘤作用[20]。另一研究发现黄芩苷衍生物02-036 能有效抑制CA46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其相关机制可能与下调凋亡相关分子表达水平有关,如BCL-2、Procaspase-9、Pro-caspase-3、PARP 和C-MYC[21]。还有研究发现黄芩苷可抑制T淋巴瘤Molt4细胞的生长,不同质量浓度的黄芩苷可明显抑制Molt4细胞的增殖能力(P值均<0.05),IC50 值为(19.2±2.2)μg/mL,并通过刺激ROS 生成从而诱导Molt4 细胞的凋亡[22]。但目前黄芩苷在淋巴瘤方面研究较少。新的研究发现,黄芩苷可通过miR-217/Dickkopf1(DKK1)抑制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和c-MYC mRNA 表达,从而诱导细胞凋亡,起到抗肿瘤的作用[23]。近年来,中药在免疫微环境的作用备受关注,而肿瘤细胞表面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结合细胞毒性T 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表面的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抑制CTL 的抗肿瘤效应,对免疫调节有抑制作用,造成肿瘤免疫逃逸[24]。黄芩苷能够抑制肿瘤表面免疫检查点,进而刺激免疫反应的作用,临床上先后有多个抗PD-1 的单克隆抗体上市,如所熟悉的信迪利单抗、替雷利珠单抗等,用药也逐渐纳入指南,尤其B 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非常快,最新研究发现ADD3有望作为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独立预后标志物,为其提供参考靶点[25]。因此黄芩苷也有望成为一个免疫治疗的辅助药物之一。
2 黄芩苷与化疗药物的联合用药及逆转肿瘤耐药机制
六亚甲基双乙酰胺(Hexamethylene bis-acetamide,HMBA)可诱导多种癌细胞分化,已有其在骨肉瘤、胃癌、肝癌、食管癌、卵巢癌等领域抗肿瘤机制的相关研究,且有部分应用于临床。有研究将20 μg/mL 黄芩苷与2 mM HMBA 合用24 h 后,对HL-60 细胞抑制率明显提高(P<0.01),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联合治疗对HL-60 细胞增殖具有协同抑制作用,为了确定协同作用是否仅限于HL-60 细胞,他们还在其他人白血病细胞系K562、thp1 和NB4上进行了平行研究,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而在这些细胞系中,联合治疗对HL-60 细胞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因此证实了黄芩苷和HMBA 联合作用可以协同抑制AML 细胞的增殖。另一方面,黄芩苷联合HMBA 对健康志愿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毒性作用不大,揭示了黄芩苷和HMBA的新组合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治疗AML的方案[26]。
顺铂是血液肿瘤较常用的化疗药物之一,目前黄芩苷与顺铂联合在血液病治疗中的研究甚少,在卵巢癌、肺癌细胞中研究均发现其对顺铂有一定的增敏作用。据报道,通过研究对顺铂敏感的卵巢癌细胞株A2780(CSC)及对应的顺铂耐药细胞株(CRC)细胞的凋亡和自噬发现包括黄芩苷在内的黄芩提取物中的功能性化合物,联合顺铂治疗明显降低了CRC 的细胞活力,细胞死亡是通过增加Atg5 和Atg12 表达的自噬而介导的,提示联合用药治疗顺铂耐药卵巢癌非常有前景[27]。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当黄芩苷(8 μg/mL)和DDP(4 μg/mL)合并使用时,在肺癌细胞系A549 和耐顺铂的细胞系A549/DDP中,肿瘤细胞侵袭的抑制率均显着提高,黄芩苷能剂量依赖性地降低A549/DDP 细胞中MARK2 的mRNA 和MARK2 及p-AKT 蛋白的表达,提示黄芩苷和顺铂在适当剂量和孵育时间下能协同抑制人肺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顺铂抵抗力的减弱与MARK2和p-AKT的下调有关[28]。
氟尿嘧啶是尿嘧啶的同类物,广泛应用于肿瘤的治疗。体外培养人肝癌细胞BEL-7402 及其耐药细胞BEL-7402/5-Fu,研究发现5、10 mg/L 黄芩苷能部分逆转耐药细胞对氟尿嘧啶的耐药,可以增强BEL-7402 对氟尿嘧啶敏感性,增加耐药细胞内药物积聚,降低MDRl基因及P—gP蛋白表达,抑制耐药细胞黏附率,降低耐药细胞β1-整合素表达,促进E-CD 蛋白表达,提示黄芩苷体外能部分恢复肝癌耐药细胞对Fu 的敏感性,可能与细胞内药物浓度增加及抑制MDRl基因表达相关[29]。阿霉素是血液系统肿瘤常用的化疗药物之一,研究显示黄芩苷与阿霉素也有协调作用,可以下调HL-60/ADM细胞中多药耐药相关蛋白1(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 1,MRP1)和肺耐药相关蛋白(lun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LRP)的表达,逆转细胞耐药,增强阿霉素疗效,进而促进细胞凋亡[30]。
3 总结与展望
目前,肿瘤的发生率逐渐上升,治疗上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化疗,一些新型靶向药物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及患者更加青睐于无化疗方案,中药作为最传统的用药,随着各种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其抗肿瘤机制广泛且不良反应少,相关研究越来越多,中药现代化是医学发展适时而存的必然趋势。
黄芩苷可通过多种途径起到抗肿瘤的作用,如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肿瘤细胞凋亡、阻止肿瘤转移和调节免疫微环境等,迄今黄芩苷在白血病、MM、淋巴瘤中的相关研究都处于细胞实验阶段,大多为分子层面的研究,具体作用机制研究文献有限且研究进度缓慢,临床应用文献鲜见,仅有极少数研究有逐渐向临床过渡趋势。新的研究发现黄芩苷尤其对MLL 和PBX1 基因重排的白血病细胞系作用明显,可以抑制细胞增殖,通过激活caspase3/7诱导细胞死亡,并且黄芩苷处理可抑制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SK3β)、上调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p27Kip1,更重要的是发现在临床收集了22 例ALL患者的骨髓细胞标本,用50 μg/ml的SBE和16 μg/ml的黄芩苷进行细胞凋亡研究,发现其对16 例(占比72%)儿童白血病骨髓细胞有促进凋亡作用,其余6例患者中分离出的骨髓基质细胞对SBE/黄芩苷治疗无效,同时健康细胞和母细胞的凋亡细胞数量均未增加。不幸的是,没有患者发生MLL 易位或TCF3-PBX1 重排[31]。综上,可以预期黄芩苷有机会被用于“量身定制”的治疗,而不是仅基于疾病遗传背景的“一刀切”疗法。同时,近年来也以黄芩苷骨架为基础开发一些列的新型抗癌药物,设计合成了多种新型的黄芩苷衍生物,其中,C-6 位含N,N-二甲氨基乙氧基的化合物8 在体外对HL-60 细胞的抗增殖作用显著增强,提示化合物8 的水溶性的改善和抗白血病的效力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前景且待进一步开发的导物[32]。
同时鉴于黄芩苷对化疗药物有一定的增敏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耐药,未来联合用药疗效可期,因此该药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前景。但现阶段迫切需要更多有效可靠的研究数据去进一步证实其的抗肿瘤作用机制,同时,黄芩苷与化疗药物的协同作用及逆转肿瘤耐药性的研究也非常局限,仅局限于HMBA、顺铂、5-FU、阿霉素这些屈指可数的几种药物,急需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发掘越来越多的药物,探索最佳的组合,最大程度起到抑制肿瘤增长作用及逆转耐药,加之对黄芩药物相互作用引起的不良反应评价的研究,尤其是临床试验方面的数据较少,故只有将体外和体内数据相关联,将临床前发现转化为临床意义的治疗策略,才有望为广泛的临床应用做好充分的准备,后续还需要学者们的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