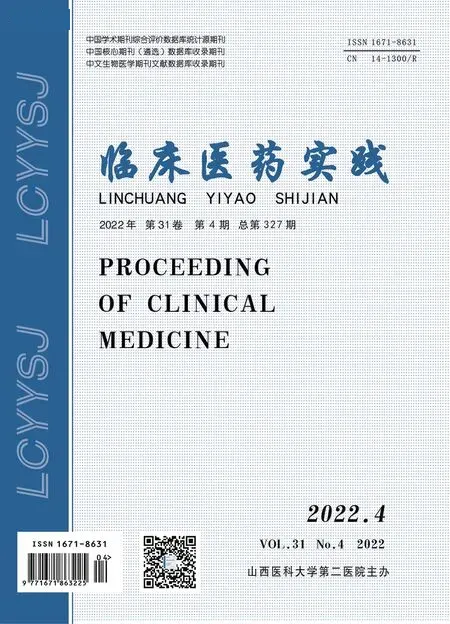封闭治疗致脓肿分枝杆菌感染3 例
2022-11-25黄美虹陆海鹏杨小叶曾尚勇林素梅
黄美虹,陆海鹏,杨小叶,曾尚勇,林素梅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广西 南宁 530001)
脓肿分枝杆菌是一种快速生长的非结核分枝杆菌,通常在水和土壤中分离[1]。该菌是结构性肺病患者慢性肺部感染的常见病原菌,肺外感染以皮肤及软组织感染为主,患者多因存在伤口并接触到受污染的物质或水而感染[2]。近来,我们收治了3 例在同一诊所行封闭治疗后脓肿分枝杆菌感染病例,分泌物培养出脓肿分枝杆菌并鉴定到亚种,根据亚种分型给予了针对性治疗并取得良好效果。
1 病例资料
病例1,女,63 岁,自诉2017年10月下旬因右踝关节疼痛到当地诊所行右踝关节封闭注射治疗,封闭注射后右踝部出现数个脓包伴疼痛,到该诊所复诊后症状无缓解并出现皮肤破溃,有较多暗黄色液体渗出,肿痛加剧,伴畏寒发热,最高体温40.0 ℃,以“右踝关节化脓性感染”收入当地医院,给予“右踝、足切开清创探查和炎症病灶清除及封闭负压引流(VSD)置入术”及抗感染治疗(具体不详),患处分泌物培养出腐生葡萄球菌,因症状无好转,于2017年12月5日转至我院。
入院时查体可见右足内踝有长约8 cm的斜行伤口,最深达肌层,肌肉膨出,伤口内可见较多脓性分泌物,少量渗血,右足内踝处皮肤肿胀,皮温升高,余正常。右足背B超:右足外踝及足背处皮下组织局部弥漫性改变。右踝关节MRI:考虑跟骨骨髓炎并周围软组织感染。
入院后给予万古霉素1 g静脉滴注,每12 h 1次(12月7日至12月14日,12月27日至12月31日)及莫西沙星0.4 g静脉滴注,每日1次(12月13日至12月20日)治疗。12月28日分泌物涂片:抗酸杆菌(++),加用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抗结核治疗,患者仍反复高热,伤口愈合不佳。2018年1月1日加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2 g静脉滴注,每日2 次,取分泌物送至外院行靶向脱氧核糖核酸(DNA)测序。2018年1月4日患处分泌物培养出快速生长型非结核分枝杆菌,当时考虑污染可能,未调整抗感染方案。2018年1月10日DNA测序结果回报:脓肿分枝杆菌(马赛分枝杆菌)。根据指南及脓肿分枝杆菌药物体外敏感性数据[3-6],2018年1月11日治疗方案调整为克拉霉素分散片0.5 g,每12 h 1次口服,联合头孢西丁(2 g,每6 h静脉滴注1 次)+阿米卡星(0.4 g,每日静脉滴注1 次)+莫西沙星(0.4 g,每日静脉滴注1 次)。7 d后,患者体温降至正常,右足外踝关节肿胀较前消退。2018年2月1日,患者再次出现高热(39.4 ℃),分析认为经治疗患者体温已正常多日,临床症状好转,现突发高热,不排除药物因素。梳理患者使用药物,其中头孢西丁常见不良反应包括发热、白细胞(WBC)减少等[3],急查患者血常规示WBC 2.87×109/L,确实存在白细胞减少现象。2018年2月4日将头孢西丁换为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简称亚胺培南)0.5 g,每8 h静脉滴注1 次。2018年2月6日,患者体温及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治疗过程中分别于2018年1月6日、1月13日、4月21日行“右跟骨骨髓炎清创+VSD负压吸引术”,4月28日行“右跟骨骨髓炎清创+VSD拆除术”。2018年5月28日患者体温正常,右踝关节愈合良好,好转出院。出院嘱患者继续口服克拉霉素缓释片0.5 g,每12 h 1 次及盐酸莫西沙星片0.4 g,每日1 次。两种药物均口服满6个月。
病例2,女,87 岁,病例1母亲,自诉2017年10月下旬因左膝关节疼痛至当地诊所(同病例1)行关节封闭注射治疗,数日后左膝关节区出现红、肿、热、痛,患处局部皮肤破溃,伴左膝关节活动障碍,到当地医院行切开排脓引流及抗感染等治疗(具体不详),症状未见好转。2017年12月26日以“左膝关节化脓性感染2月余”转入我院治疗。
入院检查患者膝关节前外侧可见一3 cm×2 cm伤口,有少量脓性分泌物,周围皮肤肿胀,皮温升高,左膝关节活动受限,余未见异常。MRI示左膝关节髌下脂肪垫及周围软组织水肿改变(炎症?)。
入院后取深部脓性分泌物行细菌、真菌涂片及培养,予头孢替安2 g,每日静脉滴注2 次。2018年1月2日分泌物培养回报多重耐药屎肠球菌,停用头孢替安,改为万古霉素1 g,每日静脉滴注1 次,并每日予伤口清创、碘伏纱布敷伤口,促进伤口愈合。2018年1月4日行“左膝关节清创+脓肿切开+关节囊修补+肌腱血管探查+髌骨成形+对口引流冲洗术”。术后切开分泌物涂片抗酸杆菌(+),当时同样考虑污染可能,未调整药物。后患者反复存在中低热,伤口分泌物未见明显减少。脓性分泌物病原学结果再次回报:抗酸染色阳性(++),为快速生长型非结核分枝杆菌。考虑患者病史与病例1类似,不排除同一感染源可能,参考病例1治疗方案,2018年1月11日停用万古霉素,改为克拉霉素缓释片0.5 g,每12 h口服1次,联合头孢西丁(2 g,每6 h静脉滴注1 次)+阿米卡星(0.4 g,每日静脉滴注1 次)+莫西沙星(0.4 g,每日静脉滴注1 次),继续左膝关节引流冲洗,定期术口换药,后患者体温逐渐降至正常。2018年2月16日患者已无发热,但左膝部仍有少量黄色液体渗出,将头孢西丁改为亚胺培南0.5 g,每8 h静脉滴注1 次。2018年3月6日患者诉耳鸣,患者既往无耳鸣史,考虑阿米卡星有前庭/听觉毒性,表现为耳鸣,听力下降[3],其余合用药物耳鸣症状不常见,故停用阿米卡星观察,余治疗同前,后患者耳鸣症状逐渐好转。2018年3月24日和4月6日分泌物培养结果转阴,患者自述左膝部术口疼痛较前明显减轻,要求出院,嘱患者出院继续服用克拉霉素缓释片0.5 g,每12 h口服1 次及盐酸莫西沙星片0.4 g,每日口服1 次。两种药物均口服满6个月。
病例3,女,56 岁,病例1妹妹,2017年10月下旬因右肩部疼痛至当地诊所(同病例1)行右肩周区封闭注射治疗,后右肩胛区出现红、肿、热、痛,伴右肩关节活动障碍,当地医院治疗无缓解,肿痛加剧,偶有发热,患处局部皮肤破溃,在当地医院行切开排脓引流及抗感染等治疗,并于2017年12月26日转至我院,诊断“右肩胛区伤口感染”。
入院查体右肩胛区可见一2 cm×2 cm伤口,有少量脓性分泌物,少量渗血,周围皮肤肿胀,皮温升高,右上肢外展稍受限,余未见异常。2017年12月30日行右肩胛背脓肿清创+切开引流+VSD负压吸引术,术后予头孢替安2 g静脉滴注,每日2 次。2018年1月6日行右肩背部VSD拆除+清创缝合术。根据病史,同样考虑与病例1同源性感染可能性大。2018年1月11日改用克拉霉素分散片0.5 g,每12 h口服1 次。1月12日停用头孢替安,加用头孢西丁[2 g静脉滴注,每8 h 1 次(1月20日—1月26 日每6 h 1次)]+阿米卡星(0.4 g,静脉滴注,每日1 次)+莫西沙星(0.4 g,静脉滴注,每日1 次)。1月26日患者右肩背伤口愈合良好,办理出院。嘱患者出院继续口服克拉霉素缓释片0.5 g,每12 h 1 次,疗程至少10 周。
2 讨 论
脓肿分枝杆菌是一种人类易感的快速生长型非结核分枝杆菌,是胞内寄生菌,在土壤和水中普遍存在。1953年首次从膝盖脓肿中分离出来,因其可致皮下脓肿得名[7]。脓肿分岐杆菌以肺部感染为主,皮肤和软组织感染较少见,主要发生在外伤、整容或外科术后,多因伤口暴露于脓肿分枝杆菌污染的土壤、水或医疗设备中所致[2,8]。追溯病史,本文所述的3 个病例曾在同一时期同一诊所行封闭治疗,后都在相应注射部位出现不同程度脓肿分枝杆菌皮肤感染,同源性感染可能性大,这与先前韩国报道的一项较大规模的针灸后因消毒不彻底而造成脓肿分枝杆菌皮肤和软组织感染事件相似[9]。我们认为此病例是独特的,因为脓肿分枝杆菌不仅影响到了皮肤软组织,还延伸到更深的区域,导致跟骨骨髓、膝关节和肩胛骨感染。据我们所知,这种涉及更深区域的脓肿分枝杆菌群体皮肤软组织感染并不常见[10-12]。
临床上治疗脓肿分枝杆菌感染的药物有限,不仅一线抗结核药物对其不敏感(这可解释在病例1的前期治疗中,采用抗结核治疗患者,病情并未改善),大多数抗生素对其也不敏感。Nessar等[13]指出,具有抗脓肿分枝杆菌体外活性的药物很少,高于组织或血清最小抑菌浓度(MIC)水平的仅有克拉霉素、氨基糖苷类、头孢西丁、替加环素和TMC-207。Lee等[2]研究显示,克拉霉素的耐药率为0~38.0%,头孢西丁和阿米卡星耐药率相对低,分别约为15.1%和7.7%,而多西环素、喹诺酮类药物(包括莫西沙星和环丙沙星)和亚胺培南则具有较高的耐药率。一项法国研究表明[14],多数脓肿分枝杆菌对头孢西丁和亚胺培南仅具有中等敏感性,二者的MIC分布非常接近折点。此外,美国胸科学会和传染病学会(ATS/IDSA)指南建议[3],在基于药物敏感性测试结果的情况下,推荐以大环内酯类为基础,结合静脉注射阿米卡星和头孢西丁或亚胺培南的抗生素疗法。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发布的《非结核分枝杆菌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12》未明确推荐具体药物组合,但提到因单药容易诱发耐药,建议可选择5~6种药物联合治疗[15]。因此,在初始治疗方案中,我们选择对脓肿分枝杆菌敏感性较好的克拉霉素、头孢西丁、阿米卡星和在骨骼浓度较高的莫西沙星4药联合方案治疗。
此外,查阅文献时发现,与脓肿分枝杆菌感染患者早期治疗失败高度相关的危险因素之一为对克拉霉素的耐药。现有资料表明[16],在脓肿分枝杆菌中发现了诱导性的大环内酯类耐药现象,红霉素核糖体甲基转移酶erm(41)基因赋予了该物种对大环内酯类药物的耐药性。目前划分出的三个脓肿分枝杆菌亚种(脓肿分枝杆菌脓肿亚种,脓肿分枝杆菌bolletii亚种和脓肿分枝杆菌massiliens亚种)中,脓肿分枝杆菌脓肿亚种和脓肿分枝杆菌bolletii亚种存在功能性erm(41)基因,它们可诱导大环内酯类药物产生耐药性,而脓肿分枝杆菌massiliense亚种则具有无功能的erm(41)基因[17-18]。因此在经验性治疗中,基于大环内酯类药物的治疗方案对于前两者敏感性差,不推荐经验性使用大环内酯类治疗,但对后者可产生较理想的结果[4-6]。本文的病例1通过高通量DNA测序方法鉴定出为脓肿分枝杆菌massiliense亚种,通常对克拉霉素敏感,因此初始治疗方案选用以克拉霉素为基础的联合方案,并坚定信心坚持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从而进一步强调对于脓肿分枝杆菌的治疗而言,能鉴定至亚种水平,将有助于取得理想疗效。
疗程方面,ATS/IDSA建议,肺外脓肿分枝杆菌感染,例如皮肤、软组织和骨骼感染,需进行4~6个月的抗生素治疗,并至少初始联合使用非肠道抗生素2周[3]。2017年英国胸科协会治疗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的指南建议[19],对于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敏感的脓肿分枝杆菌感染,初始治疗方案应包括静脉注射阿米卡星、替加环素和亚胺培南,口服克拉霉素或阿奇霉素至少4 周;对于大环内酯类耐药的脓肿分枝杆菌复合分离株,初始治疗方案应包括静脉注射阿米卡星、替加环素和亚胺培南最少4 周,延续阶段口服下列抗菌药物中的2~4 种:氯法齐明、利奈唑胺、米诺环素或多西环素、莫西沙星或环丙沙星、复方新诺明,至少12个月。根据指南建议和患者病情及经济能力,我们采用以口服克拉霉素为基础,联合阿米卡星+头孢西丁(亚胺培南)+莫西沙星的方案进行治疗,期间不断坚定患者信心,经过4个多月的治疗,取得了一定的疗效,患者相继好转出院,并嘱感染较重的病例1和病例2患者出院后继续坚持用药至6个月。在后续的电话随访中,患者皆诉恢复良好。
回顾整个治疗过程,我们认为,此次治疗成功,除了对感染组织的外科清创及处理外,培养出致病菌并鉴定至亚种水平,根据鉴定结果正确选择敏感的抗生素进行数月的治疗功不可没。为此,我们建议要提高对脓肿分枝杆菌疾病的认识,遇到此类病例,要将脓肿分歧杆菌鉴定到亚种水平,以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
猜你喜欢
——和田盘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