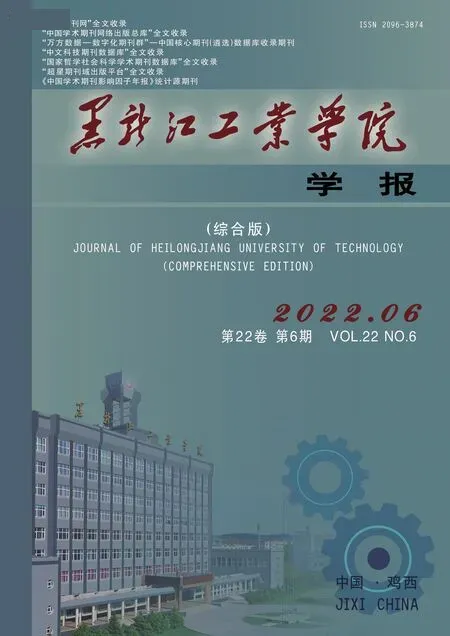《文城》:空间视域下的精神故乡
2022-11-25翟文辉吴芳烨郑云海
翟文辉,吴芳烨,郑云海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214)
2021年3月,《文城》甫一问世,便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对《文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创作风格以及主题表达层次,从历史所展现的时间线性维度进程评价和反思《文城》的“生成”。《文城》作为“新历史”的再度书写不仅是纪小美和林祥福二者作为线性维度在特定时代的对话和选择,更是两个主人公的空间移动所反观余华笔下的精神故乡。人类社会从来不是历史自动生成的,“历史的想像从来就不是完全没有空间的”[1],地理和空间同样是人类认知和感受世界的基础。余华想要展现《活着》中40年代以前的故事,就必然需要空间和场域提供社会舞台以供人物进行动作从而完成整个时代场域和景观的“建设”。中国现代作家对世界的认知和思考基本是源于他们童年时期的经验和实践,作为线性维度的时间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而单向明晰,地理和空间却可以在单一的共时线性维度中形成两个空间“自我”。列斐伏尔认为“历史必须不仅要考虑到这些空间的起源问题,还特别要认真重视它们的相互联系、变形、位移、相互作用,它们与具体社会或生产方式中的空间实践的联系等”[2]。《文城》作为余华笔下书写的空间产物,不仅是作家内在自我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跨地域式反省和观照,更是对中国80年代文学思潮和当下精神困境的一次呼应和探索,因而《文城》呈现的不是在汹涌时代下个体选择所形成的“历史决定论”,而是因人物选择所形成的空间展现完成宗教式体验的政治意识传播、写作版图的扩展以及“士志于道”精神乌托邦空间中两个“共时”自我状态。
一、人物选择所形成的空间展现
有意模糊的时代背景指向一种相对明确的历史构建意识。余华运用个体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生活体验让《文城》中的人物根据其不同的社会场域做出各自的选择,从而形成不同的空间展示。正如《文城》腰封上的话语:“时代的洪流推着每个人做出各自的选择。这是一个荒蛮的时代,结束的尚未结束,开始的尚未开始。”《文城》试图借助清末民初这一动乱的社会背景舞台呈现一种即将出现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历史进步时间观念,有意模糊的线性时间和历史背景最终只是内嵌到这个特定时代的空间舞台上,并不是推动情节发展和进入故事叙述的需要,而纪小美、陈耀武、顾同年等人物进行的选择实际内蕴了余华对在清末民初背景下不同阶层人物及其命运的不同理解和想象。余华认为,“一部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作者自己,因为实实在在的经历并不是作者全部的生活,作者的生活里也包括了想象和欲望,理解和判断,察言观色和道听途说”[3]。人物的选择可以体现作家对世界的认知和历史的思考,但历史仍在进行,现在的历史依旧是过去的反复再生,与过去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余华所言“我们这一代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总想把我们跟那个时代的关系给表现出来。我们不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一个象牙塔里的故事”[4]。余华利用共时化的写作维度完成纵向的平行和历史空间展现,通过对历史环境和当下精神思考和认知完成中华民族在同一历史轨迹和前进道路下崭新的空间生产。
在同一条历史轨迹前进过程中,《文城》的故事推动力并不仅是林祥福的“寻妻”和融入溪镇的单向时间线性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意打破人们所熟知的历史结构特征和线性文本的逻辑思维,使除了林祥福以外的人物也有属于自己的文本表达空间,并用以展示自我的历史传记,从而为实现文本的多维“侧面”提供一种可能。杨庆祥认为“溪镇实际上是文城现实的变异版或者低阶版”[5],即《文城》中的溪镇并不是没有所指功能的想象性符号存在,而是基于现实生活并蕴含余华某种思想观念的践行和行动场所。林祥福在“寻妻”过程中逐渐淡忘原有的远行目的,使更多的人物陪同林祥福走入余华所想要描写的清末民初时期,从原有的单个人物线索发展成多人共演的纵向空间事件并列。即使人物之间的关系是被想象出来的,但不能否认顾益民、陈从良、翠萍等人物都因余华有效的文本情节过渡,不仅使余华所认知的时代有发挥文本空间书写的可能,同样也让读者有更多的文本想象空间去推测各个人物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因各自选择所形成的不同空间场域呈现。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本身是过去行为的产物,它就允许有新的行为产生,同时能够促成某些行为并禁止另一些行为”[6]。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文城》中的人物大多带有儒家学说的底色,就算张一斧作为儒家伦理道德中的极恶代表,也是用以衬托林祥福的道义和儒学色彩;但“清王朝坍塌之后,战乱不止,匪祸泛滥”的民国初年,溪镇作为余华用以表现时代特征的空间舞台就必然出现用以适应新社会环境生产的新行为,而恰恰是这些新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攻击和解构余华理想中的乌托邦空间。因此,当“还没有发育完全的男孩”顾同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与妓女搭讪”,又“与妓女同床共枕到旭日东升”之后,余华将其安排在繁华的上海并与一名“自称是富家小姐”的“妙龄女子”相会,最终被“卖到澳洲去做劳工”,余华利用中国儒家传统中的性禁忌完成对其驱逐理想仁义乌托邦空间的完美“借口”;当顾益民和林祥福完成“顾同年和林百家的定亲典礼”后,因陈耀武的舍己救人使林百家“和他形影不离,不是坐在他身边,就是走在他旁边”,以致二者发生身体接触后,一起生活了十三年的两家人分开,林百家最后被送到上海的中西女塾中,陈耀武也因林百家的离开,被余华借用张一斧的出现进一步完成对儒家理想价值践行空间内部裂痕的“修补”,运用新的冲突完成文本的过渡,将其“合理地”排出余华心中儒家理想仁义的实践空间;而作为溪镇最大的威胁张一斧,尽管拿到枪支和杀了林祥福,但也因溪镇独耳民团的顽强反抗以及陈永良与林祥福的“兄弟结义”,最终在沈店的码头上被陈从良用尖刀刺死,即张一斧生前和死后都没有真正进入溪镇的地理空间中。“在接近高潮的时候仿佛又在推开高潮,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培育着将要来到的高潮,使其越来越庞大和越来越沉重,因此当它最终来到时,就会像是末日的来临一样令人不知所措了。”[7]溪镇作为余华理想仁义实践的空间场域,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和维护中,完成具有宗教式体验的写作版图扩展,并形成相应的政治意识。
二、写作版图扩展形成的宗教式体验与政治意识布道
《兄弟》有李光头到日本做国际破烂业务,宋钢到海南卖丰乳霜的情节,但并未形成真正的地理行动与互动。只有《文城》是利用纪小美的北上和林祥福的南下形成两个移动的地理空间,真正完成余华在写作版图上的扩展。朱尔斯·维恩认为“旅行是空间中的一系列运动。旅行者的经验生成一种新的秩序,借助这种秩序,地理学超越了知识”[2]。纪小美的北上和林祥福的南下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次中国南北方地理空间上的旅行,也正是在各自的旅行中通过一系列的人物行为和事件完成一种超越已有知识的新的秩序生产。杨庆祥认为《文城》中的北方是“一个敦厚、宽容、坚韧的北方,他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以谦恭和隐忍之心对待着来自南方的不速之客”[8],即运用如歌如泣的罗曼蒂克爱情和传奇式的文化英雄行动,完成一次带有悲剧意义的相逢与错失旅行,以期打破中国小说中既定的南北方政治权力视角,但实际上,“‘地域’与‘传统’,……是一种逻辑上的先取权……而且‘在同时’看起来是预先假定”[1]。(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余华自述通过林祥福这个角色完成《圣经》的“一个善良到极致的人是什么样子”[4]改写,林祥福因纪小美的北上失败才南下,而林祥福南下和融入南方的过程则意味着一种宗教式体验的思想传播和文化英雄践行,在本质上是借用地理空间版图的扩展完成一次带有政治意味和宗教性色彩体验的民族空间共同体想象的行动。
余华的出生和童年都在中国南方,直到1983年11月,时值24岁的余华在北上改稿之行后才与中国北方有了身体和地理空间上真正的接触。对于中国的南北划分,余华认为“我们北方的语言却是得益于权力的分配。权力的倾斜使一个地区的语言成为了统治者,其他地区的语言则沦落为方言俚语。于是用同样方式书写出来的作品,在权力的北方成为历史的记载,正史或者野史;而在南方,只能被流放到民间传说的格式中去”[9]。《文城》作为“新历史”题材的再度书写,则是将带有权力中心色彩的北方通过儒家知识内核和西方宗教式的神灵同人同性内嵌在林祥福的南行和定居中,完成历史主流之外的边缘视角书写和民间故事呈现,使作为地理政治边缘的空间有效补充到传统和地域意义上的北方正史中。林祥福凭借其母生前常说的“纵有万贯家财在手,不如有一薄技再身”的生存权利语句和践行,到南方后与陈永良一起修补龙卷风和雪冻后“尽是变形破损的门窗”的溪镇,以致两家在乔迁之时,面对邻居们“风卷残云似的搬空了陈永良的家”。“历经漂泊之苦的”李美莲发出了“做人是做到头了”的感慨;父亲去世后,生在北方的林祥福“在织布机吱哑吱哑的声响里和母亲温和的话语里,他从《三字经》学到了《汉书》《史记》”。在林百家十二岁时,身在南方的林祥福“迷恋起了教育”“他按照私塾的规矩给孩子们上起孔孟儒学,《论语》《孝经》《大学》《中庸》,还有《孟子》和《礼记》一应俱全”。余华将林祥福身上所展现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美好的一面用一种“传教士”方式完成从精英化天堂到世俗化尘世的彼岸和来世的超越,最终完成带有中国传统士大夫“道”式色彩的精神使命拯救。北方作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威的中心,也因林祥福在南方“寻妻”和“生根”完成具有宗教体验意义的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布道。
福柯认为“一种完整的历史,需要描述诸种空间,因为各种空间在同时又是各种权力的历史(这两个术语均以复数形式出现)。这种描述从地理政治的大策略到居住地的小战术”[1]。(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余华力图通过《活着》以前的故事完成他们这一代作家的“百年写作梦”,这个“百年写作梦”既动用时间的政治历史形成,也运用具有政治意味和意识形态的空间场域完成余华关于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民歌和史诗。叙述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认知、把握和反思当下,《文城》中的溪镇作为余华实现儒家理想仁义和《圣经》“极善之人”的空间场所,既带有个人的主观意愿,同时也可能是社会空间生产的一部分,用以联系和构建当代人的精神桥梁,作为文学中的乌托邦实质是基于现实生活经验所形成的空间想象。如果文学作品是作家被社会生活情绪化、心灵化和生命化的产物,描写的对象成了作家情感化的客体,那么《文城》的写作及其形成的乌托邦空间既可以是余华选择用大众的“公共”历史场所完成时代精神和历史思考的途径或工具形式,也可以是余华用以缓解自我内心与现实紧张关系的隐秘自我孤独感的空间存在。因此,《文城》通过空间地理版图的扩展和带有宗教式体验的政治意识传播完成余华在现时空间下的两种精神状态和空间展现,而林祥福南行和融入溪镇的历史进程实质是以一个精神完善的儒家圣人姿态走进一个注定要被历史抛弃的乌托邦空间。
三、“士志于道”的精神乌托邦空间
余华用儒家理想仁义观念来塑造笔下的林祥福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而溪镇这个空间场所也因林祥福的出现和定居让余华有发挥书写中国传统文化英雄空间的可能。“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materialpractice)。”[6](黑体字为原文所有)文学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有艺术创作者的想象和虚构,并用以表达自我心灵诉求和欲望本能的抽象空间,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者更是如此。《文城》的创作和形成的文本空间展示也是如此,即使余华对《文城》的创作完成不再享有垄断权,但作为读者的余华却依然享有阐释和空间想象的权利。在《兄弟》的创作日记中,余华提到“我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希望,接下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形态会逐步地趋向于保守,趋向于温和,因为我们人人需要自救”[10]。到了花甲之年的余华运用温和和保守的精神自救方式如同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进行“哲学的突破”:“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11]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哲学的突破”是基于现实进行新的哲理思辨和认知,从而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构想。林祥福作为秀才和举人之女的后代,尽管走向一个必然被解构的理想乌托邦空间,其南行和融入溪镇的历史进程同样可以结合当代人的精神困境,用中国儒家知识阶层完成“士志于道”的精神乌托邦空间构建,用以表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和理想对中国当代作家的追求不无存在积极的鞭策作用。
余华所着重描写的清末民初是一个乱世,让林祥福、顾益民、田氏兄弟等人用儒家之道中的仁义光辉试图完成一个在乱世中远离受政治威胁和军事参与的世外桃源。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作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本质上是承接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并以西方现代性的形式完成自我民族述说的文学表达形式,《文城》本身也是余华戏仿中国古代传统文学书写方式的文本。如果说《活着》文本中的20世纪40年代及之后是中国人为民族的救亡图存而形成的为平定天下和人民安居乐业后的现实生活实境而呈现的历史与政治权力斗争的话,那作为《活着》以前的《文城》则是从文化承接层次上反思中国古代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中国本土后的再度自省,用“新历史”的小说形式再度探寻和追问中国文化之根。无论因历史和政治权力所形成的空间有多么强大的意识形态传达,作为民族的文化之根决定着一个民族是否可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精神之核,也才有根据民族文化所形成的具有民族历史性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可抽象化空间。《文城》中为学界所诟病最明显的人物性格扁平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余华有意为之用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缩影,因社会的外在环境可以混乱和杂乱无章,但作为人性之本的基本理念和民族立人之根不可乱。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持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11]何谓“道”?余英时认为“仁义为儒家之道,故志于仁义即志于道”[11]。林祥福身上体现着入世的儒家将仁义作为社会行动的根本观点和准则,他所行动和实践的空间场域也有人间的性格,但发生在清末民初这个时间背景如同“礼坏乐崩”的春秋战国时期。因此,面临因乱世而可能产生的人性内在秩序之乱,余华力图借助林祥福这个带有人间性格之“道”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彰显中国当代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承接,也在一定程度是应对现实生活的迷茫之态所作出的文化传承断层现象的无奈之举。这个用中国士大夫传统虚构出来的“文城”,运用空间所形成余华心中的理想仁义之地,或许注定是不存在的幻想却又苦苦等待的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色彩的戈多,似乎暗示人类的某种文化寓言。可在乱世的林祥福却依旧坚信地秉承儒家的仁义信念,用原始儒学所要求的士人之“道”努力完成改造和重建社会的责任。正如林祥福和纪小美最终都在自己的家乡入土为安一样,“人的生命并不从掠夺地力中得来,而只是这有机循环的一环。甚至当生命离开了躯壳,这臭皮囊还得入土为安,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回到什么地方去。”[12]从文化传承的层面来讲,过去始终影响着我们如今的思维和生活,但作为文化的过去,我们是否要重回文化产生的土地,以此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四、现时下的两个自我空间形态
余华认为:“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当我不写作的时候,我才会想到自己是在北京生活。”[13]作家在进行文本创作时,实质是借助作为肉体的物质现实存在完成精神层次的空间想象和旅行,即在一个共时的状态中完成两个空间自我的存在。“每个人同时是两个自我:其一是处于真正绵延中的自我,表现为流动变化的意识之流,多样性意识的相互渗透是真正实在之所在,所以它是‘基本自我’,‘第一自我’,而另一种自我则是为生活和社会的需要,投射于空间的第一自我的‘广度式的象征’,‘自我的阴影’,是第二自我,柏格森称之为‘空间自我’或是‘纯一绵延’。”[14]即《文城》的文本创作本质上是余华作为第三人称视角完成自我童年精神故乡书写的空间自我,并运用溪镇这个带有文化寓意和儒家理想仁义实践的空间场所完成个体精神内在秩序的整合和重建,以期通过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知来修复作为个体自我与过去历史及文化连续的可能性。如果说林祥福进入南方是让余华重新回到记忆中的故乡,而林祥福在溪镇的儒家理想仁义实践是带有民族文化精神传承和守护的话,那林百家、顾同年和陈耀武等新生代人物并不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反而是清末民初这个内忧外患时期对传统和民族之根的批判和反对者。因此,余华作为《文城》的书写者和叙述者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时间组成的两个空间中完成个体关于现实生活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双重对话,这是文学中的现实,尽管文本发生的背景绝大多数是余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南方,但却未削弱作者彰显民族文化寓意的力度,反而借助作家童年的生活景观着重突出因民族传统文化断层出现的精神荒芜和迷茫而大声疾呼。余华“一直认为童年的经历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方向”[10],同理,具有古老文明沉淀的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生成的文化之根同样也决定着民族共同体想象上的精神朝圣之旅。林祥福作为古代知识阶层中践行“士志于道”的文人实际是作为身兼着民族文化复兴的精神标杆和重任,引领处于现代文化“围城”中所产生越来越沉重的精神无力感和无可奈何作出的一次具有反叛现代性的先锋性复古行动,林祥福的死亡和归乡不仅是身体和精神的解脱,更是现代文明的精神之死对古代传统文化酬谢之生的指向。
“在经历了最近二十年的天翻地覆以后,我童年的那个小镇已经没有了,我现在叙述里的小镇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了,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10]童年的那个小镇在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文城》等作品中被还原为成长经历形成的具有空间性心理构想的童年生活现场。余华利用文学创作他所认知的童年历史和地理,是他通过身体和精神直接与过去的历史和地理相遇并产生当下文学写作中的历史和地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因“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10],现代的生活节奏加快,人的内心节奏和思维观念认知又难以追随,现实生活空间的精神错位让现代人受到因外在环境的无序和混乱造成人内部精神的分裂和荒谬感。因此,余华试图通过《文城》的单向度理想仁义人物导向让现代人所产生精神内爆倾向转化对民族文化根本的认同,通过清末民初这一修正过的时间概念而形成的历史和地理空间书写,重新镌刻和把握民族文化之根在古今传承层次上的辩证关系,对民族文化之本的崇拜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个体内在文化秩序和精神的统一,用民族历史文化的共通性来修补文化当代性的不足和展望未来。
余华曾自述“如今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3]作为作家的童年生活景观会一直影响他后来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和看法,如同余华在《文城》中建造的空间场域,既是余华偶然性的“百年写作梦”,也是在现代性空间中艰难生存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必然性构建。
结语
也许,到了花甲之年的余华感受到因时代节奏变快而展现一种身体和精神的无力感,如同林祥福在乱世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一般,用难以跟上时代步伐的疲惫神色完成对现实的进一步妥协。“文城”或许是余华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的精神乌托邦空间,只不过基于现实镜像而创造了具有人性生活痕迹的溪镇。对个体故乡和民族精神故乡的反照和回归或许正是中国文化在试图寻找某种出路用以修补因时代精神裂缝所产生的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