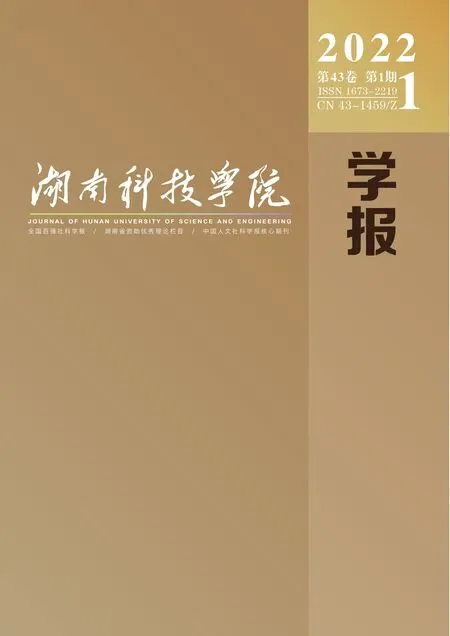孤独与救赎——弗洛姆自由观视域下的《上帝救助孩子》解读
2022-11-25马欢乐
马欢乐
孤独与救赎——弗洛姆自由观视域下的《上帝救助孩子》解读
马欢乐
(广州中医药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上帝救助孩子》是托妮·莫里森以美国当代社会为创作背景的文学作品,展示了美国当代社会各年龄、各阶层、各族裔民众孤独、焦虑的生存图景。文章以弗洛姆的自由观为理论视角,通过对比分析文本中人物逃避消极自由带来的自我救赎失败及追求积极而成功自我救赎的差异,揭示了创造性的爱与劳动是现代人重获自由,不必牺牲自我的完整性而恢复与自然及他人联结的唯一途径。
莫里森;《上帝救助孩子》;弗洛姆;自由观
《上帝救助孩子》是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最后一部小说,出版于2015年。该小说一经面世,便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被《纽约时报》《环球邮报》等多家媒体评选为2015年“最受期待”的书籍之一。沃克盛赞该书“故事迷人,措辞精妙”[1]。加尔冈称该小说写作手法独特精湛,“具有莫里森写作的经典标志”[2]51。曼努埃拉(Manuela)指出“《上帝救助孩子》是一个现代版童话故事,是丹麦小说家安徒生创作于1843年的最负盛名的童话《丑小鸭》的重新诠释。”中国学者也显示了对这部小说的极大兴趣,从儿童创伤、儿童性暴力、黑人女性成长、社会伦理学等角度对作品进行了不同的解读。王守仁等[3]通过临摹“童年创伤”探讨了如何通过“言说”的疗伤作用走出童年的阴影,庞好农[4]采用社会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围绕创伤和异化探讨了美国社会的儿童创伤和心灵扭曲问题,周权[5]以身体叙事为切入点,展示了女主人公的女性主题建构过程,李明娇[6]探讨了身体书写对当代非裔美国人实现身份认同和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意义。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从弗洛姆自由观的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弗洛姆的自由观揭示了人自由的来源、现代人普遍感到孤单的原因及追求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不同途径和结果[7]。《上帝救助孩子》是莫里森以当代美国社会为创作背景的一次尝试。现代人孤单、迷惘、焦虑是莫里森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她的笔下,社会的进步和宽容给了人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但人却成了一个个日益孤独的原子: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已经失灵,父亲纷纷逃离自己的职责或与子女关系紧张,母亲专治暴虐,成了孩子童年创伤的主要来源,老人独居或住在养老院,孩子极少来探望,人与人关系冷漠:朋友之间是紧张的竞争关系,无法向彼此倾诉秘密,恋人之间享受性爱带来的欢愉却对彼此毫不了解。现代人无力承受自由带来的后果,纷纷寻求自我救赎及自我建构的途径。
一 弗洛姆的自由观及现代人类的孤独
弗洛姆(Erich Fromm)是20世纪著名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家及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在他的第一本著作《逃避自由》中,弗洛姆阐述了他的自由观,提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前者意为“解脱什么”(free from)或免于什么,以主体摆脱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为前提,强调其行为不受干涉或免于干涉,是人的被动行为。后者指涉行为主体能“自由地去做什么”(freetoo),突出主体具有行动选择的自由,凭自己的意愿做什么或成为什么,是人的主动行为。不同于以赛亚·柏林对积极自由的警惕及消极自由的极力捍卫,弗洛姆把消极自由看作是人类的孤独感的根源,而积极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也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崇尚的自由。
在弗洛姆看来,自由源于人与始发纽带的断裂。当个人与自然尚未分离时,始发纽带像联结婴儿和母亲的“脐带”一样将个人、自然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一方面让个人处于自然、阶层及各种社会关系的束缚中,阻止人成为自由的个体,另一方面这种束缚让人一生下来就处在一个“明确的、不会改变的和没有疑问的位置”,有确定的使命和责任,因而也能获得生活在其中的安全感、秩序感及确定性。换言之,弗洛姆认为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与社会束缚性是紧密相连的。当始发纽带被切断后,人开始了个体化进程,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人们发现“新自由似乎给他们带来两件事情:日益地感到有力量,和同时日益地感到孤独、怀疑、猜忌,以及因此感到焦虑”[9]8。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革新,现代人对自然及传统社会中确定的社会关系的依赖日益减少,人们因为束缚而受到保护的领域消失得越来越多,人的孤独感和无力感也日益增强。自由于人们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那些难以忍受的人纷纷选择了逃避自由,通过“退缩,放弃自由,试图通过消弭个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的方式来克服孤独”[8]93。只有极少数人能积极地恢复与外部世界的始发纽带,通过爱和劳动找到积极的自由,最终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建构。对于消极自由的逃避以及积极自由的追求在文本中都有较明显地体现。笔者以弗洛姆的自由观为视角,通过文本细读,挖掘小说中人物追求自由的不同途径,探讨现代社会人类摆脱孤独走向自由王国的正确途径。
二 逃避消极自由之自我救赎失败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所面临的普遍困境是个人的孤独与无力,由于忍受不了这种由自由带来的孤独与无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自由。他指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主要有三种,即权威主义、破坏欲及机械趋同。
(一)权威主义
弗洛姆对权威主义逃避机制的定义是“放弃个人的自我独立的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9]93这种机制主要表现在行为主体强烈地渴望臣服或主宰欲望,即受虐与施虐倾向。受虐倾向最常见的表现为自我贬低,自甘懦弱,“极度依赖自身之外的权利、他人、机构组织或自然,他们不敢伸张自我,不去做想做的事,而是臣服于事实上或假想的这些外在力量的命令”[9]94,通过消灭自我从而为他人整体的一部分,进而消除无能为力感,极端例子包括自残、自虐、过度自责等。施虐倾向主要表现为通过操控和主宰他人,把他人工具化并让他人对自己产生依赖,从而克服自己的无力感。施虐倾向常见的逻辑推理包括:我统治你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你好。
《上帝救助孩子》中的母亲形象大多是专制的施虐狂,她们严厉但没有任何规则,仅仅把养育孩子当作展示个人意志与威权的渠道。索菲亚(Sofia)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只允许女儿阅读宗教小册子和圣经并给她制定了极其苛刻的规矩和纪律,经常以索菲亚“如今或即便当时都不记得的过错”[8]85罚她长时间站在房间的角落里。索菲亚入狱后,她从未给女儿写过信、打过电话或亲自探望,把女儿看成了彻底堕落的魔鬼。布莱德的母亲甜甜(Sweetness)则是具有受虐施虐的双重心理机制:她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黑人的身份让她“在杂货店里被吐口水,在公交站被推推搡搡,在排水沟里走而把整个人行道让给白人,在食品店里花五分钱才能得到白人免费拿的纸袋”[8]4。她非常痛恨这种种不公,但潜移默化中,她却认可了这种歧视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她以自身的浅肤色为傲,歧视比自己黑的同胞,甚至连亲生女儿也不例外。看到刚出生的布莱德黑得发蓝,她气得“快要疯了”,甚至在一瞬间失去了理智,有几秒钟,她“用一条毯子捂住她的脸按了下去”[8]5。她厌恶和女儿的一切身体接触,觉得给黑乎乎的女儿喂奶十分难堪而拒绝母乳喂养改用奶瓶。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她刻意避免身体接触,在每次不得不给她洗澡时总是敷衍了事。她自认为对女儿的教导方式“必须严厉起来,非常严厉。卢拉·安需要学会乖乖听话,低眉顺眼,不惹麻烦……她的肤色是她背上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十字架”[8]8。她的教导没有逻辑且颠倒是非,勒令她对雷先生性侵白人小男孩的罪恶事实保持缄默,却怂恿她出庭作伪证指控索菲亚性侵学生。布莱德“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做,该说什么话,该记住那些规矩”[8]88。专制的母亲给孩子造成了巨大的童年创伤,也导致了母亲们晚年孤单的下场:索菲亚在母亲去世后甚至都感觉不到难过,布莱德也从来不去养老院探望年老体弱的甜甜。
在强大且权威的母亲统治之下,索菲亚和布莱德都有强烈的受虐倾向。布莱德经常故意犯错以引来母亲对自己的肉体惩罚,因为这是可以得到母亲触碰的唯一途径。她的初潮弄脏了床单,甜甜“抽了她一巴掌,把她推到一浴缸冷水里”[8]88,难得的身体接触竟然给她病态的满足感。她们都选择放弃自我,臣服于自己的母亲,隐匿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索菲亚形成了顺从、沉默的性格,成年的她回忆起母亲家的房子最清晰的印象是那个“蓝白相间的角落”。布莱德承认,“当恐惧主导一切时,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顺从”[8]35。她们成年后不约而同“迫不及待地逃出妈妈的房子”[8]85。索菲亚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第一个向她求婚的人,却只不过是“面对着一个更大的蓝白相间的角落”[8]86。两年后由于被诬陷被判入狱25年,继续屈服于监狱这个更大的权利系统,像行尸走肉一样存活。布莱德逃离母亲后去了加州并在那里完成了人生的逆袭,实现了自己“美国梦”。然而成功的事业光环掩盖不住布莱德孤独的本质。她成了赫胥黎在他的《美丽新世界》一书中描绘的那副样子:“营养充分,穿戴讲究,性欲得到满足,但却没有自我。同她同时代的人也只有表面的接触。”[8]105与其惊人美丽外表不相称的是她极低的自我评价,她安于被物化为男人们的猎物,是他们“英勇战功”的奖牌。布克和她吵架分手后,她追问自己“到底怎么了?我不够热情?不够漂亮?我不该有主见吗?不该做他反对我做的事?”[8]10布克离开后,她的生活陷入了崩溃状态。
(二)破坏欲
在弗洛姆看来,破坏欲根源于难以忍受的个人的无能为力与冲动,旨在除掉所有与之相比使个人显得弱小的对象[9]119。它与施虐狂的本质差异在于,其目的不在主动或被动的共生,而在于消灭其对象,消灭所有的外在威胁[9]118。破坏欲无处不在,并被人们用“爱、责任、义务、良心、爱国主义”等概念加以伪装。朱莉(Julie)和亨伯特(Humbort)就是这种破坏欲的牺牲品。朱莉是苏菲亚在狄卡根监狱服刑时期的室友和唯一的朋友。她因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莫莉而入狱。不同于甜甜差点弑女的冲动,朱莉是这种冲动的践行者。莫莉“大大的脑袋,嘴唇微张,有一双世界上最可爱的蓝眼睛”[8]74。但她身体的残疾和布莱德的深黑肤色一样被母亲定义为“永远摆脱不掉的十字架”。为了释放内心的焦虑感和无力感,朱莉以爱女儿的名义残忍地剥夺了女儿幼小的生命。弑童的罪名让她堕入监狱的底层,狱中的霸凌和对女儿的愧疚与思念让她选择以上吊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未果后她彻底堕落,沦为了狱中“老资历犯人的禁脔”。亨伯特先生是一个汽车修理工,被邻居们称为“世界上最好的人”,因为他待人友善,干活利索。伪善的面具下是他孤独的本质:已经退休,经常“开着货车,一人一狗四处转悠”[8]132。为了逃避自己年老体弱的事实及孤独将死的本质,他极其残忍的奸杀了六名男童,把他们的阴茎割下来收藏在一个精心装饰的糖果罐里,并把他们的名字纹在自己的肩膀上。亨伯特先生的所作所为是破坏欲最极端的后果,冲击了人性的底线,深刻地警示了人们如放任破坏欲泛滥将是全人类之殇。
(三)机械趋同
机械趋同是指个人以失去自我为代价,“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9]123,以消除自我与世界之间的鸿沟,克服意识里的孤独感和无能为力感。在弗洛姆看来,这种逃避机制是现代社会大多数常人所采取的方式,突出地体现在人们的从众心理和模仿心理。在自我救赎的路上,布莱德和布克就曾经采用过这样的方式。
布莱德利用消费市场上大众的从众心理,即“黑皮肤是种卖点,是这个文明世界里最炙手可热的商品”[9]40,听取了“整体形象设计师”杰瑞只穿白色的着装建议,把自己的深黑肤色包装成上档次的东西向大众兜售。同时,她严格遵循消费主义的标准,用昂贵的奢侈品来包装自己,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以此标准来评价他人,看到被15年非人监牢生活摧残得憔悴不堪的索菲亚的脸后,她觉得“她完全可以用点格莱魅面膜,再用弗莫莱皱纹软化霜和乔尔斯棕色粉底给她失去血色的皮肤上点颜色”[8]18,认为索菲亚在15年前庭审时“打一剂保妥适瘦脸针,抹点不带亮彩的哑光唇膏,她的嘴唇就会更柔和,也许会给陪审团留下点好印象”[8]19。她是商品拜物教的信徒,盲目迷信金钱能解决一切问题。对于年迈的母亲甜甜,她以金钱补偿来代替亲自探望,对于被她诬陷入狱的索菲亚,她以为五千美元现金可以一笔抵消自己的罪孽,并以救世主的高姿态告知对方这笔钱可以“帮你好好开始,过你的生活”[8]23。索菲亚把她揍得体无完肤,几乎破相,这一举动也直接导致了布克和她的分手,让她的生活重新回到混乱无序的状态。
出生后立即就夭折的孪生哥哥给布克心中带来“一团温暖的虚空”[9]127,这种虚空被哥哥亚当(Adam)所替代,然而亚当的惨死让他再次堕入孤凄的境地。他去学小号,期望靠音乐去“缓解和整理混乱的思维”[8]130,然而这让他缺席了周六早晨的家庭聚会,和家人的关系日渐疏远。亚当奸杀案凶手落网后,布克成为了“呼声狂热而撕心裂肺”要求复仇的民众中的一员,参与他们法院面前的集会,但他与热闹的人群格格不入,对罪犯的处罚和定罪方式深感失望。大学后他试图和同学们保持一致,“根据色情杂志和电影对周围的女孩品头论足,根据他们看过的动作片来在彼此间分出高下”[8]134,然而这种“神奇的吸引力”(ibid)只持续了两年,他变得更加悲观抑郁,甚至绝望。
综上,作为获得消极自由的现代人,他们无力承担自由的代价。当他们纷纷采用逃避自由的机制来消解自身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时,却又堕入了更加孤独的深渊。这种自我救赎的机制注定会面临失败。
三 走向积极自由的成功自我救赎
弗洛姆认为,积极的自由是“人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以及人自发地活动——爱与劳动,借此而不是借始发纽带,把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的人重新联系起来”[9]23。在人的自发性活动中,人与世界重新连为一体又不用牺牲自我的完整性,这是解决现代人类精神危机的唯一出路,也是索菲亚、布莱德、布克等人克服自身孤独感,最终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方法。
(一)自发的情感表达
弗洛姆认为要实现积极自由,就必须充分挖掘内心,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愿望、情感,从而达到自我实现。索菲亚、布莱德通过肢体暴力、言说、忏悔、自省等方式卸下心头包袱,面对真实的自我。
索菲亚痛打了害她无辜坐牢的布莱德,觉得“打她、踹她、用拳头揍她的时候……感到一身轻松,比获得假释的感觉更自由自在”[8]86。她卸下了15年的伪装第一次崩溃大哭,“我告诉自己,想获得自由,就必须付出代价。你必须去抢夺它,为得到它而奋斗,还必须保证自己有能力驾驭它”[8]78。表达了内心真实情感后,苏菲亚觉得“再也不需要压抑情绪,再也没有满身污秽。如今的我一身干净,有能力面对新的生活”[8]78。布莱德将抛弃自己的布克揍了一顿,并在争吵中向他坦白了作伪证陷害索菲亚入狱的罪行,随后她卸下了十几年压在心口的十字架,享受了一夜无梦的睡眠,“她觉得自己有如重获新生……无比轻松,充满力量”[8]179。布克在听完布莱德肺腑之言后,也选择将亚当之死给自己带来的创伤对她坦白,并认真反省自己的自私与懦弱,“除了对亚当的感情以外,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如果对方必须、只能是个纯洁无瑕的天使时,我才会付出爱意,这种爱算什么爱?”[8]177最后他卸下防备,向布莱德伸出“她渴盼了一生的手”[8]193。
(二)爱与劳动
爱是自发性活动最核心部分,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和人内心生长的东西,它的本质是给而不是得。给的能力取决于人是否能以“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创造性倾向”[10]32来“克服他的依赖性、自恋型以及剥夺他人的要求,并能找到对自己的人性力量的信赖以及达到目的的勇气”。给的行为能唤起双方身上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在不被异化的劳动中得到真正的实践和强化,从而使双方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创造性的关系。
伊芙琳和史蒂夫是通过爱与劳动获得自我救赎的典型代表。“危机四伏、目标明确”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生活让他们厌烦,他们选择远离尘嚣“过真正的日子”,住在几乎荒废的乡村土路边,自己种菜、织布、剪草、劈柴,晚上闲暇时唱歌和弹吉他打发时间。这种被布莱德定义的“没洗衣机,没冰箱,没浴室,没钱”[8]102的穷苦生活让夫妻俩得到了内心的平静。伊芙琳认为“和一个完美的男人住在这片星空中,她觉得多么幸福”[8]105,那些现代设备“不过是些垃圾,因为没有一件能用上很久不坏的”[8]105,史蒂夫也认为钱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他反问布莱德“钱能帮你从那辆捷豹里出来?钱能救你?”[8]102质朴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发展出了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爱的形式:给予。他们不图回报地对身陷困境的人伸出援手,如把雨夜邂逅的街头流浪儿蕾恩(Rain)带回家,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她;收留腿受伤的布莱德六个星期,不厌其烦地帮她就医、做饭、擦身。他们的给予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生命感,也提高了对方的生命感,因为“他的给不是为了得,但是通过他的给,不可避免地在对方身上唤起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因此他的给的同时也包括了使接受者也成为一个给的人,而双方都会因为唤醒了内心的某种生命力而充满快乐”[10]30。蕾恩原来是一个脏话连篇、有着严重地社会人格的孩子,刚到伊芙琳和史蒂夫家时想要杀掉他们以及杀掉所有人,渐渐地被她被感化为一个懂感恩和表达爱的正常孩子。布莱德一开始认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实在太难理解也太过奇怪了……她偶尔会怀疑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预谋,有不可告人的计划”[8]101。经过六个星期的朝夕相处,夫妇俩终于让她意识到自己的浅薄:“说到底,关于无条件的善意和不借助外物的爱,她以前有过什么了解呢?”[8]102在两人的感召下,她生平第一次发展出无条件的爱,耐心地倾听蕾恩的故事,为她的遭遇伤感,并在蕾恩受到其他男孩的欺凌时奋不顾身地帮她挡子弹而受伤流血。这种有创造性倾向的爱超越史蒂夫和伊芙琳的养育之恩,是一种触及蕾恩灵魂的“为了救我,救我的命而不顾自己的安危”[8]118的爱。布莱德成了蕾恩命运真正拯救者,被她称为“我的黑小姐”。和布克一起照顾奎恩的过程中,布莱德爱的能力进一步得到了体现和验证。奎恩的头发着火了,她毫不犹豫地扯下了自己的衣服,盖在奎恩头上帮她灭火。在医院里,她像伊芙琳和史蒂夫一样,“以最细致体贴的态度”帮奎恩清洁身体。他和布克“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一样分工合作,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帮助另一个人”[8]185。爱与劳动让她经历了“被人爱”到“爱别人”最后到“创造爱”的过程,她所有女性身体特征得到恢复,并且实践了女性身体独一无二的能力,孕育一个孩子,这意味着布莱德有机会去实践最伟大、最富有创造性倾向的母爱。像史蒂夫和伊芙琳夫妇一样,她和布克有了成功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上帝救助孩子》是84岁高龄的莫里森以当代作为创作背景的一次尝试,她曾坦言写当代是一种“挑战”,“我紧张,因为当代像液体流变(fluid),我没有抓手”。莫里森的自谦之词言过其实,她的抓手非常成功,她以现代人的普遍孤独感为切入点,通过呈现一个个孤独彷徨的现代社会场景及形形色色现代人的救赎途径与成败,呼吁读者警惕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多的消极自由。人们应通过爱与劳动追求积极自由,避免由于逃避消极自由而陷入越自由越孤单的怪圈。莫里森的这一转变表明她超越了黑人族裔作家的身份,关注点从黑人的种族问题上升到更深刻、更普遍的人类共性问题,为其一生的创作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1]Walker, K. Flesh of My Flesh: Toni Morrison’s ‘God Help the Child’[N].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2015-04-19.
[2]Galgan,W.&F.C. Brooklyn.Book Review of God Help the Child[N].Library Journal.2015-06-15.
[3]王守仁,吴新云.走出童年阴影,获得心灵的自由和安宁—读莫里森新作《上帝救助孩子》[J].当代外国文学,2016(1): 107-113.
[4]庞好农.创伤与异化——社会伦理学视阈下的《上帝会救助那孩子》[J].北京社会科学,2017(6):4-11.
[5]周权.莫里森新作《上帝救助孩子》中深黑色黑人女性的主题建构[J].外国语文研究,2017(6):32-39.
[6]李明娇.《上帝救助孩子》中的身体书写[J].山东外语教学, 2019(5):91-98.
[7]托妮·莫里森.孩子的愤怒[M].刘昱含,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7.
[8]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9]艾·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建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0]Oatman,Maddie.The New Black[J].Mother Jones,2015(3): 63.
2021-08-25
广东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文化自信视阈下中医药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马欢乐(1982-),女,湖南邵阳人,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I106
A
1673-2219(2022)01-0100-05
(责任编校:周欣)